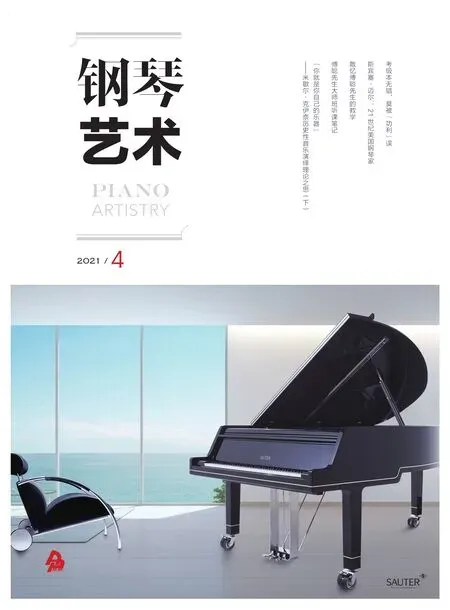羽管鍵琴與現代鋼琴演奏的驚人不同
——以巴赫作品為例
文/科林·布斯 編譯/李 博

最近,有人聽到一位專門演奏巴赫作品的著名鋼琴家提出這樣的問題:“聽人在羽管鍵琴上演奏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一個小時以上,誰能忍受得了呢?”
沒人敢這樣回答:“要是換作巴赫呢?”實際上,當今喜愛巴赫鍵盤音樂的人們與巴赫自己的聲音世界之間存在著鴻溝。作為一個愛好各種鍵盤樂器的人,我認為努力縮小這個鴻溝是很重要的。
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似乎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對待18世紀的音樂。大提琴家馬友友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對待巴赫的音樂,你差不多可以任意而為,結果他還是他。現代版本的曲譜,由于不帶有早期的編輯性建議,使演奏者面對許多“不成樂句”的音符(不連貫的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演奏者最初的反應是僅僅按照譜面彈奏,但演奏的結果可能并不令人滿意。而在18世紀,支撐曲譜中那種干癟內容的是一系列演奏傳統,其中大部分現今已軼失了。在巴赫去世之后,受各種大鍵琴和早期鋼琴新音樂風格的影響,作為輔助指引演奏手段的連線、演奏法記號和力度標記,在曲譜中就變得普遍起來了。當今時代,對于從小接受這些輔助指引的鋼琴家來說,若樂譜中的這些內容突然不存在了,可叫他們如何是好呢?對于一個創新、自信的鋼琴家來說,似乎依靠直覺即可充分滿足需要。然而,對巴赫時期作曲傳統的理解可以解決諸多問題,因為這種理解能澄清音樂中可能存在的大量聽起來不順暢或不令人滿意的成分。從更一般的視角來看,若能從過度刻板照搬曲譜的演奏中解放出來,巴赫的音樂將會更有樂感,更令人愉悅。本來,你可能認為羽管鍵琴家會告訴當代鋼琴家們什么是他們不應該做的事情,但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其實主要是你可以做的,這可能出乎你的預想。
許多當代鋼琴家最初接觸巴赫音樂的時候,會為他所作曲目的適用樂器沒有延音踏板而感到震驚與茫然。除非偶爾在非常大的演奏廳中,一般情況下,這些鋼琴家演奏時都會放棄使用踏板。實際上,大多數演奏者的琴聲能輕易充滿他們自己的房間。既然清晰度對于巴赫的對位來說至關重要,在這種情況下,踏板就可能成為音質清晰度的阻礙。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早先我跟邁克爾·克魯普老師學習鋼琴時,他是那些偉大的19世紀鋼琴教師的追隨者,沿用他們倡導的諸多規條。雖然18世紀的鍵盤演奏權威們向人們灌輸細微觸鍵技巧時沒有運用精確的時值計量手段,但是他們的專著確實向人們提供了很多內容。其中一項直至18世紀末還被建議運用的技巧被稱為“標準觸鍵”(normal touch):每個音使用清晰的運音法,即輕微的斷奏。以這一技巧作為基礎,注意力可集中于音樂中的特定內容,一方面是連奏式連線,另一方面是不同程度的斷奏。換句話說,從時間上看,不偏不倚的觸鍵方法被使用得最多,演奏者只要稍有側重,就會為自己創造出很多表現音樂的余地。這種做法當然源于演奏觸鍵對力度影響較小或沒有影響的樂器,并且不同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只要不被樂譜或教師阻止就一直連奏的習慣性傾向。
這樣來看,羽管鍵琴為音樂“表現”提供了方法,盡管這不為當代鋼琴家們所熟悉。巴赫的作曲技法倚賴于這些傳統,而它們又反過來促成了樂譜的簡單化——簡單的程度遠高于后世作曲家的作品。在演奏方面,這可能包含諸多隱含的可能性(見例1)。
例1 巴赫《降B大調第一帕蒂塔》,《小步舞曲I》,第1至8小節(原譜)

人們可以把這首曲目用作提升觸鍵及節奏均勻度的練習曲,音符的時值可以按照譜面演奏,也可以單手或雙手使用更多的斷奏。巴赫為他的學生們創作了無數的教學曲目,其中許多被收入《平均律鋼琴曲集》。但是,這一首來自他的《第一帕蒂塔》——一套為愉悅高水平的演奏者而出版的曲目。巴赫是一位熱忱的舞者,對任何將此曲當作簡單練習材料的人,他都會嘲笑應對。如果明確把這首小步舞曲作為一部美妙的舞曲來創作,他會怎樣演奏呢?例2提供了一些簡化的建議,可作為一種方案。巴赫像其同時代的作曲家一樣,沒有規定演奏者要采用哪一種方案。
例2 巴赫《降B大調第一帕蒂塔》,《小步舞曲I》,第1至8小節(演奏建議)

首先,看低音聲部。巴洛克音樂創作一般是從低音聲部開始的(賦格除外),且上方聲部的旋律嚴格服從于低音聲部。這種做法截然不同于古典主義時期的通常做法——對于莫扎特式的音樂,旋律遠比伴奏重要。巴赫所作音樂的低音聲部并非伴奏,因此演奏者必須杜絕那種過于柔和甚至是以斷奏方式演奏的低音。低音聲部的練習必須先于上方聲部,且排練時要滿懷崇敬與喜悅之情。這首曲子的低音聲部特別有趣,關于它的斷句,我給出了一種簡單而有效的方法:使連為一組的音比不連接記譜的音在演奏時銜接得更緊密。我的具體建議如下:如果沒有其他要求,那么基本的觸鍵方法是采用“標準”觸鍵方式,即輕微斷奏,但同時,節奏韻律鼓勵使用稍大力度或稍長時值的方式演奏第1至5小節左手的重拍音,但不適用于第6至7小節。
對于右手而言,巴赫在譜面上為我們提供的只是部分信息。為了發現其中的奧秘,在演奏右手聲部時,可以省略所有未用橫線標記的音。這樣做,可以揭示出作曲家作曲時依據低音聲部在上方形成高音旋律的過程。進而,我們就能知道,右手其余的各音都是裝飾音或經過性素材。巴洛克時期記譜的靈活性意味著帶有標記的音符演奏時的實際時值可以比樂譜中顯示的時值長些——這樣,隱含的旋律線條就產生了。鋼琴家們也將感到他們自己正在強調這些旋律音。一些讀者會說:“其實,我已經這樣做了——感覺很好聽。”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可以相信,如果巴赫能聽見,他也會同意的。這樣做,當然不僅是因為更有趣味,而且是因為更美妙;對于演奏者來說,雖然這樣做要求更高,但會更有回報。
雖然大多數旋律會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但相似的是,樂譜中還會存在信息的缺失,這就會讓當今的音樂家們以一種不同于巴洛克風格的方式演奏這些旋律。巴洛克時期的記譜法一般不會顯示出音樂的內在結構及隱含于其中的表情信息,假如演奏者不能明白這些隱含的信息,那么彈奏一長串音符聽上去就會顯得機械而呆板。
例3中的低音聲部比前面例1中的低音聲部顯得從容多了,且需要大致中等的觸鍵力度。保持音產生的細微變化將使音樂更美妙,且使右手旋律的表達更加突出。應注意保持旋律的節奏性律動。雖然后面的旋律需要連貫彈奏,但是此處,旋律可以被稍微分割為一些短得多的元素。這里所做的樂句劃分僅是一個建議。有標記的音符比相鄰的音符需要稍微多使用些力度。換氣符號(作為一種手法被巴赫同時代鍵盤樂器演奏家弗朗索瓦·庫普蘭所使用)標明邏輯上“呼吸”的位置。演奏者可能想到管樂器——理想情況下的巴洛克風格!

例3 巴赫《c小調第二帕蒂塔》,《創意曲》,第1至2小節(連音線、呼吸記號和保持音記號均由作者添加)當代鋼琴家格外關注的另一項內容是力度。羽管鍵琴的一個特點就是均勻地發音。盡管如此,巴洛克作曲家還是在他們的樂譜中寫入了力度提示信息。對于巴赫時期的樂器,同時演奏出的兩個音聽上去比一個音更響,所以有意識地使用六個或八個音構成的和弦可以使音樂產生力量。但我從錄音中發現,鋼琴家們有時以很弱的力度彈奏出那些和弦,將上述規律顛覆了!巴赫會感覺他們的這種演奏方式非常奇怪——當今的鋼琴家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能力嗎?關于這個問題,例4中的織體表明了作曲家的意圖,即希望一首樂曲中何時需要有力度地演奏,哪怕曲譜中沒有寫明。
例4 巴赫《e小調第六帕蒂塔》,《薩拉班德舞曲》,第1至4小節

補充一點:這首樂曲為弱起拍。在起始之處,若以小節第一拍的力度強奏,就會破壞這個慢速舞蹈的節奏感。在這一點上,當代鋼琴家比羽管鍵琴演奏者擁有優勢:為了使樂曲充滿動力感,他們可以更輕易地強調小節第一拍,而羽管鍵琴演奏者就要依賴演奏法,并且需要以琶音的方式著重彈奏小節第一拍的和弦。雖然這種技法在現代鋼琴上的使用必須謹慎,但是在此是有效的。雖然巴洛克時期的樂譜極少標注和弦的琶音奏法,但是羽管鍵琴演奏者一般需要那樣演奏。而對于節拍的強調,巴赫所使用的織體遠非如此簡單(見例5)。
這里有一個明顯的漸強:第83至85小節實質上是二聲部的寫法。第86小節中較強的兩拍上,先有個四音符和弦,然后有個五音符和弦,到第87小節,有個六音符和弦——這種情況在后來的記譜中,會以一個突強記號來標記。然后,巴赫使音樂回歸到了早先的力度水平。雖然看上去這個漸強可能很明顯,但是彈奏鋼琴時很容易在力度表現上忽視這些線索。
例5 巴赫《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二冊),《F大調賦格》,第83至89小節

某位著名巴赫演奏家彈奏例6時,使用微微的漸弱直至結尾,使這首樂曲在依依不舍的留戀情緒中漸行漸遠。實際上,巴赫的意圖是使音樂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力度停滯在全曲末尾處時值延長的和弦上——這個意圖的傳達是通過在臨近末尾處寫出一系列和弦,并且在弱拍處加入激動人心的顫音的方式實現的。雖然在鍵盤樂曲結尾處使用強力度和弦是巴赫通常的做法,但是從曲譜中偶爾可見他可能想要些不同的感覺。例7結尾處實實在在暗示出作曲家讓音樂呈現出放松狀態的意圖:低聲部突然出現的低音具有漸弱的效果,甚或叫作“突慢”(ritenuto)更顯準確。
例6 巴赫《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冊),《d小調賦格》,第38至43小節

例7 巴赫《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冊),《A大調賦格》,第50至54小節


這些例子提供的幾個線索揭示出巴赫曲譜中的隱含信息。揭示并非“詮釋”,而是在假設作曲家擁有最正確思想的前提下盡力發現其意圖。一般而言,為了讓當今音樂家們表現出對作曲家的尊重,他們接受的是“忠實樂譜”的訓練,而對巴洛克傳統的深入理解可以使他們從這種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在按照樂譜彈奏的同時,也能更多地注意巴赫這樣的天才音樂家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