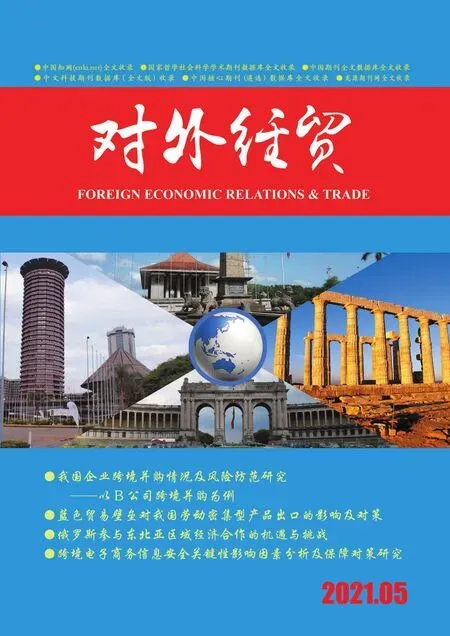混改背景下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實(shí)證研究
許 玥
(南京審計(jì)大學(xué),江蘇 南京 211815 )
一、研究背景
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是我國(guó)的一種新型企業(yè)形式,由國(guó)有股東和非國(guó)有股東共同組建而成。十八大以來(lái),我國(guó)政府一直格外重視混改。十九大報(bào)告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鼓勵(lì)國(guó)有企業(yè)深化改革,致力于提高我國(guó)企業(yè)的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和引領(lǐng)能力。目前,我國(guó)已將混合所有制經(jīng)濟(jì)視為實(shí)現(xiàn)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的重要形式。在向著新時(shí)代邁進(jìn)的社會(huì)進(jìn)程中,國(guó)有企業(yè)的混合將成為深入解決我國(guó)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提升人民群眾對(duì)美好生活需求的強(qiáng)大推動(dòng)力。
現(xiàn)有文獻(xiàn)大多關(guān)注對(duì)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論探討,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提升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研究仍缺乏大樣本的實(shí)證分析。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篩選2013—2018 年滬深上市國(guó)有企業(yè)的數(shù)據(jù),選取197 個(gè)上市國(guó)有企業(yè)的樣本,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之間的關(guān)系。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提升我國(guó)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一方面,可以加強(qiáng)企業(yè)內(nèi)部的監(jiān)管,保障各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對(duì)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權(quán)制衡度等因素的作用提供了實(shí)證證據(jù),對(duì)進(jìn)一步推進(jìn)我國(guó)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導(dǎo)價(jià)值。
二、文獻(xiàn)綜述
(一)國(guó)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概述
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概念
國(guó)有企業(yè)的發(fā)展一直對(duì)我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第十四屆三中全會(huì)中,我國(guó)就曾提出國(guó)有企業(yè)現(xiàn)代化制度改革這一理念。《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清晰地描述了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的頂層設(shè)計(jì)方案。胡敏[1]認(rèn)為此次改革主要分為三大類層次,即“公益型、自然壟斷型、競(jìng)爭(zhēng)型”。和軍、季玉龍[2]認(rèn)為完善行之有效的國(guó)有企業(yè)治理結(jié)構(gòu),使民間資本有更多發(fā)揮空間和投資渠道,進(jìn)入相關(guān)公共服務(wù)領(lǐng)域,從而推進(jìn)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收入更加的公正合理,這些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形成紅利的前提和基礎(chǔ)。平新喬[3]研究發(fā)現(xiàn)新一輪國(guó)企改革不同于之前的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即基礎(chǔ)性產(chǎn)業(yè)中的國(guó)有資本和服務(wù)業(yè)國(guó)有資產(chǎn)總值多年連續(xù)上漲且占主導(dǎo)地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現(xiàn)已成為推進(jìn)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的重中之重,進(jìn)一步完善國(guó)有企業(yè)現(xiàn)代化制度,使國(guó)有企業(yè)更適應(yīng)時(shí)代發(fā)展的潮流。
2.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問題
通過對(duì)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整理,發(fā)現(xiàn)多數(shù)是從行業(yè)領(lǐng)域、公司治理以及投資者保護(hù)的角度研究國(guó)有企業(y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難題。在行業(yè)領(lǐng)域方面,李軍等[4]從進(jìn)行混改的企業(yè)中國(guó)有股占比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得出國(guó)有企業(yè)在涉及國(guó)計(jì)民生的行業(yè)中,應(yīng)擁有壓倒性的控制權(quán)。在公司治理方面,劉運(yùn)國(guó)等[5]研究發(fā)現(xiàn)在競(jìng)爭(zhēng)性國(guó)有企業(yè)與地方國(guó)有企業(yè),企業(yè)高層有非國(guó)有股東的廣泛參與能夠提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在投資者保護(hù)的方面,秦江萍[6]發(fā)現(xiàn)國(guó)有絕對(duì)控股公司對(duì)相關(guān)利害關(guān)系人的權(quán)益保護(hù)比相對(duì)控股公司更為有效。
(二)對(duì)內(nèi)部控制的研究
最早研究?jī)?nèi)部控制的學(xué)者認(rèn)為內(nèi)部控制產(chǎn)生于組織內(nèi)部的需求,并且內(nèi)部控制本身屬于會(huì)計(jì)系統(tǒng)一部分。其后,西方理論界和實(shí)踐界分別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組織理論、審計(jì)學(xué)等多角度解釋和定義內(nèi)部控制本質(zhì)。20 世紀(jì)90年代,指導(dǎo)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的主流思想是整合框架理論。由于科技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浪潮以及公司治理逐漸公開透明,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于2013 年進(jìn)行了基于整體框架的變革。這一變革不僅推動(dòng)了企業(yè)改革的進(jìn)程,也為我國(guó)企業(yè)內(nèi)控體系改革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內(nèi)部控制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20 世紀(jì)80 年代。進(jìn)入21世紀(jì),許多企業(yè)由于內(nèi)部控制失靈而面臨破產(chǎn)倒閉的風(fēng)險(xiǎn)。2008 年和2010 年隨著相關(guān)政策文件的制定與實(shí)施,我國(guó)初步建立了內(nèi)部控制規(guī)范體系。近年來(lái)諸多學(xué)者關(guān)注內(nèi)部控制對(duì)企業(yè)的影響效應(yīng),且主要通過實(shí)證分析進(jìn)行研究。劉啟亮和羅樂[7]、劉運(yùn)國(guó)和鄭巧[5]等學(xué)者實(shí)證檢驗(yàn)了內(nèi)部控制與會(huì)計(jì)信息質(zhì)量、高管薪酬業(yè)績(jī)敏感性、非國(guó)有股東參與水平等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
由于我國(guó)引入混改時(shí)間較短,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于混改后內(nèi)部控制的研究還不全面。Hong Yu[8]認(rèn)為國(guó)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應(yīng)當(dāng)重點(diǎn)解決目前國(guó)有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問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guó)企改革的大勢(shì)所趨,因此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也受到學(xué)者廣泛地關(guān)注與研究。胡明霞、干勝道[9]等學(xué)者研究了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對(duì)管理層權(quán)力與過度投資,以及對(duì)管理層權(quán)力與高管腐敗等關(guān)系的作用機(jī)制。
不難看出,國(guó)內(nèi)外有關(guān)內(nèi)部控制的研究已經(jīng)漸趨成熟,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背景,以國(guó)有企業(yè)為樣本的研究多以理論分析為主。因此,在以往各位學(xué)者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總結(jié)與歸納,并在我國(guó)國(guó)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分析當(dāng)前國(guó)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對(duì)內(nèi)部控制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
三、理論基礎(chǔ)與研究假設(shè)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對(duì)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影響
內(nèi)部控制受控制環(huán)境、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程序、信息與溝通、控制活動(dòng)、對(duì)控制的監(jiān)督這五個(gè)因素的共同影響。逯東[10]等學(xué)者指出國(guó)有企業(yè)缺乏市場(chǎng)的開放性和企業(yè)的自主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消極作用于內(nèi)部控制有效性。劉啟亮[7]等學(xué)者探討了在高管集權(quán)的公司中,內(nèi)部控制常常能約束員工而無(wú)法約束高管,從而使內(nèi)部控制的裝飾性更強(qiáng)。其他股權(quán)的所有者在混改后會(huì)參與到國(guó)有企業(yè)的監(jiān)管與治理當(dāng)中。為了維護(hù)自身的權(quán)益,非國(guó)有股東會(huì)加強(qiáng)對(duì)原管理者的監(jiān)督,在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和管理權(quán)結(jié)構(gòu)上都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原管理層進(jìn)行了監(jiān)督與制約,從而完善了企業(yè)的內(nèi)部控制制度。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shè):
假設(shè)H1: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提高國(guó)企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二)混合主體股權(quán)制衡度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的影響
混合主體制衡度即股權(quán)制衡度,通常以前十大股東之間的持股比例來(lái)衡量。如果前十大股東之間持股比例很接近,且所有人都不能獨(dú)斷專權(quán),可以說(shuō)其股權(quán)制衡程度相對(duì)較好。學(xué)者們一致認(rèn)為股權(quán)制衡度對(duì)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有積極作用。孔玉生等[11]指出,在公司治理環(huán)境中,引進(jìn)恰當(dāng)?shù)墓蓹?quán)制衡機(jī)制能夠在公司治理過程中提升公司績(jī)效,完善內(nèi)部控制。徐慧曄[12]探討得出,相對(duì)控股股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第一大股東的控制權(quán),縮小了各個(gè)股東控制權(quán)之間的差異,為完善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奠定基礎(chǔ)。綜上,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H2:國(guó)企在混改后,股權(quán)制衡度越高,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越高。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與不同行業(yè)國(guó)有企業(yè)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國(guó)有企業(yè)根據(jù)外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可以分為壟斷型行業(yè)和競(jìng)爭(zhēng)性行業(yè)。由于壟斷性國(guó)企比競(jìng)爭(zhēng)性國(guó)企享受的政策和服務(wù)更好,無(wú)論內(nèi)部控制有效與否,壟斷性企業(yè)的盈利都會(huì)因“壟斷性收益”而表現(xiàn)良好,從而放松了對(duì)內(nèi)部控制的管控;而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通常要面臨激烈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風(fēng)險(xiǎn)意識(shí)很強(qiáng),更加注重企業(yè)成本與效益的平衡。劉啟亮[18]等學(xué)者認(rèn)為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中的非國(guó)有股東更加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收益,則必會(huì)更加關(guān)注企業(yè)的風(fēng)險(xiǎn)預(yù)防機(jī)制,并加強(qiáng)內(nèi)部控制建設(shè)以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最大化。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H3:混合所有制改革對(duì)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提升作用比壟斷性企業(yè)更顯著。
四、實(shí)證研究
(一)樣本選取與數(shù)據(jù)來(lái)源
以2013—2018 年上市國(guó)有企業(yè)為樣本,基于國(guó)泰安數(shù)據(jù)庫(kù)獲取數(shù)據(jù)并按下列條件對(duì)其進(jìn)行篩選:1.從國(guó)泰安中篩選出所有滬深A(yù) 股國(guó)有上市公司;2.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減少來(lái)定義混改,從而篩選出已進(jìn)行混改的國(guó)有企業(yè),并且剔除了股權(quán)比例連續(xù)變化的公司;3.剔除金融保險(xiǎn)類企業(yè)、財(cái)務(wù)數(shù)據(jù)缺失的企業(yè);4.剔除ST、*ST 的企業(yè)。最終獲得符合混改發(fā)生定義的上市國(guó)有企業(yè)的共計(jì)197 個(gè)樣本數(shù)據(jù)。所有數(shù)據(jù)均來(lái)自于國(guó)泰安數(shù)據(jù)庫(kù),有關(guān)數(shù)據(jù)變量的統(tǒng)計(jì)分析主要借助STATA15.0 和EXCEL 兩款軟件。
(二)變量選擇與模型設(shè)計(jì)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IC-DIBO 表示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迪博內(nèi)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shù)通過內(nèi)部控制五要素,具體地刻畫了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水平,具有權(quán)威性并受到業(yè)內(nèi)的認(rèn)可。采用劉運(yùn)國(guó)、鄭巧、蔡貴龍[5]的研究方法,利用迪博內(nèi)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shù)衡量?jī)?nèi)部控制質(zhì)量。
2.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
將混改的發(fā)生定義為國(guó)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下降,以此對(duì)虛擬變量AFTER 進(jìn)行賦值。將年份在混改年份之前的,賦值為0,年份在混改年份之后的賦值為1。通過分析與整理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2011—2018 年進(jìn)行混改的國(guó)企分別有23、11、22、20、65、33、23 家,其中在2015 年發(fā)生混改的國(guó)企最多。BAL 為股權(quán)制衡度,可以通過該變量的顯著性來(lái)驗(yàn)證假設(shè)H2。
除此之外,選取財(cái)務(wù)杠桿,公司規(guī)模,企業(yè)成長(zhǎng)能力,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行業(yè)及年度虛擬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該模型涉及的變量名稱和釋義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與說(shuō)明
基于以上分析及變量構(gòu)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βi(i=1,2,…,6)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ε 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
五、實(shí)證分析與結(jié)果
(一)描述性統(tǒng)計(jì)
各個(gè)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表2 所示。
從表2 中可以看到,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IC-DIBO 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36.883、18.390 和48.500,說(shuō)明不同的國(guó)有上市公司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各有千秋,但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shù)企業(yè)的內(nèi)控還是較好的。股權(quán)制衡度的平均值為0.580,說(shuō)明國(guó)企的股權(quán)制衡相對(duì)穩(wěn)定,平均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略微超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quán)制衡度最大值為2.813,此時(shí)非國(guó)有股東占據(jù)主體地位,國(guó)有股東話語(yǔ)權(quán)較弱。股權(quán)制衡度最小值為0.032,此時(shí)第一大股東占據(jù)絕對(duì)控制權(quán),制衡作用非常微弱。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最大值74.98%,平均值39.57%,最小值11.85%。說(shuō)明進(jìn)行混改后各企業(yè)之間的股權(quán)占比情況存在較大差異,依舊不能避免“一股獨(dú)大”現(xiàn)象的存在。
(二)相關(guān)性分析
在描述性統(tǒng)計(jì)后,繼續(xù)對(duì)各個(gè)變量進(jìn)行相關(guān)性分析。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矩陣如表3 所示。
表3 中僅考慮了兩個(gè)變量之間單獨(dú)關(guān)系。可以看出,混改虛擬變量和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008,可以得知國(guó)企進(jìn)行混改后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初步驗(yàn)證了假設(shè)H1。財(cái)務(wù)杠桿系數(shù)和企業(yè)成長(zhǎng)能力與內(nèi)部控制為負(fù)相關(guān),表明其對(duì)內(nèi)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133、-0.059。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呈正相關(guān),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081,顯著性水平是5%,相關(guān)程度較高,且股權(quán)制衡度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負(fù)相關(guān),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020,與假設(shè)H2 稍有沖突,其結(jié)論有待進(jìn)一步檢驗(yàn)。
(三)多元回歸分析
在相關(guān)性分析的基礎(chǔ)之上,繼續(xù)對(duì)國(guó)企混改虛擬變量、國(guó)企股權(quán)制衡度與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等變量之間進(jìn)行多元回歸分析。為了排除內(nèi)生性的影響,下列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變量均采用滯后一期的數(shù)據(jù)(F.ICDIBO)。
1.模型1:混改虛擬變量與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觀察表4,模型1 的回歸結(jié)果只考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一虛擬變量,可以看出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F.ICDIBO)與混改虛擬變量(AFTER)之間的回歸系數(shù)為1.218,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顯著性水平為5%,說(shuō)明國(guó)企進(jìn)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驗(yàn)證了假設(shè)H1。再引入財(cái)務(wù)杠桿(LEV)、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CON)、國(guó)企規(guī)模(SIZE)、國(guó)企成長(zhǎng)性(GROWTH)、這幾個(gè)有關(guān)國(guó)企績(jī)效的指標(biāo)后,混改虛擬變量(AFTER)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回歸系數(shù)從1.218 上升至1.880,說(shuō)明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與公司規(guī)模負(fù)相關(guān),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正相關(guān)。而財(cái)務(wù)杠桿系數(shù)越高,企業(yè)成長(zhǎng)性越高,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越低。

表4 混改虛擬變量和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的多元回歸分析
2.模型2:股權(quán)制衡度與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從表5 可以看出,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F.ICDIBO)與股權(quán)制衡度(BAL)之間的回歸系數(shù)為1.595,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顯著性水平為5%。這說(shuō)明在國(guó)有企業(yè)中,加入非國(guó)有性質(zhì)的制衡股東能提高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即股權(quán)制衡度越高,內(nèi)部控制會(huì)質(zhì)量越高,驗(yàn)證了假設(shè)H2。

表5 股權(quán)制衡度和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的多元回歸分析
3.模型2:不同行業(yè)國(guó)有企業(yè)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根據(jù)劉曄(2016)等學(xué)者的研究,將壟斷型行業(yè)界定為石油加工及煉焦業(yè),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yè),化學(xué)纖維制造業(yè),橡膠制造業(yè),化學(xué)原料及化學(xué)制品制造業(yè),醫(yī)藥制造業(yè),采掘業(yè),通信設(shè)備制造業(yè),交通運(yùn)輸設(shè)備制造業(yè),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yè),電子計(jì)算機(jī)制造業(yè),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chǎn)和供應(yīng)業(yè),計(jì)算機(jī)相關(guān)設(shè)備制造業(yè)等,除此以外的其他行業(yè)均為競(jìng)爭(zhēng)性行業(yè)。將總樣本分為壟斷性國(guó)有企業(yè)和競(jìng)爭(zhēng)性國(guó)有企業(yè),其中壟斷型企業(yè)定義0,競(jìng)爭(zhēng)型企業(yè)定義為1,為并分別進(jìn)行回歸分析,具體結(jié)果如表6 所示。在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中,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F.ICDIBO)與混改虛擬變量(AFTER)在5%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guān);而在壟斷性企業(yè)中則不顯著。這說(shuō)明國(guó)企進(jìn)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對(duì)壟斷性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提升作用不明顯,對(duì)于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提升效果顯著,驗(yàn)證了H3。

表6 不同行業(yè)國(guó)企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多元回歸分析
從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中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會(huì)提高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國(guó)企的股權(quán)制衡度越高,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越高。混合所有制改革對(duì)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提升的效果相對(duì)于壟斷性企業(yè)來(lái)說(shuō)更顯著。可能的解釋是,當(dāng)進(jìn)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其他股權(quán)的所有者會(huì)參與到國(guó)有企業(yè)的監(jiān)管與治理當(dāng)中。公司中沒有任何一個(gè)人能夠獨(dú)斷專權(quán),股權(quán)制衡度增加,企業(yè)的內(nèi)部控制得到有效監(jiān)督,其質(zhì)量也相應(yīng)增加。另外,由于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也更傾向于節(jié)約成本、提高效率,混改后新加入的非國(guó)有股東也更加注重經(jīng)濟(jì)利益,其加強(qiáng)內(nèi)部控制建設(shè)以提高最終效益的意愿也就更強(qiáng)烈。
六、穩(wěn)健性檢驗(yàn)
通過分析比對(duì)發(fā)現(xiàn),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IC-DIBO 不僅受同期各種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過去某些時(shí)期各種因素的影響甚至自身過去值的影響。為了檢驗(yàn)上文中的實(shí)驗(yàn)結(jié)果是否穩(wěn)健,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滯后兩期的數(shù)值F.FICDIBO 來(lái)衡量?jī)?nèi)控,并在此進(jìn)行驗(yàn)證,得到表7 的回歸結(jié)果。

表7 股權(quán)制衡度、行業(yè)分類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
模型(1)(2)顯示進(jìn)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壟斷性國(guó)有企業(yè)與在5%的水平上和滯后兩期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F.FICDIBO)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系數(shù)為3.776;而進(jìn)行混改后的競(jìng)爭(zhēng)性國(guó)有企業(yè)在1%的水平上與滯后兩期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顯著相關(guān),說(shuō)明混改對(duì)競(jìng)爭(zhēng)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提升更為顯著,驗(yàn)證了假設(shè)H3。模型(3)說(shuō)明在考慮了財(cái)務(wù)杠桿(LEV)、企業(yè)規(guī)模(SIZE)、企業(yè)成長(zhǎng)性(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CON)、行業(yè)(INDUSTRY)、年份(YEAR)等因素后,股權(quán)制衡度(BAL)與滯后兩期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F.FICDIBO)在10%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guān),系數(shù)為1.748,驗(yàn)證了假設(shè)H2。
上述分析表明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影響具有滯后性,滯后期為2 年,且滯后影響具有持續(xù)性。回歸結(jié)果和基本回歸中的顯著性一致,因此實(shí)驗(yàn)結(jié)果是穩(wěn)健的。
七、研究結(jié)論與局限
(一)研究結(jié)論與啟示
以2013—2018 年全部A 股國(guó)有上市企業(yè)為研究對(duì)象,在現(xiàn)有的研究基礎(chǔ)上,利用多元回歸模型分析已經(jīng)發(fā)生混改的國(guó)有企業(yè)的股權(quán)制衡度以及行業(yè)類型對(duì)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影響。通過對(duì)變量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1.混合所有制改革會(huì)提升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2.股權(quán)制衡度越高,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越高;3.相對(duì)于壟斷型企業(yè),混改對(duì)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提升作用更顯著。
研究結(jié)果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在選擇是否進(jìn)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時(shí)可以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1.企業(yè)要結(jié)合自身發(fā)展情況進(jìn)行混改。國(guó)企進(jìn)行混改的確會(huì)給有利于企業(yè)發(fā)展,但是企業(yè)不能為了混改而混改,而是應(yīng)遵循和利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律,結(jié)合企業(yè)自身的實(shí)際情況,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把握機(jī)遇,應(yīng)對(duì)挑戰(zhàn)。只有進(jìn)行適合于企業(yè)發(fā)展需要的混改,才會(huì)提升企業(yè)的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
2.股權(quán)制衡度應(yīng)保持在合理的區(qū)間內(nèi)。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使國(guó)企中的國(guó)有資本和非國(guó)有資本各歸其位,增加了非國(guó)有股東的比例,積極發(fā)揮非國(guó)有股東的治理作用。但這還需要股權(quán)制衡度應(yīng)該在一個(gè)合理的區(qū)間范圍內(nèi)。如果太低,過度集權(quán)可能導(dǎo)致國(guó)企僵化;如果太高,國(guó)有企業(yè)可能會(huì)失去其國(guó)有的性質(zhì),影響公司的決策效率,最終影響經(jīng)營(yíng)和績(jī)效。
3.加快推進(jìn)國(guó)有企業(yè)分類改革。真對(duì)競(jìng)爭(zhēng)性企業(yè),要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使資源配置的權(quán)利真正回歸市場(chǎng),促進(jìn)國(guó)有企業(yè)更加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
(二)研究局限與可改進(jìn)之處
研究局限主要有兩點(diǎn)。
第一是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的衡量不夠準(zhǔn)確。借鑒劉運(yùn)國(guó)、鄭巧、蔡貴龍[5]的研究方法,利用迪博內(nèi)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shù)衡量?jī)?nèi)部控制質(zhì)量。然而目前國(guó)內(nèi)對(duì)內(nèi)部控制的度量尚無(wú)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采用這種方法雖然定量評(píng)價(jià)研究了內(nèi)部控制,但不能較好地反映公司內(nèi)部控制水平的差異性。
第二是研究的還不夠深入。以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來(lái)衡量股權(quán)制衡度,僅停留在數(shù)據(jù)層面的分析,對(duì)于國(guó)企混改后性質(zhì)是否發(fā)生變化沒有做出進(jìn)一步的分析,比如公有資本包括國(guó)有資本和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包括民營(yíng)資本和外國(guó)資本,它們?cè)谄髽I(yè)中的占比也會(huì)影響內(nèi)控質(zhì)量。
根據(jù)以上局限,可以采用標(biāo)準(zhǔn)化法對(duì)內(nèi)部控制各目標(biāo)變量進(jìn)行無(wú)量綱化,再運(yùn)用算術(shù)平均法給各變量賦予權(quán)重,更全面的衡量?jī)?nèi)部控制質(zhì)量,合理體現(xiàn)出各樣本公司內(nèi)部控制水平的差異性。此外,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混合主體多樣性,混合主體深入度對(duì)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的影響,這些數(shù)據(jù)更能體現(xiàn)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影響機(j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