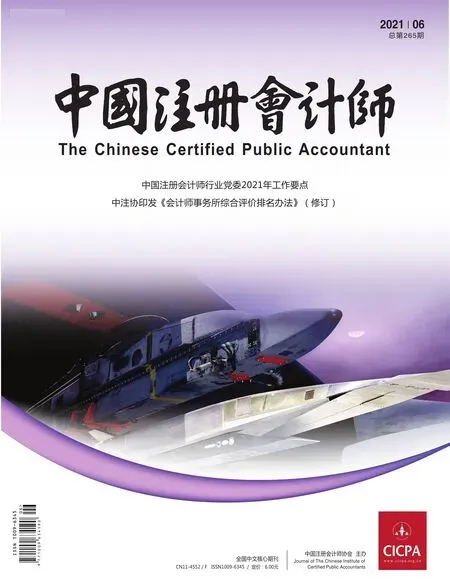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職業使命與審計倫理行為
薛文艷
一、引言
近年來,康得新、康美藥業、輔仁藥業等上市公司財務丑聞層出不窮,投資者在質疑上市公司會計造假的同時,也在質疑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作為出具審計報告的注冊會計師難辭其咎,通過了注冊會計師考試,具有豐富的執業經驗,持續接受職業教育的注冊會計師在面臨審計困境時,為什么不能堅守正義?具有較高的道德認知水平,能做出正確的倫理判斷,卻為何實施不道德的倫理行為?怎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本文基于上述問題,以即將步入社會的“準審計執業者”為研究樣本,探究“準職業人”面對倫理困境時,其道德勇氣與執業正義的力量源泉。
道德認知水平高的審計人員能做出更符合道德的倫理判斷。那么,具有較高的道德認知水平是否更傾向于做出恰當的倫理行為?學者們對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關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實證研究表明,處于較高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的個體比處于較低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的個體更有可能提交誠信報告,并放棄從撒謊中獲得的潛在經濟利益(Chung&Hsu,2019)。審計師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決策之間存在高度顯著的線性關系(楊書想和曾繁英, 2014)。然而,也有研究發現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Bay&Greenberg, 2001)。
除了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可能影響倫理行為,還有哪些個體因素會引起倫理行為的偏差?行為產生于動機,而動機取決于個體既有的信念和價值觀。職業使命是體現工作價值觀的核心信念,崇高的職業使命可以激發人們工作的熱情,奉獻的精神和高尚的職業行為。因此,研究職業使命觀對審計道德困境下倫理行為的潛在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雖有國外學者研究了個人哲學及價值取向對倫理行為的影響,但大都局限于個人倫理取向(如理想主義還是相對主義)、心理控制源(如內控型還是外控型)、道德評價取向(如功利論還是道義論)等對倫理決策影響的研究,尚未有國內外學者直接研究職業使命觀對審計倫理行為的影響。本文將個人導向、職業導向、審計目標導向與社會導向的四種職業使命觀區分為較低層次與較高層次的職業使命觀,并根據計劃行為理論,運用情景模擬與問卷調查的方法,對財務管理與審計專業大學生的道德認知水平、職業使命觀與倫理行為進行了調查研究,實證檢驗了職業使命觀對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的調節作用。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道德認知發展理論
美國心理學家Kohlberg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了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該理論將個體道德認知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水平,六個階段,具體如表1所示。
該理論認為個體的道德發展需經歷一個由低到高、由他律到自律的過程。個體道德成熟的標志是個體行為從以自我為中心到為以他人為中心,再到以原則為中心。為了測量個體的道德認知水平,Kohlberg設計了九個道德兩難故事和問題,采用面對面的道德判斷訪談法來測定受試者的道德認知水平。由于該方法費時費力、操作性差,Kohlberg的學生Rest于1979年在綜合了道德判斷訪談法的利弊之后提出了“確定性問題測驗法”(Defining Issue Test,以下簡稱DIT)。該方法共設置了六個道德兩難情景,每個情景下設12個影響道德決策的因素,根據受試者后習俗水平(第五、六階段)的得分來衡量其道德認知水平,得分越高說明受試者的道德認知水平越高,在遇到道德兩難困境時,就越傾向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遵從個人良心式原則,越可能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決策。
(二)倫理決策模型
Rest于1986年提出了倫理決策模型,該模型將個體做出倫理決策的過程分為倫理認知(倫理敏感性)、倫理判斷、倫理意向和倫理行為四個階段。意識到倫理問題的存在是倫理決策開始的關鍵,具有較高道德認知發展水平的個體對道德問題更敏感(Reynolds, 2006),倫理敏感性越高,形成倫理判斷的可能性也越大(Martinov&Mladenovic, 2015),審計師感知到的倫理問題對倫理判斷具有積極的影響(Zakaria等, 2010) 。這些研究表明,意識到倫理情景存在問題的個體更能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判斷。
Kohlberg認為,個體道德能力的高低主要通過道德判斷加以體現,后來的研究成果證明了這個觀點。大多數學者將審計人員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評分作為倫理判斷的替代變量(Ho&Lin, 2016)。Thorne和Magnan(2000)開發并測試了基于審計倫理情境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測量工具,并于2002年和Massey一起運用這一測量工具證實了審計師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評分與倫理判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以上研究結果支持使用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評分作為倫理判斷的替代變量。此外,大量的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道德認知發展水平作為倫理判斷的替代變量對倫理決策的積極作用(Shang等, 2008;Holian,2006)。

表1 道德認知發展階段
判斷是建立在對特定情況的態度和感知之上的,而意圖則代表了根據這些態度和感知采取行動的意愿(Fan等, 2014)。如果一項行為被判斷為是不道德的,那么個體就不太可能形成實施該行為的意向。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倫理判斷和倫理意向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Culiberg&Miheli,2016;Latan等, 2019)。個體實施行為的意愿越強烈,則執行該行為的可能性越大。Wagner和Sanders(2001)實證檢驗了倫理意向與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一個人如果有意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從事不道德的行為。
綜上,個體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越高,表明倫理推理能力越強,越能意識到存在的倫理問題,越傾向于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判斷。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評分可以作為倫理判斷的替代變量,評分越高,越有可能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判斷,執行該行為的意向越強,實施該行為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呈正相關關系,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越高,越傾向于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行為。
(三)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認為,所有可能影響行為的因素都是通過行為意向來間接影響實際行為的,影響行為意向的因素包括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三方面(Ajzen, 1991)。態度和行為產生的基礎是價值觀(Hilton,2003),工作價值觀指導員工實施特定的職業行為。在行為決策過程模型中,價值觀被認為是影響決策行為的重要個體特征因素。而使命正是核心價值觀的載體與反映,擁有崇高職業使命觀的個體希望能從所從事的職業中獲得意義感、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并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職業使命觀體現了個體對不同導向工作價值觀的認同,公平、正義的利他主義價值觀與倫理行為呈正相關關系,而與自我提升有關的利己主義價值觀與倫理行為呈負相關關系(Fritzsche&Oz,2007) 。審計目標導向和社會導向的職業使命觀屬于與社會公平、正義有關的利他主義價值觀,個人導向與職業導向的職業使命觀屬于與自我提升有關的利已主義價值觀,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表4 道德認知發展水平的效度分析

表5 正式問卷的人口統計變量數據

表6 描述性統計
假設2:職業使命觀與倫理行為呈正相關關系,具有審計目標導向和社會導向的利他主義職業使命觀的個體,更傾向于做出符合道德的倫理行為。
計劃行為理論提出,個體在行為決策過程中擁有大量的行為信念,但能夠秉持的行為信念卻很少,這些被秉持的信念稱為顯著信念,顯著信念是行為意向產生的基礎。工作價值觀正是個體執業過程中應具備的基礎性信念,而職業使命就是影響個體實施特定職業行為的核心突顯信念,當個體已經對一種倫理情境持有強烈的信念時,這種信念隨后會對結果起中介作用(Lehnert, 2015)。職業使命作為個體所持有的一種強烈的核心信念,會激勵個體提高倫理敏感性與道德認知發展水平。持有利他主義職業使命觀的個體具有崇高的信念,在實施特定倫理行為時,可能會表現出更高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進而促使其做出更符合道德的倫理行為。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職業使命對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的關系存在正向的調節作用。

表7 方差分析F值和顯著性指標

表8 各主要變量的相關關系

表9 假設驗證結果表
三、研究設計
(一)調查問卷設計
本文運用問卷調查方式獲取相關研究數據,問卷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統計變量和職業使命觀問卷。人口統計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專業、地域和家庭教育背景;職業使命觀以受試者認為的“從事審計職業的意義”作為代理變量,下設4個選項,分別代表個人、社會、審計目標與職業導向的職業使命觀,要求受試者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選項。
第二部分包括三個常見的審計倫理困境情景。前兩個改編自Arnold等(2011)開發的在時間預算壓力下減少必要審計程序和提前簽字的審計情景,第三個是自行開發的關于專業勝任能力問題的審計情景。每個模擬情景下設有影響倫理決策的12個題項,這些影響因素的設計也借鑒了Arnold等開發的審計倫理情景下的“確定性問題測驗”(Auditing Defining Issue Test,簡稱 ADIT)。除兩個無實際意義的干擾項(Meaningless Items,以下簡稱M條目)外,其余題項均為原則性條目(Principled Items,以下簡稱P條目),P條目代表Kohlberg道德認知發展水平的第2至6階段。
第三部分為審計倫理行為測試。相比于其他不道德的審計行為,超時勞動下減少必要審計程序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此,本文選用了第一個審計情景,下設6個題項,題項借鑒了Johari等人于2007年的設計,分別代表受試者在該情形下可能采取的實際行動。測試要求調查對象作為情景當事人,在面臨超時勞動及生存壓力的情形下,選擇他們將會采取的倫理行為。6個選項分別表示協調、轉嫁、妥協、承擔、辭職、違規的倫理行為方式,行動越適當,得分越高,表明采取的審計倫理行為越高尚。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測量
為驗證假設1至假設3,探究財審專業大學生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職業使命觀與倫理行為等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構建了模型(1)至模型(4):


其中,被解釋變量倫理行為(EB)是指受試者在給定的審計程序執行不到位情景下所決定采取的實際行動,不同的倫理行為代表的恰當性程度不同,根據適當性程度的高低分別賦予了0至4分,分數越高,表明采取的審計倫理行為越恰當。
解釋變量包括道德認知發展水平(CMD)、職業使命觀(CC)以及二者的交乘項。道德認知發展水平運用審計道德認知測量工具(ADIT)進行測量,每個案例的12個影響因素都采用Likert 5點量表進行評分。根據受試者的選擇結果,計算出P條目中反映道德認知后習俗水平第5、6階段的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試者的道德認知水平越高。職業使命觀變量通過受試者對“認為從事審計職業意義”的選擇加以確定,個人導向與職業導向的職業使命觀賦值為0,審計目標導向與社會導向的職業使命觀賦值為1。如選擇后者,表明受試者具有崇高的利他主義職業使命觀。控制變量包括性別(GEN)、年齡(AGE)、地域(LA)、專業(MAJ)、家庭教育背景(FEB)。上述變量定義如表2所示。
(三)測試數據的收集與處理
1.預測試問卷基本情況及信效度分析。預測試對象為大四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共收回有效問卷60份。預測試采用SPSS25.0軟件對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變量進行Crobach’s α系數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評估問卷數據的信度與效度。具體的信度檢驗指標見表3。由表3可知,各題項校正的項總計相關性均大于0.3,且項已刪除的α系數均未明顯高于整體的Crobach’s α系數,表明無須將對應題項做刪除處理,Crobach’s α系數為0.831,大于0.7,說明具有較高的信度,達到了預測試數據的信度要求。

表10 職業使命觀與審計倫理行為方式的交叉(卡方)分析結果
第三個審計倫理情景為自行開發,因此對變量的效度也進行了檢驗。具體的效度檢驗指標見表4。從表4可知, KMO樣本測試值為0.8,大于0.5,Bartlett半球體檢驗顯著,適合探索性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兩個因子,分別為道德認知發展的第5、6階段,各題項在因子1上的載荷系數均大于0.4,共同度也均大于0.4,進一步表明無需對各題項進行刪除。方差累計解釋比例大于50%,表明問卷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2.正式問卷基本情況。2018年12月發放了正式問卷,調查對象為審計學與財務管理專業大學生,問卷均為現場發放、測試與收集。共發放185份問卷,全部收回。剔除填寫不完整問卷10份以及不認真問卷33份后,共收回有效問卷142份,問卷有效率為76.76%。正式問卷的人口統計變量情況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受試者大多為女性,這符合我國財審專業女性偏多的特點。現有的研究結論表明,男女性別在道德行為上沒有顯著差異,被調查者女性居多不會影響研究結論。由于調查對象為大學本科三、四年級學生,因此年齡大多在21~23歲之間。從生活地域看,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農村,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城市。父母學歷普遍不高,只有少數學生父母的學歷在大專以上,且無碩士及博士學歷。在受試者中,審計學與財務管理專業學生所占比例大致相當,兩個專業均未設置單獨的審計職業道德課程,但學生都主修過審計學相關課程,對審計知識有一定的認知與理解,能滿足問卷調查要求。
3.正式問卷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6列示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6可以看出,倫理行為、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年齡與家庭教育背景的均值與中位數接近,且標準差均小于平均值,說明樣本之間的差異不大,在倫理行為上大多采取了積極的方式來處理審計倫理道德的兩難困境;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平均得分為25.72分,按百分制計算,折合平均得分為71.44分,說明學生具有較好的道德認知水平。職業使命觀的平均值接近0.5,表明學生總體對職業使命觀不存在偏向性。
4.正式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分析。在預測試樣本數據信效度檢驗的基礎上,對正式問卷所涉變量道德認知發展水平依據DIT測試量表采用的檢驗標準進行了信度檢驗。首先,每一個審計情景下的12個題項中都包括了1至2項無實際意義的M條目,如果受試者將M條目列入了影響其倫理判斷的最重要的四個項目中,且M條目在四個最重要項目中的總分大于5分,即被認定為無效問卷,共剔除了3份此類問卷;其次,檢驗受試者對12個題項重要程度的排列與影響其倫理判斷的四個最重要題項的選擇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即被認定為無效問卷,收回問卷中共剔除此類問卷23份。Crobach’s α系數為0.786,大于0.7,說明具有較好的信度,樣本測試結果較為可靠。由于每個審計情景下的12個題項均選自于成熟量表,且經過了預測試樣本的效度檢驗,因此這里不再重復做進一步的效度分析。為提高倫理行為變量測試結果的可靠性,本文打亂了測試選項順序,并嚴格按照事先制定的評分細則進行計分。對于同時選擇相互矛盾的選項如違規與拒絕違規、拒絕違規與逃避行為,則被認定為無效問卷,共計剔除此類問卷7份。
四、假設檢驗
(一)單因素方差分析
本文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來確定對審計倫理行為具有顯著影響的人口統計變量。經檢驗,樣本數據的偏度與峰度均符合要求,滿足正態總體。問卷為隨機發放,在95%置信水平下,數據具有方差齊性。表7列示了審計倫理行為的方差分析F值和顯著性指標。從表7可以看出,性別、生活地域和專業對倫理行為的影響均不顯著,這與以往的研究文獻較為一致(Sweeney&Costello, 2009;Eweje&Brunton, 2010;Craft,2013)。本文還研究了家庭教育背景與倫理行為的關系,結果顯示具有正向影響,但影響并不顯著。因此,上述變量將不被納入回歸模型中做進一步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表8列示了各主要變量的相關關系,其中CC與EB、CMD、AGE的相關性檢驗使用了Spearman系數,其余變量間的相關性檢驗使用了Pearson系數。分析結果顯示,CMD、CC與EB的系數顯著正相關,這與上述提出的假設1、2預期一致。CC與CMD系數顯著為正,與假設3預期一致。AGE與EB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因此,AGE不被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中進行分析。各解釋變量之間相關系數均小于0.5,表明方程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假設檢驗
通過上述分析,原假設模型中的不同控制變量對審計倫理行為均未呈現出顯著性差異,因此表9中的模型去除了性別、年齡、生活地域、專業和家庭教育背景變量。表9第(1)列和第(2)列分別列示了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職業使命與倫理行為的回歸結果。CMD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對倫理行為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假設1得到驗證;CC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職業使命觀對倫理行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
假設3提出職業使命觀會強化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倫理行為之間的正向關系。本文運用SPSS25.0軟件,使用分層回歸的方法對調節效應進行了驗證。在計算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交乘項之前,對二者進行了去中心化處理。研究結果如表9第(3)列和第(4)列所示,CMD與CC交乘項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職業使命之間的交互作用會對倫理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崇高的職業使命觀會增強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對倫理行為的正向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
五、進一步研究
區別于前文審計職業使命觀對倫理行為影響關系的研究,本文進一步從審計倫理行為方式的角度探究不同導向的職業使命觀在倫理行為方式上的差異。根據審計倫理行為恰當性程度的不同,具體分為協商、轉嫁、妥協、承擔、辭職與違規六種行為方式。由于職業使命觀與倫理行為方式都是分類數據,故而使用了卡方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具體結果如表10所示。
由表10可知,Pearson卡方值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Phi與Cramer相關系數均大于0.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兩個變量之間關系緊密,不同導向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對倫理行為方式的選擇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導向職業使命觀的人數比重大約在20%~30%之間,分布較為均衡。
在上述所有樣本中,選擇不拒絕或妥協、違規減少必要審計程序的人數有89人,其中,持利已主義導向(個人導向和職業導向)職業使命觀的有72人,占80.9%,持利他主義導向(社會導向和審計目標導向)職業使命觀的有17人,占19.1%;選擇拒絕減少必要審計程序的人數共有53人,其中,持利已主義導向職業使命觀的有5人,占9.4%,持利他主義導向職業使命觀的有48人,占90.6%;上述研究發現表明,持利他主義導向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在面臨道德兩難困境時,更傾向于堅持正義,遵守審計職業道德準則,更有勇氣抵抗上級壓力,做出更道德的審計倫理行為;而持利已主義導向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在面臨道德困境時,更傾向于妥協、違反審計職業道德準則,做出不道德的審計倫理行為。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調查了職業使命對顯示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和倫理行為的影響,研究審計職業使命觀和審計倫理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結果表明,職業使命作為工作價值觀的核心信念,在倫理行為決策過程中能發揮重要作用,職業使命觀能顯著增強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對倫理行為的正向作用。對比持有利已主義職業使命觀的學生,持有利他主義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具有更崇高的職業信念,在面臨道德兩難困境時,會激發高層次的道德推理能力,提高道德認知發展水平,進而決定實施更符合道德的倫理行為。進一步研究發現,持有不同導向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在面臨審計倫理困境時,所采取的倫理行為方式不同。持有社會導向和審計目標導向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在面臨道德兩難困境時,更傾向于采取拒絕減少必要審計程序、承擔責任等符合道德的倫理行為,而持有個人導向與職業導向的利已主義職業使命觀的學生則更傾向于采取轉嫁責任、減少必要審計程序等不符合職業道德的倫理行為。
鑒于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與職業使命觀在倫理行為決策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將審計職業道德設置為大學審計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并鼓勵開展審計倫理案例教學,以提高學生對倫理問題的敏感性和倫理推理能力。第二,在大一年級學生進行專業認知學習時,即利用新生可塑性強的優勢,幫助其樹立崇高的職業使命觀,為今后的審計執業行為堅定“主心骨”,點亮“指明燈”,并為踐行職業初心與使命打下基礎。第三,會計師事務所在招聘時,應優先聘用那些具有審計目標導向與社會導向職業使命觀的人員。具有崇高職業使命的員工,其行動目標更加清晰、明確,對工作充滿激情且更有責任心,愿意為職業使命奉獻和犧牲(Duffy等, 2011),在面臨審計倫理困境時,也更能堅守社會公平與正義,踐行崇高的職業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