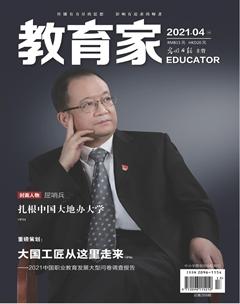讓大腦的成長有跡可循
楊寧 左西年



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關(guān)于健康的定義是:身體、精神和社會的全面幸福狀態(tài),而不僅僅是不存在疾病或虛弱足矣。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長發(fā)育,更是人類健康的基礎(chǔ)。
“WHO兒童生長標準”珠玉在前
1977年和2007年,WHO先后發(fā)表兩版“兒童生長標準”,就全世界每一個兒童應(yīng)怎樣生長提供證據(jù)和指導。縱觀兩版標準的發(fā)展變化,樣本來源由依托單一地區(qū)發(fā)展為全球多站點,且由關(guān)注身體生長擴展到身體生長、營養(yǎng)狀況和運動發(fā)育多角度,從而幫助我們了解什么時候兒童的營養(yǎng)和衛(wèi)生保健需求未得到滿足,有助于在早期發(fā)現(xiàn)和處理營養(yǎng)不良、體重超重和肥胖以及其他與生長有關(guān)的狀況。
兒童生長標準率先向全世界所有兒童提供最佳衛(wèi)生保健和營養(yǎng)的一個重要的新工具。并且在該工具的輔助下,清晰地反映出群體趨勢的變化,為提出改善及預防措施和政策提供依據(jù)。以超重和肥胖為例。2016年,超過3.4億名5—19歲兒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5—19歲兒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流行率從1975年的僅4%大幅上升到2016年的18%以上。男孩和女孩中的上升情況類似:在2016年,有18%的女孩和19%的男孩超重。1975年時只有不足1%的5—19歲兒童和青少年出現(xiàn)肥胖,但在2016年超過1.24億名兒童和青少年(6%為女孩和8%為男孩)存在肥胖情況。為此,WHO在2004年世界衛(wèi)生大會通過《世衛(wèi)組織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戰(zhàn)略》;2016年4月1日,聯(lián)合國大會宣布2016—2025年為“聯(lián)合國營養(yǎng)問題行動十年”;2018年發(fā)布《世衛(wèi)組織2018—2030年促進身體活動全球行動計劃:加強身體活動,造就健康世界》;2019年發(fā)布《5歲以下兒童的身體活動,久坐不動行為和睡眠指南》。
與身體健康同等重要的精神健康,同樣因為心理、神經(jīng)和精神障礙在人群中的加速流行,成為個人、家庭、社會的沉重負擔。2009年,美國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提出精神疾病是“腦疾病”的理念,并相應(yīng)提出基于腦的精神疾病研究策略。未成年人處于神經(jīng)發(fā)育旺盛期,也是神經(jīng)精神疾病重要的起病期。流行病學證據(jù)表示,精神障礙類疾病患者中50%首次起病在14歲前,67%在21歲前。已有研究證實:心理、神經(jīng)和精神疾病易感性出現(xiàn)的時間窗口是可以識別的:幼兒易感時期常出現(xiàn)破壞行為、表現(xiàn)出沖動和焦慮,而青春期則是情緒發(fā)作、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等易出現(xiàn)的階段。然而,心理、神經(jīng)和精神疾病在醫(yī)學上仍然缺乏“兒童生長標準”這樣客觀或生物學測試工具來進行大腦發(fā)育狀況的監(jiān)測,只能依靠臨床癥狀表現(xiàn)進行診斷,對神經(jīng)精神類疾病處于長期被動應(yīng)對狀態(tài)。幸運的是,隨著磁共振成像的最新進展,現(xiàn)在可以全面研究大腦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發(fā)展特點,點燃了將腦成像應(yīng)用于神經(jīng)精神疾病的臨床應(yīng)用中的希望。
腦發(fā)育軌線初探
科學家從神經(jīng)發(fā)育角度總結(jié)異常腦發(fā)育的模型,包括早熟、晚熟、停滯、未發(fā)育成熟和異位(圖1)。一旦對該模型的坐標實現(xiàn)量化,即可檢測發(fā)現(xiàn)對患病風險或發(fā)病具有提示意義的發(fā)育障礙;確定干預的敏感期;確定可修改的干預目標;監(jiān)測環(huán)境暴露和干預對發(fā)育的影響;檢測當前診斷分類的異質(zhì)性,以使診斷結(jié)果具有更堅實的神經(jīng)生物學基礎(chǔ)。
這個量化過程即基于普通發(fā)育兒童腦發(fā)育繪制“腦生長標準”,以及對特定神經(jīng)精神疾病刻畫其異常發(fā)育特點。想要繪制“腦生長標準”必須具備:可靠的測量指標;穩(wěn)定的測量工具;足夠數(shù)量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高精度的算法模型。顯然,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shù)已成為腦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和功能測量的有力工具。在目前的技術(shù)程度下,腦形態(tài)指標的可靠性已經(jīng)可以達到臨床應(yīng)用水平。這也大大降低了對樣本量的需求。研究者分別使用大樣本量橫斷數(shù)據(jù)、小樣本量縱向數(shù)據(jù)、大樣本量混合加速隊列數(shù)據(jù),在6—20歲兒童青少年的腦容量、灰白質(zhì)體積、腦脊液等指標上發(fā)現(xiàn)一致規(guī)律。這也與WHO繪制兒童生長標準的經(jīng)驗相符,即“兒童之間雖然存在個體差異,但是在區(qū)域和全球大規(guī)模人群之間,平均生長顯著相似”。
中國兒童腦模板
參照“WHO兒童生長標準”的發(fā)展歷程,“兒童腦生長標準”只是剛剛邁出萬里長征第一步。如前所述,我們在有限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中美兒童腦發(fā)育軌線呈現(xiàn)出相同的形狀。然而,再進一步,當我們使用已獲得的中國兒童青少年腦影像數(shù)據(jù),與在美國同步開展的國際合作項目獲得的美國兒童青少年數(shù)據(jù),分別制作出中美學齡兒童青少年基于年齡的腦模板和生長發(fā)育曲線時,一些有趣的結(jié)果浮出水面。
首先,在中美樣本分別制作出的基于年齡的腦模板中,腦灰白質(zhì)、腦脊液指標的總體發(fā)育軌線趨勢是類似的。然而局部年齡和變化速率還是能夠看出明顯差異。在明確這些差異的來源之前,對中美樣本采用各自且年齡相近腦模板進行處理,可能是最大程度降低配準誤差的必要手段。下面這個嘗試就充分體現(xiàn)這一點的重要性。
這一次(圖2),我們使用新制作的腦模板,按照功能區(qū)分出不同的區(qū)域,再計算每個功能區(qū)域的體積生長曲線。在初級功能的視覺網(wǎng)絡(luò),中美樣本的曲線完全平行;而在高級功能的默認網(wǎng)絡(luò)、控制網(wǎng)絡(luò)等,則表現(xiàn)出很大差異。有趣的是,如果對中美樣本采用單獨一方腦模板配準,這一差異就立即消失,有樣學樣地變成和對方一樣的曲線形狀。
已有的研究告訴我們,大腦的生長不僅是有跡可循的,而且會因某些因素造成區(qū)域間差異。而具體是哪些影響因素?是否能夠通過一些手段消除影響?現(xiàn)在尚未可知。WHO兩版“兒童生長標準”的誕生歷程也已經(jīng)為我們指出了前行方向——國際多區(qū)域站點、統(tǒng)一一致的采集策略和條件、縱向追蹤樣本。這些也是我國科學家們已經(jīng)和正在致力發(fā)展的,并且需要眾多適齡兒童、學校和家庭的關(guān)注和參與。能夠奔跑在該領(lǐng)域的國際前沿,是科學家們的驕傲,更是中國兒童健康乃至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福祉。
少年強則國強。這需要科技、教育、社會、千家萬戶共同攜手,讓腦生長標準早一天服務(wù)于兒童健康監(jiān)測,造福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