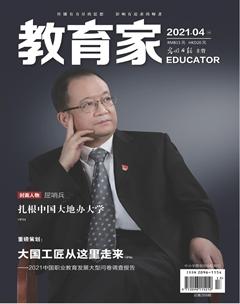讓“在線”變得更自然而然
楊斌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lái),在線教學(xué)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方式,師生一起接受了一次以信息技術(shù)促進(jìn)教學(xué)的大培訓(xùn)、大練兵,在社交隔離狀態(tài)下維護(hù)了正常的教學(xué)秩序,是大功一件。但隨著國(guó)內(nèi)疫情的有效控制,師生重返教室。在線教學(xué)的應(yīng)用,似乎又回到了疫情前,刀槍入庫(kù)、馬放南山。
著實(shí)有些可惜。在線教學(xué)當(dāng)然不是方方面面都優(yōu)于面對(duì)面的教學(xué),或者說(shuō)在虛擬現(xiàn)實(shí)(VR)和增強(qiáng)現(xiàn)實(shí)(AR)技術(shù)還沒(méi)有取得關(guān)鍵突破時(shí),還缺乏那種面對(duì)面才具有的“現(xiàn)場(chǎng)力”。但我們也許不該用非此即彼、完全取代的機(jī)械思維來(lái)分析,在線和現(xiàn)場(chǎng)并非零和關(guān)系,而是打出組合拳,自然融合,取長(zhǎng)補(bǔ)短。
試想一下,當(dāng)我們重新回到熟悉的教室,在線教學(xué)有哪些仍然可以發(fā)揮的優(yōu)勢(shì)呢?
很簡(jiǎn)單的設(shè)備,就可以實(shí)現(xiàn)教室中課堂教學(xué)的線上直播,給那些不能按時(shí)出現(xiàn)在教室的學(xué)生一個(gè)不落下課程的選擇,比如生病、外出比賽、國(guó)際旅行未恢復(fù)常態(tài)無(wú)法回到校園的海外學(xué)生等,教師也不必過(guò)于照顧遠(yuǎn)程、線上的同學(xué),能讓他們聽(tīng)課跟上進(jìn)度并通過(guò)其他方式交流,就是個(gè)難得的進(jìn)步。
一旦出現(xiàn)流感、諾如病毒等容易在校園群體中傳播的疾病,除了佩戴口罩之外,可能在未來(lái),生病的同學(xué)也會(huì)更自然地居家學(xué)習(xí)。那時(shí),簡(jiǎn)單的線上教學(xué)方式——當(dāng)然如果有條件的學(xué)校還可以加上更多交互手段,就很適合,也讓居家養(yǎng)病的學(xué)生和師長(zhǎng)親友更安心。
在線教學(xué),其實(shí)可以成為一種易行的教師聽(tīng)課觀摩、互幫互學(xué)的方式。標(biāo)桿示范教學(xué),能通過(guò)在線方式為新教師學(xué)習(xí)教學(xué)法、提升基本功提供極大的方便。聽(tīng)課的教師可以減少對(duì)課堂的打擾,并通過(guò)回放、對(duì)照來(lái)揣摩細(xì)節(jié),收獲更多。新教師也可以請(qǐng)自己的“師傅”(mentor)在線聽(tīng)課,提出改進(jìn)意見(jiàn),這樣比面對(duì)面聽(tīng)課更放松。
遇到我們希望有實(shí)務(wù)經(jīng)驗(yàn)的人現(xiàn)身說(shuō)法、現(xiàn)場(chǎng)教學(xué)時(shí),傳統(tǒng)模式要請(qǐng)嘉賓來(lái)到課堂,異地的話,還涉及旅行安排,費(fèi)時(shí)費(fèi)力。一旦請(qǐng)來(lái),還要鄭重其事,以嘉賓為中心,希望他多講些,包括但不止于課程所需。通過(guò)線上方式,更容易請(qǐng)到嘉賓出現(xiàn)在課堂屏幕上,以教學(xué)內(nèi)容為中心,講10分鐘20分鐘都可以,并即時(shí)回答師生們提出的問(wèn)題。中小學(xué)生集體組織去博物館、天文臺(tái)、實(shí)驗(yàn)室并非易事,通過(guò)在線方式,遠(yuǎn)端“向?qū)А笨梢詭е矗m然隔著屏幕,但比收看事先錄制好的節(jié)目,更互動(dòng)、生動(dòng)。較之傳統(tǒng)模式,嘉賓遠(yuǎn)端連線比旅行到校更容易,他們也會(huì)更愿意參與到教學(xué)中,教學(xué)中鮮活內(nèi)容的可得性能大大增加,花費(fèi)也更節(jié)省。這樣的線上方式,不僅降低了校園圍墻的高度、拉近學(xué)校與社會(huì)的距離,也實(shí)實(shí)在在減少了“碳足跡”,為碳中和做了貢獻(xiàn)。
現(xiàn)在的學(xué)生論文答辯或者學(xué)校講座、論壇,都是極好的知識(shí)擴(kuò)散、分享的機(jī)會(huì)。很多博士論文都有著難得的創(chuàng)新,研究者也很愿意跟同行們交流,只是很多交流都局限在現(xiàn)場(chǎng)參加的十多人甚至幾個(gè)評(píng)委中。如何通過(guò)線上方式,讓新知加速流動(dòng),讓同行更多交流,讓校園圍墻更低,讓創(chuàng)新走進(jìn)社會(huì),都值得進(jìn)一步探索、實(shí)踐。疫情中的線上答辯是為了減少流動(dòng)和應(yīng)對(duì)社交隔離,但合乎規(guī)范的線上答辯,還有著推動(dòng)學(xué)術(shù)交流和增強(qiáng)學(xué)術(shù)他律的“副作用”,如果隨著疫情解除就此擱置,著實(shí)可惜。
線上教育更有利于終身學(xué)習(xí)。現(xiàn)在越來(lái)越多的校友,希望不斷地利用母校豐富的學(xué)術(shù)資源更新知識(shí),在可持續(xù)學(xué)習(xí)的環(huán)境中提升能力。在線方式可以讓校友們的這種“念想”變成惠而不費(fèi)的“日常”。就像斯坦福2025計(jì)劃中的開(kāi)環(huán)大學(xué)所設(shè)計(jì)的,大學(xué)學(xué)習(xí)生活的on-off開(kāi)關(guān)會(huì)更靈活,社會(huì)和大學(xué)、工作和學(xué)習(xí)之間的串聯(lián)關(guān)系會(huì)走向某種并聯(lián)或串并融合。
總之,我們需要自覺(jué)地思考和實(shí)踐,把在線方式融入日常教學(xué),把在線當(dāng)作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非傳統(tǒng)教學(xué)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