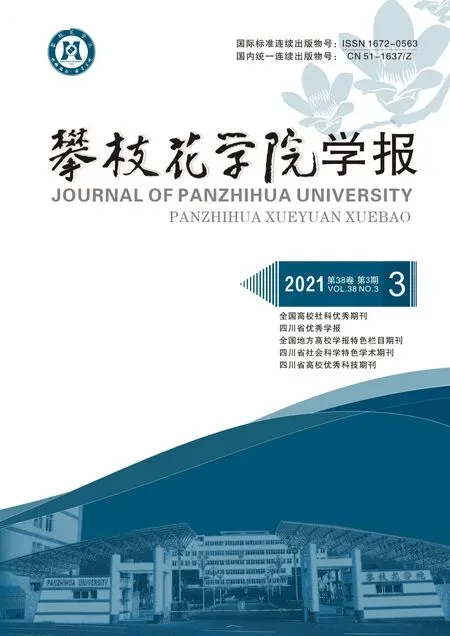基于微型語料庫的《茶經》英譯本風格對比研究
楊紅梅
(四川工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一、引言
《茶經》被譽為“茶葉百科全書”,對中國和世界茶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歷史性的推動作用。這部作品共三卷十章,七千余字,科學系統地概括唐代及以前有關茶學的知識和經驗。中國古籍翻譯是一種文化行為,對發展和傳播中華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中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茶經》的外譯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意義重大。迄今為止,《茶經》有兩個英文全譯本:一部由美國學者Francis Ross Carpenter所譯,名為TheClassicofTea:Origin&Rituals,1982年收錄于英國《大百科全書》;另一部由中國學者姜欣、姜怡合譯,名為TheClassicofTea,為中國對外文化輸出重大工程——《大中華文庫》分冊之一。
翻譯比較研究包括不同時期同一種語言平行譯本的研究或同一時期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研究,旨在發現不同語言的譯本中所使用的翻譯策略(Toury,2001)。[1]自Baker(1993)第一次提倡應用語料庫來探索翻譯現象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用語料庫驅動的方法來研究翻譯和改進翻譯實踐。[2]Sarah Laviosa(2002)從描述翻譯研究與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之間的聯系入手,以語料庫與翻譯研究為題,提出了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范式,其最大的優勢在于新穎靈活的研究方法和關于不同語言及翻譯現象的大量真實語料。[3]
本文運用描寫翻譯研究的方法對Francis和姜氏姐妹的兩個譯本進行描寫分析。為了科學客觀地比較兩個譯本的特點,筆者利用計算機平行語料庫從詞匯、句法和語篇三個方面對兩個版本的語言特點進行了研究和比較。其次,本文還對涉及文化相關的信息進行了對比研究,分析兩個譯本在中國傳統文化翻譯方面的得與失。數據分析之外,筆者采用例證研究,文中所有例句樣本均為對陸羽原文句子按順序標號后,在線隨機抽取。
二、兩個譯本不同的語言特點
利用語料庫進行研究,對一些難以捉摸的和不引人注目的語言習慣進行描述、分析、比較和闡釋,能比較令人信服地說明譯者的烙印確實存在(張美芳,2002)。[4]首先,建立兩個平行的微型語料庫:一個是Francis譯本語料庫,另一個姜欣、姜怡譯本語料庫。在此基礎上,利用AntConc對比分析兩個版本的形符、類符、詞匯密度、平均字長、平均句長、最常用的連接詞和代詞等統計數據,并采用香港大學英語中心的在線詞匯分析工具Online Vocabulary Profiler對兩者的常用詞詞頻進行比較。
(一)兩個譯本的詞匯特征
詞匯特征的分布規律包括詞匯密度、詞匯變化和詞長。形符是指語料庫中不同單詞的數量,類符是指語料庫中單詞的總數量。形符與類符的比率(TTR)雖然不能反映語篇的本質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詞匯的多樣性。比率越高,文章中使用的詞匯就越靈活和豐富。標準比(STTR)可以根據文本的一定長度(通常是1000字)分批計算,這樣更科學。表1為AntConc統計表示的兩種譯本的形符、類符及其比率:

表1 兩個譯本標準比
從上表數據可以看出,姜欣、姜怡的譯文總詞匯量略高于Francis譯文,她們的譯文比Francis看起來更復雜,句式更長,詞匯更多。姜氏姐妹的譯文類符及標注比都高于Francis譯本,由此可見,她們在翻譯過程中更注重詞匯的多樣化。然而,用香港大學英語中心建立的語料庫Online Vocabulary Profiler進行分析,不難發現,Francis譯本有更多的常用詞匯,而姜欣、版本則有更多的低頻詞匯,這與譯文的可讀性密切相關(見表2)。

表2 兩個譯本常見詞頻率比較
為了客觀地比較兩種譯本中詞匯的使用情況,作者計算了兩種譯本中少于4個字母的詞匯、4-6個字母詞匯及多于6個字母的長難詞的比例和使用頻率,其結果見表3。

表3 兩個譯本平均詞長比較
從表3統計數據顯示,姜新、姜怡版本中6個字母以上的單詞頻率和百分比高于Francis版本,而4個字母以下的單詞頻率和百分比低于Francis版。
平均詞長可以反映語篇詞匯的復雜程度。平均單詞長度越長,文本中使用的單詞就越復雜。如果這個數字低于4——普通文本中單詞的平均長度,那么文本的詞匯量就相對簡單,而高于4的詞匯運用則更為復雜。根據AntConc的統計,Francis版本的平均單詞長度是4.3,姜欣、姜怡版本的平均單詞長度是4.6,這意味著姜氏姐妹譯本的詞匯稍顯復雜。
通過對標準比、常用詞頻度及詞長的比較可以看到Francis更喜歡簡單的高頻詞匯,而姜欣、姜欣更喜歡選擇復雜的詞匯,這使得他們的版本相比較而言更難理解。以下列從原文中隨機抽取的樣本為例:
(例)原文:洪州以瓷為之,萊州以石為之。
Francis譯文:In Hung Chou the cauldrons are made of tile and in Lan Chou,of stone.
姜欣、姜怡譯文:In Hongzhou,tea boilers are usually made of porcelain while in Laizhou,ceramic is used as the material for tea boiling woks.
在單獨的句子中計算 TTR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此例的重點在詞匯運用上。Francis的譯文中僅有1個長詞有6個以上的字母,而姜氏姐妹的譯文中,除了地名外,還有6個長詞。此外,根據Online Vocabulary Profiler的分析,Francis譯文中有10個詞為最常用詞匯,其中有5個不在數據庫中;姜欣、姜怡使用了13個最常用詞匯,4個次常用詞匯,另外5個不在數據庫中。
(例)原文:翼而飛,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間,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
Francis譯文:Born to this earth are three kinds of creatures. Some are winged and fly. Some are furred and run. Still others stretch their mouths and talk. All of them must eat and drink to survive.
姜欣、姜怡譯文:Fledged birds are able to soar; fur-bearing beasts are able to scurry; and language -bestowed humans are able to speak. These three dominant beings on earth have long been in existence,eating and drinking to survive.
兩個版本同樣的詞匯特性也體現在上例中。Francis的譯文里只有2個超過6個字母的單詞,最常用詞匯占86%;姜欣和姜怡的譯文中有7個長詞,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占78% 。通過以上的討論和案例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Francis更喜歡簡單而頻繁使用的單詞,相比之下,姜氏姐妹的譯本對于詞匯的選擇更為復雜和多樣化
(二)兩個譯本的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包括句子的平均長度、從句分布、句型結構及句式復雜性等(Chesterman,1997)。[5]平均句子長度是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平均長度。就語料庫而言,句子的長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句子的復雜性(楊惠中,2002)。[6]一般來說,句子的平均長度越長,語篇的句法結構就越復雜,也就越難理解。兩種譯文中句子信息的統計結果(見表4)。

表4 兩個譯本平均句長比較
Laviosa(1998)發現,英語源語文本的平均句長為15.62個單詞,而英語翻譯文本的平均句長為24.09個單詞,從而得出結論:源語文本的平均句長明顯低于譯文。[7]上表數據顯示,Francis譯文和姜氏姐妹譯文的平均句子長度分別為16.3和20.4個單詞。這兩個數據都介于英語源語文本和英語翻譯文本的平均句長之間,這說明兩個版本都使用了較多的中等長度的句子,這有助于讀者理解。Francis的平均句長較低,接近Laviosa研究發現的英文原文的平均句長,說明Francis的母語優勢在翻譯中得到了充分利用,他的句法構架更符合真實的英語表達。而姜欣、姜怡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了顯化策略,通過增加修飾語、明確原文的隱含意義和解釋等方式來提高翻譯的清晰度,這導致譯文句子長,句式更復雜,從而降低了其可讀性。
(例)原文: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
Francis譯文:Tea is from a grand tree in the south. The tree may grow from one to two feet to as much as twelve.
姜欣、姜怡譯文:Tea (botanically termed “camellia sinensis”) is a fine plant indigenous to South China,the size of which varies from one or two feet up to dozens of feet in length,depending on where they vegetate.
以上例句中,Francis版本的平均句長是11.5詞,姜欣、姜怡版本的平均句長是35詞。姜氏譯本用詞更加專業,在“茶”一詞之后,譯者用增譯的方法在括號中補充了植物學上的術語。后文的“depending on where they vegetate”也為增譯內容,如若刪除,不影響句意。此外,姜欣、姜怡譯本的句子結構比較復雜,漢語原文的兩個句子譯成了一句,其中包含定語從句和賓語從句。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發現,Francis的譯本更加精煉,更接近《茶經》的句法結構,而姜欣、姜怡的譯本更像是一部科普著作。
此處第八章的類符、句子數量及平均句長未在表中描述,因為Franics在這一章節的譯文沒有完整的句子。他采用非網格表描述了主產區不同茶葉的品質狀況,并根據區域對茶葉進行分類。這種方法不僅清晰地傳達了原文的意思,而且使讀者對不同地區各種茶葉的優劣有了比原文更直觀的認識。這體現了西方人嚴謹的邏輯思維和譯者的職業規范,也符合譯文讀者的期望。
(三)兩個譯本的語篇特征
銜接和連貫是語篇研究的兩個核心概念。銜接是詞匯、語法和其他關系的網絡,它提供了文本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連貫是構成文本表層結構的概念關系網絡。語篇正是通過銜接手段來實現其連貫性。在翻譯過程中,有時候譯文中并不存在顯性的銜接關系,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譯文讀者有必要的背景知識來成功地理解其隱性關系。銜接是語篇分析或篇章語言學中可用于翻譯的最有用的成分(Newmark,2001)。[8]漢語喜歡使用更簡短的結構,并只有在必要時明確標明這些結構之間的關系。但英語常以相對較小的模塊來傳遞信息,并以明確的方式表達信息之間的關系,使用各種連接詞來標記分句、句子和段落之間的語義關系。因此,在漢英翻譯過程中,適當地增加銜接關系、銜接標記和連貫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翻譯質量。表5列舉了兩個譯文中的出現頻率最高的10個連接詞,以此為例來研究翻譯中的銜接問題。

表5 兩個譯本常用連詞頻率及百分比比較
上述連詞在Francis譯本和姜欣、姜怡譯本中分別占7% 和6% 。結果表明,雖然Francis譯本中連詞使用的頻率和百分比略高,但兩個譯本都非常關注原文中隱含的邏輯關系,通過添加連接詞使原文連貫流暢。
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照應關系。Barker認為英語和其他語言中最常見的照應關系是通過代詞來實現。相比之下,不難發現,Francis 使用更多的代詞,比如“ it”和“they” ,“that”無論是作為代詞還是連詞,在他的版本中出現得更加頻繁(見表6)。

表6 兩個譯本常用代詞頻率比較
(例)原文: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
Francis譯文:Do not pick on the day that has seen rain nor when clouds spoil the sky. Pick tea only on a clear day. All there is to making tea is to pick it,steam it,pound it,shape it,dry it,tie it and seal it.
姜欣、姜怡譯文:When it comes to the proper weather for harvesting fresh tea,rains are definitely out of the question,and cloudiness should be excluded as well. Only clear and fine days allow for this activity. Following the initial step of plucking,the curing then would go from steaming,pounding,molding,baking,stringing,all the way to packing in a row for fresh tea leaves to be processed ready.
在Francis的譯文中,代詞“ that” ,“it”及連詞“ nor” ,“ when” ,“ and”起到了銜接上下文的作用。他把7個“之”翻譯成7個“ it”,通過銜接手段給目標讀者一個完整而毫不含糊的句子。在姜欣、姜怡的譯本中,使用了 “when”,“and”,“as well” 和 “then” 作為銜接手段。詞匯重復在指稱可能出現歧義的情況下是一個更安全的選擇。例如,“fresh tea” 在她們譯文中出現了兩次。此外,他們還使用替代的方法讓譯文更加的順暢,“this activity” and “the initial step of plucking” 被用來代替“harvesting fresh tea”。英語傾向于使用更多的代詞,通過指稱來傳遞邏輯信息,而漢語則常常依靠名詞的重復來傳遞邏輯信息。姜欣、姜怡的英譯本也體現了漢語的這一特點,這與代詞相比,無疑使得譯文冗長而復雜。
(例)原文:其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水多者.
Francis譯文:If you must use river water,take only that which man has not been near; and if it is well water,then draw a great deal before using it.
姜欣、姜怡譯文:If river is the only accessible source,bail the water from a spot away from human habitation. Where well water has to be used,choose a well that is frequently drawn from.
上例中,Francis使用了“ that”“ it”和“ before” “and”等銜接手段,為了避免重復,他用“ that”代替“ river water”。在姜欣、姜怡的譯本中,“water”,“river”等名詞多次重復,以避免歧義,但與Francis的譯本相比,她們的翻譯似乎不夠簡潔流暢。此外,姜欣、姜怡譯本中的“accessible” “habitation” “frequently”等詞匯也較為復雜。
總之,基于語料庫和AntConc的語言特征比較發現,Francis選擇了最常用的簡單詞語和相對較短的句型,他的譯本非常流暢易懂,不僅符合當時的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需要,中國讀者讀起來也不費勁。姜欣、姜怡采用了較多的難詞,其中包括一些術語,更注重詞匯和句子結構的多樣性,因此他們的譯文讀起來比較復雜,可讀性稍差。
三、兩個譯本不同的文化特征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反映了文化和思維方式,表達了人們的世界觀。翻譯是一項跨文化對話活動,是一個文化移植的過程。文化和翻譯是人類交際中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變量,因此文化影響譯文的質量,文化傳統的差異是文化意象差異的主要和直接原因(Mohammad,2012)。[9]在翻譯中,譯者應注意原文化的獨特內涵和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而且他們也應考慮如何克服目標讀者理解的障礙。
(一)兩個譯本文化信息的傳遞
1.度量衡的不同翻譯
古代中國的度量衡與現代中國不同。中國古代大多數獨特的計量單位在英語語言和文化中沒有精確的對應。表7顯示了兩個版本中長度、容量和重量的不同換算。

表7 兩個譯本度量衡的翻譯對比
為方便西方讀者理解,Francis把度量衡單位“尺、寸、丈、升、斗、斤” 分別譯成了目標語文化中的“feet,inch,ten feet,gallon,pints and catty”。在159頁的尾注中,他解釋說衡量標準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附上各種衡量標準的轉換。其中,“斤”是中國傳統的重量單位,起源于唐代,陸羽生活的時代。Francis將“斤”翻譯成中國古代的“catty”,反映了過去和現在一斤的不同概念。
總的來看,姜欣、姜怡兩位譯者也采用了將中國古代的度量方法轉換成全球讀者熟悉的度量方法。為了讓讀者了解“斤”,譯者在括號內注明“一斤 = 0.5公斤”。然而,他們忽略了 “一斤”在唐代與現代的細微差別,造成了中國文化意象的扭曲。
2.名稱的不同翻譯
《茶經》原文包含眾多人名、地名和工具名。在Francis的版本里,人名和地名都采用當時流行的威妥瑪式拼音法表示。例外的是那些在西方以不同名稱而聞名的地方(Francis,1974)。[10]例如,Francis將廣州譯為Canton 而不是KuangChou。在尾注中,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地方的確切經緯度,這充分證明了譯者對學術的忠誠和對讀者的責任。相應地,當代漢語拼音系統被用在姜欣、姜怡的譯本中來翻譯各種名稱。譯者在翻譯地名的時候,不僅提供漢語拼音,而且還補充了當前的地理位置,這既符合目標讀者的需求,又反映了譯者的職業規范。兩個譯本的區別在于,目標讀者可以通過Francis的版本了解確切的緯度和經度,從而判斷其地理位置,這符合西方較嚴密的邏輯思維習慣;而姜欣、姜怡的譯本補充的是當前的地理位置名稱,與過去的地名形成了對比。
《茶經》第二章主要論述了采茶和貯茶的工具,第四章主要介紹的泡茶工具。表8中的10個工具是從這些章節中隨機選出的。Francis 采用了本地化策略。這要求翻譯以一種透明、流暢、隱形的風格方式進行,把譯文的異質性減少到最少(Venuti,2004)。[11]基于目的語的文化翻譯策略有助于譯文讀者的理解,但有時會降低翻譯的準確性,導致文化內涵的喪失。例如,Francis版本中的“basket”不能表達“籯”的完整含義和形象,為了彌補文化信息的缺失,譯者在這里加入了一副竹籃的插圖。在姜欣、姜怡的譯本中,第二章采用了音譯法加解釋。在第四章中,譯者放棄了音譯法,她們試圖表達這些器具的功能。例如,“chopsticks”意味著火夾有撿起東西的功能,“supporting”也表達了支撐的功能,但是“fire”用來修飾“chopsticks”可能會導致誤解。

表8 兩個譯本器具名稱的翻譯對比
3.官職的不同翻譯
《茶經》記載了唐代許多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官名,在英語語言文化中很難找到對應的詞語。從第七章中隨機抽取下面的八個正式官職,從中可以看出兩個譯本的翻譯策略(見表9)。

表9 兩個譯本官職翻譯的對比
兩個譯本的譯者對以上官名的翻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上述表格可見,Francis在翻譯中忽視了如“相”,“太傅”,“內史”和“司空”這樣的一些官職。此外,在第七章第五段中一共提到了24個官員,但在Francis的版本中只找到了其中的19個,其他5個被省略了。與Francis的版本相比,姜欣、姜怡的譯本更加完整,24個官員沒有任何缺失,而且譯者解釋了每位官員的職責和職能,還對部分原文進行了增譯。例如,在上表中《茶經》原文對“陸吳興納”并未給出其官職,姜欣、姜怡在查閱了參考資料后為其補上了職位,譯為“a procuratorof Wuxing named Lu Na”。
4.顏色的不同翻譯
《茶經》是一部關于茶科學的科學專著,如何準確地將顏色詞翻譯成英語是茶葉經典翻譯成功的重要部分(姜怡,2010)。[12]

表10 兩個譯本顏色詞的翻譯對比
《茶經》第四章中陸羽用表10中的顏色描述了茶碗對茶湯色澤的影響。Francis提供的色彩詞中,“cinnabar”為朱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它經常出現在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是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色彩。姜欣、姜怡的譯本也可使讀者體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妙之處。“white” 和“crystal”傳達出 “as white as snow” and “as clear as crystal” 等意象,使讀者感受到不同瓷器的質感和色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jade” “emerald”和 “cyan glaze” 等詞語更是生動形象地描繪出“綠”和“青”的細微區別。
(二)兩個譯本中的傳統文化
陸羽的《茶經》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思想淵源——儒、釋、道。“其山水,慢流者上”和“非渴甚莫之飲”,體現的是儒家中庸即適度的思想。“坎上巽下離于中,體均五行去百病”象征著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平衡可以去除疾病,是道家思想的體現,廣泛滲透到中國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學、語言等各個領域。陸羽還認為茶適用于“精行儉德之人”。崇尚誠實、簡樸也是儒、釋、道三家的共同哲學,體現了中國人內在的道德規范。對于這樣一部具有豐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經典之作,譯者能否傳達其深邃博大的世界觀、人生哲學、美學以及中國文化哲學家思想精髓,是翻譯成功與否的關鍵。
原文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的文化距離越遠,就越需要各種手段的使用,如增譯、解釋、腳注等。雖然兩個譯本的譯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但他們都盡最大努力避免了文化意象的丟失和扭曲,保留其文化內涵。譯者自身對原文語言的期待規范也其將影響原文的理解和翻譯策略。
(例)原文:坎上巽下離于中。體均五行去百病。
Francis譯文:K’an above; sun below and li in the middle. Harmonize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body and you will banish the hundred illnesses.
(Note77:K’an,Sun and Li are three of the eight trigrams on which 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the Changes is based. The trigrams consist of……)
(Note 77:The five elements are fire,earth,water,wood,metal.)
(Note 77:The hundred illnesses are defined by one commentator as troubles arising from disruption and deceit.)
姜欣、姜怡譯文:Water above,wind below and fire inside.Balancing five elements to cure all diseases.
陸羽在介紹風爐時,遵循“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的哲學,將茶的本性與自然法則相結合。煮茶體現了自然法則,是金、木、水、火和土混合以保持平衡和消除一切疾病的過程。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Francis采用直譯加注釋的方法來彌補文化信息的空缺,給出了長達183字的三條尾注,由于篇幅有限,此處省略了第一條尾注后面的部分。由于“坎”、“巽”、“離”這三個漢字在目的語中為空白,譯者采用了音譯的方法,再附加尾注將其解釋為八卦中的三卦。另外“五行”、“百病”的翻譯也采用尾注加以補充。
姜欣、姜怡在翻譯這部典籍時,正值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兩位譯者直接把“坎、巽、離” 譯作“water,wind and fire ”,把“五行” 譯為 “five elements”,“百病” 譯為 “all diseases”而沒有更多的解釋。實際上眾多讀者并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兩個譯本的譯者對“況非此者,設服薺尼,六疾不瘳”譯文的處理也與上例類似。在直譯之后,Francis對于何謂“六疾”、“六疾”從何而來、“六疾”與“氣”之間的關系給出了長達59字的尾注;而姜欣、姜怡給出的譯文為“No illness can hopefully get cured if balloonflower root is taken for ginseng.”譯文雖簡潔明了,讀者卻無法體會其中的文化元素。
中國古籍是高語境文化的典型產物,傾向于直接交流,通過語言本身清晰明確地表達意義,而英語屬于低語境文化,傾向于間接交流,從上下文語境中推斷出意義。中國古籍文本是為古代中文讀者編寫的,因此能夠很好地匹配相關的語境信息,實現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有效溝通。然而,翻譯的過程往往會打破這種自然的和諧,將原文從其特定的交際環境中剝離出來,將其所攜帶的信息轉化為另一組完全不同的語言符號(姜欣、姜怡、林萌,2009)。[13]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之間存在文化差異較大,除了目標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外,譯者還應探索盡可能多的傳播文化信息的途徑。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通過增補來表達隱含的語義和文化內涵信息,最大限度地實現信息的充分傳遞,西方讀者才不會茫然不知所措。
四、結語
本文以AntConc為研究工具,在利用語料庫對《茶經》的兩個英譯本進行描寫和比較的基礎上,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兩個譯本在語言特點和文化信息處理上有著明顯的差異。Francis譯本的詞匯和句子更簡潔,而姜欣、姜怡的譯本讀起來較復雜難懂。Francis使用了更多的銜接手段,因此他的譯本讀起來更加順暢。在文化方面,兩個譯本都有一定的文化扭曲和失落,但Francis力圖保留其文化內涵,并以引言和尾注補充了一些文化信息。姜欣、姜怡的譯本中簡化了一些西方讀者不熟悉的文化信息,但翻譯全面完整,未遺漏原文中的任何字面信息。其復雜的詞匯、專業術語和復雜的句型讀起來象一部科普作品,似乎比較符合中國讀者學習英語的需求。
譯文的接受程度與譯文的可讀性密切相關,這可能會受到翻譯策略和原文與譯文之間關系的影響。影響兩種譯本相對可讀性的語言選擇差異與原文的特點沒有多大關系,而只與譯者在譯文系統本身內部所做的選擇有關(Puurtinen,1995)。[14]而譯者在理解和詮釋譯文方面所做的選擇是由翻譯的目的決定的。姜欣、姜怡兩位譯者認為,“茶典籍應當既保留東方茶韻,又能為希望了解中國文化的目標讀者欣賞并益智。保持文本的異域性無疑將有益于世界各國的目標語讀者了解、品賞、學習純美的中國茶文化”(姜欣、姜怡 2009:前言25)。[15]Francis(1974)在其譯本的序言中所說,如果能夠在任何程度上促進東西方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那么這個譯本的目的就達到了。除此之外,造成兩個譯本差異的原因還有很多,如譯者身份、譯者所處社會文化背景、個人進行翻譯的時間不同、譯者對目標讀者的期待規范的理解不同、譯者與委托者的關系及溝通程度不同等等。而且,從不同的研究層面出發,各個譯本可能又會呈現各自其他不同的特有風格。從語料庫著手研究能使源文和譯文的全貌比較客觀的得以展示,但還是應結合與翻譯本質相關的理論來進行研究才能更全面的理解這兩個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