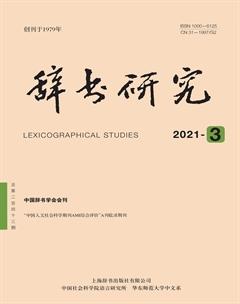網羅中外 匠心精斷
徐時儀 劉靜靜
摘?要?《經律異相》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佛教類書, 《經律異相校注》廣搜博檢現存各本,比勘異文,從語音、詞匯、語法各要素聯系著手,考斠是非,補正成說,有裨于漢語史研究及文獻的整理校訂和語言辭典的編纂。
關鍵詞?《經律異相校注》?版本?異文?考斠
漢魏以來,佛教傳入中國,大小二乘、三藏圣教等釋典成為漢語文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梁僧寶唱等纂集的《經律異相》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佛教類書, 博采釋典所載傳說、寓言、譬喻等因緣故事,以類相屬,闡釋佛陀“真如本性”和隨緣說法的方便法門,不僅展現了大千世界的紛繁事相,而且勸諭世人棄惡揚善,集出世與入世思想于一編,具有佛教百科全書的性質。
《經律異相》早于隋虞世南所編類書《北堂書鈔》近百年,更早于唐釋道世所編《法苑珠林》一百五十年,對《北堂書鈔》《法苑珠林》等后出類書的體例及內容皆有重要影響。200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周叔迦、蘇晉仁校注的《法苑珠林》點校本,而《經律異相》的點校一直闕如。值得慶幸的是,2018年巴蜀書社出版了董志翹教授等所撰的《經律異相校注》。志翹教授多年來傾心力于訓詁研究,長于考證,碩果迭出,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匯研究》《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注》《世說新語箋注》《大唐西域記譯注》《啟顏錄箋注》等,以其在漢語史和佛典語言學研究上的厚實功力,校注《經律異相》可謂得人矣。該書以《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經律異相》為底本,以《中華大藏經》本對校,并以南宋《資福藏》《磧砂藏》,元《普寧藏》,明《永樂南藏》、《徑山藏》(即嘉興藏),清《清藏》(即《龍藏》)以及新發現的日本古抄本三種——七寺古抄本、金剛寺古抄本、興圣寺古抄本為參校,既有詳細的校勘和通俗易懂的注釋,又有精當而嚴謹的考證,具有僧俗皆宜、雅俗共賞的特性,填補了釋典校注的這一空白。
讀好書是人生的一種享受,讀到好的校注更有頗多心有靈犀豁然開朗的享受。細品其書,主要體現有如下三大特色。
一、 注重版本的精益求精
要做《經律異相》的解人,首先要知人論世。作者對寶唱的生平事跡及《經律異相》的成書等做有專門的研究,可謂對寶氏其人以及有關研究了然于胸,尤其是作者積數十年專注研究佛典語言之功,十分注重語料的可靠性,力求使所做校注建立在扎實的基石之上,從書中所做考證可見其考察了《經律異相》現存于世的每一種版本,不僅囊括中土,而且旁及域外。作者早在2011年就以通行的《大正藏》作為底本,以《趙城金藏》《高麗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1]等八個版本作為對校本,從文獻學的角度對《經律異相》做有點校,撰成《〈經律異相〉整理與研究》(董志翹2011),凡94萬字。嗣后又廣搜博檢,爬羅剔抉,張皇幽眇,將視野拓展至域外寫本藏經中的日本七寺、金剛寺、興圣寺藏古寫本《經律異相》,進而使《經律異相》的校注更上層樓。七寺、金剛寺、興圣寺藏古寫本所據底本可能是我國早期未經刻版印行的寫本,與刻本相比,甚有特色。如七寺一切經被認為是繼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窟出土大量經文以來的又一大發現,受到各界的矚目。[2]七寺建于奈良時代天平七年(735),正式名稱為“稻園山正覺院長福寺”。據落合俊典(1990)《七寺一切經和古逸經典》一文所考,七寺所藏寫經源自奈良古寫經,屬于較早傳入日本、非常接近原典的奈良朝寫經系統的經典。其中有不少學術價值很高的古逸經典,有些經文的原本我國本土已不明去向,甚至被認為是“虛構的經典”。如久已失傳的署名“羅什造”的《大乘入道三種觀》、唐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及《馬鳴菩薩傳》等。因此,這三種古寫本《經律異相》可以說是漢語史研究的理想語料,運用了大量俗體字、簡體字、異體字,從中可見漢文文獻東傳日本過程中漢字使用上發生的一些變化,為中古漢語的音韻、文字、訓詁研究及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修訂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經律異相校注》既是作者多年來研究《經律異相》的心血結晶,也是日本七寺、金剛寺、興圣寺藏古寫本《經律異相》研究的新成果,不僅奠定了日本古寫本《經律異相》研究的扎實基礎,而且也必將推動日本古寫本藏經的研究更加深入。
二、 注重異文的洞微燭幽
《經律異相》共50卷,40萬言,博取佛經中782則故事傳說。這些故事傳說大都構思巧妙、哲理深邃、譬喻貼切,后漸演化為家喻戶曉的成語和民間傳說,為戲曲、小說所取材。如出自《賢愚經》的國王智判二母共爭一兒案的故事,至元代演變為《包待制智勘灰闌記》雜劇,近代和現代歐洲又有人把它改編成《高加索灰闌記》等三種戲劇;原出《摩訶僧祇律》的商人驅牛以贖龍女得金奉親的故事,啟迪產生了唐代龍女牧羊、柳毅傳書的傳奇;眾多的神怪、動物故事則對六朝、隋唐志怪小說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催發和推動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經律異相》引用的270多種佛經,既有早期佛教的重要經典四部《阿含經》,也有部派佛教的重要律典,還涉及大乘佛教時期的相關經典,不僅可供鉤沉今已亡佚的近百種佛經原文,而且提供了類型豐富的大量異文,較全面地反映了東漢至梁代的語言事實。這270多種佛經既有錯綜復雜的各本異文,又有所錄文獻與所出原經的異文,還有所錄文獻及相關傳世佛典的異文。其中相關傳世佛典的異文涉及不同佛典中同一內容的異文,如《諸經要集》《法苑珠林》《出三藏記集》等其他佛典所載同一佛教故事的異文,慧琳《一切經音義》和可洪《隨函錄》所釋《經律異相》2000多條音義的異文,《磧砂藏》所載《經律異相》每卷下2000多條音義的異文,《大正藏》《卍續藏》所載歷代佛經義疏所引《經律異相》的異文,尤其是慧琳《一切經音義》和可洪《隨函錄》所載往往多為早于現存藏經的異文,其指出的文字正俗、通用或體、非誤等現象反映了《經律異相》最初的原貌。作者指出分析《經律異相》的這些異文,不僅為破解佛典和相關文獻中的疑難疑義詞提供了信息和幫助,而且促進了中古漢語在文字、詞匯、訓詁方面的研究和語料發掘。
三、 注重是非的考斠識斷
點校的功夫不在于羅列異同,而在于勘定是非的識斷力。作者逐詞比勘了日本七寺、金剛寺、興圣寺藏古寫本《經律異相》的異同,積累了大量翔實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確保了考斠的周密可靠,不僅列出了諸本異文,糾正了有關此書校注中的一些失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修正了原來的一些斷句和標點,而且精于探索,善于考證,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慧眼獨到的學識見識,注釋了一些較難理解的佛教術語和中近古的方俗詞語,尤其是就一些異文的是非做有考斠,不僅力求知其然,而且于明其所以然上亦用力甚勤,勝義疊出,每每從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各要素聯系著手,于眾說紛紜中獨辟蹊徑,創立新見,補正成說,所下斷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多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有裨于漢語史研究及文獻的整理校訂和語言辭書的編纂。
下謹略舉八例以見其三大特色之犖犖大者。
(1) 如來應跡投緣,隨機闡教,兼被龍鬼,匪直天人。(《經律異相》卷一“序”)
投緣,作者認為當從日本《七》《金》《興》三本作“逗緣”。指出在佛典中“逗緣”出現較早,《大藏經》中就有近百用例。如隋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今以付屬汝,汝可秉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后斷種人也。”(T50—192b)而“投緣”在唐宋以后方見到,且在《大藏經》中僅一見。
(2) 自茲厥后,傳譯相繼。(《經律異相》卷一“序”)
傳譯,《麗》《資》《磧》《普》《南》《徑》《清》本作 “翻譯”。作者認為當從日本《七》《金》《興》三本作“傳譯”。指出“傳譯”“翻譯”意思雖相近,但早期漢譯佛典中均用“傳譯”,“翻譯”則較為晚起。如后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卷一:?“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T08—425b) 又如與《經律異相》同時代的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古經現在,莫先于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張騫之使。”(T55—5b) 僧佑《出三藏記集》中“傳譯”凡十二見,而未見“翻譯”。
(3) 又勅新安寺釋僧豪、興皇寺釋法生等相助檢讀,于是博綜經籍,擇采秘要。上詢神慮,取則成規,凡為五十卷。(《經律異相》卷一“序”)
神慮,《資》《磧》《普》《南》《徑》《清》本均作“宸慮”,作者認為原應作“神慮”,當是后之版本改為“宸慮”,應從《大藏經》《麗》本及日本《七》《金》《興》三本作“神慮”。指出“神慮”“宸慮”雖皆有“天子的思慮、意圖”義,但“神慮”一詞出現較早。如《三國志·魏志·劉劭傳》:?“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而“宸慮”之“宸”原指“屋檐”,引申有“深邃的房屋”義,又指北極星所居,即紫微垣,再引申有“帝王之住處”,從而用以稱代帝王。由“帝王”這一義位組合的復音詞如“宸心”“宸念”“宸旨”“宸恩”“宸威”等無不產生于唐宋之后,“宸慮”的最早用例也始見于唐代。如柳宗元《王京兆賀雨表四》:?“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李德裕《論救楊嗣復李玨陳夷直》:?“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
(4) 入池沐浴,詣香樹下,枝條垂曲,取香涂身、衣莊嚴具、華鬘寶器、果實樂器,各有樹出。(《經律異相》卷一“四天王天”)
作者指出據寶唱原注,此段文字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又出《大智論》《樓炭經》。例中“衣莊嚴具”,《資》《磧》《普》《南》《徑》《清》本作“衣具莊嚴”,認為當從日本《七》《金》《興》三本作“衣莊嚴具”。“莊嚴具”即裝飾物,亦可簡稱“嚴具”“莊嚴”。所謂“衣莊嚴具”指兩物,即衣服和裝飾物,與下文之“華鬘寶器,果實樂器”均為并列關系,乃言衣服、莊嚴具、華鬘、寶器、果實、樂器各有樹出,可隨意所取。
(5) 其四園中各有二石垛,各各縱廣五十由旬,七寶所成,軟若天衣。(《經律異相》卷一“忉利天”)
作者指出據寶唱原注,此段文字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又出《樓炭經》《大智論》《華嚴經》《涅槃經》。例中“垛”,《大藏經》《資》《磧》《普》《南》《徑》《清》本均作“墮”,日本《七》《金》《興》三本作“隨”,當從《麗》本作“垛”。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二:?“石:?徒果反,《通俗文》:?‘積土曰。經文作墮非也。”(T54—650c) “”乃“垛”之異體,“墮”乃“垛”之同音借字,“隨”乃“墮”之形近而訛。
(6) 遍凈天(梵言韋細,《依品》云:?“以上方便生此天。”)王名凈智,四臂捉具持輪,御金翅鳥。(《經律異相》卷一“遍凈天”)
作者指出寶唱原注此段文字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又出《樓炭經》《大智論》。經查閱,“韋細”“捉具”,《長阿含經》中未見,然其他經文及工具書均作“韋紐”“捉貝”,認為當從日本《金》本及《大藏經》《資》《磧》《普》《南》《徑》《清》本作“韋紐”“捉貝”。“貝”為西域傳來的螺、蠡一類吹奏器,可用以令兵聚眾,也可僧道用作法事。“輪”是一種能拋擲出去并可回收的輪狀殺器。印度武器中有 cakra(爍迦羅或斫迦羅)可譯為旋輪、投輪或斗輪、劍輪。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輪者,西國有戰輪,以作輪,上施利刀。漂飛遙擊,斷彼命根。或傷手足,或損身分。其輪卻回,巧妙接取。名曰斗輪。遠即弓弩,次近用輪,更近羂索刀棓及用槍矟矛。”(T54—708b)慧琳所釋反映了其時作戰,遠距離用弓弩,不近不遠用斗輪,很近的距離用刀槍棍棒。戰輪是其時一種可以飛擲出去傷人,又能再收回的中程武器。據周緯先生(1993)《亞洲古兵器圖說》介紹印度古兵器說,印度民族有一種用手指遙擲的兵器,名為恰克拉,系以第二指搖轉旋動遠擲,以傷敵人之頭頸、咽喉而置人死命的殺人圈。佛經中又稱此兵器為劍輪,據志翹教授(2000)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匯研究》,“劍輪”最早見于漢譯佛典。從文獻用例來看,“劍輪”當是一種人工制作的,可以飛擲出去傷人的,遍施鋒刃的輪狀武器,大致可以看作是冷兵器時代的一種中程武器。
(7) 一切惡道及阿修倫,皆悉蕩盡。罪終福至,皆集第十五天上。十四以下,盡成炎墨。(《經律異相》卷一“三大災”)
炎墨,作者指出當從日本《七》《金》《興》三本及《大藏經》《資》《磧》《普》《南》《徑》《清》本作“灰墨”,認為“灰墨”指暗黑色的劫后余燼,在中土文獻及佛教文獻中常見。如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三:?“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后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隋達摩笈多《起世因本經》卷九:?“彼等如是,極大熾然,猛焰洪赫,無有余殘灰墨燋燼,可得知別。”(T01—410c)而“炎墨”,查遍中土文獻、漢譯佛典皆未見,僅大正藏版《經律異相》中一見,顯誤無疑。
(8) 又方一由旬石山,士夫以迦尸衣百年一拂,拂之不已,石山鎖盡,劫猶未竟。(《經律異相》卷一“劫之修短”)
“石山鎖盡,劫猶未竟”,日本《七》《金》《興》三本均作“石山銷盡,劫猶未竟”,作者指出當以寫本為善。又據寶唱原注此段文字出《大智度論》《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等。考“劫猶未竟”,《大智度論》卷三十八作“劫猶不澌”。“‘澌,【宋】【元】【明】【宮】作‘儩‘賜。”“盡”“賜”“澌”為同義詞,均有“竭盡”義。考揚雄《方言》卷三:?“、鋌、澌,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濮生;物空盡者曰鋌。鋌,賜也。”作者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異文說明了一個重要語言現象,“盡”為通語,“賜”“澌”為方言詞。《經律異相》此則原本作“劫猶不賜”,而《大智度論》中原本作“澌”或“賜”(因為當時“澌”即音“賜”,兩字同音,方言往往用記音字),日本的古寫本很好地保留著原貌(外國人不可能用方俗語“賜”去替換通語“盡”),而我們國內宋后刊刻《大藏經》時,已部分用通語詞替換了方俗語詞(將《經律異相》中的“賜”改成了“盡”,而《大智度論》中的“澌”仍保留著)。這正符合官方刻書“改俗為雅”的常例。
凡此種種,足見作者建立在扎實的語料與實學實證基礎之上的深厚功力及卓有創獲。
四、 結語
釋典義理博雜,名相浩繁,“吾儕今讀佛典,誠覺仍有許多艱深難解之處。須知此自緣內容含義,本極精微,非可猝喻”(梁啟超1936)。釋典的校注非急功近利者所能為,沒有語言文字訓詁方面的扎實功底亦難為也,而《經律異相》的校注更是需要有金剛鉆才能做的瓷器活,唯有樂于上下求索而不倦者方能為矣。陳寅恪先生(1930)在《敦煌劫余錄》序中曾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綜觀全書,可見作者善于利用域外文獻資料從事古典文獻整理與漢語史研究,在取用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上可以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入流”來概其大要,且于所校所注的字里行間滿溢著作者從事古典文獻整理與漢語史研究的強烈使命感。該書作為志翹教授主持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語史語料庫建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可以說實實在在地展示了作者多年來辛勤耕耘所做的新開拓,從中可以觸摸到作者憑借其淵博的學識和扎實的語言及文獻功底,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學術高峰攀登的辛勞甘苦,更可以感覺到一個有志于古典文獻整理與漢語史研究的學者志向的高遠和腳踏實辛勤耕耘的難能可貴。
附?注
[1]上文提到的幾本古籍在下文中均寫作簡稱:?《中華大藏經》以下簡稱《大藏經》;《資福藏》以下簡稱《資》;《磧砂藏》以下簡稱《磧》;《普寧藏》以下簡稱《普》;《永樂南藏》以下簡稱《南》;《徑山藏》以下簡稱《徑》;《清藏》以下簡稱《清》;《七寺古抄本》以下簡稱《七》;《金剛寺古抄本》以下簡稱《金》;《興圣寺古抄本》以下簡稱《興》。
[2]參名古屋稻園山七寺的介紹資料《稻園山七寺の由來と沿革》。
參考文獻
1. 陳寅恪.敦煌劫余錄·序.∥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
2. 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 董志翹.《經律異相》整理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1.
4. 董志翹.日本七寺、金剛寺、興圣寺古寫本佛教類書《經律異相》的異文考察.∥徐時儀,梁曉虹,松江崇.佛經音義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5. 董志翹.經律異相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8.
6.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中華書局,1936.
7. 落合俊典.七寺一切經和古逸經典.∥日本佛教史學會.佛教史學研究(第三十三卷),1990.
8.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 周緯.亞洲古兵器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徐時儀?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劉靜靜?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上海?200083)
(責任編輯?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