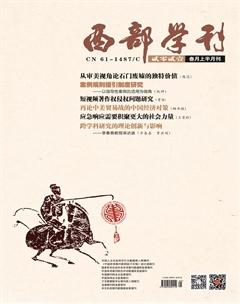于闐地區佛教信仰轉變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探析
摘要:公元三至四世紀,于闐地區佛教信仰發生了從小乘向大乘轉變。在分析佛教傳入中華的路線的基礎上,從有關典籍記載中推斷出于闐地區佛教信仰轉變的時間是公元260—399年間。該地區佛教信仰的轉變,一個因素是與印度有關,佛教來自印度,印度地區流行大乘佛教,于闐也受到了影響;另一個因素是漢文化,包括漢族君主對于闐的統治、漢族僧人與移民帶來的漢文化,對其佛教信仰的轉變都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于闐;佛教信仰;漢文化
中圖分類號:B949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5-0009-03
新疆位于我國西北邊陲,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季羨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總結說:“世界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1]
于闐國在今新疆和田一帶,地處塔里木盆地南沿,東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有著至今都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是絲綢之路南道的重鎮,為東西方貿易商旅的集散地、東西文化交匯之要沖,其商業發達、社會繁榮,文化交流絡繹不絕。
有關于闐的記載,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傳》,稱其在西域之東。《漢書》對其有著較為確切的記載:“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軍、東西域長、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若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往西海;其東,水東流,往鹽澤,‘河源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2]
一、佛教入華的傳播路線
(一)佛教從印度傳入于闐的路線
“隨著佛教在迦濕彌羅、蔥嶺以西廣大地區盛行,客觀上為印度佛教向蔥嶺以東和西域廣大地區的傳入奠定了基礎。蔥嶺以東,是西域的塔里木盆地,該盆地南北側有一系列沙漠綠洲連接起來的通道,于闐即是南道的中心,經于闐到莎車,由莎車翻越蔥嶺,向南即到迦濕彌羅。在民間的交往中,有一條捷徑,即直接從于闐至皮山,由皮山經子合、烏紇而達迦濕彌羅。于闐通過這條交通要道與迦濕彌羅和中亞保持著經常性地往來。”[3]
(二)佛教從于闐傳入中原的路線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的文物來看,中原與西域地區的交流很早就發生了。“新疆與中亞和中國內地的聯系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4]所以,新疆和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是對“先輩的活動”的繼承和發展。到了漢朝,這條道路被當作“國道”踩了出來。約公元前105年,漢朝派出一個商隊到達安息(今伊朗)。
“絲綢之路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分為絲綢之路的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南道(又稱于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于闐)、莎車等至蔥嶺。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干納盆地(大宛)。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5]
絲綢之路的開辟,為佛教僧侶東來或西去提供了很大便利。朱士行、法顯等高僧都曾沿此路到達于闐地區,并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記載。
二、于闐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轉變的時間
關于“一乘”“二乘”“三乘”和“五乘”的說法,《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中提到“或說一乘,如法華經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或說二乘,如攝論等。一者大乘謂即上乘,二者小乘謂即下乘。或說三乘,一菩薩乘,二獨覺乘,三聲聞乘。……及說五乘。”[6]“五乘者,乘以運載為名,五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此五力有大小,載有遠近。”[7]
“乘”梵語yana,有道、船、車,運載之義。小乘佛教被認為包括“聲聞乘”“緣覺乘”以羊車譬喻,大乘被認為是一乘教,以牛車譬喻。又有“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之大乘。何等為六?檀、尸、羼、惟逮、禪、般若波羅蜜。”[8]“大乘者與聲聞乘則有差別,以廣大故。”[9]873“志求大愿”[10],“自度尊身又濟眾生。”[11]“是故大乘微妙甚深,其心廣大。”[9]于闐地區佛教信仰經歷了從小乘向大乘的轉變。
三國時期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到于闐尋得大品《般若經》,“遣弟子不如檀……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之間,于闐小乘學眾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12]由此可見,當時于闐地區民眾信奉小乘佛教。
公元399年,法顯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尋求戒律,游歷30余國,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后歷時14年,于義熙九年歸國。《法顯傳校注》記載:“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禮樂,人民殷勝,盡皆奉法以禮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13]此時于闐國已經流行大乘佛教。
公元260年,朱士行到達于闐時,該國的信仰以小乘佛教為主,甚至對國王有一定的影響。公元399年,法顯到達于闐國時,大乘佛教已流行開來。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看到于闐地區民眾的佛教信仰從小乘轉變成大乘的時間就發生在公元260—399年間。
三、于闐地區佛教信仰由小乘向大乘轉變的原因
根據于闐地區出土的漢佉二體錢,可知該地區既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又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源源不斷地向于闐地區輸送各種教派和思潮,其社會主流思想的改變,勢必會影響其他地區,當印度社會的主流信仰從小乘佛教轉變成大乘佛教,也會影響到于闐地區。從漢代開始,西域被納入中原統治范圍,于闐無疑也受中原影響,甚至在漢代之前,于闐就與中原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與漢地保持相似的于闐官吏名稱和計量單位也可看出中原對于闐地區的影響。
(一)印度的影響
1.佉盧文的影響
由于地緣上的接近性,于闐地區更容易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比如佉盧文就是其中的證明之一。佉盧文起源于印度次大陸古代十六列國之一的犍陀羅地區,后流行于于闐。隨著貴霜王朝瓦解,其一些難民遷入塔里木盆地,佉盧文開始在于闐、鄯善等地傳播,成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語文和佛教語文。到五世紀左右,佉盧文就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使用,成為一種死文字了,五到十世紀于闐文開始流行。
現在的印度北部地區民眾信仰印度教,當時的印度北部流行大乘佛教,佉盧文也是流行于印度北部地區,當時有許多佉盧文的大乘經典。而于闐和鄯善都是后來的大乘佛教中心,因此推斷,于闐地區的佛教信仰由小乘改變為大乘,受到佉盧文傳入的影響。公元308年,僧人法護的梵文漢譯經典《佛說普曜經》中說:“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14]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以佉盧文為載體的經典對于闐地區信仰的影響。
2.大月氏的影響
佉盧文是貴霜王朝的文字,貴霜王朝的建立者是月氏人,月氏人對于闐地區、中原漢地的宗教信仰情況都有一定的影響。在與匈奴勢力的角逐中,小月氏留居河湟地區,大月氏西遷中亞阿姆河流域,《后漢書》載:“月氏自此以后,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15]大月氏在西遷前文化發展相對落后,而大夏人具有較高的文化,“在貴霜王朝時期,尤其是貴霜帝國迦膩色迦統治時代,對各種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包、保護鼓勵的方針,與中國、羅馬、安息等帝國進行頻繁的貿易,并且利用帝國在東西方交通中的樞紐地位,發揮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中轉站的作用,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16]把佛教傳入中原的是大月氏人,第一個將大乘佛教傳入中國的僧人就是月氏人支婁迦讖。這些月氏僧人對中原宗教信仰影響深遠,對西域佛教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朱士行在于闐地區取得大乘佛教經典可以得知,于闐地區早就存在大乘經典,但并未使當地民眾的信仰發生普遍性的轉變,因此印度雖然是于闐地區佛教信仰從小乘向大乘轉變的影響因素,但不是促成這一轉變發生的原因。
(二)中原地區漢文化的影響
由于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統治,使中原和西域有一定程度上相似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西域都護府的設置使得中原文化以官方形式對于闐地區造成影響,雖然早期的管理更類似軍政一體的政權,但還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對其造成了深遠影響。在政治上,于闐國仿照中原王朝建立統治機構,官吏名稱采用侯、將、騎軍、都尉等和中原相同的名號。在經濟上,受中原影響,于闐地區的貨幣采用佉盧文和漢文兩種文字,計量單位也使用中原的“銖”。
1.漢族君主的影響
前涼(公元301—376年)時期,漢族人張軌建立割據西北的政權,在西域推行中原文化,崇尚儒學,《晉書·張軌傳》記載他“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17]。這一時期,于闐也在張軌政權的統治之下,當地人民受到儒家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心理上逐漸與漢族文化靠近。隨著漢族君主在當地建立統治,推行漢文化,內地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共同構成了其佛教信仰由小乘變成大乘的歷史文化根源和心理基礎。
2.漢族僧人的影響
公元399年以前來華的外國僧人有安世高、支讖、安玄、康僧會、支謙、竺法護、竺叔蘭、尸梨蜜、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鳩摩羅什、佛陀耶舍、曇無讖,中原去西域的僧人有朱士行。根據他們翻譯的佛教經典可看出當時大小二乘皆傳,但根據中國情況,佛教信仰的主體在大乘,其原因就是這些西域來的僧人所信仰的是大乘,由此可看出僧人對一個地區民眾信仰可能造成的影響。這種情況同樣適用于于闐地區,中原僧人在于闐地區對于大乘教義的推崇,勢必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朱士行至于闐得大品《般若經》,欲送還洛陽,遭到信仰小乘佛教的學者阻撓,于是“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燒……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故,大眾駭服稱其神感。”[12]43這個記載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朱士行對于闐王、小乘僧眾及當地人信仰的影響和沖擊。又“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眾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遂斂骨起塔焉。”[12]朱士行受到了于闐僧俗的崇敬,人們無不稱奇,收斂其遺骨,專門供奉。大品《般若經》在中原引起轟動與狂熱的同時,朱士行仍在于闐讀經、修行、弘揚佛法,因他信仰大乘佛法,所以在于闐地區應該是宣說大乘。朱士行因自身堅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學功底,深受當地人民敬重,也因此在歷史書寫中為其添加了一抹神秘色彩,以上記載充分說明了朱士行作為有影響力的僧人對于闐國造成的影響。
3.漢族移民的影響
民族構成成分的改變決定了這一轉變。“中原漢族移民新疆(公元1882年清光緒八年置省前稱西域)的歷史源遠流長,但有歷史的記載卻在西漢,兩千多年來從未間斷。”[18]人口成分比例的改變,漢族人口不斷增多,對于闐地區信仰轉變有著一定影響。
四、結語
三至四世紀于闐地區佛教信仰的轉變既受到印度的影響,又受中原的影響。具體來講,于闐信仰從小乘轉變為大乘,受到印度佉盧文和大月氏的影響,受到統治于闐的漢族君王、中原大乘僧人、中原移民的影響。但漢文化的影響因素是促進于闐地區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轉變發生的原因。在漢代,于闐被納入中原統治后,于闐與中原地區間往來密切,民族融合、文化互鑒是其信仰發生轉變的深刻歷史文化根源,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漢文化的認同,是其信仰發生變化的心理基礎。同時,個別有影響力人物的推介是于闐地區佛教信仰從小乘轉向大乘的重要促進因素。
參考文獻:
[1]季羨林.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148.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4:3881.
[3]魏長洪,等.西域佛教史[M].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8:18.
[4]邵會秋.《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新疆哈密地區古代人群的變遷與交流模式研究》評介[J].人類學學報,2018(3).
[5]趙澤瑋.論絲綢之路的異同[D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e2d4e227d3240c8547ef1a.html.
[6]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DB/OL].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09_001.
[7]宗密.盂蘭盆經疏[M]//中華大藏經:第9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301.
[8]無羅叉.放光般若經[M]//中華大藏經: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44.
[9]道泰,等譯.入大乘論[M]//中華大藏經:第30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10]法炬.法海經[M]//中華大藏經:第3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615.
[11]支謙.梵摩渝經[M]//中華大藏經:第3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43.
[12]僧祐.出三藏記集[M]//中華大藏經:第5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13]法顯.法顯傳校注[M].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
[14]竺法護,譯.佛說普曜經[M]//中華大藏經: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394.
[15]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921.
[16]馮英.大月氏對漢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J].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1(2).
[17]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22.
[18]傅仁麟.淺談中原漢族移民新疆史及“絲綢之路”的開拓[J].地域研究與開發,1989(1).
作者簡介:王晨悅(1995—),女,漢族,河北保定人,單位為陜西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佛教。
(責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