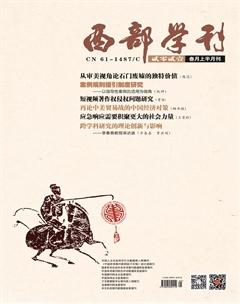淺析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擱置爭議”理念
摘要:針對一些較為棘手的邊界問題,我國政府采取了靈活務實的態度,通過“擱置爭議”的方式優先建立與相關國家的友好關系。數十年來,處理邊界問題的“擱置爭議”理念不斷豐富完善,形成了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主旨的思想理論體系,在緩和邊界爭端、減少與周邊國家分歧以及營造積極有利的外部環境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擱置爭議”理念當今也面臨著不同類型的挑戰,其主要內容亟需得到進一步的補充與完善,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擱置爭議;邊界問題;共同開發
中圖分類號:D823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5-0033-03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邊鄰國普遍對我國抱有警惕和猜疑的態度,這種態度背后往往是新獨立國家對被欺壓、被侵略歷史的敏感性[1]。此外,某些西方國家精通“分而治之”的策略,不斷炒作我國與周邊鄰國的領土邊界矛盾,妄圖在國際上孤立新中國。對此,我國領導人審時度勢,主張在邊界問題的解決條件尚未成熟之前爭取在其他領域打開局面,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將爭議暫且擱置起來。
一、“擱置爭議”理念的歷史演進
清朝末年以來,迫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與壓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讓了大量的領土。此外,印度等國家在獨立之后并沒有擺脫殖民思維的束縛,不斷蠶食中國的邊界領土,意圖攫取更多的戰略利益。新中國同周邊各國的邊界線或是由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規定,或是傳統習慣線和實際控制線,甚至沒有一條通過平等談判確定下來的邊界線。我國需要將解決邊界問題作為實現民族獨立、營造和平發展環境的重要前提,但周邊某些國家也準備“寸土不讓”,將邊界問題作為試探與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擱置爭議”理念的形成
在與周邊國家的外交工作開展之初,新中國政府并沒有選擇以“四鄰驚擾”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而是選擇以“爭取緩和”“爭取亞非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出發點,避免了“四面皆敵”的不利局面。在此時,“擱置爭議”理念主要表現在優先爭取保持邊界地區的穩定,保持與周邊國家的平等協商、睦鄰友善,盡可能地緩和、化解邊界問題,防止因為邊界爭端造成大規模的沖突或區域環境的惡化[2]。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綜合考慮各種復雜因素,提出以爭取世界局勢緩和、保障我國和平建設為首要目標,在此基礎上爭取亞非國家的友好關系,避免在邊界問題上采取過于強硬的姿態[3]。
在此理念的指導之下,中緬邊界問題得到妥善處理,兩國政府于1961年互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批準書,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解決的第一例邊界問題,為之后中國與鄰國劃定邊界工作的開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4]。中緬邊界問題得以妥善處理之后,中國經歷了第一波“劃界潮”。在之后的劃界協商中,中國政府堅持以明確邊界,保持與周圍鄰國的友好關系為大前提,對確實復雜且難以處理的邊界問題采取了暫時擱置的態度,爭取通過平等協商為國內建設營造穩定安全的外部環境。
(二)“擱置爭議”理念的進一步演繹
“擱置爭議”的理念并非一成不變,在其早期的實踐中,更加關注的是妥善化解矛盾,為新中國爭取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避免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武裝沖突,是一個“沒得選的選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以中日建交談判為代表的海上邊界爭端處理過程中,中國政府提出了“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原則,在擱置爭端的基礎上嘗試采取更加積極的應對策略。此時的“擱置爭議”理念體現出中國政府更多的自信和能動性,實現了從“迫不得已”化解邊界問題到主動擱置邊界爭端的轉變。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望,兩國有實現關系正常化的迫切需要,但也受困于歷史包袱,其中還涉及領土與邊界爭端。中美關系“破冰”后,國際形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都希望能夠改善雙邊關系,加快建交的步伐。中日兩國在建交談判過程中曾就釣魚島問題進行協商,關于釣魚島“擱置爭議”,是中日兩國領導人本著著眼大局、面向未來的精神,在邦交正常化談判和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達成的諒解與共識[5]。
在處理南海問題、實施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政府認識到“和平與發展”必將取代“戰爭與革命”作為新的時代主題,及時調整外交工作的主軸。在提出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國家統一問題的基礎上,中國政府相當密集地就中印邊界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以及有關國際爭端等問題發表談話,組織政治協商與外交談判,通過實踐不斷完善“擱置爭議”理念,將其確立為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邊界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
(三)“擱置爭議”理念的邏輯內涵
在建國以來處理領土邊界問題的實踐中,“擱置爭議”理念得到了發展完善,現今已經具有了完善的邏輯體系和思想內涵。
首先,“主權在我”是“擱置爭議”理念中最重要的原則。決定擱置某些領土邊界爭端問題并不等于放棄了國家主權,而是在行使國家主權遇到現實困難或者有可能造成“得不償失”的局面時,暫時放下爭執,爭取在別的領域達成共識與合作。同樣,“擱置爭議”也并不等于“共享主權”或像處理南極問題時所采用的“凍結主權”模式,“主權在我”是處理邊界問題時不可動搖的立場。
其次,對“擱置爭議”中的“擱置”應當進行正確的理解。擱置也是有選擇的,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擱置,領土邊界事項能否擱置需要結合時代背景,經過辯證的分析后才能做出選擇。譬如中日兩國對釣魚島問題的擱置,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兩國建交過程中所面對的阻力,為兩國邦交正常化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2012年所謂的“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中,面對日本政府對釣魚島爭端采取“不擱置”、甚至主動挑起爭端的態度,中國政府堅決還擊,向有關國家表明態度。同時,擱置是處理對外關系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在擱置的基礎上也應當積極進取,有所作為。擱置爭端本身也是爭端各國通過合意達成的,因此它不是一種被動、消極的“未解決”狀態,而是國家間為了穩定、合作和發展的積極嘗試[6]。在當代社會中,國家主權、國家安全被視為一個國家不能讓步、不能忽視的核心問題。但在這些問題項下的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科學合作、政治交流等領域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爭端而導致各個領域的合作被延誤是各國都不愿看到的結果。
最后,“擱置爭議”的目的是達成現階段的“共同開發”,達成“雙贏”的局面。所謂“共同開發”既可以理解成在南海、東海就油氣資源與相關國家進行共同開發,也可以從廣義上理解為在采取“擱置爭議”的前提下,采用“迂回戰術”,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與爭議國家先一步進行合作,在“不正常”的外交關系中謀求其他領域先達成“正常”合作[7]。
二、“擱置爭議”理念面臨的現實挑戰與應對
“擱置爭議”理念為新中國在建國之初以及改革開放時期提供了重要發展機遇,使新中國從被孤立、被排斥的困境中脫身而出,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穩定的發展環境。但當前,“擱置爭議”理念也面臨嚴峻的現實挑戰,受到了諸多的質疑[8]。
(一)“擱置爭議”理念面臨的現實挑戰
盡管“擱置爭議”理念的初衷在于優先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為我國的自身建設與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但隨著區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發展,有些邊界問題會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持續存在,隨時可能會產生新的威脅。
就陸上邊界問題而言,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我國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在近年來有愈演愈烈之勢,印方不斷挑戰我國“擱置爭議”的理念。歷經漫長的外交談判與政治磋商,中印兩國政府就管控邊界分歧、增進政治互信與軍事互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識,同時也通過簽署雙邊協定的方式賦予各項階段性成果以法律效力。近年來,印方主動在中印邊境爭議地區屢次挑起沖突,對峙事件的發生頻率與激烈程度逐漸升高,兩國自1993年開始構建的涉邊協定體系面臨沖擊。對此,印方應當負主要責任,印度政府通過軍事、行政和外交等手段在邊界問題上向中方施壓,妄圖單方面改變現狀,威脅實際控制線沿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加劇了區域內的緊張局勢。2020年,印度政府在中印邊境地區又一次挑起爭端,在國內挑動民族情緒,導致雙邊關系惡化。
就海上邊界問題而言,我國與周邊諸國的領土爭端成為國際反華勢力圍追堵截中國政府的抓手。釣魚島問題的暫且擱置是中日雙邊關系正常化的基礎之一,是“擱置爭議”理念在處理邊界問題實踐中起到良好作用的典范。但新世紀以來,中日兩國圍繞釣魚島問題進行過數次交鋒,美國政府也通過對《美日安保條約》的解釋從中作梗,利用邊界問題挑撥中日友好關系。在美國的影響下,部分日本政治人士拒絕承認邊界爭議的存在,不斷強化對釣魚島的管控力度,派出海上保安廳船只在釣魚島周邊海域巡邏,阻擾我國漁民的漁業經營,意圖在國際社會中混淆視聽,創造“事實占有”的假象。在南海地區,“擱置爭議”理念主要體現于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發表或簽署的聯合宣言、聯合聲明、聯合公報和聯合新聞公報等文件中。這些文件總體上缺乏明確的權利義務內容,法律約束力較低,也沒有具體的監督落實、責任追究和制裁懲罰機制。近年來由于域外大國的介入,有關南海的爭議不斷,某些南海周邊國家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肆意妄為,“你擱置,我開發”或者“擱置爭議,我先開發”的亂象在區域內層出不窮[9],“擱置爭議”的理念在當前并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
(二)完善“擱置爭議”理念的若干建議
“擱置爭議”的理念雖然面臨嚴峻挑戰,但就總體而言,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沒有發生改變,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任務沒有改變,和平解決爭端的立場也并沒有改變。我國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邊界爭端時仍然要靈活使用“擱置爭議”的方式,一方面仍然要堅持“擱置爭議”的理念,并積極開展實踐;但另一方面也要構建完善解決爭議的有效機制。
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發展的大環境下,完全拋棄“擱置爭議”理念是不可取的。一方面,在涉及國家主權的南海、釣魚島問題上采用針鋒相對的態度,希望實現“單贏”的想法是難以實現的,甚至會進一步惡化我國的周邊環境。就某些歷史遺留問題而言,急于推動爭端的解決反而會導致雙方關系緊張,進而錯過合作開發、發展的時機,需要以更加務實的態度避免這些損失。另一方面,采用強硬的手段解決爭端也有損中國幾十年來在國際舞臺上所樹立開放、包容、合作的大國形象,會為國際反華勢力鼓吹“中國威脅論”提供借口。
中國“擱置爭議”的實踐與其理念是高度統一的,其對“擱置爭議”理念的運用是對戰略利益的追求。從根本上講,“擱置爭議”的理念和實踐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為根本出發點,它在維護中國周邊的和平環境的過程中,也對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起到了示范和引導作用,有益于中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和平發展。反思“擱置爭議”的理念,中國在未來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與邊界關系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擱置爭議也要重視軍事實力的發展,在任何歷史階段里,軍事力量都是保障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堅強后盾,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無論是擱置、和平還是合作的意愿才能被相關國家所重視,否則再友善、真誠的政策都會被視為軟弱和妥協。其二,在與相關國家簽訂協議時,要更加重視規定明確的權利義務規范,在原則性共識的基礎上將理念制度化,形成可以落實、實施和監督的法律文件。其三,要把握“擱置爭議”理念的根本在于辯證地看待周邊外交問題,在相關國家出現“不擱置”甚至故意制造爭端的行為時,應當認識到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轉化,積極行動,捍衛主權。
中國需要以更加自信和開放的姿態來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在處理邊界問題時也需要繼續推進“擱置爭議”理念,保障和平友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周邊國家與中國通過共同發展,形成高度的相互依賴關系,中國的發展成果可以不斷惠及周邊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共同利益可以弱化雙邊矛盾,為解決邊界問題創造有利條件,這也使“擱置爭議”的理念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云.解決東亞領土爭端需有大智慧[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04-12.
[2]關培鳳,胡德坤.新中國邊界政策:從陸地到海洋[J].現代國際關系,2009(10).
[3]曹瑋.擱置外交——解決領土爭端問題的外交理念新探索[J].太平洋學報,2011(1).
[4]齊鵬飛,馮越.中緬邊界問題研究述略[J].當代中國研究,2008(2).
[5]喬林生.論釣魚島“擱置爭議”的共識[J].國際論壇,2013(6).
[6]黃瑤.論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和平擱置爭端[J].中國社會科學,2019(2).
[7]石源華.“擱置外交”: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J].世界知識,2014(4).
[8]楊澤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的困境與出路[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9]張曉君.實施“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戰略的法律機制探究[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作者簡介:劉泮(1995—),男,漢族,河南商丘人,單位為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方向為中印邊界問題。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