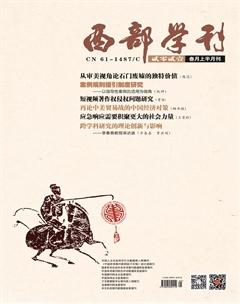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視域探析國內選秀類綜藝節目
摘要: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分析當下國內選秀類綜藝的演播心理分析提供了重要參照。其中“歸屬”“愛與尊重”等需求角度,正體現在投射崇拜類、移情養成類和比較審丑類綜藝節目之中。投射崇拜類節目,可以幫助觀眾緩解自體內部的焦慮和沖突;移情養成類,分為正向移情與負向移情,觀眾可以陪伴偶像共同成長、能參與偶像的制造,從而獲得成就感;比較審丑類,雖然受眾范圍較窄,但憑借著“消費丑態”來滿足觀眾獲得尊重的需求。但是此類節目的單一面向難以建立客觀的社會比較準則,并拉大了觀眾對奇觀與現實的期待落差,從而形成錯誤期待,難以清晰地進行自我價值的確定。
關鍵詞:選秀類綜藝;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偶像崇拜
中圖分類號:G222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5-0115-03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ical theory of needs)將人的需要分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五個等級。從歸屬、愛與尊重等需求角度出發,通過對個體與他人間的情感關聯與認同渴求進行辨析,能夠發現:選秀類綜藝正是牢牢把握觀眾的以上兩點心理需求,并由此進行針對性的創作調適。
根據選秀類綜藝節目中選手的發展模式和觀眾獲得心理滿足的不同方式,選秀類綜藝節目可以區分為投射崇拜類、移情養成類、比較審丑類這三種類型。本文結合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選秀類節目的受眾出發,通過觀察其在投射認同、移情和社會比較中獲得滿足感的三種方式,分析三種不同類型選秀類綜藝對觀眾的歸屬與愛的需求與尊重的需求的滿足,從而試圖歸納出三種典型類別的選秀類綜藝節目的觀眾心理設計原理。
一、投射崇拜類綜藝節目
《超級女聲》 《我是歌手》《聲入人心》《這!就是街舞》等投射崇拜類選秀綜藝是選秀類節目最早出現的類型,并且仍是當下選秀類綜藝節目的主流類型。從二十一世紀初發展至今雖然出現了一些變化,但在這類節目中,選手實行的“先培養后曝光”的發展模式,依托他們成熟的形象和實力發展,讓人們產生仰慕的心理,形成投射性認同,即“個體通過認同這一防御機制對榜樣的行為方式進行模仿”,渴望“在幻想中占有其特質,提高自身價值感”,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歸屬與愛的需求與尊重的需求的特性仍舊沒有改變。
從歸屬與愛的需求來看,崇拜類選秀綜藝節目可以幫助觀眾緩解群體內部的焦慮和沖突,這一特點在2018年前的節目中主要表現為對于主流審美的反叛。隨著觀眾自我意識的提高,一味提倡個性與反叛難以滿足觀眾對歸屬感的需求從而贏得大量支持與追捧,在2018年后的節目中更多表現為對于小眾文化的追求。
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偶像標簽敬仰、膜拜和神化的色彩開始褪去,標準、統一的審美模式被個性、潮流的風尚所替代。”在這樣的背景下,觀眾對于崇拜類選秀綜藝節目中選手欣賞和崇拜的過程,實際上是將自我的反叛意識投射到選手身上,尋求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過程,從而滿足歸屬與愛的需求。例如《超級女聲》中觀眾對于李宇春中性風格的崇拜,或是《快樂女聲》中觀眾對于曾軼可綿羊音的追捧,都是對標準、統一的審美模式的反叛,以及對個性的追求。這些選手是觀眾內心反叛意識的投射,觀眾觀看選手在節目中做出自己喜愛但與主流審美相違背的行為獲得批判或是贊美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將自己的個性投射到舞臺上與大眾面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觀眾對這些選手產生投射,并將他們當作偶像進行崇拜,以節目和選手為中介獲得外界對自己個性發展的認同與支持,獲得歸屬感與認同感。
而到2018年后,在《聲入人心》《這!就是街舞》等綜藝節目中,同樣是通過“引發觀眾心理認同和情感共鳴”,讓觀眾感受到對節目和美聲、街舞等小眾藝術的歸屬感,滿足歸屬與愛的需求。在這類節目中,題材的選擇通常是觀眾有所耳聞但并沒有詳細了解的領域,讓觀眾產生了陌生感和好奇心。同時,節目組選擇在該領域有較強實力或較大影響力的人物充當選手與嘉賓,在觀眾心理上提高了這一節目的觀看門檻。雖然這一門檻在吸引觀眾觀看節目時并不會實際存在,因為節目通常只會涉及該領域比較容易讓觀眾理解和接受的部分,嘉賓也會盡量將一些專有詞匯用通俗的語言進行解釋,但是觀眾心理上會認為該節目專業屬性較強,能喜歡這類節目說明自己已經擁有了一定的專業欣賞素養。
以《聲入人心》為例,美聲和歌劇在我國目前都屬于小眾且具有欣賞門檻的藝術,多數觀眾在觀看這一節目前并不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但音樂特別是流行音樂在大眾中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有關綜藝節目將美聲、歌劇與流行音樂元素相結合后,打破了大多數觀眾與這一小眾藝術的壁壘。同時,節目組選擇廖昌永、梁寧、許蕾、張璋等在行業內具有較高聲望的專家和音樂人參與歌曲的選擇、演唱的語言控制和表達,并將美聲、歌劇等相關知識科普穿插其中,讓觀眾在心理上認為該節目專業屬性較強,但自己在觀看節目的同時已經完成了對于這一小眾藝術的初步認知,將自己與完全不了解此類小眾文化的其他人區分開,從而滿足其歸屬感需求。
二、移情養成類綜藝節目
隨著《創造101》《偶像練習生》《明日之子》《青春有你》等節目的火爆,養成類選秀綜藝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例如《創造101》在騰訊視頻平臺獲得超5億次的播放量,在微博獲得165億次的話題閱讀量和1.1億次的話題討論量。該類節目的特質是觀眾可以陪伴偶像共同成長、能參與到偶像的制造當中,選手依賴觀眾和粉絲的支持獲得更多的曝光度和更多的資源,觀眾通過支持陪伴選手成長獲得成就感,滿足歸屬與愛的需求與尊重的需求。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將移情分為正向移情與負向移情,而這兩種移情都是養成類選秀綜藝不可或缺的觀眾心理。
從正向移情來看,觀眾從選手的成功中可以汲取對自己的激勵。養成類選秀綜藝節目中的選手可能存在與觀眾相同的缺陷或是處于同樣的困境,卻能在觀眾的支持下獲得靠前的名次、成團機會、C位①資格等象征成功的榮譽。這種節目形式既是對觀眾打榜、投票等行為價值的認可與尊重,肯定了觀眾行為對于節目和選手的價值,也給予了觀眾自己也能像選手一樣獲得成功的暗示,使其更有信心與歸屬感,給了觀眾“‘替代性的假想對象與認同空間”。
從負向移情來看,觀眾也會因為選手或節目“不符合自己的力比多投注”而產生負向移情。例如,當觀眾認為自己喜歡的選手實力很強、發揮也不錯卻沒有取得較好的名次甚至被淘汰時,觀眾將力比多投注到外界的釋放途徑被阻斷,力比多被迫淤積產生緊張的感覺甚至產生心理痛苦,從而對節目中的選手或是節目本身呈現出不滿、抗拒甚至是敵對的移情,出現自發抵制或是脫粉回踩等行為。在這些行為中,觀眾通過努力將自身與節目所傳導的價值區別開,體驗到“‘我們與‘他們的差異而獲得‘社會認同”,以滿足歸屬與愛的需求。但當這些行為與獲得正向移情觀眾的行為形成沖突時,節目更能獲得較大的熱度。
以《創造101》這一養成類選秀綜藝為例,節目中楊超越這一選手的形象則同時滿足了觀眾的正向移情與負向移情。楊超越農村家庭出身,家境貧寒,初中學歷沒有良好的文化修養,甚至因為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唱歌跳舞訓練而在節目中個人實力較差。但這些缺點卻給了大量觀眾進行正向移情的基礎,他們將對自己經濟實力、個人能力并不出眾的遺憾移情到了選手身上,選手在節目中細微的實力提升或為人處世的進步都會被帶有這種心理的觀眾當作是自己的進步,并給予大量鼓勵與打投支持。根據楊超越個站②的數據,僅決賽一輪粉絲的集資就超過了300萬元,為節目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收益,也向品牌方證明了楊超越粉絲的經濟實力和購買能力,一定程度上給了楊超越獲得更多資源的機會。最終楊超越順利出道,也給了這些觀眾正向的回饋,既說明他們的集資、打投和控評等行為有效果,又向他們傳遞了即使家境和學歷都沒有優勢也能憑借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的堅定信念。
與此相反,唱跳實力都差卻能次次排名靠前獲得追捧,又使部分觀眾因自己曾遭受過不公的待遇或是身邊存在類似楊超越這樣業務不熟練而給他人帶來麻煩的人卻進行了負向移情,自發組織了“黑粉團”等組織與楊超越粉絲進行抗衡。這部分觀眾在節目組的官博或者是視頻的彈幕與評論區中不斷發表自己的看法,宣泄自己的不滿,與產生正向移情的觀眾特別是粉絲行為形成較為激烈的沖突。《創造101》節目播出期間,僅楊超越一人就因為雙方的爭論而上過89次熱搜,給節目帶來了可觀的流量與話題討論度。
觀眾在觀看養成類選秀綜藝時的移情,能獲得較好地滿足其歸屬與愛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這也是該類選秀綜藝流量和關注度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這種移情在節目全部播出完后很難一直持續,觀眾在節目播出后面對奇觀世界與現實生活的巨大落差,往往選擇投入新的養成類選秀節目,選擇新的主體進行移情,這也使得該類節目受到了一定的批判。因此,現在部分養成類選秀節目也會重視在主題上對于觀眾現實生活中的引導,讓這種移情可以更多地反饋到觀眾自身的日常生活中。
三、比較審丑類綜藝節目
除上述兩種接受程度較廣的選秀綜藝類型外,另一種綜藝雖然受眾范圍較窄,但憑借著“消費丑態”來滿足觀眾尊重的需求,在市場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隨著社會壓力的增大,個體在沉重的壓力下難以進行較為客觀的自我評價,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價值,自尊及希望受到別人尊重的需求越來越難以滿足。根據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社會比較理論,“社會比較可以為個體提高自信心,并且成為合理自我完善的基礎。”與哈克·米勒(Hak Miller)在1962年提出“當個體的自尊受到威脅時,會傾向于和比自己差的人進行社會比較”的下行社會比較模式,類似審丑類選秀綜藝節目恰好給予觀眾一個利用他人作為比較的尺度,進行向下的社會比較的機會。
在《天使之路》《非你莫屬》《中國夢之聲》等節目中,選手們的“撕×辱罵”、下跪賣慘或是輸出與大眾普遍認可的倫理道德相違背的觀點等行為都是觀眾關注和議論的焦點。此類節目觀眾在觀看時注意力并不在誰的實力更強或是誰的舞臺表演更好上,而是在誰能創造出更能引發爭議的話題上,因此節目組并不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去邀請選手和嘉賓,只需要找到愿意按照劇本或可以即興扮丑的人選,配合互聯網特別是自媒體的炒作,就能賺取大量關注。以《中國夢之聲》為例,選手長相丑陋、唱歌跑調或者是身世凄慘等具有話題性或是爭議性的內容一直都是試音會最大的賣點。例如專業歌手楊成瑞唱歌跑調、喜劇女演員被導師稱長相重口等話題在節目被刻意剪輯,突出帶來的關注度遠遠超過了節目本來的熱度。在與這些選手進行下行社會比較的過程中,觀眾不需要對選手產生崇拜或是移情,在無意識的比較中更容易得出“自己唱歌還不錯,長相還不錯,家境還不錯”的結論,緩解現有壓力,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和滿足感。
觀眾在觀看審丑類選秀節目的過程中,在獲得娛樂和搞笑的同時,還完成了一次向下的社會比較。個體原本普通的背景或是平凡的能力,在與節目組刻意選擇的選手進行比較中顯得格外突出,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提高觀眾自信心的需求。但當觀眾將過多的關注力放到這類節目上時,則難以建立實際的社會比較準則,反而不能很好地滿足觀眾的尊重的需求。
四、結語
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進行分析,選秀類綜藝節目在制作和發行的過程中都考慮了觀眾的歸屬與愛的需求與尊重的需求,所以獲得了較好的發展。觀看以上三種選秀類綜藝節目,觀眾可以分別在投射認同、移情和社會比較中獲得娛樂和滿足感,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心理壓力。但一旦觀眾將過多注意力放在選秀類綜藝節目時,審丑類選秀節目的單一向下,社會比較難以建立客觀的比較準則,觀眾易形成錯誤判斷;崇拜類選秀綜藝的投射認同和養成類選秀綜藝的移情容易拉大奇觀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落差,在回歸現實后更難進行自我肯定。因此,在面對選秀類綜藝節目時,仍要堅持適度原則,明確奇觀世界與現實生活的差異性和邊界位置,這樣才能更好地享受到該類節目帶來的心理滿足。
注 釋:
①C位指獲得團隊中心位置,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曝光度。
②個站指粉絲為明星個人在社交平臺上建立的賬號,用于應援和提高曝光度。
參考文獻:
[1]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第三版.許金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車文博.弗洛伊德文集01:癔癥研究[M].長春:長春出版社, 2010.
[3]利昂·費斯廷格.認知失調理論[M].鄭全全,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4]賴黎捷,等.媒體奇觀視域奇觀下的中國電視娛樂文化轉型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
[5]徐展.電視娛樂奇觀的多維透視:內容生產、文本與受眾[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8.
[6]陳勁驍,陳巍.投射性認同的三次轉向:內涵演變與概念比較[J].心理科學進展,2015(4).
作者簡介:張景怡(2000—),女,漢族,湖南長沙人,單位為西南大學,研究方向為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