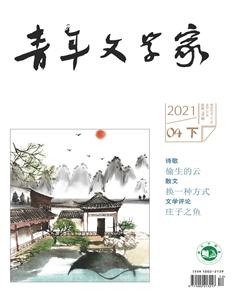從龔鼎孳唱和詞中窺見其復(fù)雜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
李陽
在明清易代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詞壇唱和活動卻空前繁盛,成為“清詞中興”的一種表現(xiàn),同時也推動了清初詞的發(fā)展。龔鼎孳作為出仕新朝為官的“輦下大臣”,通過自己的努力促進了“稼軒風(fēng)”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傳播,還促成了多人唱和活動——“秋水軒唱和”活動的展開。作為清初之際詞風(fēng)轉(zhuǎn)變的有力推動者,龔鼎孳也創(chuàng)作了許多獨具特色的唱和詞。
龔鼎孳詞集《定山堂詩余》共四卷,其中唱和詞大約占一半,可見其數(shù)量之多。本文將對龔氏唱和詞的唱和對象進行梳理歸納,并進一步探析龔氏在唱和詞中所呈現(xiàn)出的復(fù)雜創(chuàng)作心態(tài)。
一、龔鼎孳唱和詞分類
龔鼎孳雖因“貳臣”身份飽受詬病,但因其縱觀今古、博物洽聞的才學(xué),以及體恤窮交、弘獎英俊,所以在清初詞人中地位卓然。龔鼎孳詞作中有數(shù)量相當(dāng)多的唱和詞,唱和對象眾多,大致可分為前人、貳臣、遺民和后進四大類。
(一)追和前人的唱和詞
龔詞中追和前人的唱和詞不在少數(shù)。龔氏詞集《定山堂詩余》共四卷,總體上可分為兩個時期。追和前人的作品主要分布在前兩卷中。從卷二開始,追和詞與酬和詞平分秋色,然前者仍有 22 首之多。不難看出,龔鼎孳前期的唱和詞主要以追和前人為主。其追和對象除少數(shù)其他朝代詞人外,主要追和宋代詞人。
崇禎十七年三月,入仕資歷尚淺的龔鼎孳果敢諫言,彈劾奸宦權(quán)貴招來了牢獄之災(zāi),此后便顯露了無奈與漂泊之感。如第二卷開篇之作《燭影搖紅·吳門元夜值雨和張材甫上元韻》(花信爭傳,玉鉤草色寒猶淺),為追和宋代南渡詞人張掄《燭影搖紅》(雙闕中天,鳳樓十二春寒淺)。龔詞同樣也通過寫節(jié)日來抒發(fā)家國之感,但它不像張掄詞上片追憶往昔,下片感傷今時那般濁涇清渭,而是把過去現(xiàn)在的事?lián)诫s在一起來寫。龔詞相比張詞的直吐胸懷來說,更多是在借景抒情,在景中糅合自己的幽情離恨。
除了張掄,龔鼎孳還選擇了呂本中等宋代詞人追和。這些詞人風(fēng)格各異,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更看重原作的主題與韻部對于個人情感抒發(fā)和情境構(gòu)造有無幫助。雖然大部分唱和與原作主題一致,但都深具龔鼎孳本人的個性特質(zhì)和審美風(fēng)格。
(二)以遺民為對象的唱和詞
龔鼎孳是有一腔抱負(fù)的,明覆滅之后,在“出”與“處”之間選擇了后者,因此成為多被詬病的“貳臣”。但因為當(dāng)時特殊的歷史背景,許多貳臣與遺民之間并非涇渭分明,也有很深的交往。
其中明確唱和遺民的只有《燭影搖紅·方密之索賦催妝,即用其韻》(一揖芙蓉)。此詞后注明“時予南鴻初至”,可知是龔鼎孳心上人顧橫波初聚之時所做的催妝詞。詞中字字可感受到詞人有無數(shù)喜悅與纏綿綺語縈繞心頭。方密之,即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生平正值明清易代之際,政權(quán)更迭,使得他的經(jīng)歷也十分坎坷。明朝未滅亡時,尚且還能過著閑適的富貴生活。中期自明朝滅亡后,開始流亡。晚年北歸,到六十一歲時,秘密組織反清復(fù)明活動被捕,押解途中病歿。龔鼎孳與復(fù)社成員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與方以智交好。
龔鼎孳與曾燦、杜浚、紀(jì)映鐘、方以智、柳敬亭、冒襄等遺民都有來往,雖然明確唱和他們的詞較少,但在詞集中提及一些事時,往往也有遺民參與其中。
(三)以貳臣為對象的唱和詞
龔鼎孳身為明臣,降闖又降清,是典型的貳臣身份。同時,龔鼎孳的交際圈之中也有許多與之相同身份的貳臣,如李雯、曹溶、熊文舉等,他們之間也有很多的唱和往來。
縱觀龔鼎孳與貳臣之作,其中唱和曹溶詞的數(shù)量最為豐富,貫穿龔鼎孳詞創(chuàng)作整個時期,從卷一中較為濃艷的愛情詞到卷三中悲慨蒼涼的感懷詠史詞,可見二人交情深厚,秉性相投,因此身為貳臣的苦悶當(dāng)然是二人共鳴的前提與基礎(chǔ)。所以龔曹唱和之詞甚多。例如二人和韻:曹溶原作 《薄倖·題壁》、龔之和作 《薄幸·秋岳將以病去湖上,留飲寓齋命制此詞,即用其題壁舊韻》。龔詞采取原韻框架與原詞悲傷的基調(diào),融入二人離別之情,不失為唱和佳作。
縱觀龔鼎孳與貳臣的唱和詞,既表現(xiàn)了仕新朝的懺悔,又表現(xiàn)了對于故國的追思,正是身份相同,貳臣詞人之間更容易抒發(fā)心中隱秘的深愁。
(四)以后進為對象的唱和詞
吳偉業(yè)評述龔鼎孳:“后生英雋,弘獎風(fēng)流,考槃之寤歌,彤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也……此先生之性情也。”龔鼎孳體恤窮交又好提攜后進,落魄的陳維崧入京之后,不僅在生活上予以陳維崧很多幫助,還發(fā)起了三次大型的多人唱和活動,將陳維崧詞名揚于京城。
以二人《賀新郎》唱和為例,陳維崧作《賀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二首》其一,龔鼎孳填詞和作《賀新郎·和其年秋夜旅懷韻》,龔之和作下片呼應(yīng)陳的以古喻今,隨著時間流逝世事變遷,人杰都湮沒在歲月長河中,而在這些英雄人物之中,有著陳維崧這樣的江東人杰,是對于陳維崧的品行高潔的贊譽,結(jié)尾轉(zhuǎn)而希望陳維崧改變心態(tài),多行樂事。
除此之外,施閏章、宋琬、王士禎、朱彝尊等大家得以名揚海內(nèi),也與龔鼎孳的助力有很大關(guān)系。
二、唱和詞中的復(fù)雜心態(tài)
清初貳臣士人群體體現(xiàn)出來的普遍創(chuàng)作心態(tài)是“亡國失節(jié)”兩大主題,而龔鼎孳在這兩大主題之外還有著若隱若現(xiàn)的歸隱之意,但總體上只是心中有意,行動無意。
(一)舊朝覆亡的家國之悲
明清易代之時,朝代更迭,政局動蕩,生活在這一時代的文人們經(jīng)歷了國破家亡,因此這一時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題便離不開家國之悲。但龔鼎孳作為貳臣群體中的一員,故國之悲的抒發(fā)又與遺民群體和烈士群體有所不同。例如其前期追和前人的一些詞,就體現(xiàn)出了一定的歷史興亡之感。總體上看,《定山堂詩余》中的表達故國之思的唱和詞作于明覆亡之后至龔鼎孳漫游吳越時期,例如作于李自成攻陷,龔想要投井身亡被人救起所作的《綺羅香·同起自井中賦記,用史邦卿春雨韻》中,詞人將自己比作屈原,將愛妻顧媚比作洛神,國破家亡,只能與心上人做一對“并命鴛鴦”亂后相依,再看宮外戰(zhàn)火紛飛,感慨萬千。史達祖原作是詠春雨的詠物詞,龔詞運用原韻框架,卻寄托了昔盛今衰、興亡家國之感。
與前人相比,龔鼎孳對于故國追思的心態(tài)有一些不同,前人在易代之際多表達對于故園之思和故主的忠貞,而龔詞中多是對于故園的追思和蒼生社稷的關(guān)懷,鮮少表現(xiàn)對于故主的忠貞,這種心態(tài)也與他出仕新朝,未能做到忠貞不二的個人選擇相關(guān)。
后期秋水軒活動中龔鼎孳多為遺民作詞,與遺民相比,龔氏在表現(xiàn)自己的故國之思時是故意節(jié)制的,將自己對于家國之悲的情懷借物借人隱晦地表達出來。
(二)重仕新朝的悔愧之意
明朝滅亡后,有節(jié)氣節(jié)的明遺民如黃宗羲、王夫之等都選擇隱逸。而此時,龔鼎孳卻選擇出仕新朝。在這種生活環(huán)境之下,龔鼎孳的一腔憤懣之情只能借唱和詞抒發(fā)。
例如與之唱和最多的貳臣曹溶,二人的關(guān)系,鄧之誠說:“雜憶舊友,首數(shù)之遴,次及鼎孳。”二人曾同為御史,并且在明朝時都是有名的敢言敢諫之臣,且后來都降清,同為貳臣,二人在道德上遭人詬病,所以他們都希望做出一些事情能夠彌補自己內(nèi)心的悔意,于是他們都保護了一批自明入清的遺民并且希望通過提攜后進重振詞壇,曹溶提攜了朱彝尊,龔鼎孳則是獎掖陳維崧,想通過做這些事來彌補自己仕清的悔意。二人不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創(chuàng)作上都能產(chǎn)生強烈的共鳴,所以唱和詞也是表達二人相同心情的情感樞紐。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種后悔出仕的情感與其他貳臣詞人也表現(xiàn)出來一些不同,曹溶、李雯這樣的貳臣雖也是被迫降清,但他們詞作中表達出來的更多的是一種蒼涼悲慨,極為后悔自己仕清,李雯更是因自己的悔恨和心理壓力而死,可見這種悔意是相當(dāng)濃厚的。雖然龔內(nèi)心也有愧悔之意,但是并沒有流露出不想再出仕的想法,他的許多作品中都透露出一種帶有實干抱負(fù)的思想。
(三)進退迍邅的歸隱情懷
歸隱是中國古代士人常有的情懷,尤其是在朝代更迭,易代之際,一腔抱負(fù)無法實現(xiàn),壯志難酬之下則希望歸隱田園,實現(xiàn)內(nèi)心的清凈。龔鼎孳的唱和詞中也偶有一種希望隱逸的情懷,但相比那些真正想要追求隱逸田園生活的詞人們,他看似擁有淡然的心境,卻又充滿著不甘與不平。
其晚年《賀新郎》中的一首典型的歸隱詞《賀新郎·其十三·秋日蒙遣祭至唐家?guī)X因游西山》,豪放與頹唐交雜。上片看似想要通過歸隱來擺脫這樣的處境,但下片頭句“少豪妄意功名顯”看似是對于年輕時追求功名的悔意,實際是對于自己年老無法施展抱負(fù)的無奈,因此,龔的這種歸隱不是真正地看破塵世超然想要皈依山水,詞中依然流露出對于浮宦名譽的留戀。
綜上,在龔詞中,他的歸隱心境與真正想要“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并不相同,而是因為自己處于一種進退迍邅的境地而被迫所產(chǎn)生的想法。
三、結(jié)語
龔鼎孳的復(fù)雜經(jīng)歷使他時時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心態(tài)也極為矛盾復(fù)雜,因此其詞中的感情也紛繁復(fù)雜,詞作風(fēng)格也經(jīng)歷了變化,前期“綺艷”頗有云間之致,后期趨于“豪放”,向“稼軒風(fēng)”靠攏,這也印證了當(dāng)時明詞向清詞演進的軌跡。他還是清初詞壇的主持者,他用自己的行動與創(chuàng)作傳承著詞的文化意義,因此他的詞作值得我們研究并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