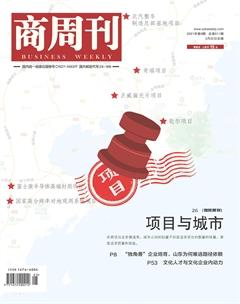張燕生:中國的一個長期戰略部署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如何形成差異化結構?這意味著要互補,包括差異化互補、共享性互補、合作型互補,這是我們下一步貿易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當前,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突出的表現為中美之間的沖突和對抗。全球化下半場如何在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此,首先要胸懷兩個大局,一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大限度避免中美兩個大國由競爭沖突對抗逐步升級,走向中國國家領導人在G20大阪峰會所指出的“要避免因一時短視而犯下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另一個大局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大勢、大局、大策,對中國而言,就是輕易不能犯常識性錯誤。就是要保持平常心。
全球化下半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表現為“三新”。過去四十年重點講了三個故事,一個是市場經濟的故事,二是外向型經濟的故事,三是工業化的故事。新發展階段,除了繼續講好這三個故事,還要講好三個新故事。一是講好創新的故事,也就是新三十年推動我們的科技創新,推動“中國大腦”和“世界大腦”的構建,推動全方位高質量發展。這是一場國際拔河,是中美兩個大國的較量,科技領域被一些人稱為決定兩國命運的生死存亡之戰,在此形勢下,如何從兩國戰略競爭、戰略對抗、戰略脫鉤、選擇性脫鉤,走向戰略合作,這是新30年要講好的故事,也就是中國未來30年發展需要的世界大腦,世界大腦離不開中美全方位的創新合作。第二是要講好法治的故事。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現代化,治理的現代化,法治的現代化。這就涉及我們下一步的體制機制如何對標國際高標準并相互銜接。什么是國際高標準?誰代表國際高標準?我們應當如何銜接和對接?這是我們新30年需要講好的新故事。第三個故事,就是要講好共同富裕的故事。我們過去4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新30年要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而且要分階段、分步驟推動共同富裕。
全球化下半場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創新要成為第一動力。我相信在新發展階段,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全社會都會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我相信未來無論是大學、科研院所還是頭部企業,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投入都將大幅上升。2020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經費投入是2.44萬億元,研發強度2.4%,這在全球也處于比較高的標準。我個人預測,未來十年,珠三角投入創新的經費,累積可能達到四萬億元。長三角投入創新的經費,累計可能超過八萬億元。從這個角度,中國確實到了新發展階段,如何使這么一大筆資金和資源產生更高的效率和效益,能夠推動全員勞動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涉及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生態以及跨境創新網絡問題,這是下一步必須解決的問題。此外,新發展理念的綠色發展要成為普遍形態,2030年前要達到碳達峰,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這意味著下一步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新舊結構轉換、新舊模式轉換圍繞著綠色發展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在這些方面,我們和美國、和世界也都存在如何更好地開展合作的問題。
全球化下半場還要構建新發展格局。
這主要包括三句話。一是確立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用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話講,這是一個長期戰略部署,為此,下一步如何將擴大內需作為重要戰略基點,如何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動全國統籌和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如何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實現倍增,如何推動農村剩余人口市民化等,這些都是下一步要解決好的問題。確立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是按照越來越封閉的方式發展,還是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如果是按照更高水平開放的路徑走,將有三個指標體系亟待建立:一是市場開放的指標體系,也就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的平均關稅率持續下降,非關稅措施持續取消;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和效率進一步提升,降低貿易投資成本;服務業市場準入大門越開越大。這幾個方面其實都可以通過指標體系、統計體系、評價體系,通過績效考核,建立起約束性的硬指標,從而保證未來建立國內大循環是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條件下推動的。第二是制度型開放。也要建立相應的指標體系,如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是越來越和國際高標準制度相銜接還是相偏離,可以用硬性指標來衡量。第三是知識型開放,即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以及開發和試驗研究等的開放創新、開放合作以及開放共享,是可以用指標體系進行衡量的。在此基礎上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下一步高質量發展就會邁上新臺階。
第二句話,就是構建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深耕東亞,二是深耕“一帶一路”,三是深耕美歐生產網絡。我個人預計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后,全球會出現需求東移、供給東移、創新東移、服務東移、資本東移、貨幣和金融合作東移等全球性新趨勢。關于創新東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發表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簡稱GII)報告,指出了一個全球性創新趨勢,就是創新格局的東移,而且國際新增加的專利的百分之五十,是用漢語、日語、韓語寫成的。如何把握住東移的趨勢?首先要做好中日韓FTA的談判,中國在中日韓區域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就是RCEP,原來是“10+6”,現在是“10+5”,我稱之為包容性的區域貿易協定,下一步如何落地并邁上新臺階?以及中國將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是中國已經宣布積極考慮加入CPTPP。那么,中國要考慮一種可能性,未來兩年甚至更長時期內,美國可能重返CPTPP,此外,英國也正式提出加入CPTPP,這對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是積極的。我認為,對于中國的進步,過程比結果重要,在未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如果中國能夠真正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體制性問題上,如國有企業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工業補貼問題、產業政策問題、勞工標準問題、環境標準問題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步,我們的制度開放和制度進步、法治進步都會再上新臺階。
下一步如何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我想重點談一點,如何避免落入“薩繆爾森陷阱”。這意味著隨著我們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的不斷轉型升級,不可避免地會和美國、歐洲、日本核心競爭利益和重要領域形成競爭性關系,也就是會動美日歐發達國家的“核心奶酪”,同樣,也不可避免地會動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奶酪”,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對抗和沖突。如何在未來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就必須妥善處理和應對競爭、沖突和對抗。我以為,我們過去和美日歐貿易結構、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主要是互補性的,隨著我們轉型升級,會越來越呈現競爭性部分,出現“薩繆爾森陷阱”。未來如何在轉型升級以及崛起為制造型強國的過程中,和美日歐形成更高層次的互補性結構,包括貿易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都是未來要著力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同美歐日,也包括新興和發展國家以及欠發達國家等。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如何形成差異化結構?不要動別人為數不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奶酪”?這意味著,互補包括差異化互補、共享性互補、合作型互補,都是我們下一步貿易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中國如何能夠給別人提供“奶酪”,而不去動別人的“核心奶酪”以及為數不多的“發展奶酪”。這也是我們未來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在此情勢下,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到了新發展階段,作為負責任大國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必然回答的問題。
(據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原秘書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在中宏論壇第十二場在線研討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