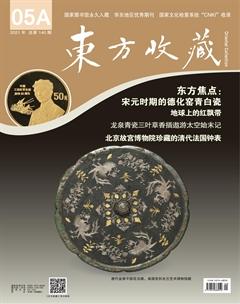淺談巖山寺金代壁畫中的民俗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延續五千年間所創造的輝煌燦爛的民俗文化,對人類的進步作出巨大的貢獻。中國民俗作為古典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山西北部的風俗民情在它漫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僅受華夏民族的影響,而且還接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滲透。在長期持續不斷的演進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實現其日益細致的自我完善。顯然,促成這種自我完善演進的因素主要是內在的,即自身的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的制約情況所產生的推動力。這些制約影響的錯綜復雜,又決定了民俗在各個歷史階段上的差異。
巖山寺,原名靈巖寺,亦名靈巖院,位于山西省繁峙縣境內五臺山北麓的天巖村。寺內現存文殊殿是金代遺構,碑文載:文殊殿于“正隆三年戊寅歲四月十五日建記”,面闊五間,深六椽,單檐歇山頂。殿內有泥塑和壁畫,壁畫為金正隆三年(1158)。建筑竣工后由“御前承應畫匠王逵、同畫人王道”繪制至金大定七年(1167)畫完。“王逵年陸拾捌歲”,前后繪制了十年,從“同畫人王道”的語意分析,王逵與王道不是父子關系,也不是師徒關系,有可能是同行關系,但王逵是“御前承應畫匠”,當屬宮廷畫師,王道的身份不清楚。根據西壁王逵的題記和殿內東、西壁在畫風上的不同,西壁壁畫無疑是王逵繪制的,東壁很可能是王道繪制的,而且這種分工繪制壁畫,在中國古代畫工中屢見不鮮。
現存殿內保留下來的壁畫,東、西壁基本完整,南壁幾乎全部被毀,北壁還保存一部分。壁畫面積共計98.11平方米,壁畫內容西壁為佛傳故事,東壁和北壁是說法圖、鬼子母和羅剎國等故事。
西壁壁畫為一整幅,高345、寬111厘米,面積38.64平方米。四周有粗細兩道墨染邊闌,根據畫幅上的題記,所畫內容釋迦摩尼佛傳故事,是描繪佛教創始人釋迦摩尼的生平事跡:從天上贊明菩薩托生下凡,到出游四門,學百工射藝,最后出家成佛。描繪了釋迦摩尼神通廣大,法力無比,諸天神鬼、外道邪魔都被他降伏,皆皈依佛門。
壁畫內容為了更好地表現釋迦摩尼的生平事跡,在幅面安排的畫技上,包含了許多民俗生活的場面。如釋迦摩尼降生時“托胎”、降生后“九龍灌頂”、夫人梵香祈福、侍女“摑鼓報喜”。釋迦摩尼作為凈飯王太子,參拜的禮儀和行幸出游四門的鹵薄儀仗,以及太子和妃嬪日常生活起居,無一不是宋金時宮廷生活和儀軌制度的真實寫照。凈飯王為太子命名舉行的盛大儀式中,皇太子頭戴高冠,手執玉圭,身著朝服,端坐在金殿上接受排列在丹墀下面的文武百官朝拜。大殿兩旁還有手持骨朵、旗幡和金瓜及鉞斧威然肅立的儀行。這種隆重的儀典無疑是中國宋、金時皇太子接受冊封朝賀的真實情況。再如《出行圖》中,一群內廷侍臣和宮嬪女簇擁的一乘前后有數十人抬著的華美高大的肩輿,前邊有擊鼓奏樂的儀仗,后面有騎馬的隨行官員,城門口還有身披盔甲、手持矛戈的衛士。這種前呼后擁、戒備森嚴的出行盛大場面,實際是對中國宋、金帝后、太子出行的寫照。畫面上這種豪華宮廷的宮墻外面,卻又是一番情景,無依無靠流落道途的老翁貧病交加,奄奄一息的窮人和郊外野狗、狼等吞噎死者的悲慘場面。
《驕陳如送太子回來問訊處》是一幅描繪中國宋、金時期繁華都市的典型民俗畫。畫面上市井人煙,買賣交易十分熱鬧,有僧俗人眾,有算命卜卦的盲人,有推車挑檐賣小吃的小商小販,還有兒童婦女和衣冠楚楚的富人與紳士。街道左側是一座酒樓,酒簾高挑,樓內備有桌凳,正坐著官人在宴飲,旁邊有賣唱的歌妓正為官人們演唱。門外高挑著招幡,上書“野花攢地出,村酒透瓶香”。這幅民俗畫描繪了當時社會上眾多階層的生活狀態。
北壁西次間稍間壁畫聊為一幅,畫上題記為《五百商人□□□吹墜羅剎厄國》。畫面左上角畫羅剎惡鬼施展魔力,把一艘滿載貨物的大商船連同五百商人一齊吹卷到羅剎國的故事。畫面表現了航海商船突遇狂風惡浪,大風把桅桿吹斷,船中的乘客嚇得手足無措,船工們卻向大自然展開了激烈搏斗的驚險場面。畫面上方繪制了遠處海面出現海市蜃樓的奇異幻景,顯示了中國航海者出沒于“風雨晦冥”的險惡環境。更有趣的是右側上方,繪制一所小監獄。監獄內柱上綁著六名罪犯,三名跪著反綁于檐柱上,三名站著反綁于柱上,其中兩名綁于院中柱椿之上,六名罪犯表情不一,有的顯示出無所畏懼,有的已露出無法忍受的樣子。
東壁壁畫高345、長1100.18厘米,面積38.57平方米。四周皆以粗細兩道邊闌,整體畫面是須阇提太子本身故事,描繪波羅奈國王寵幸的大臣羅阇,心生惡逆,起兵篡奪王位。整個內容與其說是表現釋迦摩尼前生作為須闍提太子的善因,倒不如說是表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宮廷政變和原始社會餓食人肉的野蠻遺俗。全幅壁畫以山水樹石云風掩映,組成一幅完整的畫面。
《牧女獻乳》是一幅富有社會生活氣息的繪畫,畫面上山峰起伏、綠草遍野,三頭奶牛站立不動等待牧女擠奶,牧女和一孩童正蹲在前中間一頭乳牛腹旁,手捧陶盆,聚精會神地擠奶。前側還放著個盛奶的陶罐。后面一頭奶牛兩眼斜視牧童,左側一頭奶牛一動不動地等待擠奶,尾巴似乎還不停地搖擺,示意已憋不住了。畫面細微,寫實手法生動,民俗風情真實。
《鬼子母圖》和《嬰嬉圖》,把兒童天真活潑的性格描繪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嬰嬉圖》是一幅上好的兒童題材佳作,畫面上的兒童正在表演皮影戲,一個兒童在影幕后面拿著皮影正在表演,影幕前面有三個兒童,兩個席地而坐,一個兩手扶地爬著,正興致勃勃地看皮影戲。旁邊有一組兒童,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用手指著同一方向,好像在爭論什么,旁邊還有一個光屁股男孩,俏皮地翹起小腿在聽他們的爭論。更有趣的是,有一個兒童大概是和小伙伴們鬧了別扭,孤零零地坐在一邊,玩弄著皮影人。整個畫面把兒童的天賦性格和嬉戲的神情躍然壁上,真可謂把人物性格著意刻畫得栩栩如生。
《水磨□□□碓臼圖》是一幅既能磨面、又能舂米的水磨作坊圖。在水磨的橫軸中部安裝了巨大的水輪,橫軸的另一端,安著兩個舂米的杵桿,渠水沖著水輪,使橫軸迅速旋轉帶動著水磨運轉,同時帶動兩個木桿不停地一起一落舂米。這幅圖反映的既是12世紀中國勞動人民智慧的創造,又是一幅絕好的山區鄉村社會民俗生活佳作。
當時北方,遼金與宋接壤,戰事無常。遼金原為武弁民族,文化不發達,后逐漸強大,侵入中原北部后,大受中原北部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戰爭中大量俘獲藝術人才,并給予豐厚待遇,為其政治服務。特別是畫士之間應試作畫,互為競爭,各顯之所能,以互相夸示,使遼、金繪畫國運日漸興盛。巖山寺壁畫的作者王逵、王道,雖未有明文記載,很有可能也是金朝眾多畫士者之一,而且王逵是“御前承應畫匠”。
從壁畫內容看,王逵、王道兩位畫家,對宋、金時期社會上的各階層人物社會身份、階級地位,職業區分、生活民俗習慣、衣著特點和精神外貌,都能描繪得恰如其分、栩栩如生。佛的慈祥、天王的威猛、帝王的尊嚴、貴婦人的矜持、勞動人民的勤勞樸實,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無一類同。壁畫中的繪畫、山水,雖然作為人物的配景,但烘托人物故事,渲染環境氣氛是不可缺少的。壁畫中作者創造了許多優美的山水意境,如群山起伏的深山峽谷、奇峰崛起的危崖峭壁,怪石突兀的摩崖山洞、煙云縹緲的仙人幽居以及樹木蔥茂的山村野居和溪橋流水的田野風光,皆顯示了作者的功底。
中國繪畫藝術漢魏時期多取經史故事,盛唐以后而代之為中國封建禮制和風俗民情,并混合而陶熔。盛唐以后,審美導入自由創作的藝術境地,一反漢魏古簡之風,技術的進步、審美程度的提升、學理性經驗的積累,以及畫師的慎重程度,都已完全民俗化。特別是畫師也由帝王貴族、畫院畫師之手移向于民間,較多地跳出封建禮教的范圍,尤其是來源于民間的畫師,在畫面內容上較多地反映了風土人情和通行習見的民俗志尚。一時社會上好畫者,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畫技上脫離了皇室的法式,深入純粹藝術之鑒賞。王逵、王道特別是王道這樣的大畫家,繪畫出巖山寺如此精湛的壁畫,卻在史籍記載中榜上無名,故宋、金時期名畫家蔚起,闡微發奧,群雄競秀,萬壑爭流,法備而藝精,為后代所師法。
審美趣味是人對周圍事物的直接的有情感的審美評價,它表明事物在人們身上會引起什么樣的審美感受。但審美情趣常常要受一定的制約和影響,也就是繪畫藝術品也總是要反映出作者的某種審美情趣,審美情趣既有個人的特性又有社會時代的共性。巖山寺壁畫中之所以能夠用較大篇幅反映當時的風俗人情,一方面反映作者的審美情趣,另一方面由盛唐以后社會制度的變化、民間藝術的成熟,較多地想方設法來反映風俗民情。因此,巖山寺金代壁畫中的風俗民情是時代的產物。
(作者簡介:李雋,工作單位:山西省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