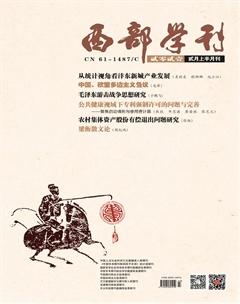“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維制度體系及其關系價值解析
摘要: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者作為代表三個不同層面的制度體系各自包含了不同內容從而體現出不同內涵意義。三者從不同維度表現出其內在關聯:在哲學理論層面,基于唯物辯證法的普遍聯系三者鮮明地體現了事物發展規律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對立統一;內容方面體現為“全局管總—階段發展—具體針對”;在形式上表現為“三維制度體系邏輯樹”構架。三維制度體系的價值體現在具有高度耦合性、創新發展性、雙重漸進性,從而保障了制度體系系統集成、協同高效。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三維制度體系;關系價值
中圖分類號:D6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3-0021-05
1992年,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長期性做出了科學的判斷:“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我國制度體系正持續趨向“定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我國制度體系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與闡述。其中強調要“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2]。只有深入理解“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構成的三維制度體系內涵、關聯以及價值所在,才能找準著力點,結合現實推動我國治理體系成熟定型。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內容構成及其內涵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體系內涵及構成
“根本”一詞初現于《韓非子·解老》:“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誕生之初即以“腸胃”在人生存中的“生存決定性”地位來表達其含義。而后用于植物的根干,將“本”化為樹木的“根”,由此根本得以聯結。如今我們講根本,更多表現為“事物的本源根基”。從“根本”的誕生之初及其后來含義發展可以看出其內蘊的“決定性”“基底性”。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根本制度即“起頂層決定性、全域覆蓋性、全局指導性作用”的制度,這一定義正是基于“根本”本意做出的研判。因此,根本制度的內涵意義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兩方面。一為“生存決定性”,即根本制度是制度體系這棵“大樹”根基樹立的保障,是確保我國成功“站起來”且站住站穩的基石。二為“生存根基性”,根本制度體系下的各種制度是我國未來發展理念、方針、政策制定之根基原則,絕對不能夠出現違背脫離的現象,對其制度體系的堅持是穩定我國社會主義國家形態,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全面發展的基礎。因此,根本制度體系是貫穿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的制度體系。《決定》輔導讀本中,施芝鴻全面闡述了我國根本制度的構成,即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構成的根本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成的根本政治制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地位構成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構成的根本社會治理制度;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構成的根本軍事制度。五大根本制度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根本制度體系,成為我國“站起來”“富起來”繼而“強起來”的根本保障。
1.根本領導制度——一張藍圖繪到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黨的全面領導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根本觀點,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必要保證。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我國制度優勢的首項予以提出。從“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到“堅持黨的領導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標志”,再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最大優勢”,可以說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了我國70多年的發展和繁榮,描繪著偉大事業的藍圖。
2.根本政治制度——實質民主的中國彰顯
十九屆四中全會中指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制度,是被實踐證明契合我國發展需要必須毫不動搖堅持的制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被證明了的能夠救中國于水火之中的制度,從而有了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所體現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理論原則以及基于其所構建的政治制度規范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推手,實現黨與人民的共同治理。
3.根本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的科學穩固
思想是一切行動的先導,思想引領若發生錯誤,現代化建設事業將無法接續發展。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開放的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思想指南,這必然要求我國的一切政策制定、工作部署都要遵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國情相結合的原則。因此,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樹立作為根本文化制度進行闡釋,認為其不僅是我國文化建設發展之成就,亦是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更是黨與人民齊心協力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思想保障。
4.根本社會治理制度——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和重要表現。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指明了我國國力增強的同時亦指明我國未來發展方向的著力點,人民治理訴求的提升與現實社會的多樣化發展亟待我們在社會治理方面完善上層建筑,基于此充實社會治理政策制度以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因此,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共建共治共享”作為社會治理制度予以提出,這不僅是對我國制度體系的完善,更是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的根本路徑。
5.根本軍事制度——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支柱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確保人民軍隊忠實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起源于“三灣改編”,是對我國革命、建設、改革歷程的全部經驗的總結。革命時期“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與“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為我國當前處理黨軍關系奠定了思想基礎,不僅指明了軍隊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性,更突出了政權建立后黨與軍隊的思想行動一致性的必要性。正是因為我們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從而確保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穩定性。綜合來看,當前我國發展轉型的關鍵性,以及世界格局發展的嚴峻性,我國海陸雙具的地緣政治條件下安全的復雜性,都要求我們必須堅守這一根本軍事制度。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體系內涵及構成
“基本”一詞即為“基礎、基于”,最初用于建筑學,指建筑底部與地基接觸的承重物件。因此,基本制度體系一方面基于根本制度體系契合我國發展的基本國情,另一方面作為重要制度制定的先決條件持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以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其闡釋為“貫徹和體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基本原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等發揮重大影響的制度體系”。在此基礎上詳細地概括了基本制度體系的內容構成,其中包含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等。基本制度體系不僅成為推動我國社會實現“富起來”、邁向“強起來”的助力器,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發展。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體系內涵及構成
“重要”形容產生或具有重大影響或者后果。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我國的重要制度給予明確定義: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來的,體現在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相對于根本制度與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時效性方面表現更為突出,其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進行充實與修正。黨的十九大做出了“新時代”的時代定位,原文中“進入新時代”含有一種“完成時”理念,即在此次大會召開前綜合各項因素我國已經處于“新時代”環境下。在這個意義上就不難理解我國推進現代化建設,于十八大至今在行政體制、機構以及社會生活等多方面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在思想教育方面推出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制度,在政府治理方面推進“放管服”改革,在居民租房問題上提出“新房新租”,黨政機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等,所有重要制度的立項源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旨在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全方位制度體制改革的形成以及作用對象是基于并針對現實發展的,因而邁向“強起來”的新發展階段之際,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完善重要制度體系。
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維制度體系的內在關聯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這反映出我國制度體系具有強烈的綜合性、聯系性與發展性。三者內在關系在哲學層面上表現為科學的理論構架、客觀的遵循并反映事物發展規律,在內容層面上表現為“全局管總—階段發展—具體針對”漸進深化的層次性,而在組織構架方面則表現為“制度體系三維邏輯樹”格局。
(一)科學理論構架:遵循并反映事物發展規律
任何事物都有與其內容相契合的表現形式,三維制度體系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表現形式。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發展已經證明了我國制度體系的優越性與強大的生命活力,同樣如此優越與強大的制度體系亦是源于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國家治理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從實際出發,及時制定一些新的制度”[3]。所有“新的制度”逐步完善了三維制度體系,而三維制度體系“逐步成熟”的過程中表現出“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對立統一。“必然性”與“偶然性”分別象征著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穩定性”與“可變性”。在三維制度體系中,根本制度體系的行成切實彰顯“穩定性”,而基本制度體系與重要制度體系所展現出的不同程度的“靈活性”分別表現為其“可變性”。“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里面的形式”[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于中共十四大提出,彼時并非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組成因素。基于其為我國經濟社會帶來的發展紅利以及我國現實國情發展需要,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將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范疇。正是這樣的“穩定”“可變”與“必然”“偶然”推動三維制度體系涵蓋內容逐步豐富、功能逐步齊全,不斷向現代化治理體系邁進。
(二)內容層次性:全局管總—階段發展—具體針對
作為系統性的理論體系,不同國家基于民族特色、文化背景等多重原因形成的治理體系層次劃分類型往往不同。例如有學者基于作用對象不同將制度體系劃分為操作層次、集體選擇層次、憲政選擇層次、元憲政層次四個層次;有的學者針對社會作用角度將社會體系劃分為非正規制度、基本制度環境、治理機制、資源配置和雇傭制度四個層次[5]。結合我國制度體系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將其分為“全局管總—階段發展—具體針對”三個層次進行理解。
1.根本制度體系——全局管總
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歸納出的五大根本制度,其綜觀全局性表現為充分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國家屬性,屬管總性制度體系。這一管總的“總”指的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總的發展歷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后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國仁人志士多次尋求救亡之法失敗后的歷史選擇。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意味我們選擇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更意味著在實現這個遠大理想的征程中必須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視為行動指南。因而馬克思主義是推進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管總理論。黨的領導的根本領導制度確立源于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成為政黨”必要性思想。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將存在一個……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里“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6]。另一方面共產黨人所具有的先進性是其領導地位確立的原因重柄。馬克思認為“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中最先進和最堅決的部分,是推動所有其他部分前進的部分”,相對于其他無產階級他們更加“清楚地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路線、條件和最終的一般結果”[7]。因此,黨的全面領導的根本領導制度是社會主義事業長期平穩發展的根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制度保障。1956年我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公有制標志著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同時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根本上保證國家權力歸屬于人民。而在制度發展建立的全過程中,更是時時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治理制度正是在遵循“以人民為中心”價值導向所得,是對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主義因應。
2.基本制度體系——階段發展
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在以經濟基礎的重大變革為劃分依據的不同發展階段上的上層建筑的具體表現,囿于經濟基礎的重大變革好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基本制度體系的階段發展具有長期性與穩定性。以基本經濟制度為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是保障社會主義性質的規定,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對我國具體國情的規定。我國GDP總量雖位于世界前列,但人均來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因此我們仍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調動起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生產力,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對照來看,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基本制度只有在生產關系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上的質變發生時才會變更。此外社會生產力的漸進發展往往會帶來生產關系的階段性變化,由此導致社會基本制度根據社會發展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與完善。從十九屆四中全會總結來看,我國的基本制度體系正式提法主要體現為基本政治制度與基本經濟制度,從其內容來看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發展完善視域。例如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中中國共產黨領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基于革命建設時期群眾型政黨以及統一戰線的基本經驗而來。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展,村民委員會對于推動生產力發展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居民委員會的成立在城市同樣促進了社會和諧,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正是在汲取了這些自治經驗基礎上于十七大作為基本政治制度予以確立。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原有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添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的字樣更加說明基本制度的階段發展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提出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將其作為基本制度體系一方面肯定了過去幾十年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也表示未來其將持續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紅利。仔細觀察基本經濟制度提法中會發現增添了“等”字,“等”的增加更加說明了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完善發展性。未來亦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增添新的內容。從基本制度體系內容的發展過程來看,其確立需要長時間的驗證,因此基本制度體系在確定穩固后相較于根本制度體系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3.重要制度體系——具體針對
重要制度體系涉及的領域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全方位,是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所產生的具體問題具有針對性解決方案的制度體系。重要制度時效性最為鮮明,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動態漸進性。過去在某些階段對社會生產力起重大推動作用的制度,往往伴隨生產力歷經一段時間的發展效用有所降低,從而轉化為不重要的制度。例如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基于計劃經濟體制制定的對彼時社會生產力發展起重要作用的制度,伴隨市場經濟的推進則逐漸變為不重要的制度有些甚至不予采用。當前伴隨互聯網與人民生活的深度融合以及人民參與治理意識的提升,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其中包含當前國內外發展的復雜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基于此形成了包括國家安全風險研判、防控協同、防范化解機制等。由此可見,社會發展過程中矛盾運動的前進運動及其過程中矛盾新特點的層出不窮是重要制度體系內具漸進性與創新性的根本,因此相對于基本制度來說其靈活性更為顯著。
(三)形式表現:三維制度體系邏輯樹
基于上述論述,從內容組成內涵以及內在關聯來看,三維制度體系組織構架呈樹狀。象征著頂層決定性、全域覆蓋性、全局指導性的根本制度體系作為樹根,樹根若發生動搖,整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大樹將會“風雨飄搖”;體現黨關于經濟社會發展基本原則基本理念的基本制度體系則是樹干,基于樹根穩固之上形成覆蓋各領域建設且自身亦不斷發展;派生于根本制度與基本制度并貫穿于國家治理各領域的重要制度體系則是樹葉,其依托樹根與樹干且具有較強的靈活性。三者的“質”與“量”共同決定著三維制度體系邏輯樹的生機與活力,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科學與完備。
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維制度體系的價值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決定》中指出,各方面一致認為《決定》中對于我國制度體系的闡述“突出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體現了強烈的問題導向和鮮明的實踐特色”。這表明我國制度體系建設要通過“堅持和鞏固”“完善和發展”朝著“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方向邁進。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而三維制度體系所衍生出的高度耦合性、創新發展性以及雙重漸進性保證了制度全面系統性,從而確保制度發揮最大效能。
(一)高度耦合性
制度作為上層建筑其建設目的是為了實現某種目標,作為體系化形成的制度更是要確保這一目標的一致性。三維制度體系的高度耦合性即表現在其能保障在制度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相互制約從而確保制度目標同向性。例如民主集中制最初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制度與領導制度適用范圍擴展至國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從而實現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結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政治制度鮮明回答了黨權、人權、法權三者在現代化建設中扮演的角色,保障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權利與權力的平衡發展。
(二)創新發展性
制度創新發展是當前我國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我國成功實現崛起的重要因素即制度體系一直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完善。從整體性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發展,體現為《決定》所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從具體制度制定來看,我國制度建設源于人民的切實需要,因此制度的建設與實際需求總是形成“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完善過程。例如重要制度的高度靈活性有效應對了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所產生的一些時效性突發問題的制度完善。對此,《決定》所強調的“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都隸屬于重要制度的范疇[8]。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我國制度體系分為三個維度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軍事等全方位制度建設領域的“十三個制度體系”。《決定》中“十三個制度體系”下分別有建立、完善、健全、堅持與完善、鞏固與發展等字樣,針對不同制度建設的現有發展態勢以及發展方向給予定位,鮮明地體現了制度作為上層建筑要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而具有的發展性。
(三)雙重漸進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我國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的制度演變、制度創新”,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形成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歷程,是以總的制度體系所展現出來的,其漸進性源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漸進性,尤其是改革事業的漸進性。三維制度體系的漸進性具體表現為溯源性與層級性兩個方面。
漸進性的深化理念表現出的溯源性。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問題的多樣化,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確定矛盾本質以及責任主體是建設現代化制度體系的重要路徑。通過制度的逐步深化形成錐形制度溯源體系才能有的放矢準確落實主體責任。漸進性所具有的逐步理念彰顯層級性。層級性表示為高級層次的制度(根本制度)、中級層次的制度(基本制度)以及低級層次的制度(重要制度)。將制度分層能夠確保制度設立時的價值導向歸一化,即每一層次制度設定之時都要遵循上一級制度所代表的理念屬性。例如當前我國經濟轉型下的一系列重要經濟制度制定絕對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冠名確保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價值落腳點在公平、正義。
四、結語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三維制度體系保障了我國“兩大奇跡”①的實現,同時說明了該制度之“型”的科學性與高效性。同時我們也要充分意識到當前我國制度體系的有待發展。例如基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②的考量,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生態文明制度等等仍然需要進行充實,在重要制度層面亦是如此。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萊茵報》檢查制度時指出的:“一切發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9]。作為發展中的新興大國,作為發展至現代化征程潮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實現“堅持和鞏固”“完善和發展”的齊頭并進,從而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注 釋:
①兩大奇跡: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偉大成就概括為“兩大奇跡”,即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社會長期穩定奇跡。
②“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推進。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2.
[2]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J].求是,2020(1).
[3]習近平.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J].前進,2012(12).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0.
[5]楊開峰.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概念性框架[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0(3).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4.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5.
[8]施芝鴻.系統集成的新時代科學制度體系[N].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06-18.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
作者簡介:朱厚敏(1997—),女,漢族,遼寧丹東人,單位為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