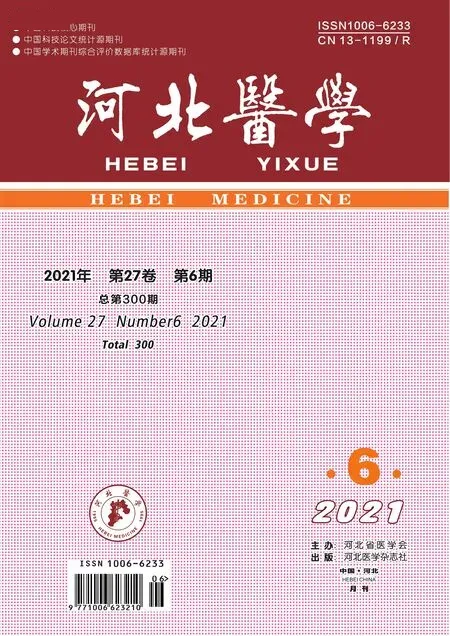Myosin1H基因多態性與蒙古族骨性下頜后縮易感性的關系
李曉暉, 程書玉, 巴格那, 陳玉友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口腔科,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下頜后縮(mandibular retrusion,MR)是骨性Ⅱ類錯合畸形發生的重要病機,此類錯合畸形常表現為上頜正常或前突,但下頜后縮,伴前深覆合,開唇露齒,影響口腔頜面部形態及口腔功能[1]。長期以往可能誘發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增加心腦血管疾患發生風險[2]。前期調查顯示,我國青少年安氏Ⅱ類錯合畸形發生率超過20%,其中骨性MR比例超過1/2[3]。最新研究指出,骨骼肌收縮功能的正常維持有賴于肌球蛋白重鏈異構體的調節[4]。肌球蛋白由重鏈復合組成,承擔骨骼肌纖維收縮功能,與骨骼肌可塑性密切相關。I類肌球蛋白(Myosin1H)為非經典肌球蛋白,參與肌肉收縮、膜泡運輸、細胞極性建立等過程,該蛋白遺傳性改變可能影響骨骼肌生長發育,已證實與南亞人群下頜骨發育異常[5]。但東南亞人群存在種族、地域差異,或存在遺傳易感性區別。為探討Myosin1H基因多態性與蒙古族骨性MR易感性的關系,現對本地區蒙古族骨性Ⅱ類錯合畸形、骨性Ⅰ類錯頜畸形患者Myosin1H基因多態性進行檢測,探究Myosin1H基因多態性與骨性MR患病的關系,從遺傳基因學方面分析骨性MR的病機,以期為該病防治提供指導,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納入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我院口腔科就診的以MR為主的骨性Ⅱ類錯合畸形61例作為觀察組,同期就診骨性Ⅰ類錯頜畸形61例作為對照組。觀察組納入標準:均為內蒙古境內蒙古族;無不同族群、不同種族婚史或同居史;均表現為以下頜MR為主骨性Ⅱ類錯合畸形,屬安氏Ⅱ類錯合畸形,經現代口腔正畸學診療手冊確診[6],SNA角(蝶鞍中心、鼻根點、上齒槽座點構成角)為78~86度,SNB角(蝶鞍中心、鼻根點、下齒槽座點構成角)<76度,ANB角(上齒槽座點、鼻根點、下齒槽座點構成角)≥5度;磨牙遠中關系,伴前牙深覆合、深覆蓋;上頜較下頜位置靠前,或下頜角較上頜后縮或兩者均存在;履行告知義務,獲得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對照組納入標準:均為內蒙古境內蒙古族;確診為安氏Ⅰ類錯合畸形;上下頜形態、位置關系正常,SNA角78~86度,SNB角77~83度,ANB角0.8~4.6度;FH-MP角(眶耳平面與下頜平面構成角)在26~37度之間,下頜角在114.2~125.4度之間;磨牙中性關系;無不同族群、不同種族婚史或同居史;患者均知情,已簽署研究同意書。排除標準:既往有正畸治療史;功能性或牙性Ⅱ類錯合;經口呼吸、咬下唇、吸吮手指等不良習慣;替牙障礙;嚴重心肝腎肺功能不全;牙齒缺失;萌芽順序異常;口面肌功能異常;小下頜畸形綜合征;唇腭裂;頜骨手術或頜骨外傷史;合并影響頜面部發育疾病者。兩組臨床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見表1。
1.2方法:①Myosin1H基因多態性檢測。采用聚合酶鏈式反應-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s length polymorphism,PCR-RELP)法測定Myosin1H基因多態性,從NCBI數據庫檢索Myosin1H基因組mRNA序列,查閱文獻選擇基因位點(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7]。就診時采集肘正中靜脈血5mL,抗凝管保存,超低溫冷凍保存待測。參照Trizol試劑盒(美國invitrogen公司)使用說明提取全血基因組DNA,蛋白核酸分析儀鑒定純度及濃度滿意后用于后續檢測,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設計引物,Myosin1H rs11611277位點上游引物序列:5’-TCCCAGGGTTTAGCATCTTG-3’,下游引物序列:5’-GAGTGGCGCCTCAGTATCTC-3’,擴增片段長度386 bp,限制性內切酶Hpy1881,Myosin1H rs3825393位點上游引物序列:5’-GGCTTACTTCCCTCCCAGAG-3’,下游引物序列:5’-CTGTGGCAACAGCATTCTTA-3’,擴增片段長度302 bp,限制性內切酶Sau961,對目的基因進行PCR擴增反應(試劑盒購自美國Sigma公司),反應體系:DNA模板500~100 ng+2×Easy Taq PCR Super Mix 12.5 μL+上下游引物各1 μL+無菌無離子水補足至25 μL。PCR反應條件:95℃預變性120s,94℃變性60s,68℃退火30s,72℃延伸30s,30個循環,獲取PCR產物5μL,瓊脂糖凝膠電泳,UVP-640型凝膠成像分析儀(美國UVP公司)觀察擴增條帶,確定擴增成功后拍照保存。并檢測PCR產物RELP,限制性內切酶Hpy1881/Sau961行產物酶切,反應體系:PCR產物10μL+Hpy1881/Sau961內切酶2U+酶切緩沖液2μL+無菌去離子水補足至25μL,37℃恒溫水域120min,Myosin1H rs11611277位點酶切位點為C,AC型酶切后為241 bp+146 bp兩個片段,純合突變CC型無法被酶切,僅有386 bp一個片段;rs3825393位點酶切位點為G,酶切后野生GG型為76 bp、226 bp兩個片段,雜合突變AG型為76 bp、226 bp及302bp三個片段,純合突變AA型無法被酶切,僅有302bp一個片段。②頭顱側位片測定。入組時均拍攝頭顱側位X線片,每周重復測定1次,重復3次取均值作為最終結果,記錄SNA角、SNB角、ANB角、FH-MP角、MP-SN角(下頜平面與前顱底構成角)與Z角(軟組織頦部與突出前齒部切線與眶耳平面形成后下角),明確上下頜位置關系。

表1 兩組臨床資料對比

2 結 果
2.1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遺傳平衡檢驗: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基因型頻率分布經檢驗符合Hardy-Weinberg遺傳平衡定律(P>0.05),說明樣本有群體代表性,見表2。

表2 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 rs3825393位點遺傳平衡檢驗[n(%),實際頻數/預計頻數]
2.2兩組頭顱側位X片測定結果比較:觀察組SNB角、Z角小于對照組(P<0.05),ANB角大于對照組(P<0.05),見表3。

組別nrs3825393 GG型 AG型 AA型 χ2 hw-P觀察組6119(31.15)/18(29.51)37(60.66)/35(57.38)5(8.20)/8(13.11)0.7750.679對照組6139(63.93)/40(65.57)15(24.59)/14(22.95)7(11.48)/7(11.48)0.0470.977

表3 兩組頭顱側位X片測定結果比較
2.3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基因型分布比較: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位點基因型分布及等位基因頻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Myosin1H基因rs3825393位點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頻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攜帶AG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頻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Myosin1H基因rs11611277 rs3825393位點基因型分布比較n(%)
2.4觀察組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不同基因分布患者頭顱側位X片測定結果比較:觀察組rs11611277位點不同基因型分布患者SNA角、SNB角、ANB角、FH-MP角、SP-SN角及Z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攜帶rs3825393位點AG基因型患者SNB角、Z角低于攜帶GG型與AA型患者(P<0.05),ANB角高于攜帶GG型、AA型患者(P<0.05),見表5。

表5 觀察組rs11611277 rs3825393位點不同基因分布患者頭顱側位X片測定結果比較度)
2.5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基因多態性與MR易感性關系: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法分析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基因多態性與MR易感性的關系,以MR易感性作為因變量(是否易感:是=1,否=0),以Myosin1H基因rs11611277、rs3825393位點基因多態性作為影響因素進行賦值,攜帶rs11611277位點CC型作為參照組,A等位基因作為參照組;攜帶rs3825393位點GG型及A等位基因作為參照組。結果顯示:Myosin1H基因rs11611277位點基因多態性與MR易感性無關;以GG型作為參照組,攜帶rs3825393位點AG基因型可增加MR易感性2.571倍,見表6。

表6 Myosin1H基因rs11611277 rs3825393位點基因多態性與MR易感性關系
3 討 論
MR由下頜發育不對稱引起,遺傳、外部環境因素均與MR發生有關,現已明確環境因素包括替牙障礙、不良習慣、鈣磷代謝障礙、肌平衡調節紊亂、中耳炎癥等,均對髁突、下頜骨發育產生不良影響;髁突或下頜骨外傷同樣也可引起下頜骨發育障礙[8]。近年來遺傳因素在MR中的作用日益引起研究者重視。據報道,Ⅱ類錯合畸形患者子代、親代頜骨結構相似度較高[9]。姜玲玲等[10]發現安氏Ⅱ類錯合畸形發病存在家族聚集特點,1級親屬遺傳率超過90%。之后多項研究均指出,安氏Ⅱ類錯合畸形存在帶典型基因遺傳特征[11,12]。
胚胎發育早期形成附著于上頜骨咬肌、舌骨上肌群所控制的張閉口運動直接影響下頜骨發育。動物研究顯示,咬肌力減弱大鼠下頜骨較咬肌強大鼠下頜骨更短[13]。肌球蛋白重鏈異構作為細胞骨架內關鍵分子,是為肌肉收縮提供動力的主要蛋白,咬肌肌球蛋白重鏈異構體變異對下頜平面角有較大的影響。前期已證實Myo1c基因可通過參與細胞內葡萄糖轉運等過程影響咬肌代謝、肌纖維分型,導致錯合畸形進展[14]。而Myosin1H基因為參與肌球蛋白功能調控的候選基因,屬Myo1c為旁系同源體,推測可能與MR發生存在一定的關聯。國外Arun等[15]研究者首次報道,Myosin1H單核苷酸多態性與下頜骨退變有關。本研究發現,安氏Ⅱ類錯合畸形患者Myosin1H rs3825393位點基因型分布與Ⅰ類錯合畸形有明顯區別,而rs11611277位點基因型分布與Ⅰ類錯合畸形類似,支撐上述報道結果,說明Myosin1H基因rs3825393位點單核苷酸多態性與MR發生有關,攜帶rs3825383位點AG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患者MR易感性更高,此類人群Myosin1H基因rs3825393位點G→A突變率較高,會增加MR發病風險,說明蒙古族人群Myosin1H基因rs3825393位點基因突變可能會導致MR發生。展開邏輯回歸分析發現,攜帶rs3825393位點AG型患者MR易感風險為攜帶其他基因型的2.571倍,進一步說明rs3825393位點G→A突變可能增加MR易感風險。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尚未對其他種族人群進行對比,存在一定的局限,對MR易感人群特征基因型特征有待進一步擴充樣本量進行總結。此外,本研究還發現,觀察組SNB角、Z角小于對照組,ANB角大于對照組,攜帶rs3825383位點AG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患者SNB角、Z角更小,ANB角更大,進一步證實rs3825383位點基因突變與MR發生有關,可引起下頜骨結構改變,造成咬合異常。
綜上,本研究首次發現內蒙古地區蒙古族Myosin1H基因rs3825393位點G→A突變與MR易感性有關,攜帶該位點AG基因型患者有更高的MR患病風險。說明內蒙古地區蒙古族攜帶Myosin1H基因s3825393位點AG基因型人群有更高的MR患病風險,而rs11611277位點基因多態性則與MR發病風險無明顯關聯,說明同一基因型不同位點基因多態性對MR發病的影響存在復雜多樣性,為MR病機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可為早期識別MR易感高危群體及MR個性化預防提供指導,后續可作為MR早期診斷、預防及個性化治療的方向。但由于研究樣本量較少,尚不能代表整個蒙古族人群特點,需要擴大樣本量進一步研究Myosin1H基因與蒙古族MR易感性、下頜骨退變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