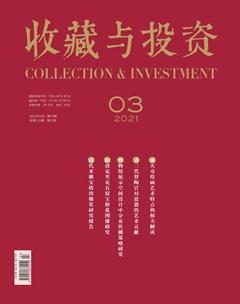博物館展示空間設計中分眾傳播策略研究
陳東陽 黃燦

摘要:博物館作為新時代公共文化非正式教育服務機構,履行教育與服務公眾的社會職能。本文結合分眾傳播的理論觀點,細分博物館參展群體的差異化需求,梳理展示空間形式的演變過程,得出博物館展示空間分眾策略建議,從而提高博物館文化信息傳播效能,更好地實現博物館教育公眾、服務公眾的社會職能。
關鍵詞:分眾傳播;博物館;展示空間設計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受到公眾關注,從而對博物館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近期國家從政策層面多次突出強調了博物館對傳播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作為傳播優秀歷史文化與知識交流共享的重要場所,除了滿足公眾對展品的參觀需求之外,還需適應公眾對日常的文化消費需求。當前,發展博物館事業上升為國家文化戰略,博物館的發展必將再次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自博物館免費開放以來,每年數以億計不同年齡、不同知識層次的參觀者走進博物館。根據國家文物局數據,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已備案博物館已達到5 535家,免費開放博物館的數量為4 929家,舉辦陳列類展覽28 630場,社會教育活動334 610次,2019年接待受眾數量近12.27億人次[1]。依據分眾傳播理論,可以為觀眾提供多樣化的展覽,滿足觀眾的差異化需求,從而更好地向公眾傳播文化信息,進而提高公眾的觀展效果。
一、博物館分眾傳播相關概念
“分眾傳播”是基于傳播學視角,傳播者根據受眾的特點量身定制,提供專屬的信息傳播[2]。許多學者和專家對此展開深入的討論研究,嚴建強[3]認為展示設計應重視人與物的安全,考慮觀眾的感受,進行分眾教育的探索。黃洋[4]則從觀眾的角度提出了博物館展覽因觀眾各異,當下博物館的傳播應該從“廣播”再到“窄播”,即針對不同觀眾的特點進行分眾傳播。劉文濤[5]從分眾傳播的角度思考博物館展覽,把博物館作為一個信息傳播的主體,根據觀眾的差異性和不同需求,為觀眾提供多樣化的展覽,滿足觀眾差異化的需求。
博物館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提供給觀眾分眾化服務,觀眾可根據興趣、動機作出選擇,從而獲得優質的參觀體驗和學習需求,這是博物館與觀眾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搭建溝通橋梁的關鍵一步。真實地了解公眾的參觀需求,以追求“最佳的文化傳播效率”為目標,達到受眾與展品的深層次溝通。
二、博物館展示空間形式的演變
觀眾日益豐富的差異化需求以及參觀形式的改變,使得博物館展示空間形式順應時代需求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從傳統的圖文展板、實物展出,到以觸摸、互動為主的多功能展示體驗空間,都體現著博物館與時俱進、貼近公眾、融入社會的轉變。
(一)單一的展示空間
最早的博物館其功能是收藏、保存,屬于私人的收藏場所,后期才逐漸向公眾開放展出。因此,這一時期,博物館展示空間形式相對單一,僅作為陳列展品的輔助空間,或者烘托展品的背景空間。觀眾參觀行為停留在觀看層面,缺少互動性、參與性,“展品-觀眾-展示空間”三者之間很難形成有機統一的互動整體。博物館也多以信息展示空間為主,站在“教育者”的角度,以自身的權威學術研究向公眾單方面地傳輸文化信息,公眾處在一個較為被動的學習過程當中,自然也就很難滿足公眾的差異化需求。
(二)多功能的空間
當觀眾參展行為不再停留于簡單的觀看,而開始向多元化、差異化發展,博物館展示空間形式也開始從單一的輔助展示空間向多功能的空間過渡。博物館也開始注重觀眾研究,結合觀眾參觀偏好,將展示空間由單一化向多元化不斷地延伸,一些基于觀眾真實觀展行為的博物館空間也相繼出現,如臨時餐飲空間、文創銷售空間、臨時休閑空間、互動交流空間等。博物館作為文化消費的公共場所,雖然在國有體制下尚無經濟方面需要盈利的壓力,但從整個國家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看,實現事業單位的企業化、市場化運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因此,優化博物館的運營管理,研究公眾的“真實需求”便是擺在博物館經營管理者面前的迫切問題,即便只是從發揮公共事業單位服務公眾的職能角度看,對公眾“真實需求”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多功能空間的拓展
博物館的免費開放,吸引了更加多樣的參觀群體,其中包括親子、校園組織的考察團體、情侶以及同事朋友等,這使得博物館公眾參觀行為模式變得更加復雜。參觀形式不同,對展示空間的要求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博物館做到因人而異,尋找更人性化的解決方案。如父母帶著孩子參觀,設計師應在展示空間里設置一些親子互動裝置,倘若孩子單獨操作、要提供父母照看和臨時休息的空間。博物館只有照顧到觀眾參觀的真實需求,才會讓不同訴求的觀眾找到自己被關愛的點,以體現新時期博物館教育公眾、服務公眾的社會職能。
三、博物館展示分眾策略實施
博物館展示空間設計是用一種“空間編輯”的方式來講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其展示形式多樣,可以同時滿足不同的受眾群體。觀眾由不同形式的參觀群體組成,興趣、動機和習慣各不相同,設計師應借鑒博物館觀眾研究的成果設定“目標觀眾”,并以參觀者的受益程度作為指導設計的核心意見。在今天博物館已經由“如何教育觀眾”轉向“觀眾希望獲得什么,怎樣讓他們的學習更有效?”,這種從以教育為中心向以學習為中心、從施教者向傳播者的轉變,正是當前博物館社會角色轉變的一種趨勢。作為傳播者要了解觀眾類型,不同類型的觀眾進入博物館會帶著不同的愿望、動機和習慣。麥克亞瑟(Bernice McCarthy)將學習者分為想象的學習者、分析式學習者、常識性學習者、探索型學習者四個類型。想象的學習者關注“為什么”,參展時通過聆聽講解、視頻采訪來學習,并基于自身直接經驗來給予評價。分析式學習者關注“是什么”,傾向于了解抽象概念、詳細資料、專家想法,喜歡具體細節的長篇說明。常識性學者關注“它怎么動起來”,以實際經驗來整合信息。探索型學習者關注“如果……那么是什么”,希望通過實驗和錯誤來確定自己的發現,他們通常不會遵循展覽的順序,在閱讀之前就尋找可以互動的展項。因此,博物館展覽要充分研究觀眾,與觀眾保持較高的關聯度,由此使觀眾產生認同感。

博物館要針對目標觀眾,解決核心問題,獵豹用戶研究中心最新博物館觀眾調查研究表明:“滿足興趣愛好是公眾前往博物館的最根本目的,其次是為學習知識,年輕人將博物館變成新的社交場所。”[6]以上趨勢表明,年輕群體的知識層次普遍較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他們正成為參觀博物館的主力軍,參觀博物館也正逐漸成為年輕人新的社交活動。這也充分地說明了觀眾認知結構的差異是影響博物館文化信息傳播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公眾真實的參觀偏好,博物館才能不斷地調整展示策略,優化展示內容和傳播媒介,提高傳播效率。
(一)展線分眾
展線分眾,是基于參觀者真實參展需求設定不同的參觀路線并可供選擇,滿足不同類型觀眾的參觀需求。常見的形式有“田”字型、“A”字型、“V”字型、“H”字型等[7]。展線的設定遵循簡單便捷、方向明確、連續暢通、布置靈活的原則。對時間計劃、興趣動機不同的觀眾安排不同的參觀動線,使他們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選擇。與此同時,大部分博物館會在展廳入口免費提供一份導覽手冊,手冊上面詳盡地標注了展廳與展項的位置關系,觀眾可根據興趣偏好決定參觀路線。上海自然博物館將展線設計成兩套方案,即簡單路線與復雜路線,如果觀眾行程匆忙或對展覽毫無興趣,則可以選擇簡單路線快速了解博物館。反之,則選擇復雜線路進行參觀。日本大阪歷史博物館也采用了相同的做法,通過設置不同的參觀路線,為前來參展的觀眾提供差異化的需求。
(二)裝置分眾
裝置分眾是面向不同學習程度、不同知識結構的觀眾量身定制的。參觀群體中僅有少部分是專家型觀眾,他們知識儲備豐富,不需要借助任何輔助展示信息就可以讀懂文物,但對于絕大多數參觀者而言,直接讀懂文物的信息是個不小的挑戰。獵豹用戶研究中心的觀眾調研結果發現,大部分觀眾參觀過程中最不滿意的部分集中在展品信息上,他們認為許多展品的介紹信息過少[8]。對于這一現狀,究其原因是觀眾觀展的行為是不斷移動的過程,晦澀難懂的文字介紹很難引起普通觀眾的注意力,更不會激發其學習興趣。因此大部分博物館展示形式主要以實物展出輔以少量圖文介紹。也就是說在博物館的角度來看,簡化信息的目的是方便知識的高效傳播,而在觀眾角度,這些簡化的文字反而造成了理解的困難。要解決這一矛盾,需要博物館在簡化信息的同時,做到形象生動便于理解。喬治·E·海因(George E·Hein)與瑪麗·亞力山大(Mary Alexander)在《博物館:學習的地方》(Museum:Places of Learning)中指出,有文字說明牌與根本沒有文字說明牌相比,前者更能對觀眾注意力產生巨大影響。他們援引了B·皮爾特(B·Peart)1984年的調查結論:給動物展增添了文字說明和聲音后,觀眾的參觀時間和所得到的知識量均增加了一倍[9]。在這一問題上,故宮博物院搭上數字化快車,擁抱新技術、擁抱互聯網,成為文物創新領域的“弄潮兒”,相繼推出《皇帝的一天》《胤禛美人圖》《每日故宮》《故宮展覽》等App,建立“數字博物館”,借助新媒體向公眾傳播傳統文化。
(三)年齡分眾
年齡分眾,是為不同年齡段的觀眾同時提供不同的使用系統或操作平臺,分別提供給成年觀眾和青少年觀眾。成年觀眾的操作界面比較正式,青少年觀眾所使用的界面則采用較淺顯的文字與活潑的形式。故宮博物院為青少年量身定制、成立“故宮博物院青少網站”,設置了許多卡通形象,迎合青少年兒童的參展需求,疫情期間又推出《我要去故宮》免費公益視頻課,用寓教于樂的形式將優秀文化資源分享給年輕受眾,不斷推陳出新向青少年普及傳統文化知識。
四、結語
博物館利用“分眾傳播”的觀念,深入研究不同觀眾的認知層次和差異化需求,設計策劃出滿足不同年齡、不同知識層次觀眾的個性化展示空間和教育項目,才能更好地履行博物館的教育職能。這一做法既適應世界博物館發展潮流,也順應當前我國博物館的發展態勢。“分眾傳播”的目的是讓更多不同訴求的公眾走進博物館,高效率地尋找適合自己的展項,實現分眾教育的目標,從而體現新時期博物館教育公眾、服務公眾的社會職能。
作者簡介
陳東陽,1994年生,男,漢族,江蘇宿遷人,南京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環境設計及其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展示設計。
黃燦,1996年生,女,漢族,江蘇揚州人,南京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工業設計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展示設計。
參考文獻
[1]博物館觀眾調研報告:10億流量擁抱科技升級[EB/OL].(2019-12-17)[2021-03-20]. http://wap.traveldaily.cn/article/133589.
[2]李劍欣,張小琳.受眾心理與媒體分眾化[J].新聞愛好者,2005(7):22.
[3]嚴建強.“十二五”期間我國博物館陳列展覽概述[J].中國博物館,2018.
[4]黃洋.博物館展覽“窄播”與“廣播”的雙向轉換—《博物館陳列展覽設計十講》推介[J].東南文化,2019(6):119-121.
[5]劉文濤.從分眾傳播的角度思考博物館展覽—以南京博物院的展覽實踐為例[J].中國博物館,2019(4):79-84.
[6] 同[1].
[7]劉媛媛.論博物館展覽的邏輯展示順序及展線布局原則[J].美術教育研究,2018(4):69.
[8]獵豹用戶研究中心.博物館觀眾調研報告10億流量擁抱科技升級[EB/OL].[2019-12-16].https://www.tmtpost.com/4213616.html.
[9]嚴建強.在博物館里學習:博物館觀眾認知特征及傳播策略初探[J].東南文化,2017(4):93-101,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