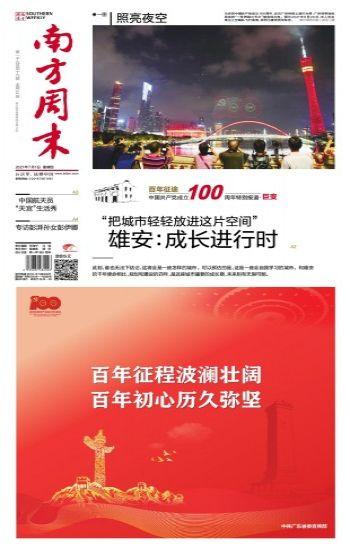留下 ﹃成語﹄最多的文章家
張煒
人性決定詩性,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致勃發。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的姿態。這種表達常常豪氣大發,宏巨開闊,呈現出無可抵擋的沖刷力,每每有酣暢淋漓之感。他的表達,因峻急而強烈,因強烈而觸目,因觸目而備受質疑。為了完成這種超常的表達,他必要尋找抵達極境的一些詞語,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無論是比喻還是描述,都要濃烈深切,絕不會淺淺劃過。從詩文中看,他始終是一個精力飽滿的、雄赳赳氣昂昂的形象,是一個手臂揮舞得意忘言的形象。他即便在沮喪之時,比如兩次被貶之期,寫出的為數不少的消沉牢騷之詩,也仍然充滿了力量。叫苦,痛恨,埋怨,抨擊和頌揚,全都加大臂力,悉數出擊。
他的五言長詩《苦寒》寫于803年長安任四門博士期間,記述了一次嚴重的季節反常現象,即三月大雪“倒春寒”。全詩銳思镵刻,才華飛揚,奇異獨特的豐富想象,極盡夸張的細膩描述,使凜冽的寒意浸透詩章,奇崛崚嶒的筆鋒閃爍著愛憎強光:“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氣寒鼻莫齅,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簽。侵爐不覺暖,熾炭屢已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纊與縑。”“中宵倚墻立,淫淚何漸漸?天乎哀無辜,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調和進梅鹽。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憸。”當他在貶所陽山喜聞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回京有望,在頒布赦書的隆隆鼓聲中,意氣風發,壯志滿懷:“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圣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聽一位琴師的高妙演奏,本來是賞藝的過程,但在韓愈筆下仍舊是擊節有聲,逼真生動之余是驚心動魄的大夸張:“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云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聽穎師彈琴》)這讓人想到杜甫力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同是這樣奇異無雙的想象和夸張,絕妙陡峭的比喻。就此看,韓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而不單是具有強勁的辯力和犀利的辭鋒,實在是一個大浪漫主義者。他的壯與闊并無審美之忌,更沒有中空之感,這中間盈滿的仍是真情實感,是充沛的人性內容。
綜觀古今,給后代留下“成語”最多的文章大家,大概非韓愈莫屬了。這絕非偶然,因為文辭的組合使用,在他那里絕不遷就含糊,而一定要找到力道最足者,一定要令人過目不忘。這樣的文辭在當時是響亮之詞,到了后世也讓人代代不舍,所以就變為“成語”,成為一個民族語言寶庫中的常備之械。像我們經常使用的“業精于勤”“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力挽狂瀾”“異曲同工”“兼收并蓄”“動輒得咎”“坐井觀天”“寥若晨星”“弱肉強食”“虛張聲勢”“形單影只”“駕輕就熟”“邀功求賞”“面目可憎”“蠅營狗茍”“垂頭喪氣”“互通有無”“語焉不詳”“無理取鬧”“休養生息”“眾目睽睽”“不平則鳴”“雜亂無章”“文從字順”“秀外慧中”“飛黃騰達”“冥頑不靈”“口如懸河”“大聲疾呼”“渾然天成”“耳濡目染”“視若無睹”“搖尾乞憐”“軒然大波”“痛定思痛”等等,一時無法盡數。
我們有時候甚至這樣想:漢語言的表述離開了韓愈,將會顯出一個空洞,這空洞無可填補。原來語言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辭章連綴功夫,而且還深刻連接著生命的激情和力度。它的來源仍然是一個人對于客觀事物的擁抱和熱愛,是生命的深刻摩擦所產生的心靈波瀾。這波瀾的涌動和沖擊,會堆積起一處又一處絢爛逼人的語言雕塑。這里面絕少呻吟,而是呼號;即便是呻吟,也是痛徹肺腑。如果是欣悅,則有一場大歡唱,我們所說的激情和豪情,在他這里席卷而來。他對世俗生活、對日常狀態的感受,是那樣新鮮和敏銳,入木三分,同時又不乏誠實懇切。他的所有表達,因為這種生命特質而變得特別個人化、獨特化和新意化。一個真正的個體生命的展現是絕少重復的,就像世上沒有相同的兩片樹葉。這一片葉子的色澤脈絡極度清晰,即便是秋霜降臨落葉鋪地的時刻,它的色彩也是非同一般的絢爛。
就詩文的風格和質地而言,韓愈與我們所熟知的同代詩人,包括或前或后的文人墨客,是那樣不同,他逼到眼前的面龐是強烈、凌厲、率真、峻急。他是眾多生命中一個震耳欲聾的大聲,在一片喧嚷中特別響亮和突出,能夠穿過時間的霧靄,一直回蕩在我們的耳畔。他的鏗鏘之聲讓我們想到振聾發聵的孟子,想到了那句幾千年來的曠世大言,即“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感染力和分貝,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比戰國時代“稷下學派”那些日服千人的辯士,韓愈離我們更近,也更加鮮活,更加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