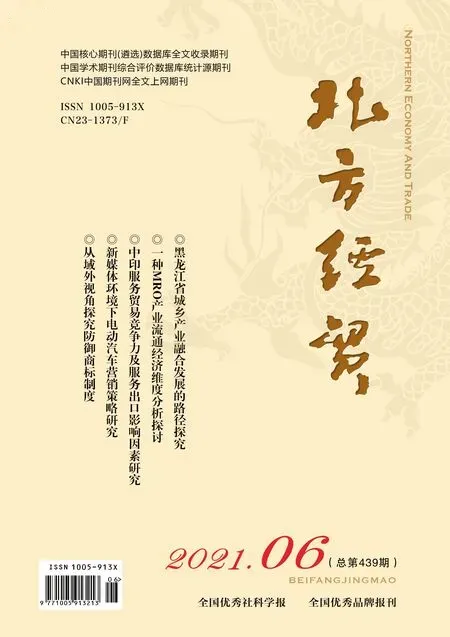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現狀及動力機制研究
劉曉萌,劉妮雅,胡葉星寒,丁利杰
(河北金融學院,河北 保定 071051)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國土整治戰略,首批試點就包括了京津冀地區,戰略要求京津冀地區聯合環渤海地區實施區域合作,共同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落實產業和人口布局優化,提升區域發展的協調性。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已經進行了近四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然面臨很多問題和困境,尤其對比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合作成果,還有明顯的差距。因此,現分析了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及其實現路徑。
一、存在的問題
(一)產業空間布局失衡
京津冀區域內“雙核”格局突出,極化效應明顯,北京和天津已經發展成兩個超大城市,而河北在眾多中小城市發展卻很落后。如表1 所示,北京、天津、河北省三地1997-2017 年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北京的國內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外商投資總額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比例均上升,而河北省這三個經濟指標所占比例卻在減少,尤其是吸引外商投資方面,北京市由1997 年的45.6%增長到2017 年的58.1%,遠超過河北省。2017 年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到69%,河北省所占比重只有31.1%。這說明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經濟水平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

表1 1997—2017 年京津冀城市群經濟指標演化表
(二)產業結構失衡
京津冀三地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也存在顯著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三地產業間的協同合作。從表2 可以看出,2007—2019 年北京市三次產業產值呈現明顯的“三二一”結構,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占絕對優勢,并且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第二產業穩定增長,第一產業從2015 年開始下降,第三產業對北京的經濟發展起到支撐作用。2019 年北京市三次產業0.3:16.2:83.5,是比較穩定和健康的產業結構。天津三次產業總體也呈現穩定上升趨勢,2015 年第三產業產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由“二三一”轉型為“三二一 ”,2019 年 三 次 產 業 結 構 為 10.0:38.7:51.3。2007-2019 年間,河北三次產業呈現穩定增長趨勢,2018 年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但第二產業的主導地位依然保持不變,2019 年三次產業結構為10.3:39.7:50.0。從三地的產業數據可以看出,河北天津兩地第二產業的經濟支撐作用仍然很突出,第三產業發展地區間差異最為明顯,2019 年北京、天津、河北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分別為83.5%、63.5%、51.5%,河北第三產業比重雖然有所上升,但仍落后于京津兩市。

表2 京津冀三地三次產業增加值(單位:億元)
二、失衡的原因
(一)區域性協調機制不足
在市場機制之下,各區域之間是以各自的經濟效益為主,彼此之間更多的是競爭關系,通常會產生惡性競爭,如地方保護主義等。這使得區域之間難以形成合作。要想改變這種情況,必須要有政府的合理干預,各個區域的政府需要展開合作,針對京津冀區域目前所存在的現狀,制定合理的政策。當前京津冀區域之所以難以形成合作,與地方政府有關,由于各個區域政府都以本地區發展為中心,形成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從而也導致了區域的市場分割。另外,京津冀區域很難協同發展和建立一體化市場,主要原因是政府沒有能夠發揮正確的職能作用,沒有去破除地方經濟壁壘和區域行政條塊窘境。
(二)要素配置不合理
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取得決定性的作用,但資本要素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一個地區的發展,首先是要具有雄厚的經濟資本,京津冀三地的資本要素指標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北京作為首都,擁有著最雄厚的資本,而且其公共預算收入和支出、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都具有很大的優勢,所以這三個區域之間,不僅資本的數量存在較大的差距,而且在資本的要素結構上也有非常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京津冀區域具有勞動力資源豐富和科研水平高的優勢。北京作為國內文化中心,總有眾多一流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等,這里的科技研發投入和研發實力非常雄厚。然而在整個區域發展中,科技要素資源分布呈現明顯的不平衡。主要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集中分布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卻遠遠不及,尤其是河北與京津差距很大。如表3 所示,河北省除了高科技產業投資額占比高達到61.1%以外,其他科技指標都處于明顯劣勢。

表3 2016 年京津冀人才及科技創新要素情況
(三)協同創新能力差
京津冀地區擁有著眾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聚集了國內最優秀和頂端的科技人才,以及最完善的科技體系,科研開發程度也是國內處于領先水平,但是京津冀三地之間卻存在較大的差距。主要的高端技術和科研人才集中在北京,而對比之下,天津和河北遠遠不及。三地之間的科技存在差距,尤其是河北省的科技投入是三個區域中最低的,所以其科技創新能力也是最低的。河北仍處于工業發展階段,采取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比較粗放的,整個經濟發展是以增長速度作為目標,而不是追求高質量和高效益。
(四)公共服務不均等
地區的公共服務能力主要取決于該地區的政府財政收入,京津冀三地之間在經濟實力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導致三者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差距。京津冀三地之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北京、天津作為京津冀最重要兩個核心城市,公共服務資源也是向北京和天津傾斜,其對外吸引資金的能力也更強,從而形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導致三者之間的公共服務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作為首都北京,擁有著國內最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和最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以教育資源來說,北京集聚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高等學府、研究機構以及頂尖專家匯集于此。從養老服務來看,2015 年京津冀三地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標準比例為5:3:1,北京的養老標準是河北的五倍。
三、動力機制
京津冀區域合作從最初的提議到實施已經過去近四十年,但取得的成果并不令人滿意,主要原因是京津冀城市群目前還沒有構建成一個自組織系統。首先,要想達到高質量的協同發展,需要政府建立共同的價值和目標導向,這一外部驅動力來自于中央政府的規劃和引導,其次,要想建立長遠合作與協調發展的自組織城市群系統,就要平衡各方利益主體的關系,包括各地區政府之間,還包括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之間等各種利益關系,要注重了解各方主體的利益訴求,協同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釋放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找到“1+1>2”的共同發展內在動力機制。最后,要想構成京津冀城市群高質量協同發展,各方主體要立足實際,建立優勢互補和協同發展的聯動機制。

圖1 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利益共享機制
由于京津冀一直以來是三個獨立的區域,各個區域的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都是本區域所形成的經濟利益壁壘,而三者之間的關系,長久以來更多的是競爭而非合作。要想建立一個協同發展的區域,首先是要打破三者之間的經濟區域壁壘,發揮京津冀區域合作的積極作用,從而去疏導北京作為非首都的功能。北京的一些產業轉移在轉移到河北和天津的同時,也要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各地方政府將稅收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指標,財政收入也是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員的重要指標之一,地區政府都以本地區經濟利益作為重點,稅收的爭奪是地方政府利益矛盾的重要體現。因此,在京津冀合作中,要做到合理分配三個區域之間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可以通過稅收再次分配來達到三者之間的利益共享。這也需要政府破除原有的地方保護主義思維,建立京津冀區域稅收共享機制,對轉移產業的稅收也要進行合理分配,這樣才能夠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
(二)成本分擔機制
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要讓成本和收益關系對等,讓付出的成本得到相應的補償。建立一個協同發展的區域,要使得區域的產業達到協同,以及建立一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因此,需要注重在整個產業中所產生的成本以及收入之間的分配,要合理地去分配三個地區對應的成本承擔比例,以及對應的紅利獲得比例,特別是在建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之中。通過三地政府之間的協商,來共同制定一個分配的協議,而且要根據在這個協議中所獲得的利益高低,分配相應的責任,受益度越高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建設好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三)跨區域協調機制
京津冀區域之所以難以形成合作,是因為行政邊界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內在聯系,阻礙了各種資源和要素在區域之間自由流通,也導致了區域的市場分割,這直接導致了京津冀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這就背離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同發展的趨勢。因此,中央層面要加強政策和制度供給,與地方政府一起建立協調機制。一方面,要從上到下建立縱向的協調機制。中央通過去建立一個跨區域的協調機制,來為京津冀產業發展布局做一個整體的規劃,在制定規劃、預算和產業布局時,將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中央政府要協調地方經濟之間的利益關系,解決區域內的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間也要構建聯系機制,形成常態化的溝通機制,對于各地區的產業發展規劃與思路、要素的跨區域流動、跨區域重大項目的建設等問題進行及時溝通。各地方政府職能部門要保證上層決策的實施與落地,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環境。同時,各社會組織也要積極構建信息共享平臺,為跨區域的企業合作服務,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四)產業匹配機制
產業轉移是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當前京津冀產業轉移中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因此要建立產業雙邊匹配機制。三地要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定位,建立一種新型產業分工與產業轉移機制,引導產業有序轉移,加強雙邊信息溝通,改變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產業結構性失衡,消除影響產業轉移的機制障礙。三地要建立產業信息發布和產業匹配的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北京可以發布向外轉移產業的具體信息,如企業規模、遷移選址要求等。同時,還需要提升天津、河北的承接能力,即對于產業配套承接能力、教育和醫療保障水平等,從而確保產業的合理有序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