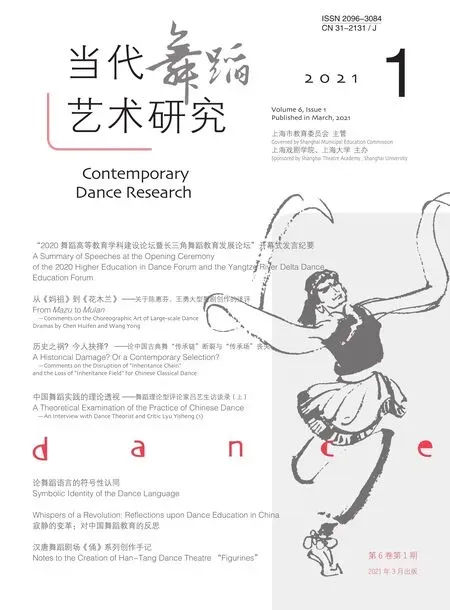歷史之禍?今人抉擇?
——論中國古典舞“傳承鏈”斷裂與“傳承場”喪失
劉青弋
引 言
中國古典舞作為中華民族舞蹈的歷史經典,至今尚未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是否表明中國古典舞的遺產尚未實現真正的挖掘和 保護?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有著令世人矚目的樂舞文化,然而,時間走到20世紀,人們驀然發現,中國竟然沒有古典舞!當代舞蹈家為了能讓中國古典舞與被稱為“藝術桂冠上的明珠”的歐洲古典芭蕾相媲美,懷著對民族文化建設的熱愛和責任感以及再造歷史輝煌的夢想,開始了中國古典舞的“重建”工程。60多年來,幾代舞蹈家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以民族傳統文化為基,追隨著時代的發展,將中華民族的舞蹈發揚光大,其成果以濃郁的民族風韻顯現了中華民族的身體美學追求,并通過其建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訓練體系培養出優秀舞者,展示了中華民族舞蹈高超的身體表現力和藝術魅力。“以古典舞的名義”建設的“中國古典舞”作為一個獨立的舞種,屹立在中國當代舞壇,成為當代中華民族舞蹈文化的一張亮麗的名片。但是,業界公認:這一“以古典舞名義”“重建”的“中國古典舞”不是歷史遺產的“本身”,而是由當代人經過研究和想象創造的“替身”(對于這類“古典舞”及“重建”本文均以引號表示,以區別對中國古典舞“本身”的重建)。而且,帶引號的“中國古典舞”在世界舞蹈文化交流領域,因“張冠李戴”“指鹿為馬”而陷入尷尬的局面,以至于有的中國學者提出,在國際交流中使用“中國古典舞”的概念時,不用與英文同義的譯文“Chinese Classical Dance”,而要用半英文半中文拼音的“Chinese Gudian Wu”,中國的“民間舞”亦不用英文同義的譯文“Chinese Folk Dance”,而要用半英文半中文拼音“Chinese Minzu Wu”了。如此做法,不僅讓人一頭霧水,也讓中國舞蹈的文化格局顯得混亂,自然也就阻斷了中華民族舞蹈文化與世界其他民族舞蹈文化平行對話的可能。
顯然,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國古典舞歷史“傳承鏈”的斷裂。一般認為,“都是歷史惹的禍”,當然,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獨立的中國古代舞蹈的經典“原本”失傳,遺留給中國舞蹈建設者們的只有歷史的碎片,或者融匯在古典戲曲中的舞蹈。如此,中國古典舞“重建”尋找“本身”的追求是否就此“歇菜”?按照約定俗成的說法:“木已成舟”,既然“本身”已逝,“替身”做了60多年,再更名,世人都不知道它是誰了。是否應該將錯就錯?是否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就是“沒事找事”?若讓“替身”更名,是否就是“多此一舉”或“勞而無益”?如果文化的“似是而非”堂而皇之地“以似為是”“以假亂真”,文化“替身”上位為文化“本身”,如此一來,“本身”是否從此將在歷史上被徹底抹去?于是,捫心自問:如果“我的祖宗”對“我”來說是一個傳說,“我”用想象創造一個“替身”取代他們,放棄“尋根問祖”,那么,“我”是否還能真正認識“我的祖宗”?……意識到這一邏輯上的荒謬,于是,筆者對中國古典舞當代“重建”的起點進行察看,發現一個問題呼之欲出:中國古典舞歷史“傳承鏈”的斷裂完全是因“歷史之禍”,還是也因“今人抉擇”?另一個問題接踵而來:中國古典舞“本身”在當代是否還有“傳承場”?這一問,不由得更讓人心慌:如果“傳承場”已喪失,中國古典舞“本身”將無復生之地。這是因“歷史之禍”,抑或也有“今人抉擇”?
“傳承鏈”斷裂:歷史之禍?今人抉擇?
人們常以西方古典芭蕾作為界說古典舞的標準參照系,因此,有人認為,中國的古代舞蹈沒有發展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對此,筆者并不認同。雖然中國古代舞蹈發展史上未經歷過歐洲近代文化史上類似的文藝復興運動,給予舞蹈以人文主義思想的浸染和改造;未經歷過歐洲啟蒙運動那般的思想解放運動;未出現一位諾維爾式的人物,銳意革新,賦予舞蹈現實主義精神與靈魂;沒有發展成現代舞臺表演藝術……但并不能因此否認中國古代豐富多彩的舞蹈文化,否則中國古典舞重建的話題就無從說起。這種重建不是進行“從無到有”或“無中生有”的建設,而是將“已有今失”或“曾有今無”的歷史進行復原和復興。因為,中國古典舞是國家和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不是“當代人創造的產物”!一般認為,中國古典舞“重建”的困境和尷尬處境“都是歷史惹的禍”!的確,中國復雜的歷史進程,走著走著,就將高度發展的古代舞蹈藝術遺產弄丟了—沒有像歐洲古典芭蕾舞那樣,給后人留下高度程式化的訓練體系、創作體系以及像《天鵝湖》《吉賽爾》《睡美人》那樣傳承至今的古典舞代表作體系。因此說,中國古典舞的“傳承鏈”發生了歷史的斷裂。然則,要說這種斷裂“都是歷史惹的禍”,又似乎并不完全準確。因為,當筆者將中國與世界不同國家古典舞蹈形成、發展或復興的歷史進行比較研究時,就看到了“今人抉擇”的決定性力量。例如,亞洲的古典舞發展歷程與歐洲古典舞的發展軌跡有著驚人的相似。但是,為什么歐洲形成了統一的古典舞蹈傳統,亞洲古典舞各自為營,而東北亞和東南亞古典舞的源頭—中國古典舞則遺憾地缺位了呢?
歐洲古典芭蕾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經過法國浪漫芭蕾的發展逐漸走向成熟,再至俄國對古典芭蕾進行創新并達到藝術的高峰。俄國芭蕾的高峰則由法國和俄國編導家共同建設而成。例如法國偉大的浪漫芭蕾編導家朱爾·佩羅和偉大的古典芭蕾編導家馬里烏斯·彼季帕都在俄國出任過芭蕾大師,為古典芭蕾在俄國達到藝術高峰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朱爾·佩羅為俄國排練了《吉賽爾》等一系列代表性的浪漫主義芭蕾作品。馬里烏斯·彼季帕則為俄國創作了幾十部新芭蕾,重編了芭蕾十余部。其中,他與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合作完成的《天鵝湖》《睡美人》《胡桃夾子》被史學家稱為歐洲古典芭蕾的代表作。即便大家熟知的“揮鞭轉”32個圈這一旋轉的核心技術,亦是由于意大利著名的女演員擔任《天鵝湖》主演而得以創造的。意大利、法國、俄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均不以國界劃分彼此排拒,而是以文化開放的心態,將意大利、法國、俄國的古典芭蕾作為自己共同的古典舞傳統。
中國的樂舞藝術在唐代發展到高峰,并與歷史上的西域少數民族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樂舞交流頻繁,其宮廷樂舞曾覆蓋了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同時,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古典舞多發源于中國,例如隋唐時期中國宮廷樂舞傳到日本,宋時傳至朝鮮半島,明時傳到越南、老撾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千百年來將“唐樂舞”進行傳承、發揚光大,或在其基礎上創作了本土的宮廷樂舞,形成了本國的古典樂舞體系,這與歐洲古典芭蕾的形成,在歷史上有著驚人的相似。
但是,中國古典舞“重建”工程的主體,既沒有傳承上述東北亞和東南亞古典舞形成過程中以隋唐時期為代表的海納百川和文化包容,亦沒有借鑒歐洲國家古典舞建設過程中的互融和開放,因而未能將中國視為亞洲古典舞蹈的源頭國之一,將亞洲古典舞視為一個整體,將亞洲國家傳承的“唐樂舞”視為自己的傳統。從而,中國古典舞在“傳承鏈”于本土歷史斷裂之后,未能借助在亞洲保存的“唐樂舞”的“傳承鏈”將自己斷裂的傳統鏈連接起來。
之所以說中國古典舞的“傳承鏈”斷裂并非“都是歷史惹的禍”,還因為,亞洲不少國家的古典舞和中國古典舞一樣,經歷過傳統的斷裂。在歷史上,這些國家大多也遭受了殖民侵略或戰爭的破壞。但是,在當代它們都將曾經斷裂的“傳承鏈”連接了起來。
日本古典舞蹈的“傳承鏈”在歷史上經歷過多次斷裂。但是,一次次地在宮廷的支持下,在古典舞蹈家用生命堅守傳承的不懈努力下,不僅將從中國傳入的“唐樂舞”、從朝鮮半島傳入的“高麗樂舞”中規中矩地傳承下來,同時創建了本土的古典樂舞“國風”,三樂整體而形成獨具特色的日本雅樂體系。如今,雅樂作為日本古典樂舞的核心,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朝鮮半島的古典舞蹈在現代也曾遭遇過歷史的斷裂。1910年,《日韓合并條約》使韓國變相地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王朝滅亡。當地人民進行了30多年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斗爭,朝鮮半島的古典舞蹈的“傳承鏈”一度中斷。戰后,韓國政府和傳統藝術工作者十分重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在古典舞的“重建”方面,通過對宮廷最后一個舞童金千興的保護,并通過一系列的文化遺產保護措施,對韓國的宮廷舞蹈(呈才)和祭禮樂舞(雅樂)進行了復原和傳承。因此,目前韓國的古典舞蹈即由復原和傳承的“唐樂呈才”(從中國傳入的宮廷舞蹈)和“鄉樂呈才”(受到中國宮廷舞蹈的影響,在歷史上由韓國本土創作的宮廷舞蹈),以及“祭禮樂”(從中國傳入后本土化的“宗廟祭禮樂舞”和“祭孔樂舞”等)組成。其中,“宗廟祭禮樂”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而祭孔佾舞亦被認定為“韓國文化財”的遺產。目前韓國繼續將“五禮”文明作為傳統的核心,將受到中國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宮廷儀式及其樂舞不斷地進行復原。這些古典舞蹈繼續在韓國的政治、外交、宗教、經濟、文化等領域發揮重要的作用。
越南宮廷舞蹈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古代的宮廷樂舞中有對“林邑樂”的記載。雅樂作為“五禮”文明的代表,在我國明代傳入越南宮廷,至越南阮朝(1802—1945)時發展成熟,每年大約在100種典禮場合舉行隆重表演。越南與中國一樣,曾是遭受殖民侵略的國家:1885年,淪為法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日本取代法國對其進行殖民統治。1945年越南的“八月革命”,迫使傀儡皇帝保大退位,法越戰爭開始,順化宮廷雅樂隨著君主制度瓦解而衰微。“20世紀80年代,宮廷音樂開始受到文化部和地方政府的關注。90年代,順化宮廷雅樂邁進復興階段,得以保護和逐步恢復,其標志是順化傳統藝術團和順化宮廷傳統劇院的成立”①。在日本與韓國學者、樂舞藝術家的幫助下,越南的雅樂復原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越南的雅樂于2003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曾通過西域流傳于長安,進入中國宮廷,后經長安傳入日本的舞蹈《撥頭》,在日本作為“林邑樂”,被認為和越南傳統舞蹈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聯系在日本雅樂傳承家三田德明對越南占族傳統舞蹈的考察中得到證明。
除了上述歷史上漢字文化圈國家的古典舞形成和復興是如此,歷史上同唐代樂舞交流十分密切的印度古典舞復興史亦是如此。在唐代宮廷“十部伎”中就有《天竺伎》。《樂書》和《通典》中都有“婆羅門樂”和“婆羅門舞”的記載。②印度和中國一樣,亦是遭受過帝國主義殖民的國家,直到1947年才從英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顯然,印度古典舞重建和中國面臨的歷史境況大同小異。但是,印度在當代對古典舞重建和復興所選擇的道路和方向與中國不同。目前,在印度被官方認同的古典舞蹈從源頭上來說都是來自歷史悠久的傳統舞蹈,其內容多是歷史傳說或宗教故事,所傳承至后世的古典舞蹈,既有完整的動作語匯和技術訓練系統,又有完整的舞蹈代表作示人。③而在20世紀初,受到俄國芭蕾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和美國現代舞蹈家露斯·圣·丹尼斯的藝術啟發,復興了卡塔克舞的梅納卡夫人及其追隨者卻沒有出現在印度官方關于卡塔克舞歷史的記載中—盡管梅納卡夫人在宮廷解體后,最先將卡塔克舞從被認為比較低俗的舞娘舞蹈中解救出來,復興了卡塔克舞,并運用卡塔克舞的語言,借鑒芭蕾舞劇的創作技法,創作了一系列印度傳統舞蹈題材的舞劇作品,還建立了專門的舞蹈學校,培養了大批的舞蹈人才,讓印度的古典舞蹈受到世界的關注。[1](將中印古典舞復興歷史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梅納卡夫人對印度古典舞卡塔克復興的路線和貢獻與“以古典舞名義”復興的“中國古典舞”的路線和貢獻有些相似)但是,印度官方未將其列入正宗的印度古典舞,而是將起源于宮廷的卡塔克舞一脈認定為正宗的印度古典舞,說明印度古典舞的復興,傳統舞蹈藝術已變成一種能夠代表印度舞蹈歷史和文化的嚴肅的舞蹈藝術。
由上可見,世界各國的古典舞無一例外地以歷史上的遺產代表作為“本身”,而將當代民族文化建構中具有卓越貢獻的現當代創作或創新舞蹈排除在了古典舞之外。然而,中國古典舞的復興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同樣“傳承鏈”斷裂歷史遭遇的亞洲諸國,在相近的條件下進行古典舞“本身”的復興,最終都將斷裂的歷史“傳承鏈”銜接了起來。但是,中國因為走了不同的道路,實際的結果卻失于對古典舞“本身”的歷史“傳承鏈”的銜接。這一結果,是否值得我們深思?
“傳承場”喪失:歷史之禍?今人抉擇?
中國古典舞“本身”的復興在當下的無果,還在于中國古典舞的“傳承場”的喪失。“都是歷史惹的禍”,抑或“今人抉擇”?
縱觀世界各國的古典舞蹈藝術,源頭大多來自古代宮廷,中國古典舞的源頭亦不例外。由于宮廷舞蹈文化在傳統文化中具有十分獨特的地位,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文化的大傳統和正宗。宮廷舞蹈文化的倡導者雖是少數上層階級,卻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壟斷者、宗法觀念的締造者、禮儀制度的建構者、舞蹈文化價值和審美取向的決策者。雖然作為上層的宮廷舞蹈文化與中層的市民舞蹈文化、下層的農民舞蹈文化之間在知識結構與審美趣味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是,作為上層文化的宮廷舞蹈,在集權制度下集聚了眾多的優秀人才,占有諸多的優質資源,并以得天獨厚的條件,打造舞蹈文化的精品,集中種種傳統舞蹈文化的精粹和要素,因而,在眾多文化形態中占據統攝地位,對其他舞蹈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能夠讓舞蹈文化形成“一統之傳”“傳之正宗”的,往往是高度集權的宮廷。雖說宮廷舞蹈的概念不等同于古典舞蹈的概念。但是,從世界各國古典舞的發展來看,其濫觴基本都可從宮廷舞蹈文化中找到蹤跡。
例如,形成歐洲古典芭蕾歷史的,無論是“席間芭蕾”“浪漫芭蕾”還是“古典芭蕾”,都和宮廷芭蕾脫不了關系。目前,無論是否還保存宮廷實體,歐洲國家對古典舞的認知,都認定為歷史上(從古代宮廷)傳承至今的經典舞蹈—這一限定在當代芭蕾舞的國際大賽中明確可見—比賽分為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表演古典芭蕾(也即歐洲的古典舞)的變奏,這些變奏多為歷史上芭蕾大師的作品。如法國編導大師簡·科拉利和朱爾·佩羅于1841年創作的《吉賽爾》、俄國編導大師列夫·伊萬諾夫和馬里烏斯·彼季帕于1876創作的《天鵝湖》……另一個環節是表演當代芭蕾(即當代舞蹈),為當代編導家創作的作品。盡管歐洲諸多國家的宮廷已經消亡,但是來自宮廷的古典芭蕾的“傳承場”,從宮廷舞臺成功地轉向現代教育場所與劇場舞臺。專科芭蕾舞校、藝術院校中的芭蕾舞系,培訓公司中的芭蕾教學,都像是傳承人培養的機構,幾百年來造就的古典芭蕾的程式和技術、大師的經典劇目,亦像是不言而喻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一代一代的舞者遵循嚴格的古典規范和要求,以生命的投入打磨塑造黃金分割般完美的身體和高雅的氣質,將其代表作完好地傳承著。隨著現代教師的教學水平、舞者的表演水平、編導的編排水平以及舞臺設計師的設計水平不斷提升,這些古典芭蕾散發著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進而,古典芭蕾的“傳承場”遍布世界各地,為現代芭蕾藝術的繼續登頂奠定了傳統基礎。
當代亞洲不少國家古典舞的“傳承場”沒有缺失。無論是從未間斷的“傳之正宗”之舞,還是在“傳承鏈”斷裂后的復興之舞,內容和形式都是“過去式”的“傳之正宗”,創作者都是“古代人”,其中不乏宮廷的帝王、御用樂官、文人雅士、宮廷貴族豢養的專業樂手和舞人,或是寺廟中的宗教領袖、僧侶、舞伎。
例如,韓國的古典舞即等同于歷史上的宮廷舞蹈,雖然當下宮廷已亡,但其古典舞一直保持著從中國傳承的古制:由宮廷宴樂和雅樂構成,以“呈才”“祭禮樂舞”謂之,共同作為韓國古典舞蹈的內容和形式。所謂“呈才”,即為“宮廷舞蹈”。其中“唐樂呈才”是從中國傳到朝鮮半島的宮廷舞蹈,以及根據中國的古制在朝鮮王朝不同時期編排的宮廷舞蹈;“鄉樂呈才”則為受中國的宮廷舞蹈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新編的韓國本土宮廷舞蹈。所謂“祭禮樂舞”,即為在古代傳承中國“五禮樂”的古制、經過本土化的改編、在涉及“五禮”儀式的不同的場所進行演奏的祭祀和禮儀樂舞。在現代,則是通過建立韓國國立國樂院,完善傳承人培養和等級認定制度,將其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其中,一方面作為古代雅樂的“祭禮樂舞”依存于世代傳衍的宗廟祭祀和廟學祭祀的“傳承場”;另一方面將“五禮樂”作為歷史的回聲和人文景觀,依存于古代建筑的旅游景點的“傳承場”。而作為古代燕樂的“呈才”則將“傳承場”由宮廷成功地轉換到旅游景點和當代劇場,原汁原味地向人們展演著這些古典宮廷樂舞。國立國樂院則像一座國家歷史樂舞活態博物館,公益性地定期向市民開放,成為韓國古典樂舞傳承、展演和研究中心。
再如,在隋唐時期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唐樂舞”(又稱左方舞)、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高麗樂舞”(又稱右方舞),以及在中國宮廷宴樂和散樂影響下創作的日本“國風樂舞”,形成了完整的日本古典舞體系。由于宮廷尚在,寺廟香火仍旺,其古典舞的“傳承場”順理成章地繼續存活于宮廷、寺廟的祭祀、儀式、娛樂活動等場所。進入現代社會的變化是:宮廷雅樂職部,除了服務于宮廷的各種需要之外,還面向社會舉行公演。由宮廷皇家欽定的樂家,除了家族世代嫡傳,還通過私傳培養學生,從而,以星火燎原之勢推動了遍地開花的雅樂社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場”,日本雅樂亦由宮廷、寺廟擴展到當代劇場、大學、中學、小學、社會各類培訓機構以及群眾會社團體。而進入祭祀活動,不僅用于祭神、祭祖,亦祭當代在災難中逝去的親人,從而讓傳統活在了當下。
印度當代,也有舞蹈家在古典舞歷史斷裂之時,立足于傳統舞蹈基礎之上,取得了新古典舞實踐極其卓越的成果,但是,官方卻未將其列入古典舞蹈范圍。再以卡塔克舞的復興為例。卡塔克舞原是莫臥兒帝國(1526—1857)時期的宮廷舞蹈。據孫慧佳在《遺產 傳承 發展 規范—印度古典舞遺產卡塔克的保護與發展之啟示》中考察所示,兩千多年來,卡塔克舞經歷了宗教舞蹈、宮廷舞蹈、宮廷衰落后的舞娘舞蹈、現代舞臺的表演舞蹈的歷程。印度獨立之后,1953年成立國家文化部,官方通過舉行舞蹈賽事等制定標準,通過認同的卡塔克學院對卡塔克風格進行統一。官方對其認定及規范標準的制定,都遵循著傳統文化的古制。將起源于宮廷的卡塔克舞蹈一脈作為正宗④,維護大師傳統和男性傳統,認同傳統,亦包括封建秩序。在傳承過程中,大師們固守著傳統,不允許做出任何改變。[1]
中國擁有悠久的社會歷史和宮廷文化,因而也聚集了諸多優秀的樂官和舞人,培育了不同時代的舞蹈精品。它們是中國古典舞(也是中國古代典雅舞蹈文化)形成的主要源頭。遺憾的是:宮廷的滅亡直接導致了“傳承場”的喪失。同樣遺憾的是:“中國古典舞”在20世紀的“重建”和世界各國的做法不同,對宮廷樂舞代表作研究的忽視和排斥,導致“傳承場”未能夠被及時“重建”,或向當代劇場和教育場所轉換。這與中國近現代革命思潮和意識形態影響下的舞蹈家們對歷史的認知和抉擇緊密相關。
20世紀以來的中國革命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為主要目標。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社會變革。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科學、白話文;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是一場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之后,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是一場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因此,宮廷舞蹈文化作為封建社會的產物,被認為是為統治階級的宗法制度服務或為統治階級的聲色享樂服務的工具,必然成為近現代革命反對和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同志于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新民主主義論》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在文化上,實行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在其基礎上產生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領了中國現當代文藝建設的方向。及至1963年,中國文化藝術界倡導的“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文藝改革方針,都將封建王朝的宮廷藝術視為腐朽、沒落的舊文化的代名詞而排斥在外,同時將來自以下層人民為主體所創造的民間舞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無論是1942年的“新秧歌運動”、1949年的“秧歌進城”,還是20世紀50年代的“向民間學習熱潮”,都是這種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即便在“左”傾的反右派斗爭期間,中央院團的舞蹈家們下鄉采風,亦能將作為“封建余孽”的民間藝人從監管中解救出來從事教學。改革開放之后,民間舞蹈亦成為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用來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消解。而于20世紀80年代始,歷時20年,由中央政府文化機構逐級向各省、市、自治區下達任務完成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更是中國文化建設在堅守“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中將民間舞蹈作為民族主要傳統認同的直接反映。
在革命思潮和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宮廷文化一直是革命的對象,作為“傳承人”的中國古代宮廷的樂師或曾為宮廷服務的樂舞世家,隨著宮廷沒落,流落民間,在生命尚存的年月里更多的是躲避戰亂,或為了躲避革命,無人問津……在中國古典舞重建起步時,令人遺憾的是宮廷舞蹈基本未能進入當代舞蹈家的視野。由此,中國古典舞喪失了像韓國、印度、越南那樣,抓住中國古典舞“本身”復興最重要的機會,隨著宮廷作為“傳承場”消失,又未在當代劇場、學校和社會其他場所建立新的“傳承場”。令人欣慰的是幸存有一部祭孔的雅樂舞蹈,由吳曉邦先生帶領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于1957年在曲阜孔廟恢復過“傳承場”,并拍攝了電影,成為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例如北京、曲阜、建水、泉州、上海等地)恢復祭孔活動參考的范本。其中的佾舞曾在天馬舞蹈工作室的公演中被吳曉邦搬上舞臺,并在同期影響了曾在民國時期作為佾舞生參加過云南建水孔廟祭孔儀式的張述孔先生(2021年94歲),他復排了佾舞并參加了會演。吳曉邦帶領中國新舞蹈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對祭孔典禮及其樂舞的搶救,為2006年5月20日山東省曲阜市申報祭孔大典及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2011年5月23日浙江省衢州市申報的祭孔大典(南孔祭典)及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均奠定了重要的活態文本基礎。但是,由于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吳曉邦領軍的研究戛然而止,由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中國古典舞中的雅樂舞只保留了祭孔佾舞一支。不過,“中國古典舞”“重建”工程并未被認同。“文革”時期,“破四舊,立四新”,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的旗幟下,宮廷文化更是“革命”對象。即便在2000年之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掀起熱潮,進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基本上是民間舞蹈。
在21世紀初期,宮廷舞蹈進入了“中國古典舞” “重建”研究和實踐的視線。主要表現如下:其一,筆者2001年發表的《中國當代舞蹈創作類型分析》一文率先明確提出:“中國古典舞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產生于中國古代宮廷。它在人類社會階級分化,文明到達新的高度和階段,對來自民間的舞蹈藝術實現了‘雅化’之后,作為一種‘執政’的統治階層推崇的‘古典’舞蹈文化形態,而和‘在野’的‘民俗’舞蹈文化‘平分秋色’。并且因為只有舞蹈藝術的發展,職業舞人的出現,舞蹈藝術的技術技能達到一定的水準,使舞蹈的規范化、程式化以及藝術化實現,古典舞蹈的建立與形成才成為可能。在中國古代,除了宮廷舞人、文人雅士以及市井職業舞人,都在建立‘雅士文化’或在建立‘市井文化’之中,為中國古典舞的構建與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貢獻。此處,中國的戲曲藝術,作為中國古代表演藝術成熟的形式,亦將中國舞蹈真正在價值的層面提升到‘古典’的高度……因此,中國古典舞在古代應該和‘宮廷舞蹈’‘市井(都市)舞蹈’以及‘戲曲舞蹈’相關。”[2]這一在理論上對古典舞的概念進行的闡釋,成為筆者其后進入操作性實踐的理論準備。其二,2006年孫穎先生在其發表的論文中明確提出關于古典舞的概念問題。他認為:所謂古典舞“主要是指歷史上為貴族服務的宮廷舞蹈;被宗教利用成為一種祭祀形式的宗教舞蹈;或者曾經走上商業舞臺,是在專業化、職業化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古代舞蹈形式”[3]。應該說這種理念在此前已貫徹于他對中國古典舞“重建”的實踐。作為對中國古典舞“重建”的“治本”策略,他對“中國古典舞”的“重建”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基礎之上的,亦是在戲曲舞蹈之外另辟路徑的。其研究成果充分地顯現在其創建的獨具中華民族風格特色的舞蹈運動方式和訓練體系之中。然而,對于“中國古典舞的代表作”建設,仍然屬于“再造”,流于當代人作曲、作詞、編舞、表演的結果。其三,王克芬、江東借日本和韓國古典舞蹈家到中國“認祖歸宗”的愿望,于2007—2008年推動中、日、韓古典舞蹈的學術交流,從而拓展了北京舞蹈學院古典舞系的學科建設文化視野,但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其四,筆者于2007年開始,至今仍在較大規模上將中、日、韓古典舞的交流推向深入的努力,并明確提出在亞洲“非遺”舞蹈的“唐樂舞”中重建中國古典舞代表作的主張,并付之于操作性研究實踐,倡導并作為會長成立了“東亞傳統宮廷樂舞國際研究會”,多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傳統宮廷舞蹈的代表作展演,出版論文集,推動系統的教學活動等。此舉雖說在樂舞學界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中國古典舞”“重建”領域則未將日韓“唐樂舞”當作自己的遺產進行應有的研究。其五,由于現有保存完好的清代雅樂舞譜、樂譜、詞譜、鹵簿及儀式程序等史料,21世紀初,北京的幾大公園,開始復原部分清代的雅樂,例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以及北海公園等,期望通過旅游活動,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獲得文化上的雙贏,似乎大有將古典雅樂的“傳承鏈”和“傳承場”恢復之勢。由于這些活動并非由政府官方組織,大多來自公園管理部門的文化保護愿望,因而,雖然所恢復上演的“祭禮樂”大多在專家指導下進行,但是主要由群眾演員表演,因此難以展現泱泱大國的風范和文化經典的品質。而作為旅游文化的行為,使歷史上帝王作為為國祈佑的“天子”和民眾作為虔誠的“香客”身份分別演變成了“扮演”和“看客”的身份。因而,這一方面失去了雅樂的內核;另一方面,因為人力、財力方面的投入過大而入不敷出,所以較難堅持。由于近年“反恐”“防疫”等要求,這類儀式活動的表演隨著廟會的衰落而漸漸停擺……而相關“宗廟祭祀樂”,因為祭祀對象和歷代君王有關,因而無人問津。以至于北京故宮莊嚴肅穆的太廟,即便每年接待1 700多萬名游客,還是被韓國雅樂表演的舞者問過這樣一個讓筆者難堪的問題:“你們中國有太廟嗎?”這也是刺激筆者提出復現宮廷雅樂代表作的主張并付諸實踐的直接原因。不禁令人感慨:雄偉的故宮,向人們展示的只有靜態的、冰冷的歷史建筑,而在這座歷史建筑空間所發生的活態的、人文的歷史,以及禮樂儀式和舞蹈,則躺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銷聲匿跡了……
中國戲曲舞蹈被選擇作為中國古典舞“重建”的主要參照源頭,首先在于它的古典藝術的品質—戲曲經過800多年的推陳出新,保留下300多個劇種和數萬部劇目,呈現不衰的藝術魅力。同時,在當代舞蹈家口中常說的一個最實際的理由是:戲曲舞蹈作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古典藝術的活態遺存,滿足了中國古典舞“重建”所需要的品質和條件,以及在百廢待舉的國家文化建設的迫切要求下,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其實,更深層的原因也在于戲曲本身所具有的民主主義傾向和人民性,更接近“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文化建設的要求。自然,不能否認,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一代戲曲大師對戲曲的改革與創新,為古老的戲曲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以精湛的藝術讓中國傳統戲曲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使得戲曲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的藝術經典在當代占據了不可撼動的地位。但是,以戲曲為基礎,卻讓“以中國古典舞名義”“重建”的“中國古典舞”偏向一隅。為了符合人民性和舞蹈化的要求,“中國古典舞”“重建”的面貌,顯現出“武”氣重“文”氣弱、趨“俗”避“雅”的傾向;顯現出以漢族樂舞為中心的單一傾向,有失中國古典舞的歷史真實。其實,20世紀50年代以來,并非唯有戲曲舞蹈是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古典樂舞形態,而是因對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薄弱以及對歷史知識的缺乏,使得人們對其他“看得見,摸得著”的古典舞蹈“沒有看見”或“視而不見”。如此,便將歷史上進入宮廷已經達到表演藝術高度的今日中國少數民族的舞蹈(這些舞蹈在宮廷消失之后依然在民間流傳),以及進入中國宮廷的外國舞蹈(既包括外國舞蹈在中國本土化的作品,亦包括保留在外國的中國宮廷舞蹈)都排除在中國古典舞“重建”的視野之外。下面讓我們還以唐代的樂舞為例察看。
據《新唐書》(卷22)《禮樂 十二》載:中國“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4]。如果我們正視歷史事實,對于中國古代宮廷舞蹈歷史有深入的認識,那么,在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舞蹈中,除了流落在民間的中原漢民族的宮廷舞蹈之外,還包括歷史上進入宮廷的西域、北方、南方等今日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民族舞蹈,以及曾建立統一的中央王朝的蒙古族、滿族等的宮廷舞蹈。例如唐“十部伎”中的《龜茲伎》《疏勒伎》《高昌伎》分別為現新疆庫車地區、喀什地區、吐魯番市高昌區的樂舞。新疆地區的“十二木卡姆”中的舞蹈作為中國古典樂舞也當之無愧。除此之外,據說還有因體系不夠完整而未被編入十部樂的倭國樂(日本)、驃國樂(緬甸)、林邑樂(越南中部)、扶南樂(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南部、泰國東南部)等,這些外來樂都進入了宮廷。[5]《西域音樂隋唐詩歌》一文指出:坐立部伎諸部樂,除了《龍池樂》為漢族雅樂、《慶善樂》為西涼樂之外,其余均雜以龜茲樂聲。而唐代太常、教坊自制、改制了大曲和法曲,作為享宴娛樂之用。大曲許多本出自西域,如《柘枝》《蘇莫遮》《醉渾脫》。而自造的新曲,多被流行的胡樂浸染。法曲起自隋代,在隋代“其音清而近雅”。[6]可見中國古典舞復興,忽視古代西域也即今日中國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區的樂舞是多么遺憾。《西涼樂》為今中國甘肅西部、內蒙古西南部及新疆部分地區的樂舞。“至唐代,法曲摻雜了許多胡樂的成分。唐最有名的法曲為《霓裳羽衣曲》。此曲本是胡樂曲《婆羅門曲》。此曲傳自西涼,唐玄宗加以潤色,易了個漂亮的曲名,成了《霓裳羽衣曲》。”[6]再如,在北周、隋、唐宮廷的“四方樂”中,也有北方民族的樂舞,例如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和契丹(鮮卑和吐谷渾的后裔先后分化到錫伯族、藏族、土族等中;部落稽和契丹后裔為達斡爾族、云南的阿、莽、蔣氏“本人”)的樂舞,以及南方的南詔⑤(8世紀崛起于云南一帶的古代王國)的樂舞……這些進入過宮廷的今日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舞蹈,本應都是中國古典樂舞“重建”探尋的方向,遺憾的是,由于“中國古典舞”“重建”對宮廷舞蹈研究的局限和忽視,一般被當作了民間舞蹈,而未進入古典舞蹈研究視野,有違中國多民族文化一體的歷史真實。
同樣,如果我們熟知并正視歷史,那些進入中國宮廷的外國樂舞,或目前保留在外國的“唐樂舞”亦不會被輕易地忽視。顯然,唐代宮廷的立部伎和坐部伎[7]⑥中的樂舞,在中國已經失傳。但是,它們大多在日本雅樂中世世代代保存著,仍然可以“看得見,摸得著”。這種“視而不見”,還包括對“看得見,摸得著”的、保存在韓國宮廷舞蹈中的中國宋代宮廷樂舞,如《五羊仙》《獻仙桃》《拋球樂》《蓮花臺》《壽延長》等古典舞蹈。雖然歐陽予倩、葉寧、孫穎對此都有提及,但是,中國古典舞當代“重建”工程基本上未對其進行認真的“看”和“摸”。
另外,十部伎中的《天竺伎》為古印度等南亞樂舞;《高麗伎》為朝鮮半島的樂舞;《安國⑦伎》《康國伎》,還有健舞中著名的《胡騰舞》(源于中亞的石國的樂舞),分別為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撒馬爾罕、塔什干附近一帶的樂舞;扶南樂、驃國⑧樂則是東南亞一帶國家的樂舞。⑨這些進入中國的外國樂舞,其實已經成為中國宮廷舞蹈的組成部分,但是在中國古典舞的“重建”過程中也被忽略不計,未被列入研究對象,使得它們對中國古典舞發展的影響無法察看,從而無法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古典舞的歷史面貌。
上述情況的出現,究其原委,其一是由于中國當代舞蹈領域對中國舞蹈歷史的認識和研究的局限;其二是由于當時的文化建設需求迫使的急功近利;其三是由于極“左”思潮影響對宮廷舞蹈作為古典舞濫觴源頭的忽視和抵制。20世紀50—80年代,對于保留在外國的“唐樂舞”和進入中國宮廷的外國樂舞被輕易地忽視,更多的是因為國家開放的局限限制了舞蹈家的視野,對中國舞蹈歷史認知的局限阻礙了舞蹈家的思維,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歷史抉擇。而2000年之后,這些繼續的“視而不見”則因為中國的舞蹈家認為,傳到日本、韓國、越南的“唐樂舞”已經被傳承國的本土文化浸染,從而不認同其為中國的古典舞。當然,也不否認有人出于捍衛作為“約定俗成”的“以中國古典舞名義”重建的“中國古典舞”之歷史地位的功利性目的。
中國古典舞“重建”的半個多世紀,沒有將宮廷舞蹈中的代表作遺存(指歷史上傳衍后世的作品“原本”)作為主要源頭進行史論考證與操作性實踐相結合的專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典舞“重建”工程的重大缺憾!因此,中國古典舞“重建”中“今人抉擇”中的誤識,導致了中國古典舞“本身”的“傳承鏈”斷裂加深,“傳承場”的喪失擴大,進而讓我們錯過了找到中國古典舞“本身”的最佳時機和更多的可能性。
從目前世界各國的古典舞蹈形成和復興歷史來看,能夠代表一個國家古典舞的,無疑均為當代人對歷史遺產的繼承,而非當代人的創新或創造;而且均屬于由國家的行為進行文化認定、規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由此對照,中國目前“以古典舞名義”“由當代人創造的古典舞”,顯然無法歸入這一范圍。
回不去的歷史,別無選擇的抉擇!
大概是時候了!以“新古典舞”之名區別于中國古典舞原型,不再做“本身”的“替身”,而是還原自己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的身份,做回“自身”!因為,既然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此“古典舞”非彼古典舞,何不實事求是地正視:當代“中國古典舞”的“重建”,是在歷史遺存“抱殘守缺”的條件下,“以古典舞名義”“重建”的“中國古典舞”中大多是由當代人的研究和想象創新的產物?何不以“新古典”謂之,拋棄“替身”的角色,讓其作為獨立的主角站上歷史的舞臺,充分地展示其作為民族當代舞蹈文化建設創新者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筆者認為,這種貢獻并不亞于對中國古典舞成功復興和“重建”。因為,一方面,它積數十年的研究成果,通過將舞蹈從戲曲中獨立出來,或將無數的歷史碎片依據中華民族的身體美學和韻律進行連綴,或將歷史上失傳的舞蹈通過研究進行再造,都不僅為找尋中國古典舞的“本身”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且在中國古典舞缺位之際,對于補位中華民族的典雅舞蹈和演藝藝術,對于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舞蹈的傳統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既承接了中華民族身體文化的優良傳統,又汲取了現代舞風,追隨著時代的發展,通過打造充滿中華民族韻味和美學的身體,展現當代中國人充滿自信、瀟灑的精神風貌,建構中華民族傳統舞蹈溝通歷史、走向當代的橋梁。于此,“新古典舞”之稱將避免帶引號的“中國古典舞”作為“替身”與“本身”糾纏不清,模糊我們的視線,影響我們繼續對中國古典舞“本身”的探尋;避免讓中國古典舞“本身”陷入“名”“實”皆亡,讓“新古典舞”這一“替身”陷入“名”“實”不符。更重要的是,避免讓中國舞蹈文化的類型體系與建設格局處于混亂狀態,妨礙中國舞蹈文化格局建設健康發展。
格局在文化建設中可解釋為“局勢”和“態勢”,亦可以說是“結構”和“格式”,體現建設者的整體思路,并最終決定文化發展的結局。當代中國舞蹈建設格局中的這些亂象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認真分析就會發現,我們在認知的邏輯層面出現了問題,拋開對舞蹈認知在內涵與外延、母子系統概念系統缺少系統性和科學性不論,在根本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將作為“文化”的“舞蹈”這一整體概念與作為“藝術”的“舞蹈”這一局部概念混為一談,從而造成文化格局建設的某些關鍵部分缺失、方向迷失、思想混亂,從而影響了中國舞蹈文化建設的健康發展。同時,也犯有混淆概念的錯誤—將此概念當作彼概念即“張冠李戴”,從而在邏輯起點發生錯誤,導致文化建設方向不明,實現不了文化建設的目標。
中國當代舞蹈的格局建設一直未進入科學化的軌道,因為往往用“約定俗成”取代嚴密的邏輯建構。這種“約定俗成”充分地體現在各大舞蹈賽事的舞種分類和高等院校的學科建設及專業劃分之中,諸種爭議由此產生。例如:中國古典舞領域的“真”“偽”之爭;中國民族民間舞領域的原生態“是”“否”之爭;“芭蕾舞”領域的“中”“西”之爭;現代舞領域的“驕子”與“孽子”之爭;當代舞領域的“軍旅專屬”的“正”“誤”之爭;國標舞領域的“體”“藝”之爭……凡此種種,各執一端,莫衷一是。最終,統統將“約定俗成”作為擋箭牌,讓所有的質疑和反思之矢有去無回。關于中國古典舞的爭論亦是如此。
例如,“舞蹈”這一概念的廣義和狹義之分已經眾所周知,然而,在舞蹈的實際建設中人們卻忘記了這一點。因為,廣義的舞蹈是文化范疇,“文化”的釋義為:被認為是屬于社會歷史的現象和積淀物,作為人類生活習俗的長期結晶,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8]因而,廣義的舞蹈作為文化的概念與內容應該包括:宗教舞蹈、習俗舞蹈、禮儀舞蹈、教育舞蹈、演藝舞蹈、宣傳舞蹈、娛樂舞蹈、健身舞蹈、交際舞蹈以及其他舞蹈(見圖1)。其中,作為藝術的“演藝舞蹈”只是舞蹈文化的一部分。以審美為主要功能的舞蹈藝術,主要是以審美的方式進行傳情達意,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因而,作為文化的“舞蹈”和作為藝術的“舞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中國當代舞蹈文化建設的格局,正是由于用作為局部的“演藝舞蹈”概念取代了作為文化的整體的“舞蹈”概念,或者是將兩者混為一談,從而將具有多元形態、多種目標、多種功能、復雜結構的“舞蹈文化”曲解為一元形態、一個目標、一種功能、一種結構的“舞蹈藝術”,從而使得中國舞蹈建設格局發生嚴重偏斜,其格局中的不同類別的舞蹈的發展及其功能實現受到嚴重干擾和牽制。

圖1 廣義的舞蹈文化概念內涵與外延
再如,由于概念系統的混亂,混淆了不同舞蹈的文化建設目標和方向,而未能根據其目標、方向的需求建立起結構與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致使中國當代舞蹈格局呈現傳統與現代雙向缺失—既缺少文化傳統的厚度,亦缺少文化創新的銳氣。一個民族舞蹈健康的格局(見圖2)應該既具有深厚的傳統積累,又具有當代創新活力。當代中國舞蹈由于沒有認識到保護、繼承傳統與發展、突破傳統是兩個不同的方向,總是以“非此即彼”的思維將兩個方向扭到一個方向,從而彼此牽扯,形成“誰也走不了”的結果,在中間地帶“拔河”或原地打轉。

圖2 舞蹈文化格局中的傳統舞蹈與當代舞蹈建設的概念和兩極方向
又如,舞蹈領域對“當代演藝創作舞蹈”的實質認識不清,導致當代中國舞蹈建設格局偏頗。筆者曾在《中國舞蹈的分類之思》一文中將當代中國演藝創作舞蹈分為三大類型:“民間風格創作舞蹈”“古典風格創作舞蹈”“現代風格創作舞蹈”[9]⑩(見圖3),并在《再論中國舞蹈的分類問題》一文中,針對“古典舞蹈”概念明確地指出:

圖3 當代中國演藝創作舞蹈的分類
我們也應該明確地認識:當代高等舞蹈院系、演藝團體與演藝賽事中的創作舞蹈中也不再有“古典舞蹈”。因為使用這一概念有三大前提不能忽略。第一是歷史概念,即古代;第二是價值概念,即經典;第三是流傳至今的活態概念。這三大因素都使得這一舞蹈文化類型與高等舞蹈教育與演藝舞蹈賽事中創作的“古典風格舞蹈”具有本質的差異:前者為歷史文化形態,后者為當代文化形態;前者發生在過去或為過去進行時,后者發生在現在或為現在進行時;前者的創造者是古代人,后者的創造者是當代人;前者是“古典舞蹈”本身,后者是對“古典舞蹈”的詮釋與表現;前者是古人的審美價值取向,后者是當代人的審美價值取向;前者的名稱為后人的追認,后者的名稱是當代人的自詡。[10]⑩
筆者對當代創作舞蹈的類型,用“民間風格”“古典風格”“現代風格”謂之,即是要強調它們和原型的概念不同。它們在“約定俗成”的稱謂中與原型“本身”混淆,可其實質卻是“民間舞”的“變身”“古典舞”的“替身”“現代舞的”的“分身”。
隨著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完善和深化,中國傳統舞蹈的兩大系統“中國民間舞”和“中國古典舞”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應該確立。中國民間舞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代表作的認定,使其“本身”與“變身”(舞臺創作的民風舞)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逐漸清晰起來。中國古典舞至今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缺位,難道還不能引發我們的警醒和思考?如果繼續用“替身”取代古典舞的“本身”,我們的前途是什么?那么,中國古典舞還能找到自己的遺產嗎?又怎樣找回自己的遺產呢?基于上述分析,建立在多年的歷史考證與操作實踐緊密結合研究的基礎之上,并因已在某些個人力所能及的方面付諸實踐,充分認識到當代舞蹈家的任重道遠。筆者認為中國古典舞復興應該明確概念、確定主要方向和主要任務并找回歷史遺產的主要途徑如下。
其一,我們應明確認識中國古典舞是國家和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以國家的行為對其認定,并進行規范。對于失傳的舞蹈文化,不能以當代“再造”取而代之。因此,“中國古典舞為當代創造”論,應該終止。應以國家的行為大規模地組織開展復興工程,對中國古典舞的歷史文化體系、代表作體系、語言體系、美學體系、訓練體系等進行全面的研究復興。
其二,對于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戲曲舞蹈的訓練體系、表演體系和經典舞蹈代表作(如《夜奔》《三岔口》《挑滑車》《拾玉鐲》《下山》《游園驚夢》《思凡》《鐘馗嫁妹》《霸王別姬》《蜈蚣嶺》《水簾洞》等以舞為主或舞蹈性較強的片段)體系,作為中國古典舞“本身”的一支戲曲流派,進入中國古典舞的表演體系,不對其進行剝離或改造,而是在保護和傳承中加以全面的藝術提升,強化其作為舞蹈藝術經典的品質。
其三,對于現存較完整的古代舞譜,展開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幾十部雅樂舞譜,依據現有中外雅樂遺存,對儀式進行全面的研究和復現,重視挖掘并保護“五禮文明”中的中國古典舞蹈的遺產。通過儀式和展演,在歷史建筑、人文地理空間以及現代劇場空間,復建“傳承場”,接續“傳承鏈”。
其四,對于進入中國古代宮廷后流落民間且能夠代表中國舞蹈歷史高度的中原舞蹈以及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舞蹈的代表作,應作為古典舞蹈進行全面的調查、挖掘、整理、研究,從而恢復中國古典舞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面貌。在服務當代生活、教育、演藝等功能的場所中復建“傳承場”,連接起斷裂的歷史“傳承鏈”。
其五,對于保存在亞洲諸國的唐樂舞,尤其是對于活態保存在日本的20多部唐樂舞、保存在韓國的數部宋樂舞,應進行全面的調查、學習與研究,追溯其為歷史上中國古典舞代表作的本土面目。將其作為中國禮樂文明未喪失的海外“傳承場”與未斷裂的海外“傳承鏈”,為恢復本土斷裂的歷史“傳承鏈”和喪失的“傳承場”提供活態參照。同時,對于歷史上傳至中國的外國舞蹈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和考察,考索它們在中國古代舞蹈的地位、影響,變異程度以及與中國舞蹈的聯系。
其六,對于中國古代舞蹈的活態與靜態遺存中的經典舞姿、舞蹈動態、舞蹈技術、舞蹈技巧、訓練方法及其舞蹈術語進行全面的研究,這在“中國古典舞”“重建”工程中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績,需要進一步加強歷史和美學的系統研究,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要求進行歷史考證、挖掘、整理、規范、研究,確保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質。
其七,對以往“以古典舞名義”“重建”的成果,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甄別,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尺度和要求,將其中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要求的部分認定為中國古典舞的“本身”,并深化對其的研究,進一步去偽存真,強化其作為國家古典舞遺產的品質。對其當代創新部分,以“新古典舞”謂之,不列入中國古典舞范圍。對“以古典舞名義”創作的中國古典舞“替身”和“以民間舞名義”創作的中國民間舞“變身”,都使其做回“自身”,以中華民族當代舞蹈的主角身份,不懈地追求藝術的創新價值和精品價值,提供民族當代舞蹈的創新成果,努力創造時代經典—打造其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為其百年之后成為后人不斷回顧和追認的中國古典舞創造條件,奠定基礎。
總之,歷史,我們回不去了。中國古典舞的“傳承鏈”斷裂、“傳承場”喪失已經歷了千百年歷史,欲想完全連接、恢復,只不過是一個夢想。但是,為了讓中華民族舞蹈的現在和未來能夠擁有更堅實的基礎,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為找回中華民族的古典舞蹈遺產逆流而上!哪怕只有一絲希望,也如絕地求生,去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我們還有機會嗎?我們有:別無選擇的抉擇!
【注釋】
① 1947—1948年保大帝母親慈宮皇太后曾召集宮廷樂工,恢復順化宮廷雅樂。西貢偽總統吳庭艷曾資助“叁”古典樂舞團與宮廷古樂團,招待來訪的外國元首和外交使團演出宮廷音樂。后來“叁”古典樂舞團倒閉,宮廷音樂面臨失傳的危機。20世紀80年代,宮廷音樂開始受到文化部和地方政府的關注。90年代,順化宮廷雅樂邁進復興階段,得以保護和逐步恢復,其標志是順化傳統藝術團和順化宮廷傳統劇院的成立。參見:百度百科.越南雅樂保護條目[NO/OL].(2013—02—05)[2021—02—05].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A%E5%8D%97%E9%9B%85%E4%B9%90/10503265?fr=aladdin.
② 《通典》(卷146)《樂六》曰:“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極铦刀鋒,倒植于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于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參見:杜佑.通典[M].顏品忠,等,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5:1966.
③ 印度古典舞內容形式豐富,既有技巧高難的卡塔克舞(Kathak),亦有采用面具和啞劇手勢表演的婆羅多舞(Bharathanatyam);既有從民間舞蹈發展而來的優美的曼尼普利(Manipuri),還有卡塔卡利(Kathakali)這類用梵語,以表現《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史詩為主的古典舞劇。
④ 孫慧佳寫道:卡塔克大師山布胡·馬哈拉杰曾在一次采訪中回憶說,他六世前的曾祖受克里希納神的庇佑,受邀創作一段納瓦里的恩弟亞舞(一種以啞劇為主要內容的表情舞蹈)。三百年后,在艾斯瓦杰時期這個舞蹈傳遍了整個印度。后來,艾斯瓦杰的長子帕卡世杰舉家前往勒克瑙并進入阿薩夫—杜拉的宮廷成為宮廷舞者。他將這段納瓦里的恩弟亞舞帶入宮廷。正是在這段時期中,納瓦里的恩弟亞舞開始被人們稱為卡塔克。(Banerjee,Sumanta.The Parlor and the Streets: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lcutta[M].Calcutta:Seagull Books,1989;Jung,Anees.Tarnished Gilt and Twinkling Feet[N].The Times of India,1969—03—18.)這段宮廷舞蹈的經歷為卡塔克帶來了高超的技藝,為卡塔克成為代表性古典舞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參見:孫慧佳.遺產 傳承 發展 規范:印度古典舞遺產卡塔克的保護與發展之啟示[J].當代舞蹈藝術研究,2018(2):52—56.
⑤ 在南詔,以往的昆明蠻、云南蠻、哀牢蠻、西洱河蠻、僰、漢等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區域,在長期的經濟、政治、文化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
⑥ 《舊唐書》(卷29)《音樂 二》載:高祖登極之后,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后分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圣壽樂》《樂圣樂》……凡八部。坐部伎有《宴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壽樂》《龍池樂》《破陣樂》,凡六部。《宴樂》,張文收所造也。……分為四部:《景云樂》《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參見:劉昫.舊唐書:第4冊(卷28—37)[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59—1061.
⑦ 安國,即漢時安息國,一般指帕提亞帝國。是亞洲西部伊朗地區古典時期的奴隸制帝國。
⑧ 據《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驃國》記載:8世紀時,毗訖羅摩王朝統治驃國時十分強盛,有18個屬國、298個部落和9個城鎮。其疆域北抵今中國云南德宏和緬甸交界地區的南詔,東接今泰國、老撾、柬埔寨接壤一帶陸真臘,西接今印度東部阿薩姆邦等地的東天竺,南至海,據有整個伊洛瓦底江流域。
⑨ 扶南樂大致相當于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泰國東南部一帶的樂舞;而驃國樂,是7—9世紀緬甸驃人所建立的國家的樂舞。
⑩ 筆者還明確寫道:“自然,作為以表現生活為主旨而非以建構舞種為主旨的創作舞蹈,會使各舞種間存在一個寬廣的交叉地帶,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應是藝術發展的常規與常態,判別這些作品的種類歸屬主要在于對其‘核心屬性’的質與量方面的考察。當一個舞蹈作品遠離一種舞蹈類別的核心屬性,在量的積累上達到質變,它便不再屬于該舞蹈種類。當它什么都不是而無家可歸之時,恰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生長出現之際。”參見:劉青弋.中國舞蹈分類問題之思[M]//劉青弋文集:3 魂兮舞兮—舞評舞論集之二(2004—2012).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