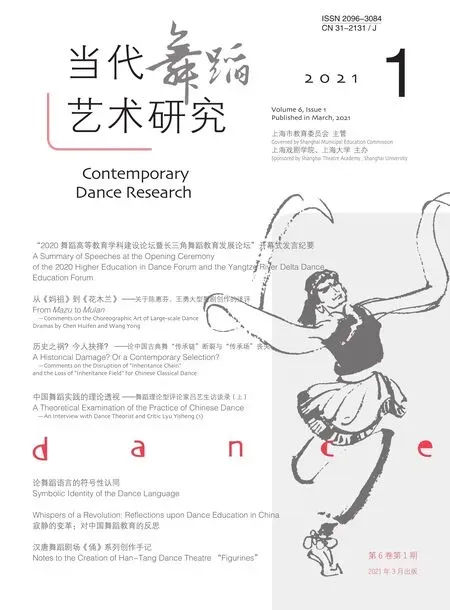尤金諾·芭芭的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及其對中國舞蹈表演教育的啟示
張占敏
一、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的定位與理念
國際劇場大師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①和羅馬大學(University Romatre)表演藝術系戲劇史教授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②共同撰寫了一本有關表演人類學的專著《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以下簡稱《辭典》)。作者把劇場作為研究空間,以劇場表演者為研究主體,通過對東西方表演藝術家的肢體研究,提出了26個劇場關鍵詞(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解剖學(Anatomy)、學徒 (Apprenticeship)、平衡(Balance)、擴張(Dilation)、演出創作(Dramaturgy)、能量(Energy)、等值(Equivalence)、歐亞劇場(Eurasian Theatre)、練習(Exercises)、臉和眼睛(Face and eyes)、腳(Feet)、手(Hands)、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蒙太奇(Montage)、鄉愁(Nostalgia)、刪除(Omission)、相反(Opposition)、有機性(Organicity)、前置表達(Preexpressivity)、行為重建(Restoration of behaviour)、節奏(Rhythm)、舞臺與服裝設計(Set and costume design)、技巧(Technique)、文本與舞臺(Text and stage)、訓練(Training)、觀點(Views)[1]2—3,構建出一套與表演密切相關的跨文化理論體系,探討了被表演者稱為舞臺生命力的共通原則,對演員的舞臺生命力表達和存在原則都提出了具體可行的方案。尤金諾·芭芭的表演理論和身體訓練融合了東西方戲劇和舞蹈的身體表達理念,《辭典》中對表演者的技巧原則探討聚焦于戲劇和舞蹈,因此劇場人類學又被稱為是“舞蹈者的戲劇”[2]622。
(一)研究定位
關于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的研究定位,尤金諾·芭芭在書中提出八個“不”和四個“而是”,強調其與一般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差異。
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不是要把文化人類學的架構應用在劇場和舞蹈上,不是研究人類學慣常研究的那些文化中的表演藝術,也不是關于表演的人類學,而是研究表演時的狀態;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不是為了解技巧本身,而是了解技巧的秘密;不是從科學角度去分析表演者的表演語言有哪些元素,也不討論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演員或好舞者,而是要了解決定舞者舞臺生命力的原則;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不是尋求普世的原理,不是要找出表演定律,而是研究劇場中人類行為之社會文化和生理肢體層面的意義。③
他進而解釋了使用“人類學”一詞的理由:人類學是對“常識”的反思與批判的實踐。他認為,“我們的文化常常喜歡把舞蹈和戲劇區分開來,這個傾向顯示了深沉的創傷和空白,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文化缺乏表演傳統的真空狀態,因此,演員會否定肢體,而舞者會窮盡絕技”[1]10。他不斷強調,劇場人類學專門研究專業表演時人的狀態和行為,以往對于表演者所遇到的問題的研究往往更關注觀演關系,即從臺下觀眾的視角看待臺上的表演,忽視了表演者個人和編導創作的過程,“因為忽視了創造性過程的邏輯,因為誤解了表演者經驗主義的思考方式,還因為無能力去克服為觀眾設立的限制,歷史上對于戲劇和表演的理解往往受到阻礙或流于淺薄”[3]12。
(二)研究理念
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的研究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是對劇場表演者的跨文化研究。尤金諾·芭芭對表演的探討是開放性的,不限國度、藝術門類,更不限各類職業群體。在跨文化、跨國和跨專業基礎上討論與表演相關的實踐與理論主題,參與討論的人員包括不同國家的西方學者和東方戲劇學者,各種傳統表演藝術家、專業舞者、導演與編舞家,還有評論家、人類學家、科學家等。
其次,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把人體動作分為日常動作和超日常動作,把演員和舞者統稱為“表演者”。演員的動作和日常動作較為接近,舞者的動作與日常動作大為不同,但是演員與舞者的表演均有普遍原則,如“用身體創作”[1]12。表演者的技巧是超日常身體技巧,其法則為:身體的平衡、身體動作的對立和身體在時空中的能量。④
最后,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以劇場表演者的身體經驗為研究內容,通過解剖學與肢體圖像分析,找出劇場中不同表演者的共通原則,建構適用于表演者的基本的心理和生理規則,使每個表演者都能夠學習,進而提升表演能力。
這本書被稱為《辭典》,內容更像一本理論與實踐兼顧的表演手冊,對中國舞蹈表演實踐與理論建設而言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的實踐路徑
(一)“解剖”表演者的身體
在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中,“解剖”的意義在于尋找演員與舞者共同的身體訓練方式,一方面克服演員和舞者之間假象的差異,另一方面尋找表演時基本的心理和生理規則。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托尼·亞陶(Antoine Artaud)認為,“劇場是我們了解人的身體解剖學的地方”[1]21,從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實踐路徑的關鍵詞看,尤金諾·芭芭分別從眼睛、臉、腳、手與脊椎等身體部位詳細“解剖”并說明每一部分在表演中的體現和功能。
眼睛是表演者的靈魂,身體動作配合雙目的表演是身心合一的外化表現,通過“看”而使動作變得有意義。尤金諾·芭芭通過例舉亞洲劇場和歐洲劇場不同的眼睛凝視方式,指出看的動作不只是用眼睛,而是用全身參與的行動,不同的注視方向可表達不同的情緒情感,可改變脊椎位置,具體的凝視可幫助觀眾建構空間感,呈現出舞臺人物關系。⑤關于臉部,表演者的表情由臉部完成,劇場人類學分析了三種“臉”[1]134—139:一是自然的臉,通過純粹的面部肌肉形成某種特定的面部表情;二是面具,讓臉部擁有超日常的、暫時的表情;三是臉部彩繪,如京劇化妝后形成各種臉譜,以及日本歌舞伎面部厚厚的白粉和鮮艷的紅唇。關于手部和腳部,這些部位通常是表演者的顯要呈現,從視覺上看,手部因動作幅度大、變化多樣并具有語言相似的功能,而形成了較為繁復的手姿動作。印度的手印被稱為最繁復的手語系統,具有兩種功能:一種是與語言一樣的價值,有確切的含義;另一種是純裝飾性動作。中國京劇有50多種手勢,主要用來分辨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巴厘島舞者經由手指、手掌和手腕的強弱、力量變化表達手的動力,手臂位置會隨著手部張力不斷改變,進而影響肢體和頭部,并強調“凝視”。日本程式化的手勢均表達某種精確的含義,西方舞者的手勢純粹表達動 力。[1]150—163在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看來,腳是具有文法的,腳的動作決定了身體在空間中的動力,造成各種不同的平衡或失衡動勢。“腳的移動方式是舞臺表演的基礎。手臂和手的動作只能加強身體已經被腳的動作決定了的既有感覺。有時,腳的位置甚至可以決定聲音的強弱和調性。演員沒有手和手臂仍能表演,但是沒有腳就很難表演了。”⑥服飾也會影響腳的表達,不同的鞋子對腳的動作具有裝飾或限制功能,光腳演出則體現出腳的自由。脊椎的位置及其連接的身體部位如脖子、背部、肩膀、肚子和臀部影響了上半身的延伸和在空中的移動,決定了肌肉的質感和動作品質。不同的劇場表演形式都可以用脊椎對肌肉的不同影響方式加以區別,如京劇演員脊椎往上延伸,日本能劇演員保持上半身脊椎微彎,骨盆往后;印度婆羅多舞者脊椎完全直立。因此,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把脊椎看作能量的舵,是肢體張力和抗衡力量的核心。[1]264
綜上所述,尤金諾·芭芭研究表演情境中表演者的身體,不僅關注肢體,還關注面部表情的細節呈現,解剖表演者的身體不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解剖”,更是從身體、情緒和意義三方面關注身心一致的表演 規則。
(二)探索表演者的動作
如前所述,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把人體動作分成兩類:一類是日常生活中的動作,比如走、坐、拿東西等自然的動作,這些動作均是在特定文化中習得與形成的;另一類是超日常動作,來源于日常并區別于日常,被看作打破日常動作原則的戲劇化動作類型。劇場表演藝術家不用遵守日常生活習慣的肢體規則,而是運用超日常技巧,呈現身體的特定表達方式。兩類動作在功能上具有明顯區別,日常生活動作的目標在于溝通,超日常動作是為了用舞蹈般的身體形態傳達信息。超日常動作存在于戲劇和舞蹈表演中。從日常動作轉變成超日常動作,是探索動作來源的基礎。通過對表演者肢體的研究,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提出了8種轉化原則⑦:
第一種,平衡。基于有意識的、控制的、轉化過的平衡,改變身體部位的位置、動作的方向、身體的距離,找到一種新的平衡。
第二種,對立。日常技巧和超日常技巧之間一直保持某種張力,表演者的身體用互相抗衡的張力對觀眾顯示其生命力。例如,京劇演員每個動作都要從相反的方向開始;巴厘島所有舞蹈形式都建立在強弱對比上。
第三種,省略。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身體控制與力量的抗衡,省略某些元素以便讓其他元素釋放出來,如古典芭蕾舞者將體重隱藏,每個動作看起來輕盈,不費吹灰之力。再如固定舞姿的空間移動,雖然在空間中停止,但感覺動作仍在進行,讓能量在時間中持續。
第四種,打破。從自然狀態抽離出來,打破日常生活身體的種種自然反應,達到想要達到的對立效果。例如日本劇場文化中,打破日常習慣動作是最常被提醒和執行的原則,舞蹈不能由外在因素如音樂或者日常動作來決定,因此舞俑要求舞者必須打破節奏,避免動作跟著音樂節拍走,還要控制呼吸,用相反的力和呼吸抗衡,重建超日常規則。
第六種,等值。即用身體動作表達等值張力,重建現實。比如印度奧迪西派舞蹈中的射箭動作,沒有實體的弓箭,但可以看到舞者動作中與射箭“等值”的張力,好像演員真的在對著某個方向,專心拉弓射箭,演員不是在演出一個射箭的人,而是重新創造人和弓箭之間的動作關聯。
第七種,能量。即演員的神經和肌肉的力量,西方稱為演員的存在感,中文語境中稱為“功夫”,日本強調“腰力”的作用。能量通常用來描述演員的舞臺表現力,動作質感具有身心合一的狀態,是身體的超日常技巧。
第八種,擴張。尤金諾·芭芭認為擴張的身體和擴張的心智就是身體和心智的戲劇性存在。有生命感的身體會擴張演員的存在感以及觀眾的觀感。擴張的身體通過三條路徑產生:“一、改變日常平衡,尋找不穩的、‘奢侈’的平衡;二、動態的抗衡;三、使用和諧的‘不一致性’。”[1]53擴張的心智具有三個特質:第一是劇情突變,相當于日常生活中的“跳躍性思維”,和慣性相反,形成無法預料的動作;第二是迷失方向,指違反常理的狀態和接踵而來的行動之間的關系,這會讓演員的身體產生驚喜,并因為自發行為感到驚訝;第三是精準,相當于擴張的身體,刪除多余的動作。[1]63—64
(三)解析表演者的表演技巧
從解剖學的視角看,演員、舞者的身體是由各個器官組成的,具有不同層次的組織,使用“器官獨立運作的原則”和“重組與蒙太奇原則”⑧,可以訓練身體并能夠控制身體完成表演。劇場的演出行為有各種不同的組織層次,表演者共同擁有的基本組織層次定義為“前置表達”。尤金諾·芭芭把“前置表達”看作表演技巧的根源。表演者的前置表達層作為一種實質性的訓練方法,用來強化演員和舞者的舞臺生命力。通過對比亞洲和歐洲不同時期的表演技巧,尤金諾·芭芭發現了主導前置表達的原則—自然技巧(Inculturation)和風格化技巧(Acculturation)[1]219。人類學把自然技巧稱為日常被動接受的、感官主導的行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訓練體系和布萊希特的“間離技巧”的訓練目標皆在使用自然技巧,使表演者將自然的日常行為轉化成超日常的戲劇行為,即表演真實的技巧。風格化技巧是各種舞蹈、默劇和亞洲傳統劇場的演員常用的一種技巧,這種技巧中的動作多被程式化,與日常生活中的肢體動作完全不同,形成超日常肢體動作。風格化技巧的演員通過改變日常生活動作,重建某種身體品質,隨時可以根據傳統體現出舞臺的存在感。
需要提及的是,尤金諾·芭芭認為不應過度強調兩種技巧在表達上的差異性。接受過古典芭蕾風格化技巧訓練的舞者,在劇場表演中需要借用自然技巧的模式,尋找解放自己的方法,訓練表演的真實性;而自然技巧也可以借用風格化技巧模式,改變日常行為,讓“會跳舞的劇場”活起來。自然技巧和風格化技巧都活化了前置表達:準備開始表演的存在感。[1]220
三、對中國舞蹈表演教育的啟示
縱觀中國舞蹈表演教育歷程,1954年北京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院的前身)建立初期,開設過“表演課”,教學內容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訓練方法,因時代所限,該體系的舞蹈表演訓練結果不盡如人意。[4]24—251978年,北京舞蹈學校升級成北京舞蹈學院,表演專業從專科教育轉向本科教育。2000年前后,全國藝術類高校開始增設“舞蹈表演”本科專業,培養舞蹈表演人才。隨著學科內部的精細化發展,舞蹈表演的每個專業方向為保持表演風格的純潔性,形成以舞種風格定人才的趨勢,舞種之間互不交叉,表演人才單一化成為目前舞蹈表演教育中的常見現象。此外,藝術高校中的舞蹈表演專業核心課程尚待完善,以基本功訓練、風格課訓練和劇目排練課為一體的舞蹈表演課程缺乏跨文化知識補給,實踐與理論有待深入融合。這些現象引起不少探討,2017年5月21日北京舞蹈學院在黑匣子劇場以“舞蹈表演學科建設”為主題開展了一次青年學者沙龍活動,探討主題從要不要成立表演學院切入,涉及諸多方面,這是對舞蹈表演專業舞種分化過細帶來的弊端所做的一次較為深入的、全面的思考。
不可否認,國內在舞蹈表演教育方面積累了一定經驗,但理論研究滯后。以《北京舞蹈學院學報》為例,以“舞蹈表演”為主題詞檢索,1987—2020年共有百余篇文章,主要內容為:(1)人物形象(角色)塑造;(2)情感;(3)舞臺表演經驗談;(4)人才培養;(5)表演課程與教學。以上內容多為個人表演與教學經驗心得,缺乏理論的深入研究。
政策六:6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被稱為“奶業振興”頂層設計方案的《關于推進奶業振興 保障乳品質量安全的意見》。
反觀中國表演藝術教育相關專業的發展,戲劇(曲)有三大表演體系⑨,音樂界的音樂表演理論研究已發展40年⑩[5],無論是戲劇還是音樂,對表演問題多傾向于“綜合研究”,跨文化研究也是要點。從舞蹈表演專業的學科定位?來看,教育部明確提出,要整合各舞種,打通舞種教學資源,解決表演人才的單一化問題,使中國舞蹈表演教育從專業單一型向綜合型轉變,適應社會和時代多學科融合的需求。舞蹈表演專業建設面臨的諸多問題缺乏現成方案。尤金諾·芭芭的劇場人類學對表演者技巧原則的探討和對表演理論研究的思路值得借鑒,或可為我們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一)融入跨文化研究理念,適應人才培養的多面向與時代需求
2018年,教育部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明確提出舞蹈表演作為“音樂與舞蹈學”門類的“舞蹈類專業”之一,其人才培養“由學科專業單一型向多學科融合型轉變”的要求。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提出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任務,以中國政法實務大講堂、中國新聞傳播大講堂、中國經濟大講堂、中國藝術大講堂“四大關鍵突破”,培養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應用型復合型文科人才。?在此背景下,高校舞蹈表演教育應該重視學生的綜合表演能力,打破之前以某一舞種為中心的表演教育,實際上,這些表演訓練更傾向于風格而非基于復雜的角色塑造和人性張力塑造。劇場人類學認為動作由身體完成,了解舞者的動作,應該從舞者的身體出發。劇場人類學“經由舞臺生命力(Scenic bios)的研究,分析演員的身體就是在做解剖”[1]22。身體是一個整體,解構身體,探討身體部位與表演的關系,實現身心合一。這不僅是解剖學的思考,在動作的分類中,劇場人類學強調的對生活動作的關注,以及對動作“特定文化中習得與形成”的分析,是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實踐。融入劇場人類學表演理論的跨文化研究理念,可促進舞蹈表演教育的理念革新,從教育部提出的培養目標而言,也是為培養文舞兼具、專業素質過強的舞蹈復合型表演人才在跨學科、跨專業方面的知識補給。就表演的本質而言,在今天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劇場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不可能再堅守單一的鏡框式舞臺和傳統劇場類型,觀演關系也在發生改變,尤金諾·芭芭對于“超日常動作”的探索和分析,更適合于今天多種藝術并存的時代變革。
(二)聚焦表演者的身體研究,回歸舞蹈表演的本體地位
中國舞蹈教育家房進激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關于舞蹈的表演教育問題”。他認為:我們現有的舞蹈教育缺乏表演性創造教育,遠沒有形成體系化、系統化和周密的組織性,更沒有達到高級的科學性。民間舞、身韻課如何與舞臺劇目有更深入的聯系?如何克服“技術至上”導致的炫技現象?如何打破專業壁壘?如何將單純的劇目排練和表演理論、實踐經驗相結合?[6]28這些問題都關涉舞蹈表演重要的載體—身體。“舞蹈教學中解決身體的運用能力及表現能力是最基本的任務。舞蹈訓練的理想境界也是要全身心投入,達到‘身心合一’。”[7]52但是,由于“身體訓練”的本位思想,表演教學的誤區表現為教師對動作的強調,如強調動作位置、運動軌跡、動作要領等方面。但對于身體能力和表演能力差異,想要突破,不只是掌握舞種風格限定內的身體動作技巧和較為雷同的情感表達、人物形象塑造等,還需關注如何從學生轉化成一名優秀的舞蹈演員,如何使表演具有舞臺表現力。一方面“舞蹈表演表現力是演員整體的能力體現,舞蹈表現力在舞蹈表演體系建設中不可或缺。”[8]8另一方面,內在情感在舞蹈表演中一直占有首要地位,但劇場人類學更強調“身體”的前置表達。聚焦表演者的身體研究,借鑒前置表達層在訓練過程忽視心情、情感與角色,從而凸顯動作的意義和動機的方法,可以讓中國舞蹈表演教學與研究回歸到舞蹈本體之上,將焦點轉移到思考如何用身體表現舞臺存在感方面。
(三)整合當前表演理論體系,拓展舞蹈表演理論研究視野
劇場人類學從不同的表演藝術和表演理論體系中尋找表演法則。這一理論還指出,在教學過程中,應不帶任何偏見地教授各類表演技巧。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inislavsky)的表演體系注重演員的創作規則,目標是創造讓演員擁有舞臺生命力的方法?;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生理機能學”?訓練舞蹈的行為模式,也訓練感官隱喻;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提出戲劇表演的“間離技巧”;鈴木忠志(Tadashi Suzuki)的劇場訓練體系強調下盤的訓練;梅蘭芳的表演訓練體系提出角色的認同;理查德·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提出對表演者的跨文化訓練[1]279—280等,上述表演訓練體系與理念在《辭典》中多次論及,提升舞蹈舞臺實踐表演能力的教學目標不應忽視對這些訓練體系與訓練方法的研究與整合。
四、結 語
劇場人類學對于舞蹈表演理論的貢獻,主要在于首先,它指出了表演者(演員和舞者)的工作包含著三個不同層次的組織:第一,一個獨特生命的特質由表演者的個性、敏感度、藝術程度和社會角色構成,表演因人而異;第二,社會傳統和社會歷史背景是形塑獨特生命特質的基礎,這是從事表演藝術的表演者共同的特質;第三,表演者的生物層次,即根據非日常生活肢體的技巧運用。前兩項決定了第三項如何轉化成表達的共同原則,劇場人類學稱之為“前置表達”。這些原則存在于不同的個人、藝術和文化之中,創造出不同的表演技巧。其次,從表演情境中的身體出發,區分了日常動作與舞蹈動作的差別,進而提出了解與表演有關的動作是了解表演者舞臺生命力原則的前提。最后,提出了表演者身體創作的表演原則。
長期以來,中國舞蹈表演教育以課堂教學為主體,以舞臺表演為目標,如何打通劇場與表演教學的深度融合,實現舞蹈表演實踐與理論的有機銜接,構建跨學科、跨文化的復合型人才為導向的培養機制,是舞蹈表演教育中亟須正視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劇場人類學的理念與主張中找到建構的方法或路徑。當然,在借鑒劇場人類學表演理念的同時,也需關注中國舞蹈表演教育的適用性問題,尋找可資借鑒的方法,而非全部照搬。
【注釋】
① 尤金諾·芭芭,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村莊,1954年在軍校畢業后移民挪威。做過焊工、水手,1956年在挪威的奧斯陸大學首次接觸戲劇文學。1961年跟隨格洛托夫斯基(Grotowski)學習導演,1964年在丹麥的奧斯陸創立奧丁劇場(Odin Teatret),在與劇場的演員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開始研究戲劇表演。1966年遷到丹麥的赫斯特堡,成立丹麥戲劇實驗場(Nordisk Teaterlaboratorium)。1979年,他在丹麥的霍斯特堡創建了國際劇場人類學學院(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heatre Anthropology,ISTA),盡管以“學院”命名,但ISTA并不是一個高等教育性質的單位,而是由眾多表演者與學者所組成的流動式的協會組織,其核心成員來自美國、非裔美籍、亞洲與歐洲的表演者以及相關國家的大學教授。該組織在各國或跨國組織的邀請和資助下,定期舉辦研習會,主要研究非日常生活肢體運用的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如何應用在演員和舞者的創作中。研習會根據特定目標確定主題,并通過實際操演課程、成果呈現與比較分析等活動深入探究。作為一名戲劇導演,尤金諾·芭芭一生成果頗豐,據不完全統計,1965—2012年間他共導演過32部戲,出版了20余部著作,也獲得許多國際獎項及榮譽學位。他導演的作品曾在歐洲、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地巡演。著作分別以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英語、丹麥語等多國語言出版或再版,除了《劇場人類學辭典》外,其著作還有1995年出版的《紙作的獨木舟:劇場人類學指南》(The Paper Canoe:A Guide to Theatre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9年出版的《劇場:孤獨、藝術、造反》(Theatre:Solitude,Craft,Revolt,Black Moutain Press)和《灰燼與鉆石之地:我在波蘭的學徒生涯》(Land of Ashes and Diamonds:My Apprenticeship in Poland,Black Moutain Press)等。
② 羅馬大學表演藝術系戲劇史教授,自從國際劇場人類學學院成立以來,他就是固定成員之一。
③ 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5—6.
④ 波蘭戲劇導演葛羅托斯基于1980年參加國際劇場人類學學院在德國波昂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中,提出了對尤金諾·芭芭研究表演者技巧的看法。他認為,芭芭發掘了三個主要原則。參見:葛羅托斯基.實用的法則[M]//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268.
⑤ 眼睛方向和情緒的關系包括:(1)注意;(2)觀察;(3)思考;(4)沉思;(5)考慮;(6)欣賞;(7)驚異;(8)莊嚴;(9)熱誠;(10)癡迷;(11)狂喜;(12)疑惑;(13)感興趣;(14)敬畏;(15)著迷;(16)洞察;(17)發狂。視線方向改變時,脊椎位置也跟著改變,由此說明眼睛與脊椎的關聯性。在印度舞劇的傳統形式和風格中,看的動作是感覺的反應,無論是害怕還是惡心,都可以通過眼睛注視的方向和身體及脊椎明顯的對話表現出來。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128—129.
⑥ 鈴木忠志(Tadashi Suzuki)在其《表演方法》(The Way of Acting)一書中提出了關于腳的文法的相關探討,尤金諾·芭芭借鑒相關內容闡述劇場空間中演員走路的藝術表達,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146—149.
⑦ 筆者根據劇場人類學對動作的兩種分類,整合出兩者的區別與轉化原則。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6—21,52—65,73—92,93—100.
⑧ 梅耶荷德和德魯克都曾對身體器官獨立運作原則有過探討,梅耶荷德的生理機能學中提出整個身體都會參與最小的器官所做的動作;德魯克認為演員必須能夠只動想動的器官,不想動的必須保持不動。打破邏輯或因果的連續性,把動作分割和重新組合,劇場人類學把這一原則稱為身體動作的一般原則。詳情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212—214.
⑨ 隨著中西方藝術交流的不斷深化,對表演理論的探討已經拓展到日本導演鈴木忠志的戲劇表演方法、尤金諾·芭芭的戲劇人類學、理查德·謝克納的人類表演學、理查德·鮑曼的口頭表演理論、歐文·戈夫曼的表演理論等跨學科研究上來了。
⑩ 音樂界于1987年在中央音樂學院首開音樂表演課,30多年來一直開展研究工作,形成了階段性的理論探討。近年來,民族音樂學的學者開始倡導“音樂表演民族志”的理論與實踐,如蕭梅提出通過“體化實踐”對“樂”進行深入研究,楊民康關注儀式化表演行為和表演過程。在這些對“樂”的研究中,也涉及部分舞蹈與身體。參見:閆兵.中國音樂表演理論研究40年[J].當代音樂,2019(12):21—25;蕭梅,李亞.音樂表演民族志的理論與實踐[J].中國音樂,2019(3):5—14,34,193;楊民康.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一種從藝術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J].民族藝術,2016(6):16—22.
? 教育部頒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中指出,“音樂與舞蹈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舞蹈類專業)”提出舞蹈表演是通過專業化學習進行舞蹈藝術呈現和交流的基礎專業,培養具備舞蹈表演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主要從事不同層次的舞蹈表演,以及與舞蹈表演相關的教學、研究等工作的舞蹈藝術專業性人才。在課程設置上,舞蹈表演專業以舞臺表演為教學中心,應在專業教學的基礎上,打通相近學科專業的基礎課程,并開設跨學科專業的交叉課程,促進人才培養由學科專業單一型向多學科融合型轉變。參見: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下[M].高等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18:915—916.
? 新文科建設進入全面啟動的新階段[EB].中國社會科學網,(2020—11—05)[.2021—04—15].http://ex.cssn.cn/zx/xshshj/xsnew/202011/t20201105_5211962.shtml.
? 尤金諾·芭芭在本書中多次提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劇場訓練體系,其中在“歷史書寫”部分專門用一節講述該體系。詳情參見:法蘭哥·魯非尼(Franco Ruきni).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M]//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170—173.
? 梅耶荷德是俄國著名的戲劇導演,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員,后創立了自己的劇團,到處巡演,1905年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邀請,回到莫斯科領導劇場,在實驗中形成“新劇場”,提出了用舞蹈表達的行動模式。在“生理機能學”中,梅耶荷德談到不穩定的姿勢、危險的平衡、對比的動力、能量的舞蹈,劇場人類學認為演員前置表達的基礎原則和梅耶荷德的生理機能學原則相同。詳情參見: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尼可拉·沙瓦里斯(Nicola Savarese).《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的秘藝》[M].丁凡,譯.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17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