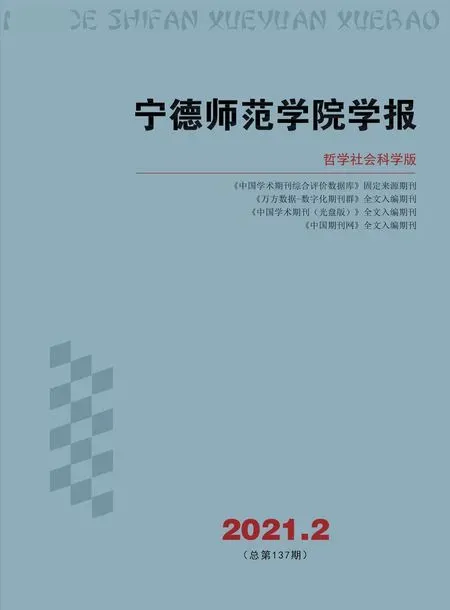黃鞠水利工程與寧德霍童的地域開發
魏煜民 楊園章
2017年,在墨西哥召開的第23 屆國際灌排大會上,福建寧德興修于隋代的黃鞠水利工程入選“世界灌溉工程”名錄,成為閩東地區的又一文化名片。當前,關于該工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對黃鞠事跡的介紹上,[1]缺乏深入的歷史研究,不利于其歷史和文化價值的進一步發掘。本文以志書、碑刻和家譜等各類史料為基礎,考察黃鞠水利工程在寧德霍童地域開發中的作用,以豐富其文化內涵。
一、黃鞠水利工程興建前后的霍童
黃鞠水利工程位于寧德市霍童鎮旁霍童溪的中游河谷地帶。據近年考古成果所示,在霍童一帶的蘆坪崗與瓦窯崗兩地點出土了舊石器晚期的石制品,這將閩東地區的歷史提到了2 萬至1 萬年前。[2]在霍童溪附近的溪尾山遺址則發現有商周時期的青銅錛、大量陶片與原始青瓷等,顯示了商周時期寧德先民較高的生產水平。[3]
在黃鞠水利工程興建前,霍童地區已有不少修道人群的活動。晉代,霍童山因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而受到修道人士的重視,逐漸成為道教重要的修煉場所,《天地宮府圖》載:“霍林洞天,在福州長溪縣,屬仙人王緯玄治之”;到了唐代,在道教茅山宗中,兩位最重要的神明“大茅君”和“南岳夫人魏華存”的洞府就在霍童山上,因此唐初司馬承貞在排列洞天時,令“天下三十六洞天,霍童在第一”。[4]霍童山下的鶴林宮始建于大通二年(528 年),是福建地區較早見諸史冊的重要宮廟,其后幾經興廢,[5]今日鶴林宮中仍存有唐玄宗御敕的“霍童洞天”殘碑,可見道教活動在該地區擁有悠久歷史。
南宋淳熙《三山志》最早記載了黃鞠的事跡:“仙湖、堵平湖、塘腹湖,會小溪水,隋諫議黃公創,溉田千余頃。淳熙二年(1175 年),有請佃者,官以其妨民,不給,仍搜獲。儲知縣詩云:‘咫尺仙湖號堵平,先賢曾此勸農耕。若教一日歸豪右,敢向黃公廟下行。’”[6]其后,弘治《八閩通志》載:“諫議大夫廟,在縣西十二都霍童山下。隋大業中,諫議大夫黃鞠嘗墾山之荒壤為田,而鑿山通澗水以灌溉之。后鄉人感其德,建祠廟祀焉。”[7]據黃氏家譜記載和實地調研,該工程可分為右岸龍腰渠、左岸琵琶洞渠兩處。龍腰渠位處霍童鎮石橋村,相傳是黃鞠在獅子峰之右名為“龍腰”的山梁上所鑿的石渠,通過引霍童溪水來灌溉松岸洋的千頃農田。整個右岸工程引霍童溪一級支流大石溪水入渠道,在龍腰自然村大榕樹處分為兩支,一支利用地形灌溉高處農田;一支引水入村,利用水位高差建有五級水碓,進行農副產品和糧油加工;之后渠水又分為兩支,一支通過客山梁灌溉石橋洋千余畝良田,另一支進入日、月、星等調蓄陂池后在石橋村內流經每家每戶形成三只蛤蟆九曲水的生活供水體系,在分水處設立石蛤蟆,以改變水流條件避免沖刷,便于對渠道進行分段管理,同時也方便村民洗滌、消防、抗旱使用,沿渠系分布著硯池、金魚池和羅星湖等調蓄湖,渠水最后依然匯入田間灌溉。琵琶洞渠在霍童溪左岸,原由明渠與七段隧洞組成,下鑿有堵平湖。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的特大山洪造成原霍童溪改道,致使該工程一度廢棄,而堵平湖也在清代時因填埋造地而消失,今日僅存有數段涵洞的遺跡。黃鞠灌溉工程通過引、輸、蓄、灌、排的合理布局,解決了霍童溪兩岸千余頃農田的灌溉問題與沿岸民眾的生活用水問題。[8]

圖1 黃鞠灌溉工程示意圖
中晚唐至宋代,南方地區免遭安史之亂的影響,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口的南移。為了有效控制新增人口進行編戶,中央政府在此頻繁增設新縣與作為縣前期形態的鄉與場。唐開成中“析長溪、古田二縣地置感德場,偽閩龍啟元年(933 年),升為縣”;宋代,寧德縣霍童地區設霍山鄉霍童里,其下黃大夫湖、程黨渡和霍山井是當地較為重要的事物。[9]黃鞠水利工程的建設改善了霍童一帶的耕種與生活條件,而人口的涌入又進一步墾辟了土地。隨著沿海與內地隔絕狀態的打破,商貿往來漸興,溝通海洋與山區的霍童溪更是成為鹽魚、山貨交易的重要集市,宋代官府在“霍童津”設官市,市中設巡攔一名以報貨物稅,[10]說明霍童成為周圍地區的區域性市場中心。另外,從一些橋梁、寺廟的興修記錄中也能看出唐宋時期霍童地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如聞名海內的支提寺及其相關設施即興建于吳越國時期,[11]普濟橋“在風山寺前,唐咸通二年(862 年)建”,千佛橋“在穹窿溪上,宋太平興國四年(979 年)建”“仙巖寺,唐咸通二年建。小支提寺,唐咸通九年建。布泉寺,唐乾符六年(879 年)建……禪寂寺,在十三都,唐咸通五年建”等等。[12]
南朝時期,霍童地區因修道人士的活動而產生影響力,逐漸成為道教第一洞天。據前引《三山志》的說法,隋代黃鞠水利工程的興建“溉田千余頃”,無疑促進了當地經濟生產,為宋代在此設立官市“霍童津”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當地人建廟奉祀黃鞠,一方面是對該工程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蘊含了以其為核心而生發出區域性社會組織的可能,而后者是我們理解黃鞠水利文化的重要線索。
二、霍童三十六村的傳說
元代罷廢了宋代在寧德設立的五個官市(霍童津即其一),明洪武元年(1368 年)復設稅課務二所,一在縣城東門,一在峬源村,不久裁革。[13]元代至明中期,地方志中關于霍童地區的記載基本延續《八閩通志》等早期志書的說法,新增的較少,如“隋諫議大夫黃鞠墓,在十二都霍童山下”;又如為霍童人顏公武立了一個小傳,贊揚他的高尚品德。[14]相反,在嘉靖《寧德縣志》卷4《景物》內,除縣域外,三、四、七、八、二十和二十三都皆有若干景的記載,如三都的“黃灣八景”,但名氣較大、開發較早的霍童地區則付之闕如,說明至少在明中期,霍童在整個縣境內還不夠重要,未引起修志者的關注。而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和當地流傳的自然災害導致的社會巨變的傳說有關。
據霍童鄭、錢二姓族譜,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 年)秋,“大雨,溪水暴漲,八月二十四日未時,霧起天黑,水淹滿村四處三丈余,至二十五日巳時水退”;“鶴陀巖傾頹,阻塞金錢渡,沖毀鶴林宮與霍童村落,淪為澤國,田廬民畜,喪失殆盡”。現在更多的說法是明嘉靖十三年霍童溪爆發特大洪水,鶴陀巖崩塌堵塞霍童溪導致洪水四處奔瀉,夷平村落。幸存的人們仍聚集到霍童來,依傍在街尾一帶建起自己的“某厝里”,加上后來的移民,霍童的村落得以擴大,再度繁榮。[15]關于這場災害,明代地方志僅萬歷《福寧州志》有一條明確的記錄:“鶴林宮,在十二都,梁大通二年建。國朝嘉靖初年,為洪水沖圮,石柱尚存,后移之水尾,不竣功,今廢。”[16]至于村落的情況則不得而知。根據《錢氏族譜》,鶴林宮的下座的兩廊分別供霍童平原三十六村的三十六爐香火,表明在大洪水之前,霍童平原的村落形成了以鶴林宮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但洪水之后,霍童溪改道,原來隔著溪的十二和十三都的主體村落,現在皆位于霍童溪的右岸,聯為一體。按明代里甲賦役制度,寧德“分為二十五都,析為三十八圖……一圖一長,而統十戶為一甲。或有過十戶之外者謂畸零,定以板籍,不容移易”。[17]又據萬歷《福寧州志》載:“霍童里統圖三,十二都,二圖:霍童、益坂、坂頭;十三都,一圖:青巖、外渺、小石嶺、石橋、松岸、嶺頭。”[18]由此,晚明時期霍童平原上的聚落較傳說中的三十六村已有明顯的減少,且十二都的人口較十三都多;十三都的聚落規模小,多散村,黃鞠水利工程的主體位于十三都石橋村。因此,不管洪水發生元代還是明代,該傳說都指向晚明時期霍童地區面臨社會重組和秩序重建的問題。
事實上,對上述自然災害還可能有更深層次的解讀。按當地族譜,原霍童三十六村已形成以鶴林宮為核心的一種村落聯盟,但從萬歷《福寧州志》載鶴林宮“后移之水尾,不竣功,今廢”來看,這套聯盟并未恢復,換言之,后來的人們放棄了原先的社會組織模式。五代至宋朝,福建以寺田多而聞名,如宋太宗就曾驚訝于泉州僧人之多。[19]《三山志》載寧德縣田2848 頃余,寺觀915 頃余,占32%強;園地等5343 頃余,寺觀489 頃余,占9%強。[20]可見宋代開始,寧德寺觀戶下就有大量的產業。霍童既有鶴林宮,也有支提寺,是道、佛兩教的重要廟宇,其名下產業之多自不待言。以支提寺為例,宋代就有田46 頃,明洪武年間載在田冊的即有16 頃,不在冊籍者與山場、園地等另計,其中有些產業就在霍童。[21]如此,較支提寺歷史悠久的鶴林宮,自然也會擁有一大批產業,而原三十六村以它為核心的聯盟,其實很可能就是一種經濟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么明代及以前的志書里提到的都是霍童的寺觀,而很少提及具體村落里的人和事。然而,隨著朝代更迭和人群關系的不斷調整,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多次重建,地方動亂和官府的賦役改革直接推動了這一歷史過程。寧德地處山海交界地帶,受到諸如閩浙贛山區“流民”“礦盜”和沿海倭寇的侵擾,明中后期福建地方的經費困難,更是導致了原有寺院田產大量易主,[22]如布泉寺,“在十三都,唐乾符六年建。嘉靖二十二年,田奉例召民官買,寺廢。”[23]又如支提寺,“正德十五年(1520 年),古田張包奴據雞啼寨寇亂,縣尉鐘奎不能平,懼罪無以報,遂以支提音同誣僧,上其事,檄寧德令桂宗美毀寺。宗美知其誣,白之。雖置勿問,而僧眾厄于殘暴不能守矣。嘉靖六年倭亂,寺遭兵燹,唯祖堂巋然獨存,實伽藍呵護之靈。”[24]筆者無意否認歷史上存在霍童溪洪水事件,而旨在提出,霍童三十六村傳說背后不僅僅是一場自然災害,而是更復雜的社會重組過程,是原三十六村脫離與鶴林宮的經濟關系,謀求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歷史。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各個版本的傳說里一定會出現鶴林宮,一定要講鶴陀巖崩塌。在此,人們將更深層次的社會變化依附于鶴陀巖崩塌事件,它既是一種歷史事實,更是一種歷史記憶,一種關于社會重組、秩序重建的記憶。
三、作為產權證明的黃鞠事跡
既然人們放棄了以鶴林宮為核心的三十六村聯盟,他們就需要找到新的可以證明其產權合法性的確鑿的“來歷”,[25]《三山志》及后代志書都有明文記錄的黃鞠及其水利工程成為當時人們援引的重要歷史資源。
據當地的說法,霍童在大洪水后得以重建,首先是在今“古街”一帶形成“華陽境”,建起了“文昌閣”“武圣廟”“功德林”等建筑(大部分建于清康熙至乾隆時期),為霍童各姓共有,統稱“二十四排林相共”;后又相繼單獨立境,出現了集居坂頭一帶的“萬全境”、街中的“忠義境”、橫街的“宏街境”,而世居街尾的則仍為“華陽境”,形成了“霍童二十四境”的格局和“二月二”燈會輪流當值的盛況。[26]亦即,在清代,霍童人民重新創立了一套人群組織模式和新的村落聯盟體系。其中,四境各宮“俱祀黃鞠,配祀宋林亙”,[27]黃鞠被當地人稱為“土主”神。關于黃鞠被作為“土主”供奉,當地人的一般性解釋是黃鞠在此興修水利,有功于民。該說法當然有其合理性,但這套解釋的關鍵在于社會重組時所必須處理的田地和山林的產權問題。
前文談到,嘉靖《寧德縣志》對霍童地區的新增記載甚少,但其中一條就是黃鞠墓,該信息弘治《八閩通志》未載,因此是明中期才被增入地方志,說明了在當時該信息足夠重要,需要被專門記錄。為什么黃鞠墓變得重要呢?這和傳統中國時期的山產確權直接相關。[28]黃鞠墓前至今仍有古碑一通,上書“戶部黃公之瑩,計一畝二角二十步”,按《三山志》所載福州田土,其計量單位即畝、角、步等,但到元、明時期則用頃、畝、分、厘、毫等,[29]該碑為宋碑的可能性較大,該碑表明在黃鞠墓這一戶頭下有產業一畝有余。換言之,黃鞠已不再是歷史上具體的某個人物,而是一個官方賦役冊籍上的戶頭,是一種得到官方認可的產權證明。而之所以在明中期要加以強調,則和當時閩東地區的“菁客”、畬民等人群的山林經濟開發直接相關。
萬歷《寧德縣志》有一段按語非常重要:“按本縣山場,無論城郭、鄉村,除附近廬舍、墳墓者始為民業,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來縣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則隨山照灶置簿收租。自辛酉倭變之后,明知官簿無存,地虎鄉豪年收其租。今考本縣冊籍,民山并無分厘,只有官山三頃二十畝九分,其稅撒于通縣,其利獨歸于數家之人,此法所當究者。宜照上年故事,拘召各鄉菁牙,開報各鄉菁客,隨其眾寡置簿收租,此公家之利,取之不為虐,舍之不為惠,與其獨飽數家之人,孰若公收貯庫以資□政之用,惠澤大小何如耶?”[30]寧德的山場除了原有的廬舍、墳墓屬民有外,其余俱為官產,外來人群在本地開發時,官府以山為單位,仿照海邊灶戶的制度將他們登記在冊收取賦稅。但倭亂之后,官方控制力減弱,官府和勢豪之間處于互相爭奪菁客上繳山林租稅的狀態。不論是后來的菁客,還是先到的勢豪,他們都需要證明自己的“來歷”,從而證明自己可以合法地占有資源。按規定,墳墓及其附屬的山產歸民人所有,黃鞠墓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從霍童三十六村在鶴林宮內供奉各村香爐,到霍童四境尊黃鞠為“土主”,反映了明中葉以來人群關系的重組,特別是晚明至清前期山林的開發沖擊著原有的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寺觀代表著舊有傳統,而黃鞠成為使新秩序合理化的歷史資源。這點通過現存霍童鎮石橋村的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遵奉憲斷》碑上所載山場糾紛案可有清楚的認識。該碑云:“為遵奉憲斷、敘碑杜患事。緣任等始祖黃鞠公系隋朝諫議大夫,由河南開封府卜居邑之十三都石橋地方。鑿龍腰,通水道,墾田百頃,崇祀鄉賢。遺下門首山場名曰大石林,上至山頂,下至田頭,左至橫林食水坑,右至煉丹巖牛牳坑,四水歸流界內。樵木、營葬至今,相傳幾千載矣。”黃仸任等人一開始就強調始祖黃鞠的來歷和貢獻,以此證明山產歸黃氏所有。但康熙年間,有十二都林伯招“結連支提寺僧濟明等,找幫謀陷,欺占官山”,雙方持續互相指控,該碑是福建巡撫處下達的審判結果錄文。究其本質,是黃氏、林氏和支提寺僧人等不同人群在爭奪山產,其目的是種菇,也就是從事山林經濟。在支提寺一方,據《支提寺田記》載,該寺原額田16 頃40 畝余,嘉靖元年寺廢后,田散入附近居民彭潮、馮口等官佃手中,由其納租;嘉靖二十二年,奉文召民林喬等承買,“即削去寺籍,糧收民戶當差”;萬歷年間,僧人大遷重開本山,在官府支持下恢復產業。但隨著明清易代,時局不穩,寺產糾紛又起,康熙五年,官府同意另立“僧戶糧米”附于十二都十排冊末,脫離彭氏的掌控,“聽僧自行庫納”,再次確立了支提寺獨立戶頭的合法性。[31]在《遵奉憲斷》碑里的雙方,一方援引先祖黃鞠事跡,宣示其對周邊山場的所有權;另一方則依靠掙脫了地方豪強控制,逐步恢復勢力的支提寺。在此,黃鞠成為與寺觀不同的話語資源和產權證明。
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黃鞠及其水利工程在晚明至清前期閩東山林開發的歷史進程中被重新賦予含義,它們不再只是具體的某段水渠,而是成為了當時人們用于證明自身歷史和產權合法性的資源,背后指向的是地域社會秩序的重建。
四、清中期以來霍童地區的深度開發
霍童地區人類活動歷史可追溯到史前時期,中途經過許多轉折,而至今仍持續影響著霍童的社會和文化的則以清中期以來霍童的深度開發最為重要。
相較于明代地方志中霍童的“缺席”,清乾隆《寧德縣志》專門繪有霍童山之圖,用大量的篇幅介紹霍童和支提山范圍內各山,還特別提出,“三十六洞天言霍童不言支提,蓋支提亦霍童之一耳……霍童可以該支提,支提不可以該霍童”,推崇霍童山。[32]從聚落上看,前引萬歷《福寧州志》載:“十二都,二圖:霍童、益坂、坂頭;十三都,一圖:青巖、外渺、小石嶺、石橋、松岸、嶺頭”;乾隆《寧德縣志》載霍童仍分二都三圖,但所統村落已有增至16 個:坂頭、蔗坂、坂墘、新顏、山下、邑坂、峻頭(以上十二都),石橋、青巖、漱石、渡頭、嶼頭、轉水宮、外渺、云門寺、小石嶺(以上十三都)。[33]以十三都看,新增的村落有的以轉水宮、云門寺這類寺觀作為地名,說明該寺觀在該村的重要性。與前述霍童四境的許多公共建筑一樣,地方志里新增的霍童地區的橋梁、寺廟都多建于康熙至乾隆年間,如鳳凰橋,“邑人陳邦校建。國朝乾隆二十三年邑人宋家鍙、陳溶倡募重建”;[34]又如小支提寺“乾隆三十八年重建于舊寺之左”,金燈寺廟“萬歷三十一年建,國朝康熙丙午年修”,碧云庵“康熙十一年建”,等等。[35]市場方面,宋代曾在霍童設官市,元代裁革,至清代,“街市在霍童司署前,列肆者二百余耳”。[36]所謂“司署”即霍童巡檢司的衙署,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改福州府倉大使駐霍童村為霍童巡檢司。[37]通過這一設置,也表明清中葉霍童地區的重要性受到官府關注,需要專門設置巡檢司以維護地方穩定。
除地方志中新增的許多霍童史事外,現存于當地的清代碑刻和族譜也說明清中葉霍童社會的深度開發,這主要反映在各類組織的運作及由此體現出的人群的聯合。
首先是紀念黃鞠與其姑父朱福的“二月一”燈會。相傳,黃鞠最初為避迫害而遷徙咸村,后與早年定居于霍童石橋的姑父朱福易地而居,為報答朱福易地之恩,黃鞠許諾每年二月初一朱福生日時舉辦燈會慶典迎接他回石橋過壽。在石橋村大宮里雕塑了黃鞠和朱福的神像,以朱福居首。后來,二月一燈會發展到霍童全村四境,每境表演一個晚上,共計四晚,稱為“小迎”;又逢五年為一輪,各境重復舉行一次,共計八晚,稱為“大迎”。霍童四境各姓以“堡”為單位,在燈會的晚上,各姓舉著寫有本堡“黃堡”“章堡”“陳堡”等字樣的燈籠為首,抬著本姓祭祀的土主神像緊隨其后,表達人神同樂之意。[38]且不論黃鞠與朱福的傳說以及“二月一”和明清以來閩東畬民之間存在著許多密切聯系,[39]就但從燈會所串聯起的聚落而言,“二月一”燈會構成了地域人群的聯盟,通過該活動凝聚人心,塑造認同。根據霍童弘街宮內展陳,當前燈會的輪值基礎其實是清康熙年間整頓里甲體系后的產物,據其引嘉慶十六年(1811 年)霍童《立本堂黃氏族譜》譜序云:“康熙間,又有割盛補衰之例行,吾族一門分三戶焉,一黃世佑即原戶也,一爐田黃陳遠,一即今二圖八甲黃謝劉是其本戶焉。”黃氏又分出兩個戶頭,一是在爐田的黃氏與陳氏合一個戶頭,一是在二圖八甲與謝、劉二姓組成新的戶頭,這從它們分別供奉一、二、三個香爐對應,也與上一節我們談到的清前期霍童地區社會秩序重建相吻合。
其次是與其他公共事業有關的組織。如轉水宮,“在十三都青巖北二里,內祀陳元君。宮外潭中有石似立劍,當秋水澄清時,舟人以竹竿指之,其石輒搖,亦奇跡也”。[40]從廟內乾隆七年《圣跡重新》碑載捐獻題名看,其信眾既有本都林正旺等人,也有十四、十八、十九等都的其他信眾,或捐山場,或捐香燈田;又廟內石供桌題名:“時咸豐五年(1855 年)十二月吉旦立,八蒲進洋境陳錦全公派下仝□。”表明轉水宮至遲在清中葉,已成為地區內重要的祠廟,并持續運營。又如現存霍童華陽宮外乾隆五十九年《天后宮志》碑(復制件)所載,清中葉“霍童地廣人稠,各商市、山場、諸邑而浮航江浙,或貿遷有無,往來臨邑、本郡者,咸輻輳于茲”,點明霍童地處因山海貿易交通線上而興旺繁榮的歷史,“鳩同人創造廟宇,視各幫子母之大小而等差,以捐資財置廟”一句更直接反映了當時霍童已出現了各類商幫,通過等差捐資的辦法,事實上是借由建廟成立了一個商幫的聯合會。又如現存于霍童媽祖宮的兩塊殘本,一為嘉慶十九年《琉璃碑》,內載鄉民捐資在天后宮設琉璃一盞供養神明,并置辦田產以充祭祀之用,殘存文字有“糧一畝零八厘”“歷年二月舉錢三千文交公辦理”等字樣,大體可以推斷這批人經營田產生息作為組織運作經費;另一塊為嘉慶二十二年《重建文昌閣志》碑,該碑原來當在霍童文昌閣,講述的是繼康熙年間縣令汪大潤在霍童首創文昌閣以后,乾隆二十四年士紳章一忠等人重建,半個多世紀以后再修的故事。相較于商人為主的天后宮組織,文昌閣的運作則以地方紳耆為主力。
最后是宗族的建設,這里以黃鞠后裔石橋黃氏為例。現存最早的石橋《黃氏族譜》修于清嘉慶年間,正是霍童地區經濟日益繁榮階段,據其記載,隋代有黃隆公生二十一子,其第十子為黃鞠,配葛(蕭)氏、于氏,居南閩鹽場石橋村,黃鞠公又生五男二女。黃鞠后裔繁衍生息,開枝散葉,據初步統計,自石橋遷出的黃鞠后裔大小共有400 余支,遍及霍童周邊地區,甚至抵達了其他的省市。[41]這些居住在各地的黃氏后人都主張黃鞠是其始祖并加以供奉,他們之間由此形成了一套共同的宗族歷史敘述,逐漸構成了黃氏宗族網絡。在前引《遵奉憲斷》碑碑陰,刻有黃氏闔族為助力官司而捐資的人員名單,其中分為黃珠和黃福兩大戶頭。現存石橋宗祠內的嘉慶二十五年《祠堂志》碑記載黃元綱等人嘉慶十四年謀劃鼎建宗祠,歷時數年終告落成一事。黃鞠祠前的益石亭內亦有咸豐十年碑文一通,[42]記錄捐款題名,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在開頭的“黃珠公捐銀五十六兩,七月祠堂會捐錢十千文;黃福公捐銀三兩正,十月祠堂會捐銀四千文”等字樣,據此,到晚清時期,黃氏宗族仍沿用清前期的黃珠、黃福戶頭,并用它們做了某種組織,名下有一定產業;而七月和十月的祠堂會則應屬另外的某種宗族組織,也有獨立的產業。石橋黃氏的案例說明,對外,他們通過聯宗與閩東多地的黃氏人群搭建起超地域的社會關系網絡,黃鞠是他們重要的族群認同標志;對外,既有與國家里甲賦役制度有關的組織,也有祠堂輪值基礎上組建的“會”,多重組織協同共事。
五、結語
早在遠古時代,霍童地區已有人類活動,歷史早期當地因優越的自然條件得到修道之人的追捧,成為道教第一洞天。隋代黃鞠水利工程的出現,提升了當地的生產水平。唐至元代,鶴林宮、支提寺等寺觀掌握著地方大部分產業,霍童三十六村與寺觀之間存在密切的經濟聯系。隨著地方開發的深入和人群關系的變化,原有社會秩序受到挑戰,新的村落聯盟選擇黃鞠這一重要的文化資源作為其產權和歷史的合法性的依據。延續晚明以來的山林開發,清中葉以后的霍童憑借其在閩東山海貿易體系中的交通優勢,獲得深度開發的契機,涌現出許多新的組織,它們共同塑造著影響至今的霍童的社會和文化。黃鞠水利工程從具體的灌溉工程演變為一種包含族群認同、民俗、歷史資源等多重意義的水利文化,其本質是一個地域社會開發的過程,而晚明至清前期霍童地區的社會重組是該過程的重要歷史時刻。
注釋:
[1]如繆品枚編:《寧德史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0 年,第30—31 頁;唐頤:《黃鞠和霍童溪》,《海國蕉城》編委會編:《海國蕉城》,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4 年,第54—56 頁;福建省水利廳、人民網福建頻道編:《尋訪福建水文化遺產》,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 年,第48—53 頁。
[2]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寧德霍童山考古調查初步收獲》,黃幼聲等編:《寧德霍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0 年。
[3]范雪春:《福建寧德縣霍童發現春秋青銅戈》,《考古》1990 年11 期。
[4]施舟人:《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1 期。
[5](清)盧建其修纂: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寺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258 頁。
[6](宋)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16《版籍類·水利》,福州:海風出版社,2000 年,第187 頁。
[7](明)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60《祠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76 頁。
[8]以上關于黃鞠水利工程的介紹詳見《黃鞠灌溉工程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申報書》,內部資料,2017 年。
[9]《三山志》卷3《地理類·敘縣》,第26 頁。
[10](明)舒應元修纂:萬歷《寧德縣志》卷3《建置志·津梁》,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歷刻本,第29b 頁。
[11](清)崔嵸修纂:《寧德支提寺圖志》卷2《寺》,福州:福建地圖出版社,1988 年,第14 頁。
[12]《八閩通志》卷19《地理》,第537 頁;同書卷79《寺觀》,第1231 頁。
[13]萬歷《寧德縣志》卷3《建置志·津梁》,第29b 頁。
[14](明)閔文振纂修:嘉靖《寧德縣志》卷2《墓冢·塋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06 頁;同書卷4《人物·長厚》,第235—236 頁。
[15]詳見宋建勛:《霍童民居探古》,寧德市霍童文史資料征集辦編:《霍童文史》(三),內部資料,1999 年,第12—14 頁。
[16](明)殷之輅修纂:萬歷《福寧州志》卷15《雜事志·寺觀》,《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98 頁。
[17]萬歷《寧德縣志》卷1《輿地志·鄉都》,第4 頁。
[18]萬歷《福寧州志》卷1《輿地志·版圖》,第26 頁。
[19]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道釋”一“披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9981 頁。
[20]《三山志》卷10《版籍類·墾田》,第123 頁。
[21]《寧德支提寺圖志》卷2《田》,第23 頁。
[22]參見鄭振滿:《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中國史研究》1998 年第1 期。
[23]萬歷《寧德縣志》卷3《建置志·寺觀》,第60b 頁。
[24]《寧德支提寺圖志》卷2《寺》,第14 頁。
[25]關于“來歷”與產權的關系,可參見張小也:《所謂“來歷”:從〈靈泉志〉看明清時期土地權利的“證據”》,《江漢論壇》2012年第9 期。
[26]宋建勛:《解讀“霍童”》,寧德市蕉城區霍童鎮文史辦編:《霍童文史》(六),內部資料,2008 年,第32—33 頁。
[27]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廟》,第187 頁。
[28]參見杜正貞:《明清以前東南山林的定界與確權》,《浙江社會科學》2020 年第6 期。
[29]《三山志》卷10《版籍類·墾田》,第122 頁;《八閩通志》卷21《食貨·土田》,第606—607 頁。
[30]萬歷《寧德縣志》卷2《食貨志·物產》,第8b—9a 頁。
[31]萬歷《寧德縣志》卷3《建置志·寺觀》,第52 頁;《寧德支提寺圖志》卷2《山場》,第24 頁;同前書卷6《逸事》,第146—148頁。
[32]乾隆《寧德縣志》卷1《輿地志·山》,第49 頁。
[33]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民居》,第206 頁。
[34]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橋梁》,第220 頁。
[35]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寺觀》,第258、260—261 頁。
[36]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街市》,第209 頁。
[37]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公署》,第149 頁。
[38]宋建勛:《黃鞠與朱福》,《霍童文史》(三),第18—27 頁;劉國平等編:《寧德非物質文化遺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67 頁。
[39]繆品枚編:《寧德史話》,第74—75 頁;宋建勛:《霍童歷代道家考略》,《霍童文史》(六),第25 頁。
[40]乾隆《寧德縣志》卷2《建置志·寺觀》,第262 頁。
[41]石橋村黃氏理事會匯編:《黃鞠》,內部資料,2017 年,第26—27 頁。
[42]當地多將該亭識別為“益后亭”,但黃鞠后裔理事會原會長黃鄭坤先生認為應作“益石亭”:原碑上作“后”而非正體字“後”,而隸書中“石”有寫作“后”的先例,“石”指石橋。綜合來看,黃鄭坤先生的理由更為充分,故本文改稱“益石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