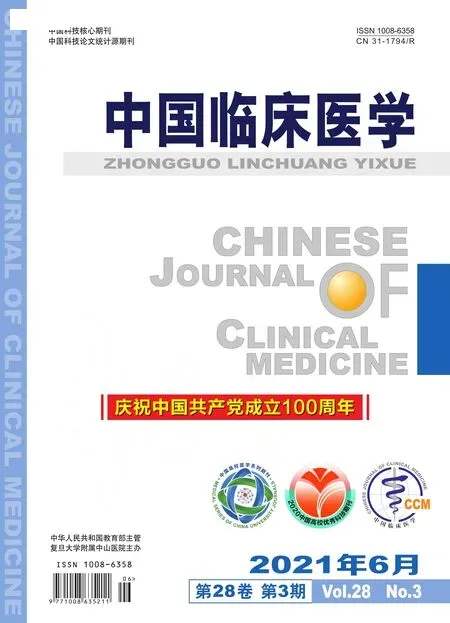抑郁、焦慮狀態人群的腸道菌群構成
莫瀚鈞, 郎 林, 柳理娜, 勞力敏, 江孫芳,2*
1.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全科醫學科,上海 200032 2.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上海 200032
抑郁癥和焦慮癥是常見的精神心理障礙性疾病,給全世界的患者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負擔[1-2]。其中,抑郁癥是一種受基因、環境等因素影響的精神疾病,以心境低落和興趣減少為主要的臨床特征[3]。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到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全球成年人致殘致死的首位原因[4]。而焦慮癥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體驗,表現為內心緊張,因預計某種不利情況將要出現,進而產生持續、強烈的擔憂和恐懼。研究[5]表明,抑郁癥患者常合并廣泛性焦慮障礙,患病率為20.5%~38.0%。因此,在精神疾病負擔日益增長的今天,對抑郁和焦慮癥的發病機制進行研究尤為重要。
人體腸道內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其基因總數是人類自身的100多倍,因而被稱為“第二基因庫”,對維持機體健康發揮著重要作用。最新的多項研究[6-8]表明,腸道菌群的紊亂與焦慮、抑郁等多種精神疾病有關。Bravo等[9]發現,對焦慮、抑郁模型小鼠行迷走神經切斷術后,小鼠原有的焦慮、抑郁樣行為消失,提示迷走神經在腸-腦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中樞神經GABA能系統的異常也被認為與焦慮、抑郁相關。逐漸形成的微生物群假說認為,微生物-腸-腦軸(microbiota-gut-brain axis, MGBA)的雙向交流系統能顯著影響大腦的神經生化和有關表型[10]。
目前關于腸道菌群與抑郁或焦慮的研究不在少數,然而在確診抑郁癥、焦慮障礙之前,患者往往處于抑郁、焦慮狀態。對于這部分患者的腸道菌群是否已經發生了紊亂,目前缺乏相關研究證實。此外,臨床上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存在焦慮和抑郁的共病狀態。抑郁和焦慮患者是否具有共同的腸道菌群組成,或是兩者各有特異的微生物群特征,仍沒有定論。因此,本研究擬采用16S rRNA測序的方法,探討抑郁和焦慮狀態人群與健康人群在腸道菌群構成上的差異,為后續進一步探索菌群異常在神經精神疾病發展中的機制奠定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全科門診及心理科門診收治的237例就診者。納入標準:年齡18~80歲;無其他精神疾病病史;經解釋后,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近2個月內使用過抗生素或者微生物調節劑;合并嚴重軀體疾病或有明顯胃腸道癥狀;合并嚴重認知功能障礙,不能配合完成問卷調查; 妊娠、哺乳的女性。本研究通過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均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所有受試者分別接受抑郁癥篩查量表(patien health questionnare,PHQ-9)和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ized anxiexy disorde-7, GAD-7)量表評估,以PHQ-9評分≥5分或GAD-7量表評分≥5分為研究組(n=117),PHQ-9評分<5分且GAD-7<5分為對照組(n=120)。根據是否存在抑郁合并焦慮,將研究組分為單純抑郁組(n=38)、單純焦慮組(n=36)和抑郁合并焦慮組(n=43)。
1.2 量表采集 調查員與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由研究對象自行填寫問卷。在被調查者完成問卷填寫后,由調查員逐一檢查問卷各個條目填寫的完整性。對于勾選不規范或者漏填的條目,當場及時與調查對象進行溝通確認。
本研究抑郁癥狀評估采用PHQ-9量表,焦慮癥狀評估采用GAD-7量表。PHQ-9量表共包含9個項目,每項采取0~3分的評級,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的癥狀越重[11]。GAD-7量表是評價焦慮癥狀的自評量表[12],一共包含7個條目,同樣采取0~3分進行評級,分數越高表明焦慮的癥狀越重。
1.3 糞便樣本采集及預處理 量表填寫完成后,工作人員在當天完成受試者糞便采集,新鮮糞便標本在排便后6 h內放入-80℃冰箱。精確稱取糞便標本200 mg,1份放入新的2 mL無菌離心管中,用于細菌16S rDNA提取,2份放入-80℃凍存。標本留取前1周內,受試者需保證正常飲食,無腹瀉。
1.4 DNA提取及測序 采用SDS裂解液凍融法進行DNA提取,基因組DNA通過PowerMax 提取試劑盒(MoBio Laboratories)提取,儲存于-20°C冰箱。采用NanoDrop 1000分光光度計(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美國)測定DNA的數量和質量,進一步做瓊脂糖凝膠電泳。
電泳檢測后通過帶16S rDNA V3-V4可變區的引物進行PCR擴增后,加入0.85× AMPure XP Beads進行磁珠純化。純化過后的產物進行Nanodrop檢測,按照所得到的值進行等量混合,2%瓊脂糖凝膠對混樣進行電泳,采用AXYGEN的膠回收試劑盒回收,用Qubit對回收的文庫進行定量,用qPCR進行接頭效率檢測,算出實際濃度后,上機測序。
使用Illumina的Hiseq二代高通量測序儀對細菌16S rDNA序列進行測序,得到所有對象樣本的腸道菌群16S rDNA V3-V4可變區的原始序列。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分析使用Vsearch v2.4.4,包括去重復序列、聚類、去嵌合體。按照97%的相似性將樣品序列聚類為OTU,稀釋曲線趨于平坦,說明測序深度足夠。使用默認參數挑選OTU的代表序列,基于SILVA128數據庫通過VSEARCH對代表序列進行物種注釋,進一步生成OTU 列表,在各個分類水平上統計各樣本的群落組成。記錄每個樣本中所有OTU的豐度和分類,去除樣本中含量低于總序列0.001%的OTU。
1.5 高級生物信息統計分析 數據分析主要使用QIIME、R軟件(v3.2.0)和STAMP軟件。使用QIIME軟件計算OTU水平的α多樣性和β多樣性指數。α多樣性包括Chao1、Shannon和Simpson指數等,繪制等級豐度曲線(ranked abundance cuve)、稀釋曲線、α多樣性指數組間差異的箱型圖,來比較樣本間的菌群豐度和均勻度。β多樣性分析主要采取基于加權UniFrac距離的主坐標分析(PCoA)展示不同組間的菌群結構差異。
通過PERMANOVA評估微生物群落結構在組間分化的標志物,使用R包“vegan”。基于R包“VennDiagram”繪制Venn 圖,將組間共有和獨有的OTU可視化。使用R stats包Kruskal方法比較組間各分類水平門、綱、目、科、屬的差異。
基于PICRUST方法預測菌群的功能差異。使用Metagenomic Profiles (STAMP) 軟件包v2.1.3對輸出文件作進一步分析。從KEGG代謝途徑第3層、COG功能分類2個方面進行差異比較。
1.6 統計學處理 問卷填寫完成后,采用Epidata 3.1建立與問卷內容一致的數據庫,由統一培訓的數據錄入員完成錄入,然后使用Excel將數據進行整理和編碼。連續變量:年齡、體質量指數(BMI)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PHQ-9和GAD-7分數采用Kruskal-WallisH檢驗。分類變量:性別、既往疾病史和吸煙情況采用Pearsonχ2檢驗。細菌菌門間的統計學差異,2組比較采用t檢驗或Mann-WhitneyU檢驗,4組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采用t檢驗和the Monte Carlo permutation檢驗比較組間的Unifrac距離。所有檢驗采取雙側,檢驗水準(α)為0.05。
2 結 果
2.1 一般資料分析 結果(表1)顯示:除了PHQ-9和GAD-7評分外,3個疾病組和健康對照組之間在年齡、性別、BMI、既往疾病史(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和吸煙情況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單純抑郁組的PHQ-9評分為(7.35±2.6)分,單純焦慮組GAD-7評分為(7.34±2.7)分;抑郁合并焦慮組的PHQ-9評分為(9.42±4.8)分,GAD-7評分為(10.3±4.2)分,顯著高于其余各組(P<0.001)。

表1 4組人群的一般資料比較
2.2 抑郁與焦慮組腸道菌群結構分析 從4組人群的糞便樣本中提取出16S rRNA進行PCR擴增,得到各組序列數和OTU數及組間分布的韋恩圖(圖1)。由韋恩圖(圖1B)可知,4組共有的OTU數為1 523,其中單獨為抑郁和焦慮所特有的OTU數分別是41和105,抑郁合并焦慮組特有的OTU數為52,健康對照組特有的OTU為181。4組在菌群組成上有較大的重疊,組間物種區分度不理想。健康對照組的豐度高于3個疾病組;曲線下降較平緩,表明4組的群落均勻度尚可,但組間均勻度差異不大(圖1C)。

圖1 4組序列數和OTU數及組間分布的韋恩圖
2.3 腸道微生物群落的α和β多樣性比較 比較4組的Chao1、Shanon和Simpson指數,結果(圖2A)表明,3個α多樣性指標在4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α多樣性Shannon稀釋曲線(圖2B)顯示,測序量已足夠,可以反映樣品中絕大多數的菌種信息。采用Weighted Unifrac PCoA的主坐標分析發現,3個實驗組與健康對照組在PC1(36.02%)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PC2(13.48%)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總體而言4組之間的β多樣性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圖2C)。

圖2 實驗組與健康對照組腸道微生物群落的α和β多樣性比較
2.4 在門、屬層面的菌群構成 結果(圖3)顯示:4組在門、屬層面豐度排名前10位的菌群組成。從門的層面來看(圖3A),不論是疾病組還是對照組,腸道菌從高到低依次是厚壁菌門(Firmicu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和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其中,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的總豐度超過50%。從屬的層面來看(圖3B),4個組里擬桿菌屬(Bacteroides)均占統治地位,剩余菌屬的比例略微存在差異,但總的構成比差異不大。4組中,普氏菌屬(Prevotella)的比例僅次于擬桿菌屬(Bacteroidaceae),共占據了總菌群豐度的約30%。

圖3 焦慮、抑郁組與健康對照組在門層面(A)和屬層面(B)的菌群構成
2.5 組間菌群差異 結果(圖4)顯示:由圖4A可見,單純抑郁(G1)和單純焦慮組(G2)中,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和TM7菌門豐度均與健康對照組(G4)顯著不同(酸桿菌門:G1vsG4,P=0.008; G2vsG4,P=0.014;TM7菌門:G1vsG4,P=0.046; G2vsG4,P=0.037)。其中,單純抑郁組中酸桿菌門和TM7菌門均低于健康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8和P=0.046);藍藻菌(Cyanobacteria)在單純抑郁組的豐度也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P=0.031)。在單純焦慮組中,變形菌門的豐度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提示變形菌門減少可能在焦慮發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圖4 各疾病組與健康對照組在門、屬層面的菌群構成差異
在屬的層面上(圖4B~4D),不論在單純抑郁還是單純焦慮組中,普氏菌屬的豐度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1和P=0.035);焦慮合并抑郁組中,未分類腸桿菌屬(unclassifiedEnterobacteriaceae)的豐度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9)。此外,從各組的差異菌豐度比較來看,單純焦慮組(G2)與健康對照組(G4)差異較多,共篩選出23個差異菌屬;而單純抑郁(G1)與抑郁合并焦慮(G3)組差異菌屬較為相似。
2.6 組間差異菌屬分析 結果(圖5)顯示:與健康對照組相比,3個疾病組的差異菌屬存在不同,其中單純抑郁組、單純焦慮組的梭菌屬(clostridium)豐度均顯著降低(圖5A)。此外,本研究還發現霍爾德曼氏菌屬(Holdemania)在單純焦慮組(G2)中顯著高于其余各組(圖5B),而剩余3組中的Holdemania屬豐度大致相當。柯林斯菌屬(Collinsella)在單純抑郁組和抑郁合并焦慮組,組內分布差異較大,2組菌屬豐度的中位數均低于健康對照組。

圖5 4組間梭菌屬(A)、霍爾德曼氏菌屬(B)和柯林斯菌屬(C)分析
2.6 疾病組與對照組代謝途徑差異 結果(圖6)顯示:疾病組與對照組KEGG代謝途徑差異。

圖6 各疾病組與健康對照組的代謝途徑的差異
單純焦慮組的差異代謝途徑較多,具體體現在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代謝、氨基苯甲酸酯(aminobenzoate degradation)降解、磷酸轉移酶系統(PTS)、輔酶Q的生物合成(ubiquinone biosynthesis)、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unsaturated fatty acids)、脂肪酸代謝、谷胱甘肽代謝等方面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單純抑郁組與抑郁合并焦慮組均有鈣信號通路(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和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相關代謝通路的變化。此外,單純抑郁組的丙酮酸代謝(pyruvate metabolism)途徑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4)。抑郁合并焦慮組膽汁分泌(bile secretion)代謝途徑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5)。
3 討 論
本研究共納入117例受試者為研究組,120例健康人為對照組。根據PHQ-9和GAD-7量表得分,將研究組進一步細分為單純抑郁組、單純焦慮組和抑郁合并焦慮組,分別與健康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4組在α和β多樣性上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門的層面上,單純抑郁組中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和TM7菌門豐度構成比低于健康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8、0.046);單純焦慮組中,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的豐度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P=0.035)。在屬的層面上,與健康組相比,3個疾病組的差異菌存在不同,其中單純抑郁組、單純焦慮組和健康對照組相比梭菌屬(Clostridium)均顯著降低。類似的研究[13-14]也報道了抑郁患者中梭菌目(Clostridiales)和梭菌屬(Clostridia)的降低,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整體上看,單純抑郁組與抑郁合并焦慮組的差異菌屬較為相似,2組普氏菌屬(Prevotella)的豐度均顯著降低(P=0.031、0.007)。
在代謝途徑方面,本研究發現單純焦慮組的差異代謝途徑較多,單純抑郁組與抑郁合并焦慮組均有鈣信號通路和光合作用代謝通路的變化。其中,單純抑郁組的丙酮酸代謝途徑高于健康對照組,提示可能與抑郁的發病機制存在關聯。榮晗等[15]通過對抑郁患者進行鳥槍法宏基因組測序,同樣探討了代謝途徑的差異,發現與對照組相比,抑郁癥組的泛酸酯、輔酶A合成和色氨酸代謝通路表達較高,而P53信號通路表達較少。
針對抑郁癥患者的菌群改變,國內課題組已有類似的研究。Jiang等[16]率先對46例抑郁癥患者和30例健康對照的糞便樣本進行了16S rRNA測序,發現抑郁癥患者與健康對照組相比, 擬桿菌、變形菌和放線菌增多,厚壁菌的數量減少。隨后,Zheng等[17]發現,抑郁癥患者的腸道菌群與健康對照組相比,α多樣性無顯著差異,而β多樣性顯著不同。具體表現為放線菌增多,而擬桿菌減少。以上實驗與本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可能是因為樣本量、測序平臺、樣本保存方法、入組患者的人口統計學、以及抗抑郁藥的使用等差異造成的[18]。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目前腸道菌群的相關研究還存在較大的不一致性,可能影響結果的混雜因素也較多。因此,如何做好有關因素的控制以產出高可信度的結果,是所有研究者面臨的挑戰。
針對發現的菌群改變,Zheng等[17]進一步將抑郁癥患者的糞便移植到了無菌小鼠,發現小鼠發生相應的菌群紊亂,并表現出抑郁樣的行為。而接受健康對照組糞便的小鼠未表現出類似的行為。由此可見,腸道微生物極有可能通過多種途徑,例如影響HPA軸和迷走神經,進而在焦慮、抑郁等神經精神疾病的發生發展中發揮作用。
近年來提出的“微生物-腸-腦軸(MGBA)”假說被認為是參與菌群和精神疾病互作的重要機制。根據Pu等[19]的小鼠試驗結果,抑郁表型通過移植糞菌的傳遞很可能與MGBA有關。Bai等[20]研究了B類清道夫受體CD36,發現其在抑郁的小鼠和患者中均表達上調。敲除CD36以后,小鼠海馬的NOD(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樣受體家族3(NOD-like receptors,NLRP3)炎性體信號通路下調,盲腸細菌的α多樣性增加。因此,CD36分子可能通過調節微生物-腸-炎癥體-腦軸影響抑郁樣行為。Deng等[21]還發現,慢性束縛應激會導致MGBA功能的異常和犬尿氨酸代謝通路的改變。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MGBA的作用機制將變得更加清晰。
抗抑郁藥也是本類研究的重要混雜因素[22-23]。Lukic'等[18]發現,與對照組相比,抗抑郁藥降低了小鼠腸道菌群的豐富度并增加了β多樣性。Lis'kiewicz等[24]也發現,在精神病醫院進行了6周的艾司西酞普蘭治療后,糞便微生物群中的α多樣性增加。然而,朱建立等[25]研究了27例首發抑郁癥的患者,通過對患者的糞便進行16S rRNA測序發現,在多樣性指數方面,首發抑郁癥組和健康對照組的菌群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抗抑郁藥對于患者菌群的影響。本研究中,患者僅表現為抑郁、焦慮狀態,未達到相關用藥指征,因此不存在抗抑郁藥物對菌群的影響。對患者的腸道菌群進行動態隨訪有助于發現從健康到抑郁、焦慮發病過程中的菌群變化,并進一步發現相關機制。
有趣的是,Liu等[26]在對比了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和抑郁癥患者的糞便微生物群后,發現兩者具有相似的改變,并定義了3種不同的“腸型”。由此推測,目前所發現的抑郁癥較健康人群出現的特征性變化并非為抑郁癥所特有,不同類型的疾病表型可能共享著某些腸道菌群的組成改變。
本研究的優勢在于,共納入了237例患者,在國內屬于針對抑郁和焦慮較大樣本量的研究。其次,在患者分組上,根據PHQ-9和GAD-7分數將病例組分成了單純抑郁、單純焦慮、抑郁合并焦慮組,很好地避免了抑郁和焦慮表型的潛在相互影響。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在研究對象選擇上,主要在全科及心理科門診入組研究對象,就診的患者相較于精神專科醫院癥狀較輕,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結果。(2)在焦慮和抑郁癥狀評估方面,選擇了GAD-7和PHQ-9自評量表,均是焦慮和抑郁的篩查量表,相較于漢密爾頓量表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容易出現假陽性,給準確識別符合標準的患者帶來了一定困難。此外,本研究患者的入組主要采取量表的數據,缺乏相應的臨床診斷作為支持。未來的研究需要完善相關的診斷依據,進一步探討具體菌群在抑郁、焦慮發病中的作用機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用高通量測序的方法,探討抑郁和焦慮狀態的患者腸道菌群組成的差異。結果顯示,單純抑郁組、單純焦慮組、抑郁合并焦慮組與健康對照組相比,α和β多樣性未發現顯著差異。在屬的層面上,單純抑郁組和單純焦慮組中梭菌屬的豐度顯著降低。單純焦慮組中霍爾德曼菌屬的豐度顯著高于其余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