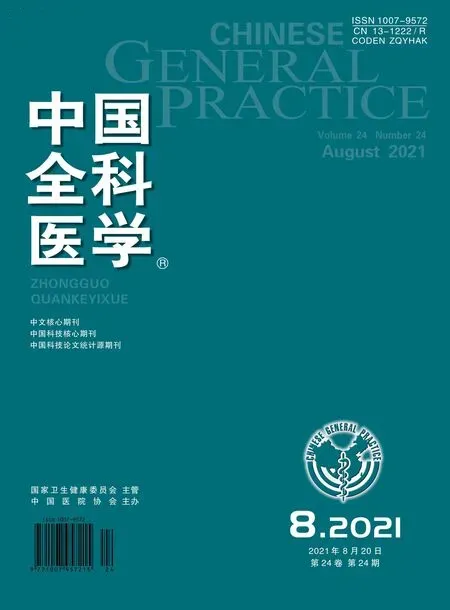甲氨蝶呤和羥氯喹雙聯與甲氨蝶呤和羥氯喹及來氟米特三聯治療活動性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頭對頭研究
陳梅卿,巫斌,劉復安,陳子卿,林慶衍,高藝桑,孫月池,陳世菊,唐國寶
本研究背景:
類風濕關節炎是一種常見的具有很強致殘性的自身免疫性炎癥性疾病,迄今仍缺乏根治性藥物。甲氨蝶呤、羥氯喹雙聯與甲氨蝶呤、羥氯喹、來氟米特三聯是臨床常用的治療活動性類風濕關節炎的聯合用藥方案,但尚缺乏頭對頭研究數據。
本研究創新性與價值:
本研究通過頭對頭研究比較了甲氨蝶呤、羥氯喹雙聯與甲氨蝶呤、羥氯喹、來氟米特三聯治療活動性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結果發現甲氨蝶呤、羥氯喹、來氟米特三聯方案有利于減少嚴重胃腸道反應的發生,并可能有一定經濟學效益,對臨床聯合使用多種傳統合成改善病情抗風濕藥物治療活動性類風濕關節炎有一定參考價值。
本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數量少,代表性有限,結果、結論有待更大規模的多中心臨床研究加以驗證。
類風濕關節炎(RA)是一種臨床常見的自身免疫性炎癥性疾病,以關節滑膜慢性炎癥為基本病理特征;其能夠破壞關節結構,具有很強的致殘性,嚴重影響患者身體功能和生活質量。據統計,我國人群RA患病率約為0.42%,且社會經濟負擔較重[1]。近年來,隨著對RA發病機制研究的不斷深入,多種治療RA的新型藥物相繼問世,但由于目前仍缺乏根治RA的藥物,因此絕大多數患者仍需長期使用改善病情抗風濕藥物(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進行維持治療。同時,由于生物制劑DMARDs及靶向合成DMARDs價格相對昂貴,因此傳統合成DMARDs仍是多數RA患者的首選治療藥物。
傳統合成DMARDs有助于改善RA患者臨床癥狀、延緩RA進展[2-3],是RA治療的“基石”,也是國內外相關指南共同推薦的治療RA的一線藥物[4-7]。既往研究表明,2/3的RA患者單用甲氨蝶呤(MTX)或與其他傳統合成DMARDs聯用即可達到治療目標[8-9]。MTX是治療RA的錨定藥[9],且療效與劑量呈正相關,但由于我國人群對大劑量MTX耐受性差,因此臨床上常采用低劑量MTX聯合1種或2種其他傳統合成DMARDs治療RA,其中MTX、羥氯喹(HCQ)雙聯與MTX、HCQ、來氟米特(LEF)三聯是常用組合,但尚缺乏頭對頭研究數據。本研究旨在比較MTX、HCQ雙聯與MTX、HCQ、LEF三聯治療活動性RA的臨床療及安全性,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1月—2019年12月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和廈門大學附屬廈門市仙岳醫院風濕免疫科門診或病房收治的活動性RA患者100例,均符合美國風濕病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于1987 年或ACR/歐洲抗風濕病聯盟(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matism,EULAR)于2009年制定的RA分類診斷標準,并處于疾病中、高度活動期。按照1∶1比例、采用簡單隨機法將所有患者分為雙聯組和三聯組,每組50例。兩組患者年齡、女性比例、病程、壓痛關節數、腫脹關節數、休息痛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分、醫生疾病總體狀況VAS評分(PhGADA)、患者疾病總體狀況VAS 評分(PaGADA)、健康狀況問卷(HAQ)評分、以紅細胞沉降率為基礎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28個關節疾病活動性評分(DAS28-ESR)、紅細胞沉降率(ESR)、C反應蛋白(CRP)、類風濕因子(RF)陽性率、抗環瓜氨酸肽抗體(CCP)陽性率及使用非甾體抗炎藥(NSAIDs)者所占比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批件號:KYH2016-020),所有患者對本研究知情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dual and triple therapy groups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年齡≥18歲且未來2年內無生育計劃;(2)入組前8周內未使用過傳統合成DMARDs或生物制劑DMARDs;(3)DAS28-ESR>3.2。排除標準:(1)活動性結核病、活動性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抗體、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抗體陽性;(2)入組前4周內發生急性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統感染、敗血癥等感染性疾病或正處于急、慢性感染期;(3)嚴重心、肝、肺(包括肺間質病變)、腎等重要臟器疾病或有相應疾病史;(4)血液、內分泌系統疾病或有相應疾病史;(5)除繼發性干燥綜合征以外的其他風濕免疫系統疾病;(6)惡性腫瘤或有相應疾病史;(7)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8)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存在房室傳導阻滯或左束支傳導阻滯;(9)對本研究所用藥物過敏;(10)關節功能為Ⅳ級;(11)白細胞計數<3×109/L或>12×109/L,淋巴細胞分數>50%,血肌酐、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或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高于參考范圍上限。
1.3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潑尼松(生產廠家:山東魯抗醫藥集團賽特有限責任公司,批號:201202)口服,5 mg/次,2次/d,1個月后根據患者病情、意愿逐漸減量或維持原劑量;同時給予奧美拉唑口服以制酸護胃,20~40 mg/次,1次/d。雙聯組患者在上述治療基礎上給予MTX(生產廠家:湖南正清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批號:2012701)聯合HCQ(生產廠家:上海上藥中西制藥有限公司,批號:200768)口服,其中MTX初始劑量為10 mg/次,1次/周,于4周內提高至15 mg/次,1次/周,之后維持至研究結束;體質量>60 kg者HCQ劑量為0.2 g/次,2次/d,而體質量≤60 kg者HCQ劑量為0.1 g/次,3次/d。三聯組患者在上述治療基礎上給予MTX、HCQ、LEF(生產廠家:福建匯天生物藥業有限公司,批號:201201),其中MTX劑量為10 mg/次,1次/周;體質量>60 kg者HCQ劑量為0.2 g/次,2次/d,而體質量≤60 kg者HCQ劑量為0.1 g/次,3次/d;LEF劑量為10 mg/次,1次/d。同時,兩組患者均于服用MTX 24 h后補充葉酸(生產廠家:福州海王福藥制藥有限公司,批號:20113010)10 mg,疼痛難以忍受者可酌情使用NSAIDs,乙型肝炎病毒攜帶(乙肝表面抗原陽性而肝功能正常)者給予恩替卡韋(生產廠家:蘇州東瑞制藥有限公司,批號:210252615)口服以遏制乙型肝炎病毒復制,劑量為0.5 mg/次,1次/d;兩組患者均連續治療24 周。
1.4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治療第12、24周ACR70、ACR50、ACR20、 使 用 NSAIDs者 所 占 比例、潑尼松劑量以評價臨床療效,其中ACR70、ACR50、ACR20分別指患者壓痛關節數、腫脹關節數至少有70%、50%、20%的改善且休息痛VAS評分、PhGADA、PaGADA、HAQ評分、ESR中的3項至少有70%、50%、20%的改善;記錄兩組患者治療期間不良反應發生情況以評價安全性。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完成情況 雙聯組患者中5例脫落、3例因不良反應而于治療第12周前退出;三聯組患者中1例脫落、3例因不良反應而于治療第12周前退出;最終納入療效評估者88例,其中雙聯組42例,三聯組46例。研究流程見圖1。

圖1 研究流程Figure 1 Study flow
2.2 臨床療效 兩組患者治療第12、24周ACR70、ACR50、ACR20、使用NSAIDs者所占比例、潑尼松劑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治療第12、24周ACR70、ACR50、ACR20、使用NSAIDs者所占比例、潑尼松劑量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ACR70,ACR50,and ACR20 responses,proportion of patients using NSAIDs,dose of prednisone between dual and triple therapy groups at 12 and 24 weeks of treatment
2.3 安全性 雙聯組患者中9例出現嚴重胃腸道反應,其中3例因反應劇烈、不能耐受而于治療第8周退出研究,其余6例將MTX改為2次/周服用后胃腸道反應緩解并完成24周的治療。三聯組患者中1例因出現過敏性皮炎而于治療第8周退出研究,經抗過敏治療后癥狀消失;4例出現高血壓,其中2例因難以控制的高血壓而分別于治療第4、6周退出研究,其余2例經降壓藥物治療后血壓控制可。
最終納入安全性評價者94例,其中雙聯組45例,三聯組49例。雙聯組患者嚴重胃腸道反應發生率高于三聯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頭暈、ALT或AST升高(<參考范圍上限2倍)、過敏性皮炎、高血壓、視力下降、口腔潰瘍、消瘦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兩組患者出現的頭暈、視力下降、消瘦因程度較輕而未予特殊處理,ALT或AST升高(<參考范圍上限2倍)、口腔潰瘍經補充葉酸后恢復正常。

表3 兩組患者治療期間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between dual and triple therapy groups
3 討論
雖然MTX是治療RA的錨定藥[9],且現行歐美相關指南推薦其以15 mg/周的口服劑量開始治療、以5 mg/月的速度提高到25~30 mg/周或最高的耐受劑量[10-12],但仍有10%~30%的患者因MTX的不良反應而被迫停藥[13]。研究表明,MTX的不良反應與劑量相關,MTX不良反應發生率隨著劑量增大而逐漸升高,但小劑量MTX(≤10 mg/周)的不良反應輕、長期耐受性較好[14]。由此可知,較高的MTX起始劑量可能導致更多的不良反應甚至導致患者將劑量降低到無效水平或停藥。因此,本研究中雙聯組患者遵照指南推薦意見使用MTX,而三聯組患者MTX劑量始終維持為10 mg/次、1次/周,結果顯示兩組患者頭暈、ALT或AST升高(<參考范圍上限2倍)、過敏性皮炎、高血壓、視力下降、口腔潰瘍、消瘦發生率間無統計學差異,而三聯組患者嚴重胃腸道反應發生率低于雙聯組,提示MTX、HCQ、LEF三聯較MTX、HCQ雙聯治療活動性RA的安全性較高,有利于減少嚴重胃腸道反應的發生,而這與小劑量使用MTX密切相關。
近年來,隨著多種生物制劑DMARDs和靶向合成DMARDs相繼用于治療RA,“達標治療”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但多項高質量臨床研究結果顯示,僅有30%~50%的活動性RA患者采用生物制劑DMARDs或靶向合成DMARDs與MTX聯合治療半年后達到疾病緩解[15-21],但約30%的患者采用MTX單藥治療也能達到疾病緩解或低疾病活動。相較而言,約2/3的活動性RA患者采用MTX與其他傳統合成DMARDs聯合治療更容易實現“達標治療”目標[22]。此外,由于MTX的臨床療效與劑量呈正相關,但我國人群對大劑量MTX耐受性差,因此臨床上常使用低劑量MTX與其他1種或2種傳統DMARDs聯合治療活動性RA。SCHAPINK等[23]研究發現,MTX聯合HCQ治療早期RA的臨床療效優于MTX單藥治療,其原因可能與HCQ增加MTX的暴露有關[24];張幼莉等[25]研究發現,MTX聯合HCQ治療RA能減少MTX引起的肝功能異常,其原因可能與HCQ對溶酶體功能的影響有關[26]。目前,MTX聯合HCQ已成為較公認的有效治療RA的聯合用藥方案,并逐漸在臨床實踐中得以廣泛應用。
LEF主要通過過氧化物酶體側膜激活受體α、差異調節多藥耐藥相關蛋白MRP2/3/4轉運蛋白而增加肝臟對MTX 及其代謝物的暴露,是目前臨床常用的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藥物之一[27]。2002年以來多次更新的ACR、EULAR及我國相關指南均推薦LEF作為治療RA的重要選擇;2015年亞太地區抗風濕病聯盟(Asia Pacific League of Associations for Rheumatology,APLAR)制定的RA治療建議推薦LEF作為一線藥物[28]。既往相關指南推薦的LEF劑量為20 mg/d,但隨著藥物應用經驗的積累及對LEF的認識逐步深入,人們發現部分患者采用小劑量LEF(10 mg/d)即可獲得良好的臨床療效,部分患者使用大劑量LEF(30~40 mg/d)仍很安全,因此針對不同個體或不同病程的活動性RA患者,采用不同劑量LEF可能更合適;需要注意的是,與 MTX單藥治療相比,LEF 與 MTX 聯合治療雖可提高活動性RA患者臨床療效,但會增加胃腸道不良反應和肝臟毒性發生風險。本研究中三聯組患者LEF劑量雖為10 mg/次,1次/d,但兩組患者治療第12、24周ACR70、ACR50、ACR20、使用NSAIDs者所占比例、潑尼松劑量間均無統計學差異,提示MTX、HCQ雙聯與MTX、HCQ、LEF三聯治療活動性RA的臨床療效相當,而使用小劑量LEF可能有助于減少MTX劑量。
HUANG等[27]研究發現,活動性RA患者采用MTX(12.5 mg/次,1次/周)與LEF(20 mg/次,1次/d)聯合治療期間肝功能損傷發生率為19.15%。本研究中雙聯組、三聯組患者ALT或AST升高(<參考范圍上限2倍)發生率均為4%,這可能與MTX、LEF用量減少及聯合HCQ使用有關,但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雙聯組、三聯組治療第12周分別有6、5例患者停用潑尼松,治療第24周分別有17、20例患者停用潑尼松,且初發RA患者能更早地減撤潑尼松;雙聯組、三聯組治療第24周分別有13、11例患者潑尼松用量仍維持在7.5 mg/d以上,且均為病程長、反復應用過多種藥物的難治性RA患者,提示早期使用傳統合成DMARDs有利于改善活動性RA患者預后,但由于研究設計之初并未將停用或減撤潑尼松情況列為觀察指標,因此未進行統計學分析,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進行完善。
總體而言,MTX、HCQ雙聯與MTX、HCQ、LEF三聯治療活動性RA的臨床療效相當,安全性和耐受性均較高,但MTX、HCQ、LEF三聯方案有利于減少嚴重胃腸道反應的發生。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筆者建議早期RA患者首選MTX(15 mg/次,1次/周)+HCQ治療,若出現嚴重胃腸道反應則可采用減少MTX劑量、加用LEF(10 mg/d)的治療策略。
作者貢獻:陳梅卿、巫斌進行文章的構思、研究的設計、結果分析與解釋,負責撰寫論文;陳梅卿、巫斌、陳子卿、林慶衍、高藝桑、孫月池進行數據收集與整理;劉復安、陳子卿、高藝桑、孫月池、唐國寶負責招募患者;劉復安進行統計學處理;陳世菊負責論文的修訂;唐國寶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