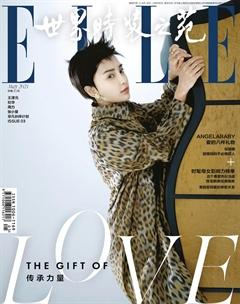張小斐:走在演員這條路上

短短一個春節過去,全國觀眾都通過《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記住了一個女演員的名字,她叫張小斐。
從農歷大年初四開始跑路演,這之后的一個月,張小斐基本沒休息,行程排得最緊時,一天跑了3個城市的8家影院,體力已經到了負荷的臨界點。但那時候,她的大腦依然是興奮的,反復說著感謝觀眾的話。
這些真實又夢幻的場面,從不敢想象到真實發生,只隔著電影上映這一件事。
雖然在此之前,張小斐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演員,甚至在《你好,李煥英》上映前一天,她還在春晚舞臺上演小品。但到了大年初一,當她買了張票,悄悄藏在北京的一個電影院里,跟觀眾一起看完了一場自己主演的電影之后,她知道,一切可能要開始有點兒不一樣了。
“藏在里面,你能感受到在每一個笑點或者哭點上觀眾最直接的反應,觀眾的反應比我想象中的還要更好。”觀眾的第一波反饋,對一部影片的前途至關重要。那一刻,她開始相信,這部電影,成了。
至于那些隨著電影的熱度上升,在網上陸續發酵的熱搜話題,就都是后話了。跑路演期間偶爾的間隙,她也會打開手機,以電影名為關鍵詞搜索網友們的反饋,但完全沒料到自己的名字也正在成為一個新熱點。
電影上映后,張小斐的微博粉絲漲了200多萬,抖音粉絲漲了快1000萬,她在社交網絡上的數據迅速增長。而對張小斐自己來說,在“一夜爆紅”后,她一邊真切感受到工作量的急劇上升,一邊又帶著點兒冷靜的抽離感去思考自己當下的境遇。“其實這一夜,我走了14年。”這個時間長度,足夠讓一個人面對這一切變化時,既開心、知足和感恩,又能保持清醒和淡定。她還是那個演員張小斐,區別只是被更多人知道了而已。

1_
和李煥英不同,張小斐不是一個性格上足夠樂觀的人。
現在回想起電影上映前自己對結果的預期,張小斐并沒有立下遙不可及的宏圖大志:“我希望這部戲播完之后,能從一個知名度不太高的演員,變成一個被大家發現的好演員,這就是我當時的野心。”哪怕前幾年的同名小品早就收獲過不少觀眾的口碑和眼淚,張小斐也不敢想這部電影能創造怎樣的票房奇跡,更別提現在被全網熱情喊“媽”的盛況,這些在當時,甚至都不能被算進“幻想”的范疇里。
現在回想起來可能算是“謙虛”的謹慎,或許是因為在過去的14年里,張小斐對事業也都沒產生過什么幻想。“我好像沒什么規劃,因為規劃也沒用,沒人找啊。”
雖然從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那一刻起,張小斐就知道演員是個被動的職業,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種靠外表就能驚艷眾人的“第一眼美女”,但真正體會到“自己需要被行業慢慢認識”這個事實,她還是花了比想象中更久的時間,內心的起伏也超出思想準備。
“剛畢業的時候去見組,覺得自己每天的收獲都是0。這種事情多了,打擊和焦慮肯定是有的。”最頹喪的時候,甚至電視里的熱播劇對她都是刺激,因為在觀眾看來那只是部劇,在張小斐眼里卻象征著機會。“我也好想演這樣的戲啊,但又覺得這種戲是不是永遠也不會找我來演了。”

好在張小斐并不是一個就此消沉的人。雖然見組的結果都“石沉大海”,但當時的她還在藝術團里有份當主持人的穩定工作,總算是有點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我見組也不太多,因為后來就不怎么去了。”那時候,支撐她還在當演員這條路上走下去的,就是老師的反復鼓勵:其實她入學成績非常優異,當年以第三名的成績考進表演系,閱人無數的老師們也預言說她會是個大器晚成的演員,會成為“大青衣”,但要等、不能急。
聽話的她,真的就這樣一路等下來。直到幾年后認識了賈玲,張小斐才以“小品演員”和“喜劇演員”這樣的身份開始被觀眾認識—雖然從那時起,她要表演在學校時就覺得最難演、最害怕的喜劇,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她開始把自己曾經學過的正劇表演和喜劇表演融會貫通,“有了一種你知道自己被打開了的感覺”。對她來說,在表演這條路上的探索,沒有一天算是被浪費的,只不過是需要個機會厚積薄發。
所以哪怕是回顧起自己走到現在都經歷了什么,張小斐也從不覺得這些時間只是坐在冷板凳上的獨自等待。“實際上我覺得我沒那么慘,還挺幸運的。”比起被大家同情怎么努力了這么久才獲得命運的獎勵,張小斐更希望自己能成為別人堅持下去的正向鼓勵。
因為這段記憶,在她心里,雖然坡度和緩,但至少是一路上揚的。
2_
不僅外界看到了她,她最重視的家里人,尤其是媽媽,在電影上映后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回應。
看到自己的女兒因為扮演李煥英這個“媽媽”家喻戶曉,張小斐的媽媽自然也為她開心和驕傲,不過跟之前不一樣的是,這次是第一回,媽媽主動打來電話表揚她。
“看完這個電影,我媽特意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她說我一直沒有夸過你,這次就是想說,你真的給媽長臉了!”跟李煥英這個善于表達感情的媽媽不同,張小斐的媽媽更像中國傳統式家長,習慣用行動證明愛意,卻很少通過語言說出最直接的肯定。“我覺得這可能也是電影給她的一個啟發。”
其實張小斐之所以走上演員這條路,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來自媽媽的支持。如果沒有小時候媽媽帶她去學跳舞,也不會有后來成為演員的機會。媽媽對她的愛,一直都深沉而低調。
“我媽自己就是個文藝愛好者,但在那個年代,很少有機會能去接觸這些東西。所以在我小時候,雖然還不知道我適合、擅長做什么,但她還是希望能多給我提供一些機會,讓我長大了可以有機會離開鞍山,去大城市看一看。”
在張小斐的兒時記憶里,印象最深的畫面,就是每天放學回家,別的同學都休息了,自己卻要被媽媽帶著,坐公交車去很遠的地方學跳舞。跳舞本身就苦,她還要在訓練之外,付出更多的體力來維持這份堅持:“在東北那種天寒地凍的地方,每天晚上8點多練完,都已經沒有車了,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到家。那時候我就夢想著家里能有一輛車,這樣我就能在那條漫長的路上睡一覺了。”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她11歲正式去北京學舞蹈。雖然很累,張小斐卻從沒覺得媽媽的鞭策是束縛:“我媽希望我努力,但不會說你必須怎么怎么樣”。跳舞是媽媽為她多選的一條路,但歸根結底還是希望她健康快樂,甚至后來考電影學院也是張小斐自己的堅持。那時候,媽媽已經開始擔心她會不會為了事業而承受太多壓力,母女兩人反過來,想主動往前沖的人是她自己了。
“我媽當時覺得我已經很好了,說這樣就行了,我說不行。如果我沒去做這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老了都會后悔的。”從此,媽媽變成了在張小斐身后默默支持的人,看著張小斐獨自在北京這個陌生的城市一路打拼,滿滿的惦記都藏在心里,兩個人對彼此的愛卻總是“舍不得”講出口。
“如果直白地對我媽說感謝,我會很害羞,所以就在不經意間表示。比如吃飯的時候說起現在,我就對她說,那不都是因為你在堅持嗎?小時候我懂什么呀?”長大了的張小斐,早就明白了要感謝媽媽潛移默化教給自己這些堅強和堅韌,媽媽也一樣,對她的成績看在眼里,樂在心上:“比如我在鞍山給她買了個房子,她就會說謝謝我的寶啊,媽媽也沾了你的光了。”這些外人看起來簡直算是“客氣”的交流,是張小斐和媽媽特有默契的一種溝通方式。
直到這一次的《你好,李煥英》上映,張小斐通過扮演媽媽,更懂得了媽媽這一層身份所承載的責任,媽媽也因為看到“別人家媽媽”的故事,發現原來母女之間的愛直接表達并不尷尬。這種因為電影帶來的變化,是張小斐意料之外的收獲。

3_
結合自己從小的親身經歷,再看到電影上映后觀眾在網上發出的評論,張小斐覺得《你好,李煥英》之所以能大受歡迎,除了故事本身感人至深,也因為它在討論母愛的表達方式,這是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
過去,很多媽媽習慣為孩子犧牲,而很少去關心自己。“有時候出去吃飯,媽媽還是習慣把好吃的留給孩子,自己卻不吃。”每次看到這樣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畫面,張小斐都感念母親的偉大,但又忍不住思考,或許能有什么其他辦法,讓一個女性在悉心照顧孩子的同時,不至于忽視了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我看到現在很多80后、90后當了媽媽,她們在付出的同時,也會關注自己,有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其實這對孩子也有好處,因為能讓孩子也知道要關注自己。”
原來我們說到“女性意識”,可能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女性是否可以通過勞動擁有自由和獨立,但當時光流轉過一代人,當張小斐這樣年紀的女孩兒早就習慣了靠自己去實現夢想,不把所謂的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屬于她們的女性話題,在向著更廣義的“平等”去延伸。
電影的效果反映著觀眾的心理狀態,觀眾的反饋也同樣會影響今后的電影題材。
《你好,李煥英》刷新了票房紀錄,作為演員,張小斐開始好奇,是不是以后能有更多女性視角的作品受到重視:“我們做了這樣一個關于女性的電影,放到市場上受到觀眾認可,這可能也會帶來一個挺好的影響,就是以后投資人可能也會把眼光往女性身上多挪一挪。”自幼練舞,她早就習慣了獨立,并沒有感受到太過強烈的性別差異,但畢竟時代變了,觀眾變了,選擇也是時候豐富起來了。
4_
至于這部電影的一戰成名,為張小斐到底帶來了什么,其實她還沒做太過長遠的規劃。她還是像原來一樣,沒有過多樂觀的想法,也沒把現在的名氣當成負擔,去左右她的下一個選擇。
“好多朋友問我有沒有什么變化,還有人開玩笑問我:你浮躁了嗎?我說我這個歲數,要是再浮躁的話,那我也真的是太浮躁了吧!”
第一部擔任主演的電影作品,票房就沖到了53.69億這個數字,任誰都能知道自己從此擁有了挑選的資本。她可以借著這個機會演個截然不同的新角色去轉型,也可以再挑個類似題材但成本更高制作更精良的,就此在喜劇電影領域立住形象……但這些都不是張小斐的標準,“我不挑題材,還是要看作品”。她不太看重那些作品之外的事情,只關心有沒有一個足夠完整的好作品,需要她去演出來。
可能伴隨著大把機會一同到來的巨大壓力,在她這兒也不是什么心理負擔。演員們總會遇到類似的境況,演了一部票房或口碑爆棚的作品后,下一部作品由于自己和觀眾期待過高,反而很難再續輝煌。但處在事業上升期的張小斐,雖然還沒具體選定下一部戲的劇本,卻早就把心態調整得足夠冷靜:“我總不能不接下一部戲,所以這時候就要往正向想。盡量跟好的團隊合作,找好導演、好劇本,好好去演,作品就不會太差。至于其他的,就先不去想。”
那當她既不介意下一部作品的方向,也不擔心之后的票房可能難以超越現在這部代表作,在表演這條路上,她覺得真正會左右她未來的因素是什么?“我希望能保持我的敏感度,還希望自己的領悟力能更強一些。”
對她來說,表演是個需要收集各種情緒的工作,演員甚至要注意,自己如果太過快樂可能會影響演技。“敏感這件事情,對普通人來說不是很好,可能會讓你容易受到傷害,在生活中,其實有點鈍性的人更快樂。但對演員來說就需要保持敏感,這是演員很重要的東西。”當別人因為年紀和閱歷的增長,擁有了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源,并且日漸追求精神上的放松和“想開”,張小斐反而關心著自己是否還擁有小時候那樣的敏感。
“有時候年紀漸長,可能看開的東西更多了,我有時候甚至覺得,會不會人生就是這樣的?或者自己會不會去選擇更容易的那條路,過一種更輕松的生活?”但每當被這樣的懷疑所考驗,張小斐想起每次表演時要調動內心各種復雜情緒的實際需要,最終給自己的答案總是“不”:“我覺得作為演員,也許太成長、太去看透一些事情,不是什么好事。”
當所有通過《你好,李煥英》認識了張小斐的觀眾,都在好奇她下一次會以什么形象出現在鏡頭前,其實用了14年才走到這個位置的張小斐,還繼續在她為自己設定好的那條演員道路上前進著。雖然從一開始她就沒有定下太明確的目的地,沒想過要拿什么獎或者要演誰的戲,但只要她還保持著她的敏感度與領悟力,拿著這些一路披荊斬棘的“武器”,風景就總會日漸清晰,值得她走過去的下一站,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