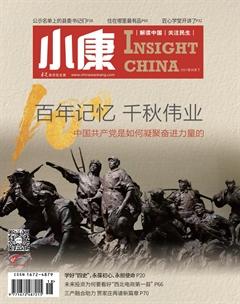兩彈一星 塵封歲月
郭玲

歷史銘記。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已經搬離“兩彈城”20多年。曾經在此工作的幾代科研工作者很多已經離去或者逝去,但歷史的天空將永遠鐫刻他們的名字。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道門是進入九院核心區域的最后一道防線,是中國最高機密的所在地,對內叫作‘902基地,對外則稱‘國營曙光公司,就連通信地址都沒有綿陽或梓潼的字樣,而是統一使用‘成都501信箱。”“兩彈一星”梓潼紀念館講解員范恒每一次帶領游客參觀,都是以精英門為起點。
精英門上,“兩彈城”三個紅色大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兩邊門柱上刻著“紅云沖天照九霄,千鈞核力動地搖。二十年來勇攀后,二代輕舟已過橋”。這是1984年,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后,時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鄧稼先滿懷豪情寫下的詩句。
位于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長卿山下的“兩彈城”,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簡稱九院)舊址,曾經是我國最神秘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之一,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9位先后在這里工作生活。
幾十年前,這里還是一片常人不能涉足的禁地。直到多年后,這片禁地連同它所承載的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才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
“消失”的科學家們
1958年8月,北京,平素不愛照相的鄧稼先走進照相館,與妻子和一雙兒女留下一張珍貴的全家福。當時,鄧稼先34歲,他的妻子許鹿希30歲,兩人結婚5年。拍完照片后,鄧稼先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28年后,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多年的秘密經歷才得以披露。
這張全家福如今就掛在“兩彈城”鄧稼先舊居中,靜靜訴說著一段往事。1958年,回國8年、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原子核物理的鄧稼先領到一份“絕密任務”。時任二機部(核工業部)副主任的錢三強找到鄧稼先,鄭重地對他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么樣?”鄧稼先心里明白,搞原子彈這個“大炮仗”不僅非常危險,而且非常艱難,甚至必須隱姓埋名。盡管如此,年輕的鄧稼先還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這一年,他進入中國核武器研制隊伍,并很快成為一名關鍵人物——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負責人。
“596”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中國在研制原子彈初期,得到了蘇聯的幫助。然而1959年6月,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專家,帶走了圖紙資料,并聲稱“中國要是離開我們的援助,休想在二十年內造出原子彈來”。為了記住這一天,九院以“596”為第一顆原子彈工程代號。為了爭口氣,中國的科研人員發憤圖強,日夜三班倒,1年多的時間里,連續9次運算,硬是用手搖計算機、拉力計算尺、算盤算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數據。
就在蘇聯撤走專家的第二年,一位正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開展基本粒子研究的中國科學家悄悄回國,成為中國核武器研制隊伍中年齡最大的科學家。就在世界科學界尋找這位著名中國科學家的時候,他已經化名“王京”,隨著解放軍的軍車,一路顛簸向著西北大漠深處挺進。此后17年,王淦昌在中國科學界徹底消失了,連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多年后,王淦昌的女兒回憶道:“我們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有些鄰居問我父親到哪兒去了,我母親說父親在信箱里。”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試驗場爆炸成功。《人民日報》號外記錄下了中國科技的這一高光時刻。它的背后是無數人的辛苦付出。
為了推動核試驗,1960年前后,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學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技能人員,以及解放軍指戰員,陸續云集青海海晏縣金銀灘,以“國營221廠”名義建設核武器基地。這是我國第一個核武器基地。
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不久,出于當時國際環境的考慮,黨中央決定將核武器研制基地遷至四川腹地的山區。“902基地”成為我國第二個核武器基地。“國營221廠”的大批科研人員和主要設備,乘坐軍事專列,分幾批秘密由青海海晏遷至四川梓潼。從此,中國核工業先驅們,積極建設梓潼基地,形成了以學科專業分工協作、較為完整的核科研、設計、實驗、定型、生產體系。
“902基地”留下了鄧稼先、王淦昌、于敏等科學家的足跡,鄧稼先在此居住了14年,王淦昌居住了8年。
中國也在無數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艱苦攻關中完成了“兩彈一星”的所有進程。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讓我國成為五個核大國中實現從原子彈到氫彈突破速度最快的國家。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1980年,中國又成功發射了洲際導彈……
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表彰并授予當年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于是,這些遠離妻子、藏身大山、隱姓埋名的英雄們,終于從幕后走到臺前。
鄧稼先與《命運交響曲》
這幾年,在范恒接待過的參觀游客中,有很多是當年參與“兩彈一星”研制工作以及核基地建設的老科研人員、老建設者,以及他們的后輩。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長胡仁宇院士曾經來參觀“兩彈城”。身為我國第一批核武科學家之一,他為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設計了核心部件,并且先后參與過十多次大型核試驗。參觀過程中,眾人邀請胡仁宇去和自己的雕像合影,卻被他一口回絕。“他說,‘兩彈一星是千千萬萬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比我有本事的人有很多,我算老幾呢?”這樸實而又謙虛的話語讓范恒深受感動。
范恒經歷了很多這樣的故事,對于那些“兩彈一星”的親歷者來說,掛在嘴邊的都是“集體的力量”“祖國的榮耀”,而從沒有提及自己。“正是無數的他們,將‘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永久地鐫刻在中國大地上。”
鄧稼先舊居中的老式留聲機是范恒每一次都要向參觀者重點介紹的物品之一。喜愛音樂的鄧稼先偶爾會聽一聽音樂,作為工作之余的休閑。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陪在他身邊的警衛員游澤華總是會聽到那部留聲機中傳來《命運交響曲》的旋律——因為意外接觸到核輻射導致內臟受損,鄧稼先患上了直腸癌。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轉年,他的癌癥擴散已無法挽救。
即使在住院期間,鄧稼先仍然心系核事業。當時他在醫院的病床上與九院的同事們商討良久,寫了一份關于我國核事業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書,為我國核事業在以后10年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鄧稼先去世后的第十年,1996年7月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實驗,當晚,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
我國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為什么要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發展核武器技術?”對于這個問題,“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程開甲有過一句擲地有聲的回答:“世界上最可靠的安全,就是讓敵人知難而退。”
時間回到1951年,在法國巴黎大學剛剛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青年物理學家楊承宗,帶著十幾箱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踏上歸國征途。臨行前,時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約里奧·居里特別和他進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談話:“你回去告訴毛澤東,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呢,就必須自己先要有原子彈。”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已經搬離“兩彈城”20多年。褪去昔日神秘的面紗,這里已經成為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全國第一批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四川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曾經在此工作的幾代科研工作者很多已經離去或者逝去,但歷史的天空將永遠鐫刻他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