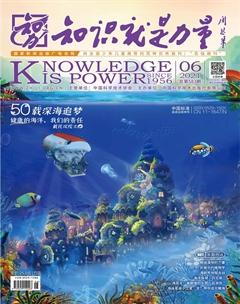海洋噪聲何時休
王治鈞

海底的人造噪聲
人類對海洋資源進行工業(yè)化開發(fā)以來,噪聲污染不斷增長,噪聲來源主要包括有海底油氣勘探、使用超強聲吶系統(tǒng)的軍民船只、繁忙的航運以及沿海的開發(fā)設施等。其中,最明顯的是軍事聲吶和地震勘探爆破,它們能直接導致海洋哺乳動物擱淺和死亡。
以海底油氣勘探為例,用來尋找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設備使用勘探氣槍超高速噴出壓縮氣體在水下產(chǎn)生巨大聲響,聲音抵達海底后產(chǎn)生回聲,通過水聽器收集并分析這些回聲,勘探船可以繪制出海底地質(zhì)圖,判斷海底油區(qū)分布狀況。這套設備每隔10~15秒產(chǎn)生一次爆破聲,需要24小時不間斷運作,并探測數(shù)月才能完成一片海域的地質(zhì)勘探圖。
按照美國海洋能源管理局的標準,高爆氣槍的分貝值應該設置在160分貝左右,然而實際操作時,有些高爆氣槍甚至可以達到260分貝。
海洋學家在幾百千米之外利用水聽器很容易就能聽到這種持續(xù)的爆破聲,敏銳的“海洋居民”同樣會受這些聲音影響。
海底噪聲污染源還有很多,比如地質(zhì)勘探成功之后,進行的石油天然氣開采會有持續(xù)的噪聲產(chǎn)生;在過往幾十年,全球海洋運輸量大幅增加,船舶越來越大、動力越來越強,海運船隊的低頻噪聲已經(jīng)增加幾十倍;再加上軍民船只的聲吶設備、海上風電場的運營噪聲等各種人造噪聲紛紛注入海洋,其影響程度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不可小覷的海底噪聲
聲音在海水中到底能傳播多遠?1960年,科學家做了一項超長距離實驗,他們在澳大利亞珀斯海灣外靠爆炸制造了幾聲巨響,結果約3.6小時之后,2萬千米之外的百慕大附近居然可以探測到這個聲音。
1991年,多國海洋科學家在南極極地偏遠的赫德島做了一次重低音遠洋傳輸測試(Heard IslandFeasibility Test),實驗目的是通過聲音測量,確定海洋的暖化效應。實驗人員將揚聲器放置在水下500米,不斷播放出一個重低音,結果這個重低音在傳播3個小時后,在美國和加拿大東西兩側(cè)海岸線都被成功地監(jiān)聽到,這表明這個重低音已傳播到了全球大多數(shù)的海域。
這兩次實驗都表明,海底聲音傳播的距離和區(qū)域范圍是非常驚人的,人造噪聲對海洋動物的影響范圍也遠超我們的想象。

海底生物的“殺手”
從浮游生物到鯊魚,大部分海洋生物都可以感知環(huán)境中的聲音,而不同物種對聲音的感知也是不同的。例如,海洋無脊椎動物如甲殼類、貝類、珊瑚等物種雖然沒有聽覺系統(tǒng),但它們通過敏銳的感覺器官在水中感覺到聲振,從而平衡重力,而噪聲環(huán)境會使它們產(chǎn)生聲創(chuàng)傷,破壞感覺器官。
一些魚類會通過發(fā)聲和聽覺進行獵食、求偶、溝通,嘈雜的噪聲會干擾動物交流的信號,影響尋找同類或配偶,進而影響其行為反應,令它們變得遲鈍,更容易和船舶發(fā)生碰撞。19世紀60年代之后,強勁的聲吶技術問世,干擾了鯨的回聲定位系統(tǒng),使得鯨大規(guī)模擱淺事件發(fā)生的數(shù)量開始急劇上升。
隨著地震勘探的迅速發(fā)展,氣槍爆破發(fā)出震耳欲聾的噪聲也釀成災難性后果:噪聲在近距離里可以殺死一片浮游生物:或?qū)е掳l(fā)育中的扇貝幼蟲畸形;距離高分貝聲源太近的魚類,由于噪聲,可能會導致它們的魚囊(魚鰾)爆掉。

鯨在正常狀態(tài)下能下潛數(shù)千米,但是當它們聽到各種刺耳噪聲時會拼命下潛和上浮,使鯨引發(fā)身體嚴重不適的潛水病。
海洋生物學家最擔心的是各種噪聲污染帶來的的長期影響:一些動物會產(chǎn)生慢性應激反應,持續(xù)處于緊張不安的精神狀態(tài)中,使其感官疲勞、形成不可逆轉(zhuǎn)的損傷,并導致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如何消除或減少海洋噪聲污染
和其他海洋污染相比,減緩噪聲問題對環(huán)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此前,由于美國東海岸國際運輸?shù)耐芯咳藛T發(fā)現(xiàn),美國東海岸海域中瀕危滅絕的露脊鯨糞便樣本中反映露脊鯨壓力大小的化學指標有所降低,意味著它們的生存狀態(tài)開始轉(zhuǎn)向較為樂觀的方向。2020年,海上運輸因新冠疫情減少,一些海洋哺乳動物和鯊魚開始回流到原來的噪聲區(qū)域。這些例子都表明,減少人為噪聲對保護海洋環(huán)境有明顯效果。

因此,海洋科學家們建議地震勘測時改用海底振動器進行地質(zhì)勘探,要求勘探船緩慢提升音頻,給海洋生物離開噪聲源充分的時間。在特定區(qū)域放慢航行速度可以降低整體噪聲,也能降低海洋動物遭到輪船撞擊的概率:此外,改變螺旋槳降噪設計能減少大部分機械噪聲;而在生物交配、覓食和遷徙的重要季節(jié)和地區(qū),設立保護區(qū)限制人類活動也可以減低噪聲污染。
海洋是自然生物鏈重要的一環(huán),而聲音也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基本要素之一。人類在海洋中的活動日益頻繁,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有著巨大的影響,城市有城市噪聲標準,在海洋中制定噪聲標準已經(jīng)迫在眉睫。希望大家及早樹立憂患意識,明確人類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