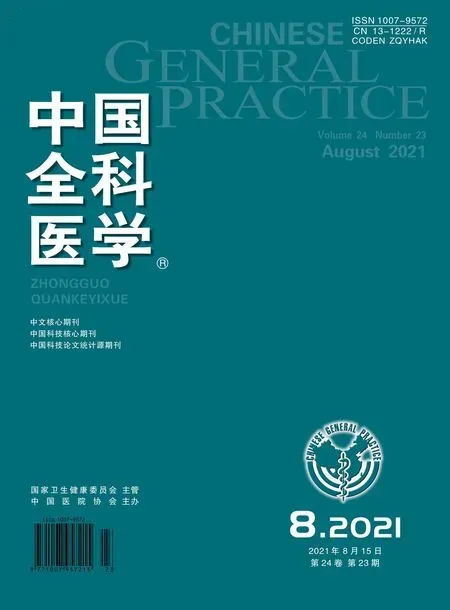動脈硬化與原發性高血壓對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的影響及聯合作用:基于8年的隨訪研究
馬一涵 ,李興雨 ,韓旭 ,劉倩 ,李國 ,吳壽嶺 ,吳云濤 *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發展,心腦血管疾病(CVD)發病率日益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現已居于城鄉居民總死亡原因的首位。中國心血管病患病率處于持續上升階段,據推算心血管病現患人數為2.9 億[1]。CVD給國家及個人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負擔,現階段對CVD危險因素的探究多集中在某一單獨指標,而探究兩種危險因素對CVD聯合作用的研究較少。故探究并尋找CVD可控的聯合危險因素成為重要話題。
動脈硬化是CVD的獨立危險因素,BEN-SHLOMO等[2]通過對17 635例觀察對象的隨訪發現:主動脈脈搏波傳導速度(Aortic pulse wave velocity,aPWV)可以在青年人中識別CVD的高危人群。原發性高血壓也是CVD的獨立危險因素,已經得到眾多研究[3-5]的證實。但以往研究僅關注兩因素的獨立作用,而未同時考慮兩個危險因素的聯合作用。開灤研究是一項始于2006年,目前仍在進行的以功能社區人群為基礎的CVD危險因素調查及干預的前瞻性隊列研究,每兩年對觀察對象進行一次包括血壓測量在內的隨訪,自2010年起隨機對部分觀察對象進行臂踝脈搏波傳導速度(brachial artery pulse wave velocity,baPWV)檢測,并每年對CVD的發病情況進行隨訪,為探討開灤隊列中動脈硬化和原發性高血壓對CVD的聯合作用提供了機會。
1 對象與方法
1.1 觀察對象 本研究依托開灤研究,將在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年 度 隨訪并完成baPWV測量的人群作為觀察對象,對觀察對象進行隨訪并收集CVD數據資料。觀察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隨訪截止時間為2017-12-31。
1.2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參加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年度隨訪者;(2)隨訪同時完成baPWV測量者。排除標準:(1)baPWV測量之前發生心腦血管事件者;(2)踝肱指數(ABI)<0.9者。本研究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并經過開灤總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號:200608)。
1.3 資料收集
1.3.1 血壓測量 受檢者于體檢當日7:00~9:00進行血壓測量,測量前30 min內禁止吸煙或飲茶、咖啡,背靠靜坐15 min。由統一培訓合格的醫務人員采用經校正的臺式水銀血壓計測量右側肱動脈血壓,收縮壓(SBP)讀數取柯氏音第1音,舒張壓(DBP)讀數取柯氏音第5音。連續測量3次,每次測量間隔1~2 min,取平均值作為測量結果。從2014年開始血壓采用歐姆龍(大連)有限公司生產的 HEM-8102A電子血壓計測量。
1.3.2 baPWV測量 采用歐姆龍健康醫療(中國)有限公司生產的BP-20RPEⅢ網絡化動脈硬化檢測裝置采集baPWV 數值,通過網絡連接,直接讀取數據。檢查室溫保持在22~25 ℃,測量前囑受檢者不吸煙,休息5 min以上,錄入受檢者性別、年齡、身高、體質量,囑其穿薄衣,檢測開始時受檢者保持安靜,去枕平臥,雙手手心向上置于身體兩側,將四肢血壓袖帶縛于上臂及下肢踝部,上臂袖帶氣囊標志處對準肱動脈,袖帶下緣距肘窩橫紋2~3 cm,下肢袖帶氣囊標志位于下肢內側,袖帶下緣距內踝1~2 cm,心音采集裝置放于受檢者心前區,左右腕部夾好心電采集裝置,對每位受檢者重復測量2次,取第2次數據為最后結果。本研究取左右兩側baPWV值中的較大值進行分析。
1.3.3 人體測量學指標 靜息心率測量使用日本光電公司生產的ECG-9130P型心電圖機,受檢者檢查前30 min內禁飲酒吸煙,無劇烈運動,靜坐5 min后進行心電圖檢查,選取肢體導聯-Ⅱ導聯描記5個連續QRS波群,計算靜息心率。身高、體質量采用經校正的RGZ-120型體質量秤測量,受檢者脫鞋、脫帽、穿輕便單衣,身高精確到0.1 cm,體質量精確到0.1 kg。體質指數(BMI)=體質量(kg)/身高2(m2)。
1.3.4 實驗室檢測 受檢者空腹8 h后,于體檢當日晨起抽取肘靜脈血5 ml用于生化檢測。生化檢測包括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glucose,FB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尿酸(uric acid,UA)、超敏C反應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等。以上分析均在日立自動化分析儀(7600Auto Matic Analyzer)上進行。
1.3.5 其他指標 吸煙、飲酒、體育鍛煉情況,糖尿病,服用降壓藥物及降糖藥物情況。
1.3.6 CVD隨訪方法 以觀察對象完成baPWV測量時點為隨訪起點,以發生CVD為隨訪終點,CVD包括腦卒中和心肌梗死,腦卒中包括出血性腦卒中和缺血性腦卒中,診斷標準采用世界衛生組織標準[6-7];發生≥2次事件者以首次發生事件的時間和事件為結局,未發生事件者隨訪截止時間為死亡時間或隨訪時間(2017-12-31),每年由經過培訓的醫務人員查閱觀察對象在開灤集團所屬各醫院及市醫保定點醫院的住院診斷并記錄終點事件的情況,診斷均由專業醫師根據住院病歷進行確認。
1.4 相關定義 平均動脈壓(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一個心動周期中動脈血壓的平均值,計算公式為:MAP=(SBP+2×DBP)/3。原發性高血壓[8]:SBP ≥ 140 mm Hg(1 mm Hg=0.133 kPa) 和/或DBP≥90 mm Hg或雖然SBP<140 mm Hg和/或DBP<90 mm Hg但使用抗高血壓藥物或有原發性高血壓史。糖尿病[9]:空腹血糖≥7.0 mmol/L和/或雖然空腹血糖 <7.0 mmol/L但使用降糖藥或有糖尿病史。動脈硬化[10]:baPWV≥1 400 cm/s。吸煙定義為近一年平均每天至少吸一支煙。飲酒定義為近一年平均每日飲白酒(酒精含量50%以上)100 ml,持續至少一年以上;體育鍛煉定義為鍛煉次數≥3次/周,持續時間≥30 min/次。
1.5 分組 根據觀察對象完成baPWV測量時隨訪情況(是否患有原發性高血壓)以baPWV是否>1 400 cm/s(動脈硬化)將觀察對象分為非原發性高血壓及非動脈硬化組(G1組),非原發性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組(G2組),原發性高血壓及非動脈硬化組(G3組),原發性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組(G4組),以G1組為對照組。
1.6 統計學方法 健康體檢數據均由各醫院經統一培訓的專人錄入,通過網絡上傳至開灤總醫院計算機室服務器,形成Oracle10.2 數據庫;采用SAS 9.4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Kruskal-Wallis);計數資料采用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壽命表法計算不同分組中心腦血管事件的累積發病率,并通過Log-rank檢驗進行比較。采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原發性高血壓、動脈硬化獨立及兩者的聯合效應對CVD影響的HR。將暴露因素作為交互項放入多因素模型中檢驗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在敏感性分析中,為排除糖尿病、血脂異常及吸煙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分別排除了患有糖尿病、血脂異常及吸煙的觀察對象重復進行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參 加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年度隨訪者且隨訪同時完成baPWV測量者共35 712例,排除baPWV測量之前發生心腦血管事件者644例,排除ABI<0.9者1 248例,共有33 820例觀察對象納入研究,其中男24 774例;年齡22~81歲,平均年齡(48.4±13.6)歲;平均baPWV(1 516±343)cm/s;平均 SBP(132±19)mm Hg。
2.1 4組一般情況比較 4組年齡、男性占比、SBP、DBP、baPWV、心率、BMI、FBG、TC、TG、LDL-C、UA、吸煙、飲酒、體育鍛煉、糖尿病、服用降壓藥物比例、服用降糖藥物比例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4組HDL-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四組一般情況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among the four groups
2.2 累積發病率 平均隨訪時間(3.34±2.38)年,CVD的發病密度為51.67/萬人年,各組CVD累積發病率分別為0.28%、1.94%、1.75%、4.70%,詳見表2;經Log-rank檢驗后,4組CVD累積發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3.36,P<0.001),見圖1。

圖1 四組CVD累積發病率比較Figure 1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four groups

表2 四組CVD的發病情況Table 2 The incidence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four groups
2.3 原發性高血壓和動脈硬化分別對CVD發病影響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以是否發生CVD為因變量(賦值:否=0,是=1),以動脈硬化情況(賦值:非動脈硬化=1,動脈硬化=2)、baPWV/baPW的標準差(baPWV-SD)(賦值:實測值)、原發性高血壓情況(賦值:非原發性高血壓=1,原發性高血壓=2)、SBP/SBP的標準差(SBP-SD)(賦值:實測值)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動脈硬化情況、baPWV-SD、原發性高血壓情況、SBP-SD均為CVD發病的影響因素,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4 動脈硬化、原發性高血壓的聯合作用對CVD發病影響的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以是否發生CVD為因變量(賦值:否=0,是=1),以不同原發性高血壓和動脈硬化情況(賦值:G1組=1,G2組=2,G3組=3,G4組=4)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與G1組相比,各組發生CVD的HR 95%CI分別為3.33(2.08,5.33)、2.81(1.57,5.03)、5.98(3.79,9.43)。校正相同的混雜因素后,將動脈硬化與原發性高血壓交互項帶入模型發現,動脈硬化與原發性高血壓對CVD發病無交互作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89),見表4。

表4 動脈硬化和原發性高血壓的聯合作用對CVD發病影響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Table 4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combined association of atherosclerosis and essential hypertension with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2.5 敏感性分析 因為使用降壓藥物會對血壓水平以及動脈硬化程度產生一定影響,為了消除影響,排除在隨訪期間使用降壓藥物的觀察對象,重復進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不同原發性高血壓和動脈硬化分組對CVD的影響,發現與G1組相比,各組發生CVD的HR 95%CI分別為3.05(1.90,4.91)、2.23(1.12,4.43)、5.66(3.56,9.01),校正相同的混雜因素后,將動脈硬化與原發性高血壓交互項帶入模型發現動脈硬化與原發性高血壓的交互作用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572),見表5。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33 820例觀察對象長達3.34年的隨訪后發現,原發性高血壓聯合動脈硬化使CVD的發生風險增加,二者具有聯合效應。此外,還發現在原發性高血壓和動脈硬化程度不一致的人群中,相較于原發性高血壓來說,動脈硬化對CVD發生的影響更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原發性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組發生CVD的風險要高于其余3組,在模型中帶入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的交互項后,發現對CVD的發生風險無影響。因此,認為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對CVD的發生具有聯合效應,在這種聯合效應下CVD的發生風險明顯高于只有原發性高血壓或只有動脈硬化的觀察群體。NIIRANEN等[11]在對2 127例平均年齡60歲的觀察對象進行12.6年的隨訪后發現,患有原發性高血壓且動脈硬化程度較高組發生CVD的HR 95%CI為2.25(1.54,3.29),高于單純患有原發性高血壓或單純動脈硬化增加組,且也未發現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交互項具有統計學意義,本研究結果與之一致。本研究證實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對CVD的發生具有聯合作用,二者聯合是CVD的危險因素。
同時本研究還發現,與未患有原發性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的觀察對象相比,單純患有原發性高血壓與單純患有動脈硬化的觀察對象均會增加CVD的發病風險,且單純患有動脈硬化組HR高于單純患有原發性高血壓組。血壓等CVD危險因素均可以通過積極的藥物治療在幾周之內恢復正常,從而降低CVD的發生風險[12-13]。而血壓等指標的迅速正常化并不能立即降低動脈硬化程度,因為動脈硬化是由于大動脈管壁彈性蛋白的斷裂以及纖維蛋白的增生而導致[14-16]。故相對于原發性高血壓來說,動脈硬化對CVD發生的影響更大。
除上述結果外,本研究還將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作為單獨變量進行分析,發現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均是CVD的獨立危險因素。LEWINGTON等[17]在對全球 61個人群(約 100 萬人,40~89歲)的前瞻性觀察研究中,基線血壓從 115/75 mm Hg 到 185/ 115 mm Hg,平均隨訪 12 年,結果發現診室SBP或DBP與腦卒中、冠心病事件、心血管病死亡的風險呈正相關,SBP每升高20 mm Hg或DBP每升高10 mm Hg,CVD發生的風險倍增。本研究還發現SBP每增加一個標準差CVD發生的風險增加。OHKUMA等[18]在對日本的14項隊列研究總共14 673例觀察對象的薈萃分析發現,baPWV第五分位組比第一分位組發生CVD的風險增加3.5倍,本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動脈硬化會增加CVD的發病風險。
原發性高血壓聯合動脈硬化導致CVD發病風險增加的機制尚不明確,根據本課題組先前研究[19]發現,動脈硬化的發生先于血壓升高。故原發性高血壓聯合動脈硬化導致CVD發病風險增加的原因可能為:(1)大動脈硬化后,血管對血壓的緩沖能力下降,導致血壓升高[20-21],增加了對動脈內皮細胞的“剪應力”損傷,加快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發展的進程[22-23],導致CVD發病風險增加。(2)觀察對象患有原發性高血壓后,體內氧化應激反應增加,造成彈性蛋白的斷裂,纖維蛋白的增生,導致動脈硬化[24-25]。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二者聯合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程度加深,使CVD發病風險增加。
本研究確定了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對CVD發生風險增加的聯合作用,但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從研究人群的預期壽命來看,隨訪時間相對較短,可能發生事件數目較真實情況較少,從而低估了CVD的發生風險。期待在隨訪時間更長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中驗證本研究的結果。本研究中觀察人群來自開灤研究,開灤研究是功能社區人群為基礎的隊列研究,所以本研究結果并不能直接推廣到其他人群,但本研究中觀察人群同質性更高,故研究結果更具有可靠性。
綜上所述,原發性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均是CVD的獨立危險因素,二者對CVD的發生具有聯合作用。
作者貢獻:馬一涵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統計學處理,結果的分析與解釋,撰寫論文;李興雨進行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韓旭進行數據收集;劉倩進行數據整理;李國進行論文的修訂;吳壽嶺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吳云濤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