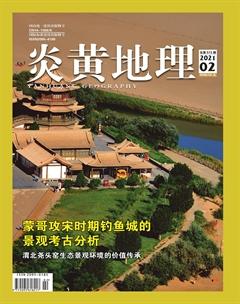滿族傳統“莽式舞蹈”在宮廷和民間的不同態勢
王舒瑤


滿族“莽式”舞蹈作為滿族歷史文化的一個典型縮影,因其豐富的舞蹈內容與鮮明的風格特征,從而成為滿族最具代表性與研究意義的舞蹈,而隨著歷史長河的發展,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物的滿族“莽式”舞蹈由于受到本民族由山野民族向中原統治民族身份轉變所帶來民族文化的變更,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宮廷與民間兩種不同的發展態勢。
莽式,是滿語maksin一詞的漢譯,意為舞蹈,與此相類似還有“蟒式”“祃克式”“祃克什密”等漢語書寫。關于“莽式”舞蹈現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對滿族某類傳統舞蹈的專指;而另一種是統稱清代所有樂舞百戲等。而本文所指的“莽式舞蹈”主要是指清代一種具有傳統的滿族風格特性的舞蹈。
“莽式舞蹈”在宮廷的發展
莽式舞蹈作為滿族傳統的民間舞蹈,其初入宮廷之際,并未形成固定程式,而依如前發展,歌舞相結。對此,根據《清史稿·樂志》中“清起僻遠,迎神祭天,邊治邊俗……而滿洲舊舞,是曰莽式,率以蘭綺世裔充選,所陳皆遼沈故事,作麾旄弢矢躍馬蒞陣之容,屈伸進反輕蹻俯仰之節,歌辭異漢,不頒太常,所謂纘業垂統,前王不忘者歟”的描述可知莽式舞蹈在宮廷中的最初形態:講述的內容以遼沈故事為主,將舞者裝扮為策馬馳騁騰躍的戰斗之容,曲調抑揚頓挫,所唱的語言與漢族大相徑庭,但都是在警醒世人不可忘卻前人功績。由此可見,初入宮廷的莽式舞蹈,舞蹈內容豐富,舞者進行裝扮,舞蹈功能雖已有記功作用,但就其根本并未形成嚴格固定的程式。
莽式舞,改稱慶隆舞。關于這一說法從《清史稿·樂志》
……隸于隊舞者,初名蟒式舞,亦曰瑪克式舞
可以得到印證。因此,基于該描述,筆者將慶隆舞作為“莽式”舞蹈在宮廷中的后期發展。慶隆舞在舞蹈內容上可分為文舞與武舞兩類,武舞展武德,文舞現文德。揚烈舞是指慶隆舞當中的武舞,是舞人騎著竹馬所表演的一種記功性樂舞,而喜起舞則為文舞,是大臣起舞在祝壽時的一種宴享舞蹈。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二八《樂部·隊舞》佐證,其形式,在《欽定大清會典圖》五十六中提道:“慶隆舞司章十三人以八旗護軍校等選充。冠冬冠,服蟒袍豹皮端罩。從右翼上,先立殿外,東向,歌慶隆之章,揚烈舞先上,歌至四章,揚烈舞退……喜起舞大臣同時入殿中對舞。舞畢,樂章亦畢。禮部官仍領出由右階下……兩翼北向立,司章下,司節隨下。皇帝三大節筵宴皆用之。”從此段描述中可知,莽式舞蹈在發展成為慶隆舞時,在服飾和樂器上已有嚴格程式要求。楊烈舞的服飾要求為,舞者頭戴冬冠,身穿蟒袍豹皮等有動物花紋之服飾,而喜起舞的服飾要求雖也為頭戴冬冠,但其身穿繡有金色壽字的石青色袍服。慶隆舞的音樂據《滿文老檔》載,最初的樂器僅喇叭、嗩吶與鼓,而后增加箏、琵琶、三弦、拍板、奚琴與節,且規模與外觀也發生變化,將樂器上每處都紋有龍紋,所用材料極其奢侈,無不透露著皇家威儀。而關于慶隆舞的樂譜發展,更多地則體現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人物的特定使用,與周朝時期的“制禮作樂”有異曲同工之妙,具有嚴格的等級要求。
慶隆舞,雖是從傳統莽式舞蹈發展而來,但與莽式舞蹈初入宮廷相比,從形式與內容兩部分來看其民族性風格逐漸被削弱,儀式性反而與日俱增。形式上,注重皇家之威儀,從參演人員到服飾到音樂到規模等都發生著變化。內容上,通過僅有“楊烈舞”和“喜起舞”這兩類舞蹈來表現戰斗與賀壽兩部分,逐漸將初入宮廷的“莽式”舞蹈內容固化,反而被賦予過多功利性目的,一步步走向嚴格的程式與僵化。
“莽式舞蹈”在民間的發展
莽式舞蹈在民間的發展由于年代久遠,因此無法窺得起其原本形態,只有借鑒流傳至今的民間“莽式”舞蹈來探討其在民間的發展。最著名的滿族民間“莽式舞蹈”是黑龍江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東海莽式”其“九折十八式”已成為滿族莽式舞蹈的動作要領,具有十分寶貴的信息價值。但通過對莽式舞蹈的調查研究,筆者還發現黑龍江省第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巴拉莽式”,因為“巴拉莽式”與“東海莽式”都以“莽式”而冠名,都是滿族的特色民間舞蹈,因此將二者放于滿族民間莽式舞蹈的所屬范圍之內進行分析研究。
東海莽式是流傳于古代黑龍江東部野人女真族中的舞蹈,關于它的記錄很少,僅在《滿文老中》一書中,提到“東海莽式”作為滿族舞蹈的一種,可分為“九折十八式”,但并未作具體的描述和說明。現如今所提到的“東海莽式”是《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黑龍江卷》根據“滿族民間故事家”傅英仁保存之民間滿族莽式最詳細、完整的排練珍本手抄本復排整理所呈現出來的。
東海莽式其舞蹈精髓在于“九折十八式”“九折”是指九個不同的舞蹈段落,它們既可以單獨成舞,又可組合起舞,擁有各自的歌訣;而“十八式”則是以手、腳、肩和腰這四個最基本的部位的轉、跳構成動勢的起點和落腳點。第一折:起式。作為“東海莽式”舞蹈的第一個呈現,它是一種由男女共同表演的集體舞蹈,主要體現女性的陰柔美和男性的陽剛之氣。第二折:穿針。女子群舞以織網為主線,主要表現女子在湖邊織網、曬網、釣魚的動作。第三折:擺水。第三折是第二折的延續,主要表現婦女捕魚、嬉戲生活,動作大多來源于生活中的捕魚動作。第四折:吉祥步。該舞段為女子結伴出行的步伐與婀娜多姿地表現婦女結伴郊游的情景。女孩以“吉祥步”為出場造型,端莊典雅,以“舉手”“甩紗”“繞腰”等手法呈現女性特有的優雅。第五折和第六折都是男子群舞,用來表現男子的陽剛、勇猛之風范。“單奔馬”和“雙奔馬”都是以“奔馬”命名的,與騎射生活有關,但內容卻大不相同。第五折“單奔馬”表現的是躍馬狩獵的勞動生活,其主要動作以狩獵動作為主。而第六折“雙奔馬”實則是戰士們在戰場上英勇作戰的場景,而且動作主要是戰爭動作。第七折:盤龍。與龍舞相類似,但與龍舞不同的是,該舞段并不是全由男子表演,而是以三男與多女來進行表演,關于龍身此折并不是借用直接代替龍身的道具完成,而是以使用手鼓、串鈴、馬鞭等極具滿族舞蹈特色的道具代替龍頭與龍尾。手鼓男被比喻成前面的“龍頭”,馬鞭男被比喻成隊伍末尾的“龍尾”,龍身是由女子手中的素絲組成的,另有一名男子手握香球,指揮整個舞隊,其動作是以表現龍戲水、翻云覆雨的狀態為主。第八折:怪蟒出洞。舞蹈以敘事表演為主。這是一種男子集體舞,改編自滿族民間傳說“呼啦啦貝子”的故事。通過動作形象、逼真地再現人們合力制服怪蟒的全過程。第九折:大圓場。此折是“東海莽式”的結尾段。通過男女之間的相對,表達慶祝豐收的喜悅。
東海莽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最基本的形態已無跡可尋,但通過對文字史料與傳承人的描述可知東海莽式在內容與形式上均出現新的變化,其作為民間舞蹈的自娛性、即興性的特點已被完整的結構性與動作的規范性取而代之,可以說它作為莽式舞蹈在民間的發展,已不單局限于民間,反而是民間自娛與宮廷規范結合的產物。
“野人舞”又叫巴拉莽式,是流傳于野人女真族之間的舞蹈,由于明末努爾哈赤對北方女真各部的頻繁征討,致使一部分女真人逃入山中定居,長期以狩獵為生,因此旗人將這部分逃入山中的女真人稱為“巴拉人”意為“不受約束的狂野之人。”這些人被后人看作巴拉人的祖先。巴拉人崇尚祭天,祭山,并且將祭祀分為家祭和野祭,而巴拉莽式就是在野祭時所跳表現古代巴拉人愛情生活的集體舞蹈,男女人數不限,但必成雙成對,男頭扎寸許寬扁帶,赤膊、穿背心短衫、衣豹皮短裙赤腿、足穿短靴雙手握手鈴;女頭系彩色扁帶、赤膊、上著內衣式緊身背心、下穿柳葉短裙、光腿、足瞪短靴。除上述表演者外還有二十人執火把助舞以烘托氣氛。以嗩吶、大鼓、手鼓、串鈴和大木梆等為伴奏。
現流傳下來的巴拉莽式與東海莽式相同,都是根據傅英仁先生保存之手抄珍本排練而成的。雖基本上保持和恢復了該舞的原貌,但從其結構與動作的規范都能夠看出文明時代加工的痕跡。
滿族莽式舞蹈之所以在宮廷與民間會產生不同發展,其根本在于統治王朝的建立。民間莽式舞蹈在進入宮廷逐漸發展成為慶隆舞,逐漸拋棄原本的民族特性,繼而形成固有的程式,最后因缺少新的藝術活力導致僵化走向沒落。而民間莽式舞蹈雖充滿活力,但卻因時代的更迭以及無人傳承的問題出現斷層,導致無法窺探其原始面貌,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就原本形態流傳至今來說,莽式舞蹈無論在宮廷還是在民間的發展都是失敗與遺憾,但通過對歷史文獻以及流傳至今莽式舞蹈的變形的研究來說,現如今可以通過寶貴的資料窺得其一些舞蹈形態,莽式舞蹈又是成功的。
作者單位:沈陽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