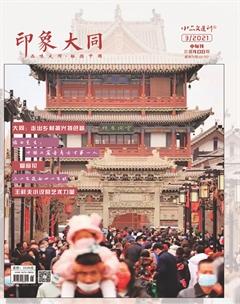彈大豆
吳素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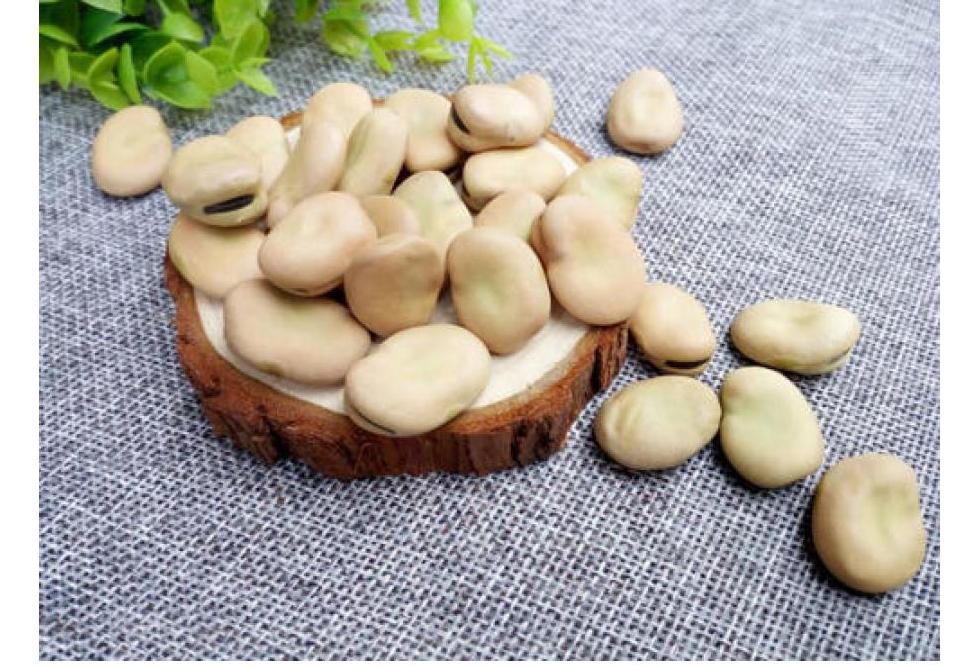
現在想想,我們那時彈大豆不亞于現在孩子們合伙打手機游戲,上癮得很。
供我們游戲的大豆,其實有一個很形象生動的大名——蠶豆。只是因為它的體積遠比黃豆、黑豆、綠豆大得多,長輩們就喊它大豆,我們也就跟著叫了起來。對于它的這一特點,我有時喜歡,有時討厭。喜歡是因為它的個頭跟我們的手指肚差不多,太適合用手指彈了,好像是專門長出來供我們把玩的;討厭是因為它泡發的時間太久,至少得三天——這無疑延遲了我們彈大豆的日期,讓我們眼巴巴地看著它窩在水里卻不得享受游戲的快樂。說了這么多,其實我想表達的是,我們那時彈大豆遠不及現在孩子玩手機游戲方便。年齡小一點的,跟爸媽一哭鬧,玩游戲的愿望瞬間實現;年齡稍長的,手機不離手,只要有網絡或流量充足,只要不怕誤事或挨罵,簡直分分鐘搞定,不必經受那種眼看到手的游戲卻又不能開玩的折磨。可我們那時彈大豆必須得等大人炒好了大豆才有實現的可能。
快過春節了,母親從某一個米缸或面壇子取出一個小袋子,從里面一碗一碗將大豆挖出來,倒在一個盆子里,先淘洗一番,再將它們浸入提前備好的溫水里,泡發兩三天才可以炒熟。從大豆浸入水里的那刻起,我那彈大豆的小心思就生根發芽蠢蠢欲動了。可越是離愿望迫近,越覺得等待太漫長,簡直太考驗人的耐心了!有好幾次,我禁不住問母親,為啥不直接炒而非要泡水?母親起初還耐心地為我解釋,說泡水后炒出的豆子比不泡的有多好吃,后來聽出了我言外的意思,狠狠地給了我一句,不炒也可以去彈大豆呀!可當我偷偷抓了一大把試過之后,發現不經火炒的豆子癟塌塌的,彈起來極不聽話,遠沒有炒后的過癮。
或許是大人們炒大豆有什么講究,也或許是母親有意為大年夜營造一種氛圍。總之是,我家炒大豆的時間大多在除夕夜,而且還正好就是現在人們舉家看春晚的那個時間段。也是呢,我們一家人圍著暖融融的鍋灶,一邊很認真地欣賞鍋里噼噼啪啪手舞足蹈的或大豆或瓜子或花生,一邊嗅著真真切切年的氣息,確實蠻有儀式感。
吃過晚飯收拾妥當,母親負責支那口平時用來炒菜的大鍋,鍋底放些早已洗凈的沙粒,等把沙粒炒熱后就開始炒大豆了,當然也會有少量的瓜子和花生。每年的那個時候,我和弟弟顯得格外聽話,不再像平時那樣提前睡覺或在炕上打鬧,乖乖擠在靠近鍋灶的炕角,認真瞅著父親一下一下翻動鍋鏟,期盼他早些讓我們品嘗瓜子或大豆熟了沒。往往是,父親的瓜子和大豆還沒全出鍋,我倆的肚子倒先成了口小鍋。
父親把瓜子和大豆炒好后,攤開晾在一個大簸箕里。稍微冷卻一會兒,母親負責用干凈的布子來回擦拭,直擦得用手摸上去沾不上一星點黑了,才分給我和弟弟一人一小碗,歸我們近期自己分派,或者吃,或者用來彈大豆。
于是,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八這段時間,街頭的鑼鼓還沒有敲起來,塞北的寒風又不容許我們長時間待在屋外,除了偶爾玩玩撲克,我們大量的時間都花在了彈大豆的游戲上了。
記憶中,在好朋友改弟家彈的時候最多。
每次彈的時候,我們先在她家西屋的炕席上找一塊兒比較平整的地方,決定要玩的小伙伴各自從兜里掏出顆粒相等的大豆和在一起,當作大家要彈的豆子。選豆子時,好像有一個不言自明的約定,我們會盡量選顆粒飽滿的,如果誰不小心摻雜了幾顆小的,那非得讓笑話半天。備好了豆子后,開始用“石頭、剪子、布”決定由誰第一個彈,其余的則按順時針方向往下排序。為了能多贏,我們都爭搶著想第一個彈,因為第一個彈的人豆子的總數最多,選擇的余地大,彈中的機會多。彈的時候,先把豆子用兩只手小心翼翼地捧起,再像潑水一樣半撒半拋地分散在炕席上,然后從散開的豆子里選擇距離較近適合一發命中的兩顆,用食指或小指在它們中間畫一下,以標明要彈的是哪兩顆豆子。為了讓豆子散開的距離恰到好處,散豆子就得格外用心,不可太用力,那樣容易讓豆子的距離太大,不好命中;也不可用力太小,否則豆子太密集不方便用手指畫痕。我的理想距離是二厘米左右,且中間沒有其它豆子阻擋。為了多贏幾次,我們幾個往往春節前的大半年就留好了小指的指甲,這樣用小指畫線時即使豆子挨得再近也方便過去。有時周邊的豆子實在太密集,別人看不明白,就得先口頭向大家說明要彈的是哪兩顆。這時,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死死頂著食指的第一個關節處,放到要彈出去的豆子旁,猛地向外彈出,彈中了,不只贏取兩顆相擊的豆子,還能繼續選擇豆子再彈,直到某一次彈不中,才乖乖地把彈豆子的權利交給相鄰的下一個伙伴。
這樣一輪下來,如果大家彈中的豆子少,可供我們玩的公用豆子數目還較可觀,就繼續下一輪;如果輪到某一位伙伴時,可供彈的豆子已經都被贏到我們各自的兜里,就可以選擇繼續玩或停止。大多時候,我們會玩上三幾個回合,直到改弟媽三番五次地喊她吃飯才作罷。現在想想,其實每次最終回家時,我們還會將所有玩的豆子和起來,再平分給各個玩伴,也就是說,我們一上午玩的只是一個輸贏的過程,最終自己拿出的豆子會一顆不少地再回到我們手里。只在彈豆子精彩的瞬間聽到同伴的喝采聲,或者手藝太臭時的“氣氣”聲,可就是那樣,也讓我們迷戀到總是忘記吃飯。好在改弟家姐妹多,有一條可以專供我們彈大豆的熱乎乎的大炕;也好在她們一家人特熱情,從沒有流露出一絲嫌棄,讓我們每年春節能夠盡興地彈大豆。
有一天,改弟最小的妹妹一定也被我們的玩法吸引了,第一次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可能是因為年齡小經驗不足,她一上午只彈中兩次,不是畫線時小指動了別的豆子,就是彈到別處去了,起先大家還顧及她是小孩子,后來就不由發出了“氣氣”聲,小妹自然聽得懂大家的意思,第三次彈完后扭轉身跳下地,“嗚嗚嗚”捂著臉到另一間屋子找她媽去了。這可把我們嚇壞了,以為小妹會叫上她媽來找我們,或是再也不讓我們在她家玩了。我們先是責怪剛才“氣氣”聲發出最響的那個,接著又互相指責。可是只一會兒功夫,小妹兜里裝了更多的豆子,竟又跳上炕,還說要跟我們繼續玩。
再后來,我知道了大豆還有一個更文藝的稱謂——蓮花豆。但吃上蓮花豆已是土地承包后我們舉家搬回家鄉以后的事了。各家各戶有了足夠吃的胡麻油、菜籽油之后,就想將大豆吃得更有味更香甜,于是也學著城里人的做法加工起了蓮花豆。蓮花豆吃起來倒是酥脆,但它給我的印象是只能下酒或當作吃涼粉的佐料,而且因為浸了油,彈大豆絕對派不上用場。更主要的是,由于遠離了那幫小伙伴,改弟家那條暖融融的大炕以及讓我癡迷的彈大豆游戲,也就成了童年書冊里珍貴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