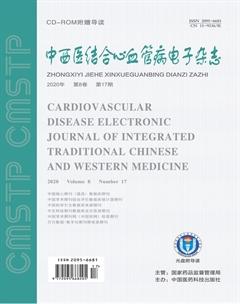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急性胰腺炎的療效觀察
王雪媛


【摘要】目的 探究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急性胰腺炎(AP)的療效。方法 取2017年4月~2019年4月在本院診治的AP患者80例,采取隨機(jī)數(shù)表法將其分為兩組,每組40例。對(duì)照組給予奧曲肽治療,觀察組給予奧曲肽聯(lián)合烏司他丁治療,觀察兩組臨床治療效果,分別檢測(cè)兩組治療前、治療后3、7 d血清淀粉酶水平。結(jié)果 經(jīng)過治療后觀察組治療效果明顯比對(duì)照組好,且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經(jīng)過治療后兩組患者的血清淀粉酶水平皆有顯著降低,并且觀察組降低范圍比對(duì)照組更大(P<0.05)。結(jié)論 對(duì)AP患者給予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的效果顯著,可降低血清淀粉酶水平,值得臨床推廣。
【關(guān)鍵詞】奧曲肽;烏司他丁;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一種消化內(nèi)科危重疾病,其病因諸多,其病情發(fā)展速度往往很快,有些患者可能在患病后迅速惡化,并會(huì)產(chǎn)生一系列諸多的并發(fā)癥,甚至?xí){患者的生命。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臨床癥狀主要有腹痛、惡心、嘔吐、發(fā)熱、休克以及血胰酶水平增高等[1]。對(duì)患者進(jìn)行抑制胰腺分泌、改善微循環(huán)、預(yù)防感染是治療急性胰腺炎的關(guān)鍵。目前對(duì)該病的常規(guī)治療方案主要是奧曲肽和烏司他丁。本研究探究以本院80例AP患者為研究對(duì)象,研究給予奧曲肽與烏司他丁配合對(duì)急性胰腺炎的治療效果。現(xiàn)總結(jié)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取2017年4月~2019年4月在本院診治的AP患者80例,納入標(biāo)準(zhǔn):(1),符合2003年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消化病學(xué)分會(huì)胰腺疾病學(xué)組制定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2)患者年齡須在18~80歲之間;(3)患者及患者家屬知情且自愿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jīng)院內(nèi)倫理委員會(huì)批準(zhǔn)。取隨機(jī)數(shù)表法將其分為兩組,每組40例。在對(duì)照組中男29例;女11例;年齡26~74歲;平均(43.24±3.12)歲;病程為1~22 h,平均病程(12.63±0.46)h;其中重度患者20例;輕度患者20例。觀察組中男30例,女10例;年齡24~71歲;平均(44.35±2.89)歲;病程為1~23 h,平均病程(12.74±0.55)h;其中重度患者21例;輕度患者19例。兩組患者男女比例、年齡、病程以及患病程度等比較均衡性良好(P>0.05),具有可對(duì)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給予常規(guī)護(hù)理治療,即對(duì)患者給予予抗感染、解痙止痛、改善微循環(huán)以及預(yù)防休克等護(hù)理措施。-
1.2.1 對(duì)照組
采用醋酸奧曲肽注射液(悅康藥業(yè)集團(tuán)股份有限公司:規(guī)格:1 ml,0.1 mg國藥準(zhǔn)字:H20163213)進(jìn)行治療,靜脈滴注每天0.6 mg,如若患者癥狀緩解則將劑量調(diào)整為0.1 mg,皮下注射為一天三次,持續(xù)一周。
1.2.2 觀察組
對(duì)患者給予醋酸奧曲肽注射液聯(lián)合注射用烏司他丁(廣東天普生化醫(yī)藥股份有限公司:規(guī)格:1 ml,2.5萬單位 國藥準(zhǔn)字:H19990132)進(jìn)行治療,在對(duì)照組的基礎(chǔ)上給予烏司他丁以10.0萬為單位溶入5%的葡萄糖注射液250 ml中,靜脈滴注,每日兩次,持續(xù)一周。
1.3 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
對(duì)治療一周后的患者進(jìn)行CT復(fù)檢和效果評(píng)價(jià)。若復(fù)查結(jié)果顯示胰腺組織無形態(tài)學(xué)改變,且血、尿、淀粉酶均恢復(fù)正常則評(píng)判為已經(jīng)治愈;若復(fù)檢結(jié)果顯示腹部CT胰腺組織有輕微形態(tài)學(xué)改變,血、尿淀粉酶顯著降低則評(píng)價(jià)為顯效;若結(jié)果顯示胰腺炎性狀態(tài)有所緩解,血、尿、淀粉酶相比之前有所改善則評(píng)判為有效;如若無變化或病情反加重則為效果無效。取患者治療前和治療后3、7 d的血清樣本,測(cè)定每個(gè)時(shí)期患者的血清淀粉酶水平。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用SPSS 20.0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計(jì)數(shù)資料以百分?jǐn)?shù)和例數(shù)表示,比較采用x2檢驗(yàn);計(jì)量資料采用“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yàn);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 果
2.1 療效
經(jīng)過治療后,觀察組得的治療效率明顯高于對(duì)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2.2 血淀粉酶
經(jīng)過治療后,兩組患者的血清淀粉酶水平皆有顯著降低,并且觀察組降低范圍比對(duì)照組更大(P<0.05)。見表2。
3 討 論
急性胰腺炎是一種由諸多因素導(dǎo)致的炎癥反應(yīng)疾病。其癥狀表現(xiàn)形式主要有急性上腹痛、惡心、嘔吐、發(fā)熱和血胰酶增高等[2]。臨。目前針對(duì)急性胰腺炎的普遍治療方案主要是在抗感染、解痙止痛、改善微循環(huán)以及預(yù)防休克的基礎(chǔ)之上給予患者奧曲肽、烏司他丁進(jìn)行治療[3]。
本研究顯示,觀察組治療后總有效率明顯比對(duì)照組高,經(jīng)過治療后,過治療后,兩組患者的血清淀粉酶水平皆有顯著降低,并且觀察組降低范圍比對(duì)照組更大,表明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可以更快速的改善患者的胰腺組織機(jī)能,降低血清淀粉酶水平,提高患者的治療效率。原因在于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可以抑制受體鈣離子內(nèi)流,從而控制血管平滑肌收縮反應(yīng),使受體胰腺組織的血流量得到增加,并使血管內(nèi)皮細(xì)胞能夠免受氧自由基損傷。因此,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急性胰腺炎在改善胰腺組織血循環(huán)和控制血清淀粉酶水平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治療效果。
綜上所述,對(duì)急性胰腺炎患者給予奧曲肽與烏司他丁聯(lián)合治療的效果顯著,可降低血清淀粉酶水平。
參考文獻(xiàn)
[1] 濮 娜,吳 瑩,張彩萍.Seldinger法區(qū)域動(dòng)脈烏司他丁灌注聯(lián)合奧曲肽治療重癥急性胰腺炎的療效及其機(jī)制[J].內(nèi)科急危重癥雜志,2019,25(5):378-380,409.
[2] 譚云輝.烏司他丁與奧曲肽對(duì)重癥急性胰腺炎PAF、ICAM-1、免疫功能 水平影響及臨床治療效果分析[J].解放軍預(yù)防醫(yī)學(xué)雜志,2019,37(1):32-35.
[3] 盛明輝,趙建勇.奧曲肽聯(lián)合烏司他丁對(duì)重癥急性胰腺炎氧化應(yīng)激及血清炎癥因子的影響[J].貴州醫(yī)藥,2019,43(1):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