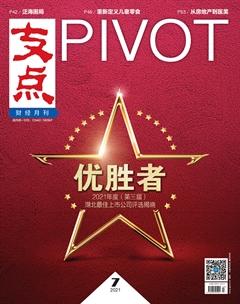中國資管行業將更規范更普惠
巴曙松
2021年底,資管新規過渡期將正式結束。在這樣一個新的經濟環境和新的制度環境下,對于參與的各個市場主體來說,資產管理市場的玩法會變得不一樣。最根本性的變化是資產管理產品必須形成清晰的市場化定價原則,打破剛性兌付,并凈值化計價。隨著這些新規則的落實,以后絕大部分的產品都可能必須要遵守市值計價原則,成本法的產品僅可以在非常嚴格的限定條件下存在。
資產管理產品大規模凈值化之后,各類資產管理機構在管理資產管理產品時,就必須要更為關注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風險管理。因此,各類資產管理機構在管理資管產品時所要求的專業管理能力必定明顯提升,也將倒逼各類資產管理機構提升投研能力。
我們應該認識到,所有的資產管理產品都是會打破剛兌的,保本兌付的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現了。打破剛兌對中國金融系統的影響總體上應當說是業務模式和理念的重構過程,市場各方都需要積極適應,當然,對于惡性逃廢債行為,無論是否存在剛性兌付,都需要嚴厲打擊,同時要防止部分企業以打破剛性兌付為名進行惡性逃廢債。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底層資產的違約是優勝劣汰和自然出清的過程,有利于社會資源尤其是金融資源的再配置;另一方面,資產管理產品打破剛兌也斷絕了金融機構表外業務風險向表內轉移的可能性。
對于資本市場而言,資管產品打破剛性兌付、去通道化和凈值化計價將大幅減少事實上的間接融資比例,降低影子銀行規模,真正推動直接融資比例的上升。一方面,資管業務模式的改變會推動各類資產管理機構更為審慎地對待資管產品所做出的投資,這對資本市場更為健康的發展、對提升社會資源的配置質量都有幫助;另一方面,資產管理行業業務模式的改變有助于推動權益類產品規模的提升,對經濟轉型發展能提供積極支持。
在我們跟蹤研究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15年中,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發展非常迅速,也歷經很多變化。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發展到今天,也是整個金融體系不斷克服不同階段的困難得以發展的成果。在不同階段,可能許多問題反映在資產管理行業,實際上是整個金融體系面臨的挑戰的一個體現,例如在2008年為了應對次貸危機沖擊推出大規模信貸刺激政策之后,宏觀政策逐步退出,但是一些市場主體還是習慣于寬松的信貸刺激,這就使得許多信貸需求從商業銀行轉移到各種經過包裝、經過各種過橋等方式的影子銀行體系中,現在宏觀政策逐步回歸常態化,也就客觀上要求資產管理市場要打破剛兌,回到市場化的軌道。
從趨勢看,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有條件沿著更為規范化、智能化和普惠化的方向發展下去。首先,規范化是資管新規對于資產管理行業的根本要求,其規范發展的程度,決定了資產管理行業快速發展對于實體經濟的支持效率;其次,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并在資產管理行業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未來我們可以看到科技能更多地改變資產管理行業的業態,使其變得更為智能化;最后,資產管理行業在金融科技等技術的加持下,服務長尾客戶的能力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強,普惠化的特征也定會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