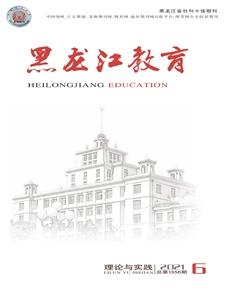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的認知語境及其教學啟示
摘 ?要: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的認知語境是譯者發揮認知思維能力,借助語境資源和手段,對英語原詞進行意義加工和轉換,并最終產出漢語譯詞的認知建構過程。科學、嚴謹的認知語境有助于提高英-漢詞匯翻譯產出的質量。教師可以從情景意識、邏輯推理和意義觀三方面入手,改進教學內容,采取相應的教學方式,對英-漢詞匯翻譯教學進行改革探索。
關鍵詞:認知語境;翻譯產出;推理;假設
中圖分類號:G64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2-4107(2021)06-0090-03
思維是認知活動的重要表現形式,翻譯是譯者的復雜認知行為。認知語言學的意義觀認為,詞義并不完全預置在文本中,而是在語境中通過識解獲得的,翻譯就是對意義的構建過程。英-漢翻譯就是用漢語識解譯義。因此,在認知翻譯觀下,英-漢詞匯翻譯不是單純地將英語詞義傳遞到漢語中,而是在漢語語境中重新建構意義,經思維內化和整合的認知語境在漢語詞義的建構和表達中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可見,翻譯是一種譯者發揮主觀能動性,創設認知語境,進而獲得譯義的認知活動,而每個譯者的認知語境在程度和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這就會影響譯者用漢語譯詞的表達效果。有鑒于此,在英-漢詞匯翻譯產出實踐和教學中,應該給予認知語境足夠的關注。
一、認知語境在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的作用
認知語境觀是隨著認知科學的興起發展而來的,它認為,話語理解不只存在于具體語篇的編碼語境層面,還存在于語言使用者通過經驗和思維內化和認知化的認知語境[1]。與傳統語境的客觀預置性、靜態性不同,認知語境是一個心理建構過程,更凸顯主觀性和動態性。這些特點使認知語境能在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有效地發揮補充和深化傳統語境的作用。
(一)認知語境及其作用模式
作為翻譯過程中的心理建構體,認知語境與語言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的區別在于有思維等認知活動的主動參與,它是譯者與語篇內外多種因素主觀互動行為的結果。也就是說,認知語境是譯者借助自身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結合外部世界輸入的當前信息,推導出新信息,從而揭示交際話語明說和暗含的內容[2]107。認知語境是所有類型的語境信息經譯者大腦認知而進行綜合加工的過程和產物,它的建構過程至少包含假設、推理、分辨、選擇等認知思維方式的參與。在英-漢翻譯產出中,譯者要將英語語境下的所有已獲得的相關信息,進行一系列的漢語認知語境化思維加工,然后把處理完的信息用合適的漢語表述。翻譯中的認知語境屬于譯者的心理特征范疇,因此,認知語境的個性化特征明顯。一般認為,認知語境的構成基礎是交際話語的物理環境、交際者的經驗知識及個人的認知能力[2]107。在英-漢詞匯翻譯中,譯者充當溝通雙語信息的交際者角色,在每個譯者面臨的交際物理環境大致相同的情況下,譯者個人經驗和認知能力的差異會體現在翻譯產出的結果上。其中,認知能力是認知語境建構的決定因素,經驗和環境是通過認知能力參與認知語境建構的間接因素。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的認知語境作用機制是一個由不同認知方式和因素協調有序參與的有機系統。
譯者在認知語境建構中的各項認知活動貫穿英-漢詞匯翻譯產出的全過程,并同語篇內外與譯詞相關的各種因素作用,組成了一個意義重構的運轉系統。第一,譯者結合英語原詞的詞典釋義、傳統語境義、個人經驗等線索,通過推理,對該詞在源文本中的意義提出若干語境假設。第二,再對這些假設進行分析辨別,去偽存真,將唯一可行的假設進行意義具體化,即得出該詞的語境意義。第三,譯者進入語境義的英-漢轉化過程中,由于英、漢詞語的詞義及各自的適用語境存在差異,原英語詞的語境意義會對應若干漢語語境選項,譯者將結合交際環境和個人經驗,選擇并確定最合適的語境選項。這個關鍵步驟將最終決定漢語譯詞的準確程度。第四,譯者將該詞的漢語意義以精確、地道的語言表達出來,完成漢語詞語產出的全過程。第五,在認知語境的建構中,推理、假設、分辨、選擇等主要認知思維形式并非是各個階段里運作的唯一方式,而是彼此交叉融合。詞語所在語篇的交際環境和譯者經驗分別是指廣義上的英、漢話語語言環境和譯者的人生經驗,二者存在并作用于譯者認知語境建構的行為中。
(二)認知語境的應用評析
以下通過解析教師所任教學生的某次英-漢翻譯作業中的重難點詞語的英-漢翻譯產出過程,來認識認知語境的作用。
Western China,comprising Tibet, Xinjiang and Qinghai, has little agricultural (1)significance except for areas of floricul-ture and cattle raising.Rice,Chinas most important crop,is(2)dominant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many of the farms here yield two harvests a year.In the north, wheat is of the great importance,while in central China wheat and rice(3)vie with?each other for the top place.Millet and sorghum are grown mainly in the northeast and some central provinces,while,toge-ther with some northern areas,also provide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barley.
參考譯文:
包括西藏、新疆和青海在內的中國西部,除了可供發展花卉種植業和畜牧業的地區以外,幾乎沒有太多的農業開發利用(1)價值。稻米是中國最重要的農作物,在南方省份的地位(2)舉足輕重,那里的田地可以一年收獲兩次。在中國北方,小麥是非常重要的作物,而在中部地區,小麥和稻米則(3)處于均勢。粟和高粱主要產于東北地區,而中部的一些省份連同北方一些地區也出產很多大麥。
該段落介紹了中國的農業發展及主要農作物的地理布局。教師重點研究了其中3個復雜詞語在英-漢翻譯中的認知語境建構情況。這3個詞語的原詞義范圍和所處語境信息量差別較大,這就使譯者在英-漢翻譯產出時面臨的困難不盡相同。本身意義豐富的詞語可能會在譯者頭腦中呈現更多的語境假設,這就增加了確定語境意義的難度;而意義較為單一的詞語可能會令譯者面臨更少的語境選項,如何為譯詞選擇最合適的漢語語境則成為焦點問題。解析如下:
1.significant的本義比較抽象,根據語境可以聯想、推測出be worth of doing、be usable、be effective等適用于significant的語境假設。分析發現,此處指中國西部地區,特別是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與農業發展的關系,需要譯者調動地理方面的相關常識,即上述地區由于地形、氣候等原因不適合大規模發展作為主流農業的糧食作物種植業,這就使西部地區在農業利用上的“有用性”降低,也就具體化為語境意義usefulness。英- 漢轉換后,usefulness在漢語情境下可能至少有3個語境選項:有益性的、有作用的和可應用的。經判斷,西藏等西部地區因自然原因盡管在畜牧業和經濟作物種植方面具備優勢,是“有利可圖”的,但總體而言不宜發展傳統糧食種植業,即無論在客觀自然條件還是經濟效益上,西部對農業發展都不太“有益”。這種“有益性”是譯者基于綜合語境所做出的最全面的認知選擇,經意義提煉、升華,“有益性”對應的最準確釋義是“價值”。
2.dominant無論從詞語本身還是所處語境分析,都不太容易推斷出很豐富的語境假設,暫且確定其中的兩個:to account for the bulk of和to exceed all others。根據其后的“一年收獲兩次”之語義并結合中國“南粉北面”的飲食地域特征綜合判斷,稻米就產量而言在南方所有的糧食作物中“占有極大優勢”,可具體化為overwhelming。在漢語語境下,這種“極大優勢”是如何體現的呢?對此可以有3個語境選項:占支配地位、居于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比較分析三者發現,“居于第一位”雖表明數量領先,但無法確定對其他因素具有壓倒性優勢;“最重要的”中語境對數量、規模等的限定模糊,也不能表明“有優勢”;而“占支配地位”則明確地展現出優劣的實力對比關系。在漢語中,有不少詞語能表示“支配關系”的語義,其中,“舉足輕重”是比較恰當的一個。
3.vie的原詞義單一固定,語境線索非常有限,可以有to compete這樣一個語境假設,具體化為“超過”,即to surpass。在英-漢轉換后,應對漢語語境做詳細分析,在中部地區,小麥和稻米是旗鼓相當的兩個直接競爭對手,任何一方都力圖超越另一方而“榮登榜首”,但競爭結果是,誰也沒有絕對實力壓倒對方而勝出,最后雙方形成了“一方無法保持獨大”的平衡態勢。能實現這一語境選項的最確切、通暢的漢語詞語是“處于均勢”。顯然,對vie的英-漢翻譯,漢語語境選項的建構至關重要,其特殊性在于側重以“行為效果”作為推理依據,這一認知特點在部分詞語的英-漢翻譯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此可知,認知語境是譯者運用認知能力對詞語及其傳統語境進行分析、加工的結果,它的建構過程呈現出因時、因地的動態變化趨勢。不同的詞語有不同的認知語境,在建構的不同階段,其繁復程度也不一而足。譯者應具備對詞語意義深刻的領悟力、對語境信息的把握和辨別力及廣博的經驗與知識儲備,才能靈活應對認知語境建構中所面對的挑戰。認知語境能為英-漢詞匯翻譯產出實踐和教學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認知語境視角下的英-漢詞匯翻譯產出教學內容革新
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的認知語境建構就是譯者盡最大努力還原、利用詞匯所在語篇的交際情境,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不斷地加工、產出意義的過程。因此,交際情境、邏輯推理和意義是認知語境視角下英-漢詞匯翻譯教學值得關注的內容。
(一)情境意識教學
交際情境是交際話語發生的具體環境,它通過規定語言使用的場合和方式而對意義加以限制。詞脫離具體語境,詞義則是“非限制性的”,受具體語境制約,詞義才是“限制性的”,語境不同,詞義即有所不同[3]。詞義嚴重依賴語境,詞匯作為最小的意義自由體,在英-漢翻譯中英語語境和漢語語境的雙重制約下,變得不那么“自由”。然而,語境因素是分散、客觀的,交際語境對詞匯意義的影響最終要通過譯者內化了的認知語境來體現,即語境是認知語境必不可少的形成條件之一。在實踐中,很多譯者由于缺乏充分的翻譯情境意識,傾向于較為孤立地看待詞義,照搬詞典義,造成譯義失準或表義不當。這些現象產生的部分原因是譯者認知語境的建構缺乏充足、可靠的語境參與,從而導致認知語境的導向偏離。鑒于此,翻譯教學應該幫助譯者培養情景意識,形成“無語境,不翻譯,譯必參語境”的牢固觀念,使“語境思維”成為譯者的自覺行為。
(二)邏輯推理教學
推理是貫穿認知語境建構全流程的基本邏輯思維形式。在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譯者不斷地打破其原有的認知框架,形成新的認知環境,在信息的不斷更新中構建出最符合原文信息的新的認知邏輯,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里進行信息提取,從而選出最合適的目的語詞語將其表達出來[4]。因此,邏輯推理是認知語境建構中有力而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翻譯教學中應加強對譯者掌握正確推理方法和監控推理過程的教學。因此,翻譯教學教授一般的邏輯規律和推理方法與過程等知識,使譯者能夠經常進行科學的思維和推演訓練,不斷修正推理誤差,最終達到熟練、準確的翻譯。
(三)意義觀教學
翻譯是一門與意義打交道的學問與技能,特別是詞義。譯者只有熟悉并準確分辨不同的詞義,才能對某個詞語在翻譯過程中的詞義演變和譯義產出過程形成系統性的認知,并追溯認知語境建構過程。詞義是解鎖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中認知語境建構的一把鑰匙。因此,譯者應在實踐中逐漸樹立意義觀,在翻譯教學中,應結合英、漢兩個概念系統的差異側重教授詞義差別和語境詞義及其形成因素,培養譯者跨語言詞義理解和融通的能力。
三、認知語境視角下的英-漢詞匯翻譯產出教學方式探索
認知語境將英-漢詞匯翻譯產出上升到譯者的心理和思維特征層面加以考查,凸顯翻譯活動的情境性、過程性和個體性特點,這些因素使得以“單純追求雙語詞義對等”為宗旨的傳統詞匯翻譯教學需要改進完善,以更加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手段體現詞匯翻譯中的認知規律。
首先,實行“體驗式”教學模式。話語本身就是一種行為方式,離不開其發生的背景,即話語的語境。就翻譯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譯者能沉浸于雙語語境,而“體驗式”教學理念能最大程度地使譯者體會翻譯語境,其教學實施方式包括:譯者課下自行搜集、掌握與譯詞及其語篇相關的信息,課堂上教師通過講解和組織課堂活動創設翻譯情境以輔助譯者的認知體驗,使譯者對詞義的領悟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發現。
其次,實行分組教學模式。認知語境尊重和強調思維的個體性差異,面對同樣的譯詞,每個譯者可能會得出不同的語境假設和語境選項,實行分組教學可以有效調動譯者的積極性,激發想象力,組員互相學習借鑒有助于譯者改進思維方式,提高認知水平。例如,譯者分成每組4人的翻譯組,先各自完成同一個詞語的英-漢翻譯任務,然后交流譯義,共同探討翻譯過程,總結利弊得失。分組教學有利于譯者深入了解認知語境的建構。
最后,倡導“回溯式”教學方法。與傳統翻譯教學重結果不同的是,認知語境視角下的英-漢詞匯翻譯產出更注重翻譯過程,準確的譯義正是譯者科學、嚴密的認知過程的縮影。因此,翻譯中應提倡由結果向過程的“追根溯源”,教師制訂追溯的內容和目標,譯者在教師的指導下反復回溯,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改進過程。
英-漢詞匯翻譯產出過程中的認知語境要求譯者以譯詞為起點,借助語言和語篇內外的各種語境資源和手段,利用認知能力,對詞義進行發現和再現。認知語境觀的嚴謹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譯詞的翻譯質量,同時也為英-漢詞匯翻譯教學指明了改進的方向。教師可以此為導向,探索更多、更有益的翻譯教學內容和手段。
參考文獻:
[1]熊學亮.認知語用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115.
[2]徐善文,范敏.認知語境視角下UCP600中譯本詞匯翻譯特點淺析[J].蚌埠學院學報,2017(1).
[3]馮國華.語境通觀,隨便適會——在具體語境中把握詞義[J].中國翻譯,2002(1):76-81.
[4]鄧江雪.基于認知語境的視角探索翻譯教學模式[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6(10):332-333.
編輯∕丁俊玲
作者簡介:樊騰騰(1978—),男,河南安陽人,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翻譯學、認知語言學。
基金項目:2018年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創新強校工程”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提高英漢翻譯詞語表達效果的教學改革研究”(2018yjjg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