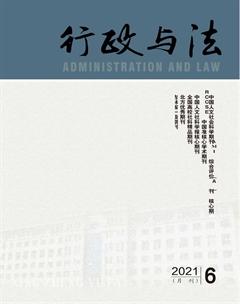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競爭法規制
吳楷文 王承堂
摘? ? ? 要: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可分層為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手段行為和優待自營業務的目的行為。該行為會侵害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權益和公平競爭利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并影響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最終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兩反法”有其規制的重點,手段行為造成的損害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更匹配,而通過反壟斷法規制目的行為更合適。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框架下,手段行為可能符合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或一般條款的構成要件;在反壟斷法的語境下,目的行為可能觸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中差別待遇的規定。
關? 鍵? 詞: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自營業務;競爭法
中圖分類號:D922.294?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1)06-0120-10
收稿日期:2021-04-06
作者簡介:吳楷文,揚州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競爭法學;王承堂,揚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經濟法。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江蘇省法學會法學研究課題一般項目“電子商務平臺非中立行為的競爭法規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FH2020B011。
一、 問題的提出
在數字技術不斷成熟的大背景下,平臺經濟的總體地位日益提高,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甚至是最主要力量,不斷涌現出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等商業巨頭,而數據則是推動這些平臺企業不斷向前的核心動力。對于電子商務平臺中的各方主體來說,更多數據意味著更大的競爭優勢,數據既可以幫助平臺經營者優化平臺服務,也可以為平臺內經營者的經營活動提供指引。傳統平臺經營者僅以提供平臺服務而非直接向消費者提供商品為根本遵循,隨著商業模式的不斷更新,平臺經營者亦開始從事自營業務并參與平臺內市場的競爭,這也為其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侵害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權益和公平競爭利益埋下了伏筆。雖然谷歌曾因將自家比價服務置于搜索結果的優先位置被歐盟罰款24.2億美元,但巨額罰款并沒有將此類行為扼殺在搖籃中,平臺企業的自我優待行為仍有不斷擴張的態勢。[1]在美國眾議院發布的《數字市場競爭狀況調查報告》中,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GAFA)四大平臺巨頭均涉及自我優待行為,其中有關亞馬遜通過訪問第三方賣家(平臺內經營者)數據使第一方業務(自營業務)獲益的調查占據了大量篇幅。[2]在大洋彼岸,歐盟則認為亞馬遜將第三方賣家數據用于優化自營業務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規則,破壞了公平競爭環境。[3]
與歐美向亞馬遜這樣的電商巨頭頻頻出手不同,目前我國反壟斷執法部門尚未關注到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現實可能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的風險。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作為2021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我國勢必不斷重視其中可能存在的壟斷和其他反競爭問題。《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的出臺更是為規制此類行為提供了微觀指引。鑒于此,本文擬聚焦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我國競爭法的框架下探尋有針對性的規制路徑。
二、 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檢視
(一) 檢視基礎: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分層
數據與算法在平臺經濟時代相輔相成,二者的協作是電子商務平臺內以平臺經營者為代表的各方主體作出正確決策的技術基礎。在歐盟副主席維斯塔格發表的聲明中,亞馬遜首先將平臺內經營者的產品和數據實時反饋到其算法中,并基于算法輸出的結果優化自營業務的產品和價格。[4]雖然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平臺基礎架構和算法的協助下可以實時完成,整個過程或許只需要一秒鐘甚至更短的時間,但這短暫的一瞬卻讓平臺經營者實際上走完了“獲取數據——分析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全過程,并基于此實現了使自營業務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競爭中占據優勢的目的。
為了分析的方便,筆者將上述行為分層為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手段行為和優待并使自營業務擁有競爭優勢的目的行為。與競爭法不同,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分層評價在刑事司法中已運用地較為廣泛和成熟,其原因在于行為人實施犯罪的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可能會符合不同的犯罪構成要件并侵害不同法益。以“套路貸”案件為例,無論案件多么復雜,其基本形態都是一個由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目的所統領的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組成的有機體。[5]當然,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分層評價并不是刑法的專利,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其亦可在競爭法中適用。即使刑法與競爭法規制的法益不同,但二者的落腳點均在行為評價上,而且一些違反競爭法的行為也可能被刑法處以否定評價。通過將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進行分層,可以分別評估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對市場的影響,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全面的競爭法規制路徑。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該行為在分層的基礎上被單獨評價,但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并非完全割裂,仍為一個有機整體。
(二)手段行為檢視
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是平臺經營者實施的手段行為。平臺經營者為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搭建了交易的橋梁,從而實現了二者的快速匹配。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電子商務平臺的存在不僅可以創造大量交易機會,還為消費者節約了搜尋成本。電子商務平臺雖然是互聯網中的虛擬平臺,但并非“海市蜃樓”,它和傳統商場一樣需要一定的基礎架構支撐,只不過支撐傳統商場的是鋼筋混凝土,電子商務平臺的基礎架構則是由代碼和互聯網通信協議構建的。互聯網的基本通信協議等技術構造決定了信息的傳播方式,而基于互聯網信息系統的電子商務平臺則像互聯網中的一個個“島嶼”,同樣具有技術能力和權力。[6]在電子商務平臺這個“島嶼”上,平臺經營者不僅擁有整個“島嶼”的產權,還能夠依托平臺基礎架構和其他技術工具掌控平臺內發生的一切。
平臺經營者擁有整個電子商務平臺的基礎架構,而平臺內經營者的經營活動則依附于平臺架構,這種技術上的優勢為平臺經營者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此外,根據《電子商務法》第31條的規定,平臺經營者負有記錄、保存信息的義務,并需確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信息保存義務是一把“雙刃劍”,該義務一方面通過留存證據的方式保障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為平臺經營者儲存平臺內經營者數據提供了法律依據,并增加了平臺內經營者數據被不當獲取的商業風險。數據獲取后,平臺經營者可以借助算法工具深度分析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從而為優待自營業務貢獻推理和預測的基礎。而且與人相比,作為機器的算法不僅能夠對海量數據進行快速“理解”與“學習”,還可以排除情感的干擾,為平臺經營者提供最符合經濟學假設的理性選擇。
(三)目的行為檢視
優待并使自營業務擁有競爭優勢是平臺經營者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目的。當平臺經營者從事自營業務時,它不再是僅提供平臺服務的中間人,在法律地位上也與平臺內經營者無異,并須承擔商品銷售者或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開展自營業務是平臺經營者縱向一體化的方式之一,而且平臺業務和自營業務同為平臺經營者的盈利來源,平臺經營者也可在優待自營業務中獲得更多利益,因為只有提升自營業務的競爭力才能使其成為推動平臺整體不斷向前的新動能。
在歐美的調查中,亞馬遜主要通過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手段優待自營業務。不管是對于平臺經營者抑或是平臺內經營者來說,數據都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在市場競爭中,競爭優勢是相對于競爭對手而言的,因而在數據優待的場景下,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獲取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提升自營業務的競爭力。大數據分析以海量數據為前提,盡管相對于平臺內經營者,平臺經營者的數據資源更為豐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平臺經營者的數據需求已經得到充分滿足。借助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平臺經營者可以更好地優化自營業務并提升其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數據被獲取的事實減損了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競爭力,從而達到間接增強自營業務競爭優勢的效果。數據承載了平臺內經營者的諸多關鍵信息,甚至包括直接影響其經營根基的商業秘密。雖然數據具有非排他性并可以被無限復制,但平臺經營者不僅可以針對特定競爭對手的數據“采其所長,補其所短”,還可以對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競爭劣勢定向打擊以削弱其競爭力。
此外,平臺經營者的平臺管理權限和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相結合能夠更好地為其優待自營業務的目標服務。根據平臺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平臺經營者在負有提供優質平臺服務義務的同時也享有管理平臺內經營者的權力,而為了保證平臺內市場的交易安全和有序運行,平臺經營者也有足夠的動機實施管理行為。除此之外,《電子商務法》第2章第2節中對平臺經營者的諸多義務性規定更是強化了其行使管理職權的正當性,這是因為平臺經營者的義務和責任也就意味著“權力”。[7]不過良好管理的另一面卻是權力可能被濫用,平臺經營者同樣可以在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后利用管理權限為優待自營業務服務。
三、 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行為對市場的影響
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給自營業務提供競爭優勢的同時,也給平臺內市場帶來了嚴重的現實損害,為此有必要在分層檢視的基礎上明確該行為對市場的影響。當然,正如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仍為一個有機整體,二者對市場的影響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各有側重,不能完全割裂。
(一)行為對平臺內經營者的影響
⒈侵害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權益。如果要對數據進行保護,就必須明確主體對數據享有是利益還是權力,因為二者代表了不一樣的保護強度。數據在平臺經濟時代的價值不言而喻,但高價值并不意味著必須通過強度最高的財產權對數據予以保護。從現實立法來看,《民法典》第5章在規定各種權利的同時并未明確數據的法律屬性和保護方式,只在第127條規定將數據和虛擬財產交由其他法律解決。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處理一系列數據爬蟲案件時同樣沒有認定主體對數據的財產權,而是將行為置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框架下分析。如一審和二審法院在“淘寶訴美景案”中均否定了淘寶公司對涉案數據的財產權,并承認了其對數據享有“競爭性財產權益”。雖然平臺內經營者對數據享有的是財產性權益而非財產權,法律也不能為其提供絕對化的權利保護,但這并不等于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行為沒有侵犯到平臺內經營者的任何權益。數據是信息的載體,它承載了平臺內經營者的產品、價格等諸多關鍵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平臺內經營者來說是則經營活動的生命線。在性質上與網絡爬蟲案件類似,平臺經營者利用自己的基礎架構地位和技術優勢獲取數據的行為同樣侵犯了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權益。
⒉損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利益。平臺內經營者是平臺經營者利用其數據優待自營業務行為的最大受害者:一方面,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可以被隨意獲取的事實意味著其公平競爭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優待自營業務的目的行為更使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無力與自營業務競爭。借助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平臺經營者不僅可以取長補短、實現自營業務的不斷優化,還可以針對競爭對手的關鍵劣勢予以打擊,從而讓自營業務在平臺內市場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在市場競爭中,一方得利的同時必然有另一方受損,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也就預示著平臺內經營者業務的競爭劣勢。競爭不可能讓每個人都獲利,競爭中產生的損失也只能被視為純粹經濟損失,不過該論斷必須以公平競爭為前提。
與優待自營業務所產生的競爭優勢相對應的是,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公平競爭利益是經營者根據自身主體性所享有的利益,其內涵在于“公平競爭資格、不受不正當競爭行為排擠和損害的地位、通過公平競爭獲取利潤的能力”。[8]申言之,在公平競爭利益的保障下,每一個競爭者都可以憑借價格、性能或質量在競爭中擊敗競爭對手并獲取利潤,且在面對不當競爭行為的排擠和損害時可以尋求法律救濟。不過,平臺經營者優待行為的實施路徑是在獲取競爭對手數據的基礎上為自營業務取得信息優勢,而平臺內經營者在數據被隨意侵犯時很難獲得真正的“公平競爭資格”。
平臺內經營者不僅很難獲得真正的“公平競爭資格”,而且因巨大的經濟壓力也無力與平臺經營者抗衡。如果說平臺經營者基于服務協議和法律規定獲得的只是管理平臺的權利,因為平臺內經營者可以隨時根據協議約定退出平臺,那么在巨大經濟優勢的扶持下,平臺經營者的權利很有可能真正蛻變成具有支配力的“私權力”。權力意味著支配,即一個行動者可以不顧他人的反對去貫徹自身意志。[9]盡管離開平臺對于平臺內經營者來說沒有任何法律障礙,但是巨大的經濟壓力使其在面對平臺自我優待行為及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時不能充分地自由選擇。
(二)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⒈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數據是平臺經濟時代市場主體最大的財富,而平臺經營者借助技術手段隨意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行為則是對競爭秩序的公然蔑視。為了防止平臺經營者對其數據的不當獲取,有能力的平臺內經營者勢必同樣會通過技術手段構筑自己的數據城墻以保證數據安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無序的市場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只要數據保護的成本大于數據被獲取的損失,理性的平臺內經營者就有足夠的激勵設置數據壁壘。但相對于那些規模效應下有能力采取技術手段的大企業,無力負擔高額數據保護成本的小企業才是大多數平臺內經營者的真實寫照,而且他們根本沒有資本與平臺經營者談判或對抗,只得任由自己的數據被平臺經營者獲取后用于優待自營業務。此外,數據城墻的構筑不僅會讓平臺內經營者背負額外的數據保護成本,還會阻斷部分有益的數據獲取行為、阻礙數據的正常流通,并造成社會總福利的流失。
不寧唯是,平臺經營者的數據獲取行為還會影響平臺內經營者的創新激勵。創新是分析市場競爭的重要工具,比如在歐盟委員會看來,創新雖然不是在認定反競爭行為時唯一甚至關鍵的核心價值,但其仍為一種以補充方式體現的政策價值。[10]數據是平臺內經營者的核心資產,更是其創新的動力源泉和成果體現。為了提升競爭力,平臺內經營者有足夠的動力進行數據收集和產品更新。但是一旦數據輕易被他人非正當獲取,在市場競爭秩序混亂、其勞動成果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形下,平臺內經營者收集數據和更新產品的激勵便會大大降低。
⒉影響市場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利益受損不僅是個人的損失,更意味著平臺內市場的競爭機制無法充分發揮。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成要素,沒有競爭就無法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的自我調節運行也以國家所確認和保護的競爭為前提。[11]在平臺內市場的競爭中,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與自營業務并非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然而,該優勢并非來自于產品的更低價格或更高質量,而是平臺經營者在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基礎上實施的優待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平臺內經營者與平臺經營者之間存在單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個人的選擇有賴于充分的信息,經營者的決策同樣如此。信息經濟學的成果表明,信息的完全性是作為經濟學模型的“完全競爭市場”成立的必要條件之一。[12]在利用平臺內經營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場景下,平臺經營者可以為自營業務提供競爭對手的完全信息,與此同時平臺內經營者卻還處于“信息迷霧”中無法發現正確的方向。在市場競爭下,一方擁有完全信息不會帶來美好的“完全競爭市場”,只會讓市場競爭機制在單方面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下進一步失靈,無法發揮應有功用。
(三)行為對消費者的影響
如上所述,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會對平臺內經營者和市場競爭造成影響,而這一切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損害消費者利益。當面對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手段行為時,平臺內經營者增加數據保護成本或減少創新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會投射到消費者身上,減損消費者福利。與手段行為類似,平臺經營者自我優待的目的行為同樣會減損平臺內經營者創新或優化產品的積極性,因為只有當平臺內經營者付出加倍努力時才有可能抹平其業務與自營業務的差距,而數據能夠被輕易獲取的事實則會讓其陷入更深層次的死循環。不僅如此,平臺經營者獲取競爭對手數據的終極目標在于仿制并取代平臺內經營者的產品,這在美國眾議院對亞馬遜的調查報告中已有所體現,且已遭到大量平臺內經營者的抗議與控訴。上述事實表明,自營業務的出現看似在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之外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但實際上卻會導致消費成本的大幅上漲并嚴重限制消費者在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之間自由選擇的權利。
不僅如此,消費者在消費選擇時還會由于信息不充分和自身的認知局限存在被誤導的可能。為實現消費者與商品的快速匹配,平臺經營者通常會借助智能算法和搜索排名工具幫助消費者節約搜尋成本,然而自營業務因優待行為產生的競爭優勢在算法的幫助下卻極易導致信息不充分的消費者做出錯誤的選擇。如果消費者想打破信息困境,則需要付出更多搜尋成本。而且即使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決策也是高度情景化的,他們通常只會關注那些顯著信息。[13]在為其量身定制的用戶畫像及場景的干擾下,消費者基于自身的認知局限只會關注那些借助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及智能算法生成的顯著信息。此外,消費者的數據隱私權也可能因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行為受到不當侵害。平臺內經營者為了優化服務和自身發展需要,會在征得消費者同意的基礎上收集消費者的行為、喜好、習慣等數據并進行整合,與此同時平臺經營者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行為并不一定取得消費者的授權。在這種情況下,平臺經營者的行為極易侵犯消費者的個人數據利益和數據所表現出來的個人隱私權。
四、 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競爭法規制路徑
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雖然在我國尚未爆發出系統性的反競爭風險,但該行為對平臺內經營者、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和消費者的不利影響卻是真實存在的。在我國加強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的背景下,有必要未雨綢繆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探討該行為在現行競爭法語境下的規制路徑。
(一)“兩反法”的適用競合與選擇
《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兩反法”)共同構建了我國競爭法的規制體系,兩法也有其各自的規制重點。其中,《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解決競爭過度時市場道德缺失導致的競爭失序問題,《反壟斷法》則更關注因競爭受限而導致的競爭不足問題。[14]兩法的側重點不同意味著同一行為在我國競爭法的語境下既可能被《反壟斷法》調整,也可能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上文的分析表明,不管是手段行為還是目的行為,都會對平臺內經營者、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和消費者造成不利影響,這也意味著“兩反法”均可作為規制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行為的法律依據。
與“兩反法”有其各自的規制重點相對應的是,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造成的損害也各有側重。雖然平臺經營者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手段行為既侵犯了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權益,又影響了其公平競爭利益,但該行為造成損害的側重點仍在數據權益上,而公平競爭利益只是數據權益受損的反射利益;優待自營業務的目的行為使得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無法與自營業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該行為相對于手段行為對公平競爭利益的損害更為明顯。此外,手段行為并不能限制平臺內市場中的競爭,只是由于市場道德的缺少會導致競爭的失序與紊亂,而通過優待并使自營業務獲取競爭優勢,平臺經營者能夠掌握平臺內市場的資源配置,使得競爭機制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手段行為造成的損害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更匹配,而通過反壟斷法規制目的行為則更合適。當然,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屬性意味著在判斷其中某一行為的合法性時也時常需要考慮到另一種行為的性質。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以手段行為為中心
⒈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規制。《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構成要件,如果要將第9條用于規制平臺經營者的手段行為,就必須從兩方面進行討論。其一,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可以被界定為商業秘密。從第9條的定義中可以得出商業秘密的三個屬性,即秘密性、保密性和價值性。因此,只要契合這三個屬性即可將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數據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價值已不言而喻,平臺經營者亦通常會對作為核心資產的數據采取保密手段,故秘密性或者說“不為公眾所知悉”才是界定相關數據商業秘密屬性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可以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平臺內經營者本身擁有且以非公開為目的的數據,另一類則是它在平臺中進行交易活動時搜集的公開數據。從數據的分類可以看出,那些非公開數據本身就為平臺內經營者私有,是其賴以經營的根本,只不過是為了交易方便平臺內經營者將這些信息作為數據在平臺基礎架構中儲存。在沒有技術手段的幫助下,這些數據中承載的經營信息和產品信息根本不可能為一般公眾和平臺經營者所知悉。此外,即使是平臺內經營者公開獲取的信息也可以具有秘密性并部分成為商業秘密。因為數據具有結構秘密性的特征,部分數據公開不意味著全部公開,或者說任何用戶都不可能整體獲得全部數據。[15]其二,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手段不正當。平臺經營者擁有整個平臺基礎架構,平臺內經營者的數據則在平臺基礎架構上儲存和流通,但儲存不代表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行為具有正當性。此外,《電子商務法》第31條要求平臺經營者需要確保信息的保密性,在立法者看來,此處的“保密性”指平臺經營者對其保存的信息負責,防止泄露的主體也僅為第三方。[16]然而,筆者認為將“保密性”針對的主體僅限于第三方過于狹隘,應通過目的性擴張解釋將針對主體擴大到平臺經營者自身,要求其僅在法律規定的用途內使用這些信息。第31條的立法目的在于為日后可能發生的糾紛留存證據,而平臺經營者獲取相關數據為己所用的行為明顯與上述目的不符,其利用這些信息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違反了保密性的要求。只有將“保密性”的對象擴大至平臺經營者本身,要求其將信息僅用于證據保存,并將平臺經營者超出上述目的獲取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行為視為非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平臺內經營者的合法權益。
⒉一般條款規制。對于那些難以構成商業秘密的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亦可以為其提供競爭法保護。首先,平臺經營者與平臺內經營者間存在競爭關系。平臺經營者與平臺內經營者原本處于不同層次的市場之中,平臺內經營者則直接面向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而平臺經營者則為平臺內經營者及消費者搭建交易的橋梁,二者之間非但沒有直接利益沖突甚至還存在典型的合作關系。但當平臺經營者通過自營業務進行縱向一體化時,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與自營業務則同在平臺內市場中競爭并存在直接的利益沖突,而平臺經營者與平臺內經營者為了爭奪消費者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其次,在判斷涉數據競爭行為的正當性時,通常需要考慮數據價值、積累數據的成本、獲取和使用行為是否正當及數據的使用方式和范圍。[17]在這四項標準中,前三項判斷標準上文均已論及,故此處著重討論第四項標準即數據的使用方式和范圍。數據的使用方式和范圍與數據獲取后的目的行為相關,如果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目的在于實質替代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那么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相結合給數據原擁有者造成的損害會比單純的手段行為更大,因而手段行為也更容易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的目的即在于優待并增強自營業務的競爭力,雖然自營業務不可能完全替代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但其不僅可以提供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類似的商品或服務,還能夠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平臺經營者獲取數據后的使用方式及范圍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存在明顯的重合,因此平臺經營者的手段行為也應當構成不正當競爭。
(三)反壟斷法規制:以目的行為為中心
在“強化反壟斷”的政策引導下,我國必定會加強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尤其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執法工作,但在加強執法的同時卻仍存在兩個問題無法得到良好解決,其一是平臺經濟特殊性導致的市場支配地位認定難題,其二是加強反壟斷執法的制度績效仍有待觀察。為了消弭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困境,不少學者主張使用全新的規制工具應對這些新問題、新挑戰,然而這些主張卻無法充分回應制度績效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為了實現政府規制與市場調節的平衡,不宜濫用市場支配權,隨意引入新的規制工具,而是應當在傳統分析框架下進行方法革新。換言之,認定一個行為是否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時,仍應當從界定相關市場出發,再分析被告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并在各個模塊內部面向電子商務平臺的新特點進行方法革新。最新出臺的《平臺指南》也是遵循了這樣的思路,從微觀上為平臺經濟反壟斷提供了指引。
相關市場界定方面,明確相關市場可分為相關商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其界定是認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邏輯起點。與微博、臉書等純粹吸引注意力的雙邊非交易市場相比,電子商務平臺這類雙邊交易市場的相關市場界定相對容易,而且可以將平臺的兩邊作為整體考慮。換句話說,在雙邊交易市場中,只需要界定一個市場而非兩個市場。[18]界定相關商品市場時應當從替代性分析的角度考慮電子商務平臺的功能和商業模式,并需要關注平臺的主要用戶群體,因為兩邊的用戶才是平臺賴以發展的基礎。除了關注線上平臺,還需考慮直播帶貨、微商等新型交易方式及線下市場對電子商務平臺的影響。此外,在物流和倉儲系統的支持下,一般而言應當根據電子商務平臺的特點將相關地域市場界定為中國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
市場支配地位方面,傳統意義上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通常以市場份額因素為出發點,輔之以其他因素的考量,我國《反壟斷法》也有依據市場份額推定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但通過動態觀察平臺經濟時代的市場變化可以發現,很多曾經占據大量市場份額的企業因無法持續創新被迫在競爭中敗下陣來,而那些看似市場份額較小的企業卻有強大的市場控制力。因此在電子商務平臺的場景下,認定市場支配地位因素的重心發生了轉移,市場份額因素的作用不斷弱化。[19]換言之,在判斷平臺經營者的市場支配地位時,應當更多考慮網絡效應、數據能力、用戶粘性、技術壁壘等符合平臺經濟特點的新型因素。當然,市場份額因素的作用弱化并不意味著其作用為零,至少該因素代表了相對固定時間內企業的市場力量。而且,由于平臺經營者更多以促成平臺內經營者與消費者間的真實交易而非出售用戶的注意力牟利,相較于注意力平臺或者說雙邊非交易平臺,市場份額因素在電子商務平臺的場景下更容易獲取和計算也更加重要。
濫用行為方面,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讓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無法在平臺內市場中公平競爭,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中的差別待遇。從私法自治的角度來說,平臺經營者給予任何一方優待條件均屬于合同自由,而且自營業務是平臺經營者業務的縱向延伸,平臺經營者也有動機讓其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競爭中占據優勢。當平臺經營者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消費者選擇和競爭機制的互動能夠讓其在網絡效應的壓力下消除優待行為;但當上述兩個條件成立時,平臺經營者的市場力量能夠支持其優待自營業務而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卻無可奈何。
當競爭機制和私法工具無法發揮作用時,反壟斷法需要介入以矯正市場失靈。《反壟斷法》第17條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實施差別待遇,《平臺指南》第17條則根據平臺經濟的特點對差別待遇的考慮因素進行了細化。從行為類型上看,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雖然不涉及價格上的差別待遇,但可將其歸入到“實行差異性規則、標準、算法”項下予以規制。此外,《平臺指南》還細化了交易條件相同的判斷標準,這也為規制平臺自我優待行為提供了依據和準則。[20]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雖然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數據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我國尚未爆發出系統性的反競爭風險,但在“強化反壟斷”政策背景下,我國勢必會進一步加強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執法工作。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將平臺經營者的數據優待行為分層為獲取并分析平臺內經營者數據的手段行為和優待并使自營業務擁有競爭優勢的目的行為,并以此為主線探討了行為對市場的影響。在規制路徑的選擇方面,以行為對市場造成的損害與“兩反法”的匹配度為標準,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可以被分別置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的框架下予以規制。當然,平臺經營者自我優待行為的法律規制是一個系統工程,本文僅選取了一個切面,更多的研究仍有待在未來展開。
【參考文獻】
[1]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信息研究所.平臺經濟與競爭政策觀察(2020年)[EB/OL].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網站,http://english.catr.cn/kxyj/qwfb/ztbg/202005/P020200530560741723821.pdf.
[2]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EB/OL].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3]Alexei Alexis.EUantitrust case against Amazon centers on unfair use of third-party data[J].2020WL6624956.
[4]康愷.反壟斷調查“第二季”:歐盟再撕亞馬遜或進一步加強立法[EB/OL].新浪網,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11-12/doc-iiznezxs1363905.shtml.
[5]梅傳強,張嘉藝.“套路貸”犯罪罪數認定問題探析[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0,(2):52-62.
[6]薛虹.論電子商務第三方交易平臺——權力、責任和問責三重奏[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39-46.
[7]高薇.弱者的武器:網絡呼吁機制的法與經濟學分析[J].政法論壇,2020,(3):80-92.
[8]朱一飛.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J].政法論叢,2005,(1):66-71.
[9](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M].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84.
[10]Pablo Ibanez Colomo.Restrictions on innovation in EU competition la[J].European Law Review41 2016:201-219.
[11]孫晉,李勝利.競爭法原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
[12]G.Stigler.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9,1961:213-225.
[13]Russell Korobkin.Bounded Rationality,Standard Form Contracts,and Unconscionability[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70,2003:1225-1226.
[14]張守文.經濟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396-397.
[15]盧揚遜.數據財產權益的私法保護[J].甘肅社會科學,2020,(6):132-138.
[16]電子商務法起草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條文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05.
[17]刁云蕓.涉數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J].知識產權,2019,(12):36-44.
[18]時建中,張艷華.互聯網產業的反壟斷法與經濟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55.
[19]陳兵.互聯網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方法再探[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6):80-88.
[20]陳兵,趙青.開啟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新局面[J].中國價格監管與反壟斷,2020,(12):21-23.
(責任編輯:趙婧姝)
The Regul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on Using the Operator Data
in the Platform to Treat Self-Supporting Business
Wu Kaiwen,Wang Chengtang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platform operators using the data of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to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ir own busi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means of obtain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and the purpose of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ir own business.This behavior will infringe th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and the interests of fair competition,disturb the order of market competition,affect the full play of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and ultimately lead to the loss of consumer interests.The two “anti-monopoly laws” have their own key points of regulation.The damage caused by means behavior is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an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regulate the purpose behavior through the anti-monopoly law.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means behavior may meet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infringement of trade secrets or general terms;In the context of anti-monopoly law,purposeful behavior may violate the provision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abusing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Key words:platform operator;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self operated business;competition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