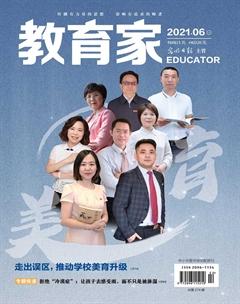找回被“遺失”的感受力
曹霽 周麗


2020年11月,江蘇省南京市17歲男孩與其母發(fā)生口角并產(chǎn)生沖突,致其母死亡。時(shí)隔一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巴彥縣15歲女孩與其母發(fā)生矛盾,將母親殺害后藏尸冷庫(kù),直到3個(gè)月后才被警方發(fā)現(xiàn)。這些聳人聽(tīng)聞的案件讓人不寒而栗,正處花樣年華的青少年,竟然感受不到寸草春暉,觸摸不到世界的美好。我們不禁思考,生活條件越來(lái)越好,可孩子們?yōu)槭裁醋兊迷絹?lái)越“冷漠”?
在社會(huì)快速發(fā)展的今天,“冷漠癥”正在兒童青少年群體里悄無(wú)聲息地蔓延。微博上,“中國(guó)加入聯(lián)合國(guó)50周年”話題沖上熱搜,不少網(wǎng)友流下感動(dòng)的眼淚,部分學(xué)生卻表示對(duì)此并沒(méi)有太多感觸。生于安樂(lè)的“新生代”,享受著現(xiàn)代文明的成果,學(xué)習(xí)著多元的知識(shí),可是卻“聽(tīng)不見(jiàn)鳥(niǎo)語(yǔ)”“聞不見(jiàn)花香”,甚至對(duì)世界失去了敬畏。未曾想,這樣的質(zhì)變,背后隱匿著眾多微小而不易察覺(jué)的量變。
被“遺失”的感受力
宋思文是一名初二學(xué)生,在她看來(lái),感受力就是能觀察生活、感受生活的一種能力。母親節(jié)那天,語(yǔ)文老師布置了以《我的母親》為題的作文,宋思文一邊抱怨著老師為什么要“蹭熱度”,在本就繁重的作業(yè)上又加一項(xiàng),一邊習(xí)慣性地在網(wǎng)上搜索“母親作文”的詞條。她點(diǎn)開(kāi)幾個(gè)范文閱讀了一下,然后花十五分鐘就寫(xiě)完了這篇600字的作文。轉(zhuǎn)天,老師點(diǎn)評(píng)他們的作品“沒(méi)有靈魂”,因?yàn)榻簧蟻?lái)的作文幾乎都是如出一轍的“頭上多了幾根銀白的發(fā)絲”“臉上布滿了皺紋”……“一開(kāi)始我們覺(jué)得很好笑,后來(lái)才發(fā)覺(jué)我們很少有人能真正走進(jìn)母親的生活,仔細(xì)觀察母親,所以又覺(jué)得有些內(nèi)疚。”
宋思文是一部分青少年的縮影,他們習(xí)慣用“技巧”替代“感受和認(rèn)知”,缺少直接的生活體驗(yàn)和沉浸于自然的機(jī)會(huì),不善于觀察細(xì)節(jié),也不會(huì)進(jìn)行情感的傳遞。他們每天家庭、學(xué)校兩點(diǎn)一線,就像生存在一個(gè)沒(méi)有時(shí)間感和空間感的盒子里,無(wú)法躍出來(lái)體驗(yàn)精彩的世界。
“現(xiàn)在的學(xué)生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接觸的內(nèi)容太單一,缺少審美能力和生活閱歷,對(duì)文學(xué)的感知力也在逐漸下降。”來(lái)自杭州的一位中學(xué)語(yǔ)文教師說(shuō)道。讓他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的,是在教《故都的秋》時(shí),讀到“從槐樹(shù)葉底,朝東細(xì)數(shù)著一絲一絲漏下來(lái)的日光”,他的內(nèi)心感受到無(wú)比安逸,但望向?qū)W生,卻發(fā)現(xiàn)他們?cè)缫鸦杌栌_€有一次是教《背影》一課時(shí),在講述了父親到車站送作者離開(kāi),給作者買橘子的情節(jié)后,他問(wèn)學(xué)生“感受到什么樣的父愛(ài)”,講臺(tái)下的學(xué)生一臉茫然地問(wèn)他“橘子和父愛(ài)有什么聯(lián)系”。對(duì)此,他深感無(wú)奈:“一些書(shū)中所描述的經(jīng)歷,他們不能感同身受,也就無(wú)法與文本產(chǎn)生共鳴。學(xué)生真實(shí)生活經(jīng)歷和感知的匱乏,讓我在教課的過(guò)程中常常感覺(jué)很吃力。”
這樣的教學(xué)困惑同樣出現(xiàn)在高中歷史教師王謙的身上。“學(xué)生們對(duì)于從古至今的中西方思想和制度演變的理解非常有限,對(duì)于那些璀璨的世界文明,他們內(nèi)心毫無(wú)波瀾,一般都是考試前死記硬背那些知識(shí)點(diǎn)。”在講到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王謙特意在班里播放了電影《無(wú)問(wèn)西東》,想讓學(xué)生感受歷史的厚重,珍惜現(xiàn)在的生活。課后他問(wèn)起學(xué)生的感受,有學(xué)生表示“挺無(wú)聊的,不知道是文藝片還是愛(ài)情片”。
不久前,一條“云南高三教師暫停講課讓學(xué)生走出教室欣賞晚霞”的新聞備受關(guān)注,人們紛紛呼吁“應(yīng)該多一些這樣的教師”。可見(jiàn),在“高考”重壓之下,學(xué)生連享受風(fēng)景的時(shí)間都很稀缺,更別提靜下心來(lái)感受自然萬(wàn)物對(duì)心靈的蕩滌。“學(xué)生成績(jī)好,家長(zhǎng)才覺(jué)得教師培養(yǎng)得好。情感傳遞到位了,但成績(jī)沒(méi)提上去,家長(zhǎng)只會(huì)覺(jué)得教師能力有問(wèn)題。”王謙感嘆道。
在我們的認(rèn)識(shí)中,孩子的感受應(yīng)該是外露的、強(qiáng)烈的,但日漸“冷漠”的青少年讓我們意識(shí)到,孩子的感受力正在被“偷走”。除了學(xué)校教育的“偏頗”,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專注于兒童心理成長(zhǎng)教育的公益機(jī)構(gòu)“藝啟夢(mèng)想”的副總干事劉艷表示,在家庭教養(yǎng)的過(guò)程中,家長(zhǎng)的過(guò)度關(guān)注和疏離都可能導(dǎo)致孩子形成負(fù)面的認(rèn)知習(xí)慣。
崔紅梅是一名高二學(xué)生的母親,她覺(jué)得自己孩子的“情感張力”越來(lái)越小了,看到別人遇到困難時(shí)會(huì)覺(jué)得“這么點(diǎn)小事都解決不了”,看到美景也經(jīng)常拋出一句“有什么好看的”。“家長(zhǎng)已經(jīng)把他需要面對(duì)的困難都解決了,他沒(méi)有什么機(jī)會(huì)能夠自己去探索生活、探索世界。”崔紅梅之前還會(huì)帶孩子看話劇、旅游,但孩子上初中之后,她將對(duì)孩子的關(guān)注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學(xué)習(xí)上,“父母之愛(ài)子,則為之計(jì)深遠(yuǎn),至少得上個(gè)好大學(xué),找份好工作啊”。
缺乏感受力的人是暗淡無(wú)光的
“感受力”一詞,眾說(shuō)紛紜,聽(tīng)起來(lái)也有點(diǎn)“玄”。簡(jiǎn)言之,感受力就是一個(gè)人對(duì)人、事、物、情等的敏感度。“感”從何來(lái)?“感”由“心”生。毋庸置疑,感受力強(qiáng)的人,生命具有更加豐富細(xì)膩的體驗(yàn),靈魂也處于更為舒展的狀態(tài)。
在鋪陳了一個(gè)個(gè)彌漫在教育、生活中難以察覺(jué)卻又“細(xì)思極恐”的事例后,我們?cè)噲D追問(wèn),為何要警惕兒童青少年感受力的失落?感受力之于兒童青少年的成長(zhǎng)有何重要性?
兒童教育專家李躍兒在其創(chuàng)辦的芭學(xué)園設(shè)定了15項(xiàng)教育目標(biāo),“使孩子成為具有感受力的人”被置于第二項(xiàng)。之所以重視感受力,與李躍兒此前的教育經(jīng)歷有關(guān)。在創(chuàng)辦芭學(xué)園之前,李躍兒曾在公立學(xué)校從事美術(shù)教學(xué)多年。其間,她愈發(fā)深刻地意識(shí)到,很多孩子五六歲剛開(kāi)始畫(huà)畫(huà)時(shí)“簡(jiǎn)直就是世界級(jí)大師”,但經(jīng)過(guò)學(xué)習(xí)后,他們畫(huà)出來(lái)的只是繪畫(huà)的技術(shù),而失去了從心靈流淌出的對(duì)于所畫(huà)對(duì)象的獨(dú)特感受。
不只是美術(shù)教學(xué),山西孝義崇德小學(xué)音樂(lè)教師岳曉麗表示,音樂(lè)作為美育課程之一,是以審美來(lái)觸發(fā)學(xué)生的。在音樂(lè)課程標(biāo)準(zhǔn)中,感受與欣賞被作為音樂(lè)教育四大領(lǐng)域之首。然而,學(xué)校的音樂(lè)教育乃至社會(huì)上各種藝術(shù)特長(zhǎng)生的培養(yǎng),往往都只側(cè)重于對(duì)學(xué)生技能的單一、機(jī)械化訓(xùn)練,而忽略了藝術(shù)本體及其本質(zhì)上的功能和作用。一項(xiàng)針對(duì)全國(guó)義務(wù)教育階段音樂(lè)教育的抽調(diào)結(jié)果顯示,很多學(xué)校的音樂(lè)課“教了和沒(méi)教一樣”。
這種本末倒置現(xiàn)象充斥在各學(xué)科的教育教學(xué)中。在李躍兒看來(lái),如果只講求知識(shí)、技術(shù),而忽視靈魂,人類無(wú)異于機(jī)器人。人類要求的并不只是知識(shí)、技術(shù),籠罩在知識(shí)和技術(shù)上的,應(yīng)該是一種人格的光輝和可以刻在人的概念之中的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感受力、情感,還有同理心、洞察力等。這些都不是在課堂上通過(guò)教師講述、問(wèn)答、抄寫(xiě)的方式能夠?qū)W到的,而是需要慢慢熏陶的。”
“很多人認(rèn)為孩子不跳樓、不自殺好像就是正常的,但是孩子的承受力、感受力、壓力、恐懼、焦慮……我們忽略得太多,沒(méi)有看到。”吉林省公主嶺秦家屯鎮(zhèn)二中教師李素懷曾發(fā)現(xiàn)班上有一名男生,常常用圓規(guī)的鋼尖把胳膊和手劃傷,舊傷未好又劃上新傷,平時(shí)也很少與同學(xué)交流、玩耍,從未見(jiàn)過(guò)他大笑,也沒(méi)見(jiàn)過(guò)他流淚。在教育生活中,李素懷發(fā)現(xiàn)越來(lái)越多孩子變得“麻木”。
“忽略孩子的心靈會(huì)讓他們變麻木。”兒童性教育專家胡萍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幸福感是從豐盈的生命、豐富的生活體驗(yàn)中獲得的。孩子的感受如長(zhǎng)期被忽視和破壞,會(huì)導(dǎo)致他們把連接心靈的通道關(guān)閉,讓他們的內(nèi)心變得粗糙、麻木、冷漠,從而侵蝕他們的幸福感。
“一個(gè)缺乏感受力的人是暗淡無(wú)光的人,也會(huì)使身邊的人感覺(jué)到暗淡無(wú)光、痛苦不已。” 李躍兒道,兒童青少年的感受力準(zhǔn)確說(shuō)是單一。造成這種單一的原因不僅在于孩子直接生命體驗(yàn)的匱乏,也在于成人正確引領(lǐng)的缺位。“成年后,我們變得準(zhǔn)確無(wú)比,那種人類的、生命的、情緒的、不可說(shuō)的東西不見(jiàn)了。”由于自身缺乏感受力,且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這方面的熏陶和訓(xùn)練,很多教育者對(duì)孩子感受力的培養(yǎng)無(wú)從做起。孩子的感受力像洪水一樣亂淌,沒(méi)有人給他們疏通,挖一個(gè)正向的渠道,朝著對(duì)人類有利的方向去引領(lǐng),朝著美好、建設(shè)性、利他的方向去培養(yǎng)。“這是教育的一個(gè)很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