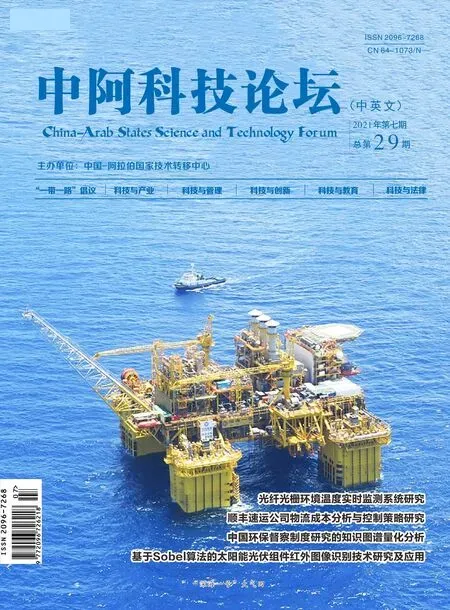中國環保督察制度研究的知識圖譜量化分析
楊騰婕 顧 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法政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4)
1 引言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該文件規定,從2016年開始,每2年左右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環保督察。由此,我國環保督察制度由著眼地方轉向縱觀中央,由以生態環境部為主轉向中央主導,致力于環保督察的常態化管理。由表1可知,截至2021年5月,中共中央共計展開兩輪中央環保督察,已辦結8 766件,責令整改5 442家,處罰金額高達18 213.33萬元。歷經6年的政策探索,目前已形成了“地方+央企+部門”的三維督察結構,通過邊督邊改的執行手段,逐步推動生態環境問題的查處與解決,對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傳導生態環境保護壓力、建立長效機制、營造督察氛圍起到重要作用。

表1 各批次環保督察進駐時間及督察對象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檢索式為“主題=環保督察or環保督查”,來源期刊類別為北大核心、CSSCI、CSCD期刊,文獻檢索時間跨度定為2010年至今,共計檢索得到192篇期刊文獻,通過人工篩選剔除了目錄、訪談、通知等條件不符的文獻,最終保留177篇高質量文獻。數據處理時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主要使用CiteSpace5.7.R2軟件對文獻進行多重分析,繪制環保督察制度研究知識圖譜,既能顯示可視化的知識圖形,也能反映系列化的知識譜系。運用NoteExpress和Ucinet軟件進行凝聚子群分析,進一步挖掘文獻數據背后的信息與意義,以期多維立體地呈現國內環保督察制度研究的態勢與圖景。
本文主要采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凝聚子群分析與聚類分析。
(1)凝聚子群分析:主要利用NoteExpress統計得到高頻關鍵詞的共現次數矩陣,進而導入Ucinet軟件構建關鍵詞網絡圖譜,通過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對該網絡中存在多少子群、某一子群中的成員關系、各個子群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個子群間的成員關系進行分析。
(2)聚類分析:主要運用CiteSpace進行聚類分析,以共詞出現的頻率為分析對象,把共詞網絡關系簡化為數目相對較少的聚類過程,進而對關鍵詞共現進行分類與概括,通過數據形象地反映該領域的研究熱點。
3 結果分析
3.1 發文結構分析
3.1.1 發文時間分布
通過對我國環保督察制度相關研究文獻的發布時間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發文時間分布圖如圖1。我國環保督察制度研究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0—2015年,該階段研究文獻數量呈現出緩慢增長態勢,年度發文量均不高于5篇,尚處于待開發狀態;第二階段為2016年至今,2015年發布的《2015年全國環境監察工作要點》中強調,上級環保部門要對下級政府的制度落實情況進行綜合性檢查,環保督察把重點放在深入一線督事上,以督事、督企來實現督政[1]的最終目的,由此,環保督察制度相關研究呈現井噴態勢。

圖1 發文時間分布圖
3.1.2 核心作者分布
根據普賴斯定律計算公式,計算得M值為1.29,即發文量大于2篇的作者為環保督察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對發文量為3篇及以上的5位作者進行統計分析可知,核心作者共發文16篇,占總發文量的9.03%(見圖2),說明該領域尚未形成核心學者研究群體。

圖2 核心作者合作網絡圖譜
3.2 研究熱點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環保督察制度研究的內在邏輯,采用Ucinet軟件進行社會網絡凝聚子群分析,以剖析聚類塊之間的聯結意義。通過對高頻關鍵詞的統計和分析,可以概括出4個探索方向:一是督查察點(見圖3關鍵詞族群1、4、6、7、9、11、14、15、16、17、19、29);二是責任機制(見圖3關鍵詞族群3、8、12、13、20、23、25、28);三是執行主體(見圖3關鍵詞族群2、18、22、27、30);四是問責程序(見圖3關鍵詞族群5、10、21、24、26)。
3.2.1 督察重點

圖3 高頻關鍵詞的凝聚子群結構(前30位)
為具體踐行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要求,我國國務院與生態環境部實施了專項治理行動,其中環保督察成為一項有力舉措。2019年出臺的《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中規定,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是兩級督察體制——中央級和省級。中央環保督察以省級政府為主要進駐單位,對各省份環境治理的進展評價分為4個檔位,即顯著進展、重要進展、積極進展、一定進展[2],并將各省的“成績單”公之于眾。數據庫中文獻多從問題視角出發,尋求優化路徑,其中揭示了中央環保督察組制度面臨的兩大問題:生態環境部對地市級政府開展的綜合督查缺乏法律依據、中央環保督察的法律依據效力過低[3]。與中央環保督察相比,省級督察機構雖然已基本完成建構,但運行機制尚未完全理順,存在監督定位不明確、督察機制不完善的問題。為形成中央和省級的督察合力,要明確省級督察是中央督察的延伸和補充的定位[4],加強省級生態環保督察的支撐作用。
3.2.2 責任機制
我國環境保護的督察機制是結合中央領導與生態環境內部體系的雙重驅動結構,中央頒布的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是我國目前關于環境保護層面的最高級規劃[5]。我國環保督察始終堅持“黨政同責”與“一崗雙責”的原則,規定中央級別環保督察組、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與各級黨委和政府的職責分配任務相同。
在環保督察執行過程中,為避免由于責任機制不明確而引發的基層執法偏差,以“一刀切”的問題為例,專家學者們各抒己見。在第二輪第一批環保督察工作中,生態環境部發函明確表示:禁止搞“一刀切”和“濫問責”,一律從簡,減輕基層負擔。有學者剖析了“一刀切”問題產生的三大原因:協同不足的治理模式、權責失衡與高壓問責、從嚴執法的政策要求[6]。為防止“一刀切”和“濫問責”帶來的消極影響,可以建立關停企業與就業轉移相結合的促進機制[7],提升環保督察在政府、市場、社會三大主體中的接受度,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共同努力、協同推進[8]。
3.2.3 執行主體
國內對于環保督察的主體分析主要分為兩大流派:一是以區域環保督察組為主體,以監督地方企業為主要內容的常規型治理[9];二是以中央環保督察組為主體,以監管地方黨委和政府為主要內容的運動型治理[10]。目前的環保督察工作是以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的名義展開,國務院成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領導小組,生態環境部牽頭負責具體的組織協調工作[11],督察政府具體執行環保政策的相關要求,督察重在督政。然而,無論屬于哪類主體分析的流派,研究文獻都強調中央環保督察依托國家的“專斷性權力”[12],中央與地方之間應當遵循合作與激勵原則,確保能夠在短期內有力推進環保督察工作。但反觀現實,執行主體僅停留在政府內部的運動型治理,難以解決后期執行主體單一、可持續性低下的問題。通過研究發現,環保督察制度中主體改革的方向必須重在完善多元共治、協同發展[13]的統籌格局。
3.2.4 問責程序
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生態環保督察工作的系列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中央環保督察組認真落實《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紀律規定》和“一督查兩報告”制度[14]。研究表明,出臺的相關文件主要對問責主體和問責方式、相關責任人的申訴制度[15]進行了明確,但對于問責的事實確立、具體標準、具體程序、結果復核等環節仍缺乏規范化的官方文件,在現實運行中多依靠實踐性的摸索,難以形成完整而系統的問責程序。從環保督察的職責來看,督察的結果需要上報到中央并反饋到地方。一方面,通過層層材料的移交,等待中央高層做出決策后執行,再經歷行政審批程序的滯后,嚴重拖慢了環境問題治理進程;另一方面,督查組的反饋意見和相關巡查數據下達到地方政府,但由于督查組不能直接對地方政府采取行政處罰的懲戒手段,只能通過約談環保部門負責人、企業法人的形式來保證督察權威[16],因此地方督察工作難以到位。問責程序的不完善導致我國環保督察治理成效顯現緩慢,很難形成長效性的正向影響力。
4 總結
通過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中關于環保督察制度的高質量研究文獻進行知識圖譜量化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從現實審視來看,2015年起始的環保督察制度已形成了“地方+央企+部門”的三維督察結構,現已對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傳導生態環境保護壓力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從發文結構來看,我國環保督察制度研究已經歷緩慢增長階段,現呈現井噴式研究態勢。由普賴斯定律計算公式可得,該領域尚未形成核心學者研究群體;
第三,從研究熱點來看,學者研究的重點在于督察重點、責任機制、執行主體、問責程序,逐步探索環保督察制度的常態化和長效性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