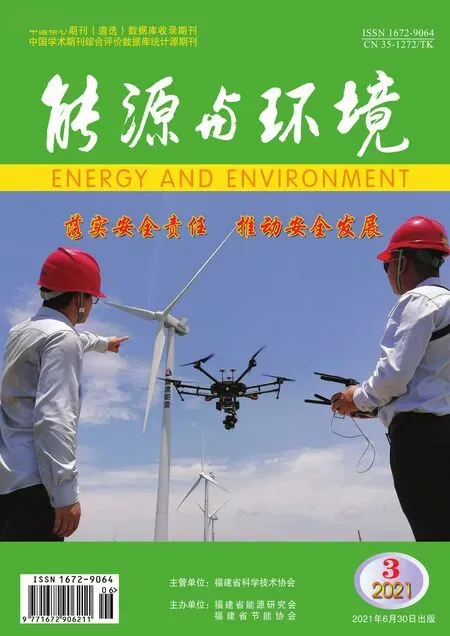次氯酸鈉對MBR 與污泥微生物的影響研究綜述
趙少宏 于成志 張新穎 張莉敏 陳美香 游麗燕
(1 福州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福建海峽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 350014)
膜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MBR)具有優良的污染物去除性能,能夠滿足污水處理提質增效的要求,近年來被大力推廣。但膜污染問題限制了MBR 的進一步發展,在線化學反洗能有效緩解膜污染的形成,次氯酸鈉是被應用最早和最廣泛的一種化學藥劑。隨著人們研究的深入,發現在使用次氯酸鈉進行清洗的過程中,有50%~60%的次氯酸鈉可從膜腔內擴散至膜區、與污泥接觸[1]。次氯酸鈉對MBR 系統以及污泥微生物的影響也逐步受到學者的關注。
1 膜污染與在線反洗
MBR 能起到良好的污泥截留效果,其功能可以取代常規活性污泥法中的二沉池,大大降低剩余污泥的產生量,其剩余污泥的產生量為傳統處理工藝的30%~50%(甚至為0),這將有效降低污泥處理設施的規模和運行費用[2]。但在實際運行中經過各種物化作用和復雜反應,導致多種有機和無機物質沉積在膜表面或者堵塞膜孔進入膜內部,改變膜孔徑及膜面結構,出現膜污染[3]。有機污染物和微生物污染是導致膜水通量衰減的主要原因[4],控制有機污染物和微生物污染的形成是延長膜過濾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線反洗是將化學清洗液加入反沖水中、注入膜腔內,并通過膜微孔滲透到原水側。此過程可有效地殺滅膜內外表面的細菌并分解附著在膜表面上的有機物,恢復膜通量。
2 次氯酸鈉基本性質與清洗機理
2.1 次氯酸鈉基本性質
次氯酸鈉是一種不穩定的白色粉狀固體,化學式NaClO。工業上通常使用的是次氯酸鈉水溶液,呈黃色或者淡黃色。次氯酸鈉易溶于水,但在光照、受熱等條件下容易分解,在貯存中會緩慢地分解而生成氧氣,并生成副產物氯酸鈉。在30℃時,次氯酸鈉水解常數為9×10-8,其水解程度受溶液濃度和pH值的影響較大,溶液濃度越高越容易水解,pH 值高有利于次氯酸鈉穩定。當pH>10 時,溶液呈強堿性,有效氯基本以ClO-為主;當pH<5 時,溶液呈酸性,有效氯主要以氯氣和HClO 為主;而溶液在微堿性、pH 約為8.5 時,有效氯主要以次氯酸鹽和HCl 為主,水解反應如式(1)~(3)所示[5]。

因為次氯酸鈉生產工藝簡單,產品成本低廉,具有廣譜、高效、安全的殺菌特點,在常溫下便可發揮高效的漂白、殺菌和氧化作用等優點,所以成為了在線化學清洗過程中應用較為廣泛的化學藥劑之一。
2.2 清洗機制
目前通常認為次氯酸鈉作為一種強氧化劑,其水解生成的次氯酸會進一步分解生成新生態氧[O]。新生態氧[O]具有極強的氧化性,氧化微生物細胞壁、細胞膜中的蛋白質,導致細胞壁和細胞膜的結構破壞,細胞質基質無法穩定存在于細胞結構中;細胞壁和細胞膜的結構破壞使新生態氧[O]進入細胞內部,氧化細胞內的酶、核糖核酸(RibonucleicAcid,RNA)和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DNA)使細胞失去活性,微生物迅速死亡[6]。其反應如式(4)和式(5)所示。

相關研究也表明次氯酸鈉作為一種強氧化劑能將膜污染中有機污染物質中疏水性官能團氧化為酮類、醛類和羧酸等親水官能團[7],使得污染物質更容易從膜表面分離。同時,它也分解了較大的有機顆粒,促進它們的溶解,迅速恢復膜通量,提高受污染膜的滲透性能,并且可有效抑制絲狀菌的沉積。
但在實際清洗中其機制可能要更加復雜。Wang 等[8]研究發現在使用次氯酸鈉進行在線清洗的過程中,溶液pH 對清洗效果具有較大影響。研究發現,雖然在pH<5 時,有效氯以HClO 為主,HClO 與ClO-相比具有更強的氧化能力,但pH=11時卻比pH=5 時清洗效率更高,而出現該現象的原因可能與ClO-/HClO 在污垢層中的擴散行為密切相關。在堿性條件下,使用次氯酸鈉導致污染層的pH 值增加,造成了污染層表面靜電排斥力增加,使基體結構產生負電荷,變得更加松弛[9],因此,在更為疏松的污染層中ClO-能有更快的滲透速率。這也表明了次氯酸鈉在清洗時,并不單純依靠活性氯物質與污染物質的氧化反應,次氯酸鈉和pH 之間存在某種相互作用。這種作用不僅影響了次氯酸鈉本身的性質,也對膜污染層或者污染物質產生了一定影響,導致了并非氧化作用強則清洗程度高的結果。
3 次氯酸鈉對污泥微生物的影響
目前,關于次氯酸鈉對污泥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污泥中脫氮功能微生物的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溶解性有機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等含量變化、化學官能團變化、相關酶活和處理效果等方面;也有部分研究對次氯酸鈉清洗前后MBR 體系中污泥微生物群落組成、豐富度變化等進行了分析。
3.1 次氯酸鈉對脫氮功能微生物代謝和活性的影響
Han 等[1]研究發現,次氯酸鈉對好氧污泥體系中氮代謝過程中的關鍵酶有抑制作用。當NaClO 濃度為5 mg/g-SS 和10 mg/g-SS 時,在數分鐘內破損細胞比例就急劇上升,高濃度的次氯酸鈉對脫氫酶(Dehydrogenase,DHA)活性有抑制作用,三磷酸腺苷(Adenosinetriphosphate,ATP)濃度的變化也有類似趨勢。當次氯酸鈉濃度高于10 mg/g-SS 時,污泥體系中的硝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均隨次氯酸鈉濃度的升高而降低,且反硝化過程比硝化過程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強。
也有學者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微生物對次氯酸鈉耐受程度存在明顯差異,自養菌相比異養菌則要更加敏感[10],但是其具體機制尚不明晰,有可能與細胞膜成分、結構的差異或者不同代謝方式中電子鏈的解耦和破壞有關。有學者從污泥本身研究了脫氮系統微生物的對次氯酸鈉的應激反應。Cai 等[11]研究發現活性污泥暴露于2 mg/L、5 mg/L、10 mg/L 和20 mg/L次氯酸鈉30 min 后,活性污泥中的EPS 大量增加,其中蛋白質(Protein,PN)含量分別增加了9%、11%、19%和39%,而多糖(polysaccharide,PS)增加了4%、4%、11%和17%。孫明[7]研究發現在線清洗條件下,次氯酸鈉沖擊后膜污染速率急劇增加。污泥絮體表面能降低了18.38%,疏水性增加了1.35 倍,污泥絮體的粘附能增加了約1.88 倍。經次氯酸鈉沖擊后的污泥具有更高的粘附到膜表面的潛勢,并且EPS 大量釋放導致跨膜壓差(Trans-Membrane Pressure,TMP)快速增加。
Zhang 等[12]進一步探究了次氯酸鈉對MBR 污泥系統中微生物的影響,推斷了次氯酸鈉在進入污泥體系中,影響其代謝和作用的機制。研究推測次氯酸鈉促使微生物釋放出大量DOM 的機理可能為如下3 種:①次氯酸鈉首先通過穿過細胞壁破壞細胞,產生大量類腐殖質和低分子鹵化副產物;②隨后細胞釋放了胞內有機物,但迅速被次氯酸鈉降解和腐殖化,同時形成相對高分子量的鹵化副產物;③殘留的次氯酸鈉和結合氯繼續與細胞反應。
3.2 次氯酸鈉對污泥微生物群落的影響
王旭東等[13]采用倒置A2/O-MBR 研究了次氯酸鈉在線反洗對MBR 系統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結果發現對氯消毒劑有一定抵抗性的變形菌門從53.4%增加到77.8%,而擬桿菌門從33.4%減少至14.5%。經次氯酸鈉反洗后,好氧池和濾餅層在科水平微生物群落分布上十分相似,固氮螺菌科、叢毛單胞菌科等相比次氯酸鈉反洗前明顯增加。這說明了某一些具有抗性的污泥微生物經歷過清洗后能夠存活下來,而之前優勢生物群落被較大程度的削弱,因此此類抗性微生物獲得了更快的成長。Navarro 等[14]使用高分辨率系統發育分析研究了次氯酸鈉水溶液對聚丙烯腈膜(PAN)洗滌性能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次氯酸鈉不能完全去除膜表面細菌,高分辨率的系統發育分析揭示了許多操作分類學單位(OTUs)的存在,表現出耐鹽性,還鑒定了一些與嗜熱耐酸菌株有關的OTUs。這些能夠耐受次氯酸鈉處理的微生物種可能是次氯酸鈉在線反洗后膜污染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對于次氯酸鈉這種在清洗后可能增大膜污染潛力的現象,Bereschenko 等[15]認為可能是以下3 個原因造成的:①存在吸引性的附著表面(即明顯的粗糙表面,可能帶有粘性EPS);②吸附在EPS 基質中的營養成分豐富(即裂解細胞產生的EPS、蛋白質和其他有機大分子);③再生的生物膜層內的微生物群落通常比結構上更復雜。
除了存在某些類型的污泥微生物對次氯酸鈉具有較強的抵抗力、在接下來的清洗中更加容易形成生物膜之外,微生物本身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機制抵御次氯酸鈉的影響。Cloete[16]研究表明污泥中微生物對游離氯的抵抗力歸因于不同微生物細胞結構和蛋白質組成的獨特變化。除了有助于抵抗游離氯的物理屬性外,微生物還通過產生EPS 的固有或適應性抗性機制來防御氧化應激。這些物質與氧化消毒劑反應,有效地降低了可能發生細胞損傷的細胞壁或細胞膜上消毒劑的濃度,尤其是在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系統,由于EPS 的產生、細胞密度,多樣性和微生物的種間相互作用或某些信號分子的傳遞等因素,都能導致生物膜系統比懸浮污泥系統具有更強的抗性以及發生更加復雜的反應。
4 結語
次氯酸鈉作為一種常規的化學清洗劑,在膜清洗中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在長期的在線清洗過程中次氯酸鈉不斷進入到微生物污泥系統中,對MBR 系統的穩定性、運行效果帶來負面影響。MBR 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為了盡可能減少次氯酸鈉在線清洗的副作用,使得清洗效果最大化并維持系統內污泥活性,保證MBR 系統經濟、高效的運行,就必須對次氯酸鈉清洗機制、微生物滅殺機理、甚至加劇膜污染的現象等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以期為實際MBR 工程的運行管理優化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