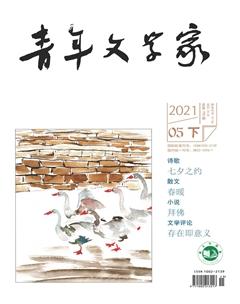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迪布宅門》中的女性形象解讀
劉馨瑤
一、引言
伊扎特·卡姆哈維(1961—)身兼小說家、記者二職,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壇享有較高聲譽,現已出版十多部作品。
《迪布宅門》講述了發生在埃及農村一個名為“迪布”的家族幾代人的故事,小說時間線橫跨三個世紀,以女主人公穆芭拉珂要求孫子在互聯網上為自己給真主寫一封信開始,從穆芭拉珂的視角講述了“歐西”村和在那兒生活的“迪布”家族的歷史,刻畫了眾多立體豐滿的人物形象。由于小說主要關注普通人物的平凡生活,因此發生在真實歷史中的大型事件只作為小說不同時間段的故事背景出現,家庭生活才是小說的主要落腳點。而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必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小說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可以作為了解當時埃及社會女性地位的參考資料。
二、埃及女性主義的發展
19世紀,女性主義伴隨著婦女運動在西方世界產生、發展,女性主義要求男女平等,主張女性與男性不應為附屬關系,女性不應被視為“特殊群體”,女性有權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女性主義者更加注重性別研究,向由父權制思想衍生出的各種習以為常的概念提出質疑,希望真正實現男女平權,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剝削和壓迫。”
女性主義在西方出現以后,開始迅速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埃及是第一個受到女性主義思潮波及的阿拉伯國家。女性主義首先來到埃及并在此迅速興起,有其必然原因。埃及土地曾經孕育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發源于公元前4500年,其中著名的法老時代始于公元前3100年,終于公元前332年。古埃及女性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享有與男性同樣的繼承權,能夠處分自己的財產,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女性能夠對事務發表獨立看法。更有甚者,一些受到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掌握了讀寫能力,能夠躋身于國家統治階層”。在古埃及,普通女性除了享有令同時代其他地區女性望塵莫及的權利外,我們不難注意到法老時代曾經出現過幾位女性法老,其中最著名、其地位也最沒有爭議的是哈特舍普蘇特法老,她為法老時代第十八王朝的繁榮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外,古埃及的王位繼承權利雖然屬于男性,女性無法直接享有繼承王位的權利,但“當國王沒有男性子嗣時,公主的配偶可繼承王位”,因此古埃及的王室女性無疑在王位繼承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學家與歷史學家的使命不同,文學家的創作素材來源于現實生活,但又不僅僅反映當時社會的宏觀現象,所謂“文學即人學”,恰恰說明文學作品是以描寫人為中心的,也就意味著“小說的基本審美范疇是塑造人物”。因此,閱讀《迪布宅門》并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有助于讀者具化當時埃及女性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
三、《迪布宅門》主要女性人物形象解讀
《迪布宅門》主要講述迪布家族的家庭生活,婚姻在家庭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作者將婚姻關系作為人物交往互動的舞臺,為讀者刻畫了多位女性人物形象。其中著墨較多的幾位女性的性格、價值觀和處事方式都迥然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哈菲沙和穆芭拉珂二人的人物形象。
(一)哈菲沙
在阿拉伯世界,“主流男性話語認識女性形象的兩大原型,要么是藏于深閨、裹著面紗、逆來順受的阿拉伯女性,要么是拋頭露面、衣不遮體、搔首弄姿的東方舞娘”。哈菲沙顯然屬于前者,她是穆加希德的大老婆,也是傳統阿拉伯社會價值體系下的典型“賢妻良母”,她不計回報、無私奉獻、善解人意。
哈菲沙與穆加希德結婚時,穆加希德剛剛開始服兵役,只有短暫幾天的休假時間,夫妻二人才勉強有接觸。哈菲沙每天家里家外地忙碌,穆加希德服滿兵役后,終于回歸家庭,卻日日不著家,完全不將妻兒放在眼里。這樣不負責的丈夫卻絲毫沒有令哈菲沙生氣,她將孩子視為帶給她幸福的精神支柱,繼續一成不變地生活。
書中在描述哈菲沙的家庭生活時,有這樣一幕,哈菲沙從地里回來,婆婆給她端來一鍋肉,吃完才告訴她這是貓肉,以此來教育她“身為女人不要眼饞男人的食物,女人不像男人,她們不需要太多的營養”。然而事實是,穆加希德不務正業,沒有擔負掙錢養家的責任,反而是身為女人的哈菲沙日夜操勞,但既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也是男權社會加害者的婆婆卻固守封建思想,倡導男尊女卑。更令人感嘆的是,哈菲沙沒有反駁婆婆的教導,哪怕在婆婆死后,依然堅持將這個觀點視為人生守則,從不違反。哈菲沙和婆婆都是父權制社會里被男性認可的母親,“她們是父權制文化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塑造出的女性楷模,起到的是輔佐、鞏固父權制文化的作用,使女性徹底喪失作為人的主體性”。
與穆芭拉珂相比,哈菲沙的結局有些凄慘,這個將自己視為丈夫和家庭附屬品的女性,終生為別人而活,最終因夜間在房頂為失蹤的兒子祈禱,失足死在了檸檬樹中。父權文化對人的影響和塑造是造成哈菲沙悲慘人生的根本原因,在男性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社會,哈菲沙從小耳濡目染,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價值,更沒有“活出自我”的意識觀念,心甘情愿地淪為父權社會的受害者。
(二)穆芭拉珂
穆芭拉珂是《迪布宅門》的女主人公,甚至可以說她就是小說故事的主線,小說的時間跨度幾乎是與穆芭拉珂一生的歷程相同步的,作者用大量筆墨刻畫了這一立體豐滿的女性形象。
穆芭拉珂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作為阿拉伯社會父權家庭中的一位女性,她雖不懦弱膽小,卻也沒有勇敢捍衛自己的利益、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正如本書譯者所言:“實際上,穆芭拉珂既不是父權制度的叛逆者,也談不上是父權制度的迎合者或幫兇。”
在少女時代,穆芭拉珂與穆泰沙爾相識相戀,但在埃及,女性對于自己的婚事沒有選擇權,包辦婚姻、一夫多妻是極其正常的社會現象。在當時的埃及,婚姻中的兩性關系不平等,男性處于強勢,女性處于弱勢;婚姻對于婦女來說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性可以娶四個妻子,女性則沒有同等的權利;男性可以隨意休妻,而女性則沒有提出離婚的主動權。因此,在父親的安排下,穆芭拉珂被迫嫁給了心上人穆泰沙爾的舅舅穆加希德。確定婚期后,穆芭拉珂雖然一心掛念穆泰沙爾,卻沒有反抗父親,甚至在去另一個城市置辦婚禮物品時,她的“臉上沒有害怕,沒有喜悅,也沒有憤怒,卻隱約有一絲對城市的好奇”。不難看出,正是因為社會大環境沒有給予男性和女性以相同的尊重,穆芭拉珂才會在被迫嫁給一位年齡與自己父親相仿的男人時沒有反抗,這恰恰證明她也是埃及父權制社會下眾多女性受害者中的一員。女性在男權社會受到壓抑,導致女性深陷“失語”處境,不像“男性擁有話語權,擁有創造密碼、附會意義之權,有說話之權與闡釋之權”。在婚姻中沒有話語權的穆芭拉珂,被父親當作“物品”嫁給穆加希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沒有原諒父親,喊完“我請求真主折磨我爸的靈魂,不管靈魂在哪兒”才咽氣。
婚后,穆芭拉珂掌握了“臥室的主導權”,對丈夫沒有任何回應。與哈菲沙不同,穆芭拉珂從不刻意迎合丈夫,只有感到自己在家中處境不妙時,才勉強應付一下丈夫。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英國人來村里抓壯丁,哈菲沙請求穆芭拉珂收留自己的兒子納吉,一起生活后,穆芭拉珂與納吉發生了關系。此時的穆芭拉珂已為人母,但她沒有淪為男性的附屬品,她大膽地釋放自己的欲望。后來,她甚至生下了納吉的孩子,穆芭拉珂沒有按照社會對一個女性、母親所下的定義而生活。用美國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話來說,“定義屬于下定義者,而不屬于被定義者”。穆芭拉珂雖然是父權文化的受害者,她沒有資格選擇自己的婚姻,但是她并未完全受制于父權制度,她對丈夫不在意、不順從,她不以丈夫的快樂為快樂,也沒有對丈夫和孩子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成為一個為丈夫和孩子而活的“賢妻良母”背道而馳。
穆芭拉珂沒有一直和納吉保持男女關系,她隨心行事。當迪布家的第三代孩子到了該上學的年齡時,她帶領七個男孩兒來到城里,在那里,她結識了公寓的女鄰居,“孩子們上學去了,女人們就湊到一起喝茶,然后去市場買菜,在孩子們放學前把飯做好”。孩子們出門上學,穆芭拉珂就開始欣賞自己的身體,她把這個只有孩子的地方視作天堂,“在這個天堂,穆芭拉珂學會了怎樣愛自己”。
作者為我們塑造了穆芭拉珂這樣一個女性角色,她或許不是近代埃及社會中的大眾女性,但她無疑反映了部分埃及女性對于傳統的父權制思想已不再逆來順受,她們有自己的想法,不再完全依附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員。
四、結論
卡姆哈維的這部作品并不是一本簡單的小說,它客觀真實,注重小說時間背景的真實歷史。在卡姆哈維的筆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躍然紙上。
盡管《迪布宅門》不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作者伊扎特·卡姆哈維也并非一位女性主義者,但作者在關注普通人的生活變遷時,從男性作家的視角,描繪了近代埃及社會的女性生活,為我們了解埃及女性生活狀況和近代埃及女性思想提供了一個獨特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