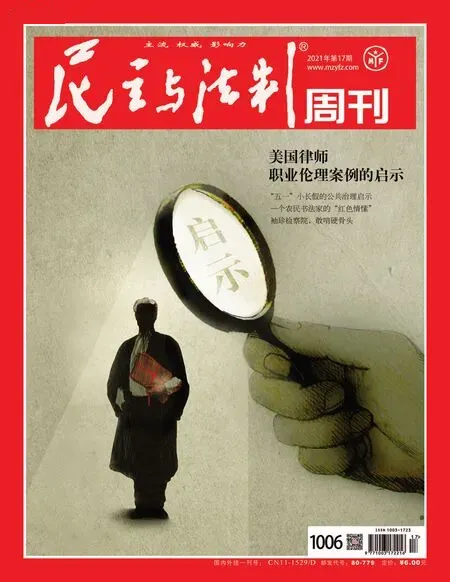尼克斯案:你會配合被告人在庭審中作偽證嗎?
劉萍
在得知客戶準備向法庭說謊時,律師如何做出反應?
這是律師面臨的最艱難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根據律師職業倫理規范,律師不得提出明知為虛假的證詞;另一方面,客戶在向法庭陳述事實時需要律師的協助,而在刑事案件中,律師的協助是被告人應得的憲法權利。
尼克斯訴懷特塞德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考慮律師在被告人意圖作偽證時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大法官們在判決中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即當律師拒絕配合被告人在審判中提供偽證時,是否侵犯了他根據憲法第六修正案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
一起因毒品引發的謀殺案
1977年2月8日,愛荷華州錫達拉皮茲市發生一起謀殺案,伊曼紐爾·懷特塞德被判二級謀殺罪。那天深夜,懷特塞德和另外兩個人去了死者加爾文·洛夫的公寓,打算拿回屬于他們的大麻。懷特塞德和同伴們到達時,洛夫已經躺在床上了,他們因大麻的事發生了爭吵,洛夫開始對懷特塞德等人進行威脅,讓自己的女友去拿槍,他伸手去摸床上的枕頭,然后朝懷特塞德走去。就在那時,懷特塞德用刀捅死了洛夫。
懷特塞德聲稱自己是出于自衛。洛夫有暴力、好斗的名聲,持有槍支,有犯罪前科。懷特塞德曾與洛夫一起在監獄服刑,他認為洛夫是個危險人物。懷特塞德在審判中堅稱,他刺傷洛夫的時候是出于對自己生命安危的恐懼。
在陪審團評議的過程中,法官問懷特塞德如何評價自己的律師羅賓遜先生,他回答說對律師的代理感到滿意。盡管愛荷華州對懷特塞德提起一級謀殺的指控,但陪審團選擇判處了二級謀殺,初審法官判他40年刑期。
隨后,懷特塞德聘請了新律師要求對他的案件重審,其中一個理由是他沒有得到律師的有效協助。
被告人懷特塞德的偽證計劃
在重審動議的聽證會上,懷特塞德作證說,他曾給過羅賓遜律師一份書面陳述,包含著這樣的意思:洛夫伸手從枕頭底下掏出一把手槍,就在那時,我殺死了他。他一直希望律師能找到那把手槍,以便在審判時能夠向法庭提交。然而,槍并沒有被找到。在審判前夕與律師的會面中,懷特塞德透露了自己的作證計劃,他準備在法庭上說他看到了洛夫手中的槍,出于自衛,他殺死了洛夫。雖然懷特塞德不記得律師具體怎樣回應,但他有一種感覺,如果他作證說看到洛夫手中有槍,律師就會退出代理。正是由于這種印象,他決定不在法庭上說自己看到了槍。這使得他的正當防衛辯護未能成功,因而被定罪。
羅賓遜律師提供了一個明顯不同的故事版本。在羅賓遜之前,法庭為懷特塞德指派的是另外一名律師,由于這位律師曾擔任過檢察官,懷特塞德覺得無法信任他,于是拒絕了。法庭隨后指定羅賓遜作為懷特塞德的辯護律師。

>>視覺中國供圖
羅賓遜承認懷特塞德在陳述中說他看到了洛夫手中的槍。經過進一步詢問,懷特塞德表示,他實際上并沒有看到過槍,但他確信洛夫有槍。羅賓遜前往案發現場洛夫的公寓搜尋了30~45分鐘,但沒有找到手槍。他詢問了在現場的三位證人,他們都說,洛夫在被殺之前手中沒有拿槍,在案件發生過程中,他們也沒有看到房間里有槍。羅賓遜又詢問了案發后15分鐘內趕到現場的警察,警察也沒有發現屋內有槍。根據這些調查,羅賓遜認為洛夫在被殺之前手里沒有拿槍,他從與懷特塞德的23次會面交談中加固了這一印象。從他接受法庭指派起的69天內,懷特塞德都沒有提到他將在法庭上作證說看到了槍,而在審前10天的會談中,他突然提出了這一點。他說,當時他在洛夫的手中看到了一個貌似金屬質地的東西。律師問及他為何改變證詞,他說,有一個熟人的類似案子就是因為咬定對方手里有槍而獲得了成功,如果我不說我看見了槍,就死定了。
律師警告要揭發他的當事人
羅賓遜告訴懷特塞德,這樣的證詞是偽證,并反復強調,槍的實際存在并不是證明自衛的必要條件,只要合理地相信受害者附近的地方有槍,從而有理由相信自己處于危險之中就可以。懷特塞德堅持要作證,說他看到了“金屬樣的東西”。
羅賓遜說,我們不能允許他這么講,因為那就是作偽證。作為法庭官員,如果我們允許他這樣做,那就是協助他作偽證。如果他堅持這么做,作為律師我們將退出代理;如果他在法庭上真的這樣做了,我們有責任向法庭披露偽證的事實,而且,我可能會被允許彈劾懷特塞德的證詞。在律師的警告之下,懷特塞德作出讓步。
庭審中,羅賓遜問懷特塞德,當他刺傷洛夫時,他是否認為洛夫有槍,他說是的。但羅賓遜沒有問懷特塞德,他是否“看到”洛夫的手里有槍或任何東西。在交叉盤問中,懷特塞德被檢察官問及在刺殺時是否看到過槍,他回答說沒有。
羅賓遜出示了證據,證明有人曾在其他場合看到洛夫拿著一把短獵槍,警方對公寓的搜查可能是粗心大意,受害者的家人在案發后不久就從公寓搬走了所有的東西。羅賓遜提出了這個證據來證明懷特塞德聲稱的“洛夫有槍”的恐懼是有根據的。
律師拒絕配合被告人作偽證是否違憲引發爭議
在懷特塞德被定罪后要求復審,他聲稱律師警告他不要說他看到了槍或“金屬的東西”,否則退出代理,這限制了他通過自己的意愿作證的憲法權利,也剝奪了他獲得律師有效協助的憲法權利。
初審法院認為并不存在無效的律師協助。愛荷華州最高法院審查了審判記錄和無效審判動議的聽證會,認為程序沒有錯誤,也沒有剝奪懷特塞德憲法權利的情形。州最高法院的裁決贊揚了羅賓遜律師“以高尚的符合職業道德的方式處理此事”。
三年后,懷特塞德以律師協助無效為由,向聯邦地區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救濟。地方法院在一份簡短的意見書中指出,被告人無權就其偽證行為獲得律師的協助,因此駁回了其申請。懷特塞德繼續向聯邦第八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聯邦第八巡回上訴法院推翻了聯邦地區法院的裁決。上訴法院稱贊羅賓遜按照法律職業道德行事,然而,上訴法院同時認為,法律職業倫理規則并不優于美國憲法的規定。根據上訴法院的裁決,懷特塞德的兩項憲法權利被羅賓遜的行為所限制:第一項權利是在面臨刑事指控時獲得律師有效協助的權利;第二是在正當程序條款中隱含的按自己的意愿作證的權利,盡管其證詞可能是不真實的。
因此,第八巡回上訴法院撤銷原判,授予懷特塞德人身保護令,愛荷華州向聯邦最高法院申請調卷復審此案。

>>尼克斯訴懷特塞德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考慮律師在被告意圖做偽證時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大法官們在判決中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即當律師拒絕配合被告在審判中提供偽證時,是否侵犯了他根據憲法第六修正案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 資料圖
律師作為“法庭官員”的角色重于他辯護人的責任
聯邦最高法院決定批準調閱此案以解決這樣一個飽含爭議的問題:當律師拒絕配合被告人在審判中提供偽證時,是否侵犯了第六修正案規定的刑事被告人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九位大法官一致認為第八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但進一步區分為兩種意見:首席大法官伯格等五位發表了多數派意見,布萊克門等四位大法官發表了附和意見。
多數意見對刑事辯護律師的角色界定采取了明確的立場,即認為律師作為“法庭官員”的角色重于他身為辯護人的責任。這與第八巡回上訴法院的觀點顯著不同。上訴法院的觀點顯然相反,認為如果被告人堅持作偽證,律師必須至少被動地配合,而不是阻止,理由是被告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愿為自己辯護。最高法院對此正本清源,認為律師是“司法正義的組成部分,應當致力于尋求真相”,律師的辯護責任僅限于通過合法的方式進行,唯如此方可與其探求真相的本質相吻合。
多數意見就以下三個與本案有關的憲法問題做了回應,大多數內容被附和意見所接受。
首先,懷特塞德獲得律師有效協助的憲法權利是否被侵害?律師勸阻懷特塞德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作證,是否與其作為辯護律師的角色沖突?根據斯特里克蘭案(Strickland v.Washington)確立的“無效律師協助”檢驗標準,須具備兩個條件:律師代理行為存在缺陷,以及律師的代理缺陷給被告人帶來損害。由于懷特塞德在提供偽證方面沒有合法利益,不能將他的不合法期待未能實現視為受到損害,因此不符合斯特里克蘭的“損害”標準。持附和意見的法官們提出了判定不存在損害的另一個理由:在他們看來,阻止懷特塞德作偽證是保護其最大利益的合理步驟,因為偽證其實難以成立,而且可能會被揭穿。這可能會導致陪審團認定他犯有更嚴重的一級謀殺罪,法官也會因為偽證提高他的刑期。因此,律師阻止被告人作偽證的行為并未給其造成損害。而懷特塞德主張的律師角色的沖突,不過是自己的偽證導致的,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利益沖突。
其次,被告人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作證的憲法權利,但不包括作偽證的權利。無論憲法規定的作證權的范圍有多大,最基本的是這種權利不應延伸到虛假作證。被告人在合理的范圍內繼續享有律師的代理服務,并實際上行使了作證的權利;他最多被剝奪了獲得律師協助提供偽證的權利。同樣,在羅賓遜律師對被告人的警告中,我們也不能看出他違反了職業責任,即他將向法院披露被告人的偽證罪。
第三,第六修正案中被告人獲得律師有效協助的權利是否包括在作偽證時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答案是否定的。多數意見對這一點進行了詳細闡述,比如被告人向律師透露,他正在想辦法賄賂、威脅證人或陪審團成員,被告人將沒有權利要求律師就此提供幫助或保持沉默。因此,懷特塞德無權要求律師幫助他作偽證。
雖然多數意見讓我們對最高法院在律師職業倫理相關問題上的想法有了一定了解,但這恰恰是附和意見與多數意見的主要分歧之所在。布倫南、布萊克門、馬歇爾和史蒂文斯等四位大法官在贊同多數意見裁決結果的同時提出,本案中唯一的聯邦問題是:羅賓遜律師的行為是否剝奪了懷特塞德獲得律師有效協助的憲法權利;問題并不在于羅賓遜律師的行為是否符合任何特定的法律職業倫理準則。
布倫南大法官認為,憲法沒有賦予最高法院為在州法院執業的律師制定道德倫理規則的權力,法院在法律倫理方面也不享有任何法定管轄權。因此,最高法院必須謹慎行事,不能輕易宣布根據美國律師協會的準則來判斷律師行為是否適合,即不要將憲法第六修正案所接受的律師行為范圍縮小,以至于將律師行業的專業行為標準憲法化,從而侵犯各州制定和適用律師職業行為準則的權力。換言之,除非聯邦權利受到侵犯,否則最高法院不能告訴各州或各州的律師在法庭上應該如何行事。不幸的是,法院似乎無法抗拒與法律界分享其對道德行為的看法的誘惑。布萊克門大法官遺憾地表示,這個問題很棘手,但它不是本案所呈現的問題,最高法院無權回答。最高法院關于律師對被告人將作偽證的意圖應如何回應的言論,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布萊克門大法官提出,長期以來,律師應如何回應有意作偽證的被告人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他不認為通過聯邦人身保護令挑戰州法院的定罪判決是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適當手段。當被告人爭辯說,由于律師勸阻他不要作偽證,所以他沒有得到律師的有效協助時,向最高法院適當提出的唯一問題是,律師的行為是否剝奪了被告人得到律師有效協助的第六修正案權利。
如同布倫南大法官一樣,布萊克門大法官對使用律師職業行為準則來衡量律師在各州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表現這一做法表示不安。認為應由各州來決定律師在本州刑事訴訟中應如何表現,而最高法院的責任僅延伸到確保各州頒布的限制不會侵犯被告人的憲法權利。因此,布萊克門大法官贊同37個州提交的“法庭之友”建議,即應允許各州對復雜的律師職業道德問題保持其不同的做法。而在調查律師的表現是否適當之前,首先應詢問被告人是否因律師的行為受有任何不利的影響,這樣可以避免聯邦對州法律的不必要干涉。鑒于認為本案被告人并未受到任何傷害,因此無權獲得聯邦人身保護令的救濟,布萊克門大法官表示同意多數法官的判決。
最高法院對律師職業倫理問題沒有管轄權
尼克斯案還涉及刑辯律師-客戶關系上的四個程序問題:第一,律師何時“知道”被告人打算作偽證,從而有義務阻止其偽證行為;第二,當律師知道被告人打算作偽證時,應該采用何種方式進行勸阻;第三,如果律師不能勸阻被告人作偽證,他也不能退出代理,這時律師該怎么辦;第四,當被告人確實在法庭上作了偽證時,律師應該怎么辦。在這些程序問題上,多數意見和附和意見也保持了大體的一致。
第一個程序問題,如何判斷律師何時“知道”被告人打算作偽證,最高法院沒有向律師協會提供一般性的指導規則。大多數情況下,律師所面對的事實比在尼克斯案中的情形更加模棱兩可。在一個案件中,證人之間的證詞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律師常常分辨不出他們中誰說的是真話。美國律師協會頒布的《職業行為示范規則》(簡稱“示范規則”)并不要求律師只提供他們認為真實的證據,律師可以提供他不確定真假的證據。如果律師合理地認為證據是虛假的,但并未達到確定“知道”的程度,應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決定,即不禁止律師將證據提交給法庭。所以律師可以提供他不確定的證據,但如果律師確定地“知道”證據是假的,則不應提交。而律師是否“知道”證據為虛假,需要結合多種情況進行判斷。
關于第二個程序問題,首先肯定,當被告人通知律師他要作偽證的意圖時,律師的首要職責是盡力勸阻。在尼克斯案中,最高法院對羅賓遜律師向被告人發出警告的做法表示認可,律師可以使用警告的方式來勸阻被告人的偽證,甚至包括采用比較激烈的方式對被告人進行威脅,聲稱如果被告人真的作偽證,他將會向法庭如實報告,或在證人席上對其進行彈劾。律師以這些方式來勸阻被告人作偽證,都不會被認為侵犯了客戶的第六修正案權利。
第三個程序問題,如果律師的警告或威脅不能說服被告人放棄作偽證的意圖,則律師可以退出代理,而且在退出代理后,可以通過親自出庭作證的方式對被告人的證詞進行彈劾。
在最后一個程序問題上,根據“示范規則”第3.3條規定,如果被告人已經向法庭提供了重要的證言,律師隨后發現是虛假的,則該律師應當采取合理的補救措施。律師首要的適當行為是秘密規勸被告人,解釋律師對法庭有坦誠的義務,就退出代理或者糾正虛假證言獲得被告人的理解與合作。如果被告人能主動配合采取補救措施,則可避免律師的披露偽證造成對客戶秘密的泄露。如果規勸工作無效,律師必須采取進一步的補救措施。如果退出代理沒有被允許,或者不能抵消被告人虛假證言的效果,律師必須就偽證向法庭進行必要的披露。
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面臨被定罪的嚴酷威脅,自然會不顧一切地尋求對自己最有利的證據,包括向法庭提供篡改重要事實的證言。刑事辯護律師兼為被告人的訴辯者和法庭的官員,同時負有忠于被告人和法庭的職責,這是極其艱難的職業倫理困境,它發生在每一個律師身上,發生在每一起刑事案件中。
尼克斯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正面回應律師的這一困境,并且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答復。然而,這一沒有反對意見的判決卻蘊含著一個巨大的爭議,即布萊克門等附和意見者所主張的:最高法院對律師職業倫理問題沒有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