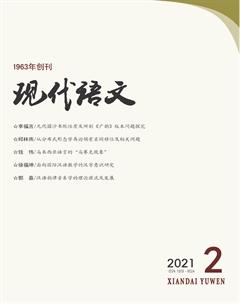標記理論下的“被”字句句式語義新解
劉琪
摘 ?要:“被”字句按照標記度大小可以分為無標記“被”字句和有標記“被”字句。這種標記性不僅體現在句法上,也體現在語義和語用上。“被”字句(A被B+VP)句法標記度大小取決于“A”“B”和“VP”三個成分:當A為原型受事、B為原型施事、VP為二價或三價動作動詞時,“被”字句是無標記的,其句式語義為“施受/被動關系”。隨著句式標記度的提高,A不再是原型受事,B也不再是原型施事,此時VP往往為心理動詞或性狀謂詞,句式語義強調的是“使因—結果”。像“被授予”類承賜型“被”字句和“被自殺”類新興“被”字式,它們都屬于高標記的“被”字句,這些句式中不再凸顯“施受/被動關系”和“使因—結果”語義,轉而凸顯的是一種情態語用義,表達主觀態度、價值或情感。“被”字句并不是歷來被認為的“一個特殊句式”,而是一組具有共性特征的句式的集合。標記度的引入解決了以往關于“被”字句句式語義的紛爭。
關鍵詞:“被”字句;標記度;句法;句式語義;主觀傾向
一、引言
關于“被”字句到底表示什么樣的語法意義,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主要觀點有:一是以王力為代表的“不幸或不愉快”說[1](P430-433);二是杉村博文的“意外”說[2];三是以祖人植為代表的觀點,強調其表“被動”的基本語義性質[3];四是以薛鳳生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它表示“由于B的關系,A變成C所描述的狀態”[4];五是邵敬敏、趙春利的觀點,作者認為,“被”是用來引進發生某個動作或行為事件的動因,但因為“被”字句中受動作的影響者才是句子的語義重心,動因則顯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可以省略,因此,“被”字句可以分為“動因被字句”和“省隱被字句[5];六是施春宏的觀點,他指出,“被”字句的語義表示“凸顯役事受到致事施加的致使性影響的一種結果”[6]。以上這些觀點,無論是對“被”表義內容的探討,還是對“被”性質功能的界定,關注點都是該語法范疇所表現出的某一方面,是從解決局部出發的,這也是“被”字句語法意義至今沒有定論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以往關于“被”字句的爭論所指向的,并非是“被”字句各句式互無關聯的個別問題,而是針對“被”字句不同標記度而產生的不同功能類。本文認為,“被”字句不是一個單一的句法語義結構,而是一個多義范疇,無論是表“被動關系”還是表“意外事件”,都只能反應“被”字句語法意義的一個側面。從原型范疇的角度來看,“被”字句是一組具有共性特征的句式的集合,不可能用某個單一屬性來解釋。就現代漢語的基本語序而言,“被”字句無疑是一種有標記的句法結構[7]。因此,從標記的角度來看,“被”字句標記度越高,就越需考慮語義、語用的解讀。因為隨著句式標記度的提高,需要付出的認知努力也就越大,甚至要依靠語用推理來理解“被”字句的意義。
二、“被”字句的句法標記度
張伯江指出,不應給“把”字句里的成分貼上“施事”“受事”的標簽,而是應該研究句式賦予了這些成分什么角色[8]。我們認為,對待“被”字句各成分的語義角色也應持同樣的態度。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將“被”字句的句法結構碼化為:A被B+VP。從標記理論出發,“被”字句各句法成分的語義特點體現了不同標記程度的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主語A、賓語B和動詞詞組VP上。
(一)A的標記度
宋玉柱指出,“‘被字句的主語是受事——幾乎所有語法書都是這樣說的。對于絕大部分‘被字句來說,它是符合事實的,但對一部分‘被字句來說,則沒有概括力。”[9](P64)在“被”字句中,主語所充當的語義角色,除了受事之外,還有系事、感受主體、當事、處所、時間等。雖然A的語義角色可以被客觀分析為多種類型,但這些類型是存在共性特征的,從宏觀來看,A都是說/寫者認定的受影響的對象。
根據對“被”字句主語A的語義角色的分類,我們確定了“被”字句主語的經常充當的六種語義角色類型。舉例如下:
(1)杯子被我打碎了①。(受事)
(2)整個星期天都被他花在了撲克上。(時間)
(3)天井被雪花裝飾得那么美麗,那么純潔。(處所)
(4)老園頭被她哭得心軟。(當事)
(5)為什么那一本充滿血腥味的《列女傳》就應該被看作女人的榜樣?(系事)
(6)他被那件事愁死了。(施事)
Dowty依據認知心理學理論創立了“原型角色”理論[10],提出了原型施事(Proto-Agent)和原型受事(Proto-Patient)范疇,還進一步提出了論元選擇原則,即施事、致事、感事等這些具有原型施事屬性的論旨角色最可能出現在主語位置,而受事、役事、目標等具有原型受事屬性的論旨角色最可能出現在賓語位置。這就形成了句法論元和論旨角色的兩組無標記組配。陳平參考Dowty的研究內容,建立了充任主語、賓語的語義角色優先序列: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點>對象>受事,并指出,以上這些語義成分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施事性和受事性強弱的不同[11]。
在“被”字句中,主賓語充當的語義角色倒置,因此,越是具有原型受事屬性語義角色出現于“被”字句的主語A時,越是無標記的。根據“被”字句主語A所充當的六種主要的語義角色的受事原型性,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標記度等級序列:受事>時間/處所>當事>系事>施事。該序列從左到右代表了各語義角色受事性的減弱、施事性的增強。也就是說,它代表了“被”字句主語標記度由低到高的一個序列。位于序列最左端的受事主語受動作影響強度最高,具備原型受事的屬性,是典型的受影響對象,因此,它是無標記主語;而施事主語則是動作行為的發出者,為有標記主語。
再來考察上面的例子。從主語充當的語義角色來講,例(1)中,“杯子”是典型的受事主語,是無標記的。例(2)中,“整個星期天”表時間,句子可以轉寫為“他花了整個星期天在撲克上”,表示“他”和“時間”之間的施受關系,因此,“整個星期天”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受事。例(3)中,A為處所,這類處所可以從整體上被看作一種事物,而作為動作的接受者出現。“天井”在例句中就是被裝飾者,有較明顯的受事性質。例(4)中,“老園頭”作為當事,表示因B發生的“哭”這一動作而使A產生了“心軟的”情緒或感受,A只與謂語部分有某種關系,不是V的受事。例(5)中,A與“女人的榜樣”是等同關系,A很難說是V的受事;邢福義將這類“被”字句稱為承賜型“被”字句[12]。例(6)中,A是施事,句子可以轉寫為“因為那件事,他愁死了”,“那件事”是致使“他愁死了”的原因,“他”發出了“愁”的動作。可以看出,從例(1)到例(6),動作對A的影響依次減弱,反映了A從無標記到有標記的變化。
(二)B的標記度
以往關于“被”字句的常見誤區之一,就是把“被”作為引進施事的格標記。從理論上來看,“施事是動作行為的發出者,應具有生命度和自主性”[5]。張伯江指出,施事的意愿性強度和其典型性有關,具有強意愿性的施事是典型的施事[12]。就此而言,如果“被”僅作為引進施事的格標記的話,那么,處在賓語B位置的語義角色應當具備[+生命度]、[+意愿性]、[+自主性]。事實上,許多實例并不支持“被”作為引進施事的格標記這樣的論斷。例如:
(7)方方試圖跟陳偉玲聊天,被她噎得直背氣。
(8)衣服被風吹走了。
(9)我剛出樓門,被高壓水槍射出的一束水柱砸了個滿臉花。
(10)自己怎么又會被一種莫名的激動和希望攫住?
(11)他臉上的花影都被歡躍給浸漬得紅艷了。
(12)他被那件事愁死了。
在上述例句中,充當賓語的成分并不相同。從B所充當的語義角色來看,它不僅可以表示施行動作的人,如例(7);也可以表示施行動作無生的事物,如例(8)、例(9);還可以表示原因,如例(10)、例(11);甚至是受事成分,如例(12)。由此可見,“被”引進的對象不一定是意愿性強的,甚至談不上具有生命度和自主性。
邢福義認為,雖然B有時候表示無生命的事物,但是它被說話人主觀意念上認定為動作的施行者[13]。因此,在格式上B的位置似乎有了語義的限定:任何成分,哪怕是沒有生命度的事物,一旦進入B的位置,也具有了施事的意味。即使如此,和典型的施事比起來,無生事物雖然同為動作的施行者,它在認知上卻具有更高的復雜度,在對動作的控制強度上也存在區別。對動作的控制力越強,越是典型的施事。Dowty指出,“具有原型施事屬性的論旨角色出現在主語位置是一種無標記組配”[10],這是對于一般的施受句來說的。在“被”字句中,由于主、賓語的施受關系對調,“被”字賓語位置和原型施事也能構成一組無標記組配。語言的標記模式和原型范疇理論密切相關,一個范疇中有典型成員、非典型成員和邊緣成員之分。典型的成員往往是無標記的,而非典型成員和邊緣成員則是有標記的,需要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據此,我們可以通過“被”字句中不同的賓語B對動作的控制力強弱判斷其標記度大小。例如:
(13)日本隊被中國隊打敗了。(施事)
(14)他被自己的想法嚇壞了。(準施事)
(15)衣服被汗水濕透了。(喻施事)
(16)他被煙嗆住了。(喻施事)
(17)他被門檻拌了一下。(偽施事)
(18)陽光被山遮住。(偽施事)
邵敬敏、趙春利對“被”字句賓語B的施事性強弱進行了探討,將施事劃分出四種類別[5]。例(13)中,B“中國隊”是表人的集合,具有高生命度,是典型的施事,標記度低。相比之下,例(14)~例(18)中的“被”的賓語,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施事。例(14)中的賓語,隸屬于人的“思想、意志、精神、信念”,它實際上受到有生命個體的控制,被稱為“準施事”;例(15)、例(16)中的賓語,屬于“水、氣、光、煙、霧、電”等帶有散發性能量的物體,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可以看作是一種轉喻,這樣就具備了一定的生命度和意志力,被稱為“喻施事”;例(17)、例(18)中的賓語,屬于客觀無生命度和意志力的物體,但通過外力的作用也可以具備一定的主動性,可以看作是一種臨時的“施動者”,被稱為“偽施事”。因此,例(14)~(18)中,“被”所引進的只是發生某個動作行為或事件的動因,它們的標記度較高,屬于非典型施事。
除了直接施事之外,B所充當的語義角色還可以是致因、間接施事和受事。例如:
(19)你回到房間,突然被疲倦攫住了。(致因)
(20)我被他派人追上了。(間接施事)
(21)爸爸被一連串的問題問煩了。(受事)
其中,例(20)值得格外注意,處在賓語B位置的“派人”是一個動賓結構表行為事件,而“追”這一動作的發出者,我們可以判定為“派的人”,它是具有[+生命度]、[+意愿性]特征的語義成分,可以歸入到非典型施事的一類中。而例(19)中作為心理動詞的“疲倦”和例(21)中作為客體的“一連串問題”,都是致使各自的主語達到某種狀態的使因成分,它們的施動性需要依靠說/寫者的主觀認定,除此之外,其致使力無法通過外力或隱喻、轉喻的方式得以實現。和非典型施事相比,這類成分的標記度更高,我們稱其為“邊緣施事”。
B的語義角色看似復雜,事實上它們也是有共性的。無論B是典型施事、非典型施事還是邊緣施事,它們都是對主語施加影響的主要責任者和主要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被”字句賓語B語義角色標記度連續統:典型施事>非典型施事>邊緣施事。在這一序列中,B所能充當的語義角色,從左到右的標記度越來越高。
隨著“被”字句句法標記度的提高,B所充當的語義角色對動詞的控制力減弱,受動作的影響者占據了句子的語義重心,施加影響者的地位相對來說就沒有那么重要。因此,B往往可以承接上下文省略,或者補出B之后句子變得不合法,或者根本不需要B的出現。
(三)VP的標記度
VP的標記度等級差異直接制約著“被”字所表達的意義。一般來說,“被”字前后出現的是典型受事主語和典型施事賓語的時候,“被”字句的基本語義性質就是表被動。這時,VP中的動詞往往是二價和三價的動作動詞。可以說,這種典型“被”字句的標記度低,如“杯子被我打碎了”。再如:
(22)范登高拿回來的衣服被別人替換了。
(23)一張上好的楠木椅子被他坐斷了。
這種典型的“被”字句語義上的施受關系和句法成分是對應的,因此,也最容易和“主動賓”句、“把”字句、受事主語句進行轉換。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現施受關系,我們省去了句中的修飾性成分:
(24)a.別人替換了衣服。
b.別人把衣服替換了。
c.衣服別人替換了。
(25)a.他坐斷了椅子。
b.他把椅子坐斷了。
c.椅子他坐斷了。
還有一部分“被”字句,主語和賓語的關系是非典型的施受關系,此處的“被”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引進施事,而是著意凸顯動作行為對“被”字所標記對象的影響。這時,VP中的動詞往往是心理動詞或性狀謂詞。相對于一般的VP而言,其標記性更強。例如:
(26)他被牛奶喝胖了好幾斤。
(27)她被繁忙的工作累病了。
例(26)中的“他”和“牛奶”之間、例(27)中的“她”和“繁忙的工作”之間,都是非典型施受關系。其中,“喝胖”屬于性狀謂詞,“累”是心理動詞,“病”也屬于性狀謂詞,它們均是非典型的動作動詞。“被”字句的各個成分都是非典型的,標記度高,因此,它們無法同“主動賓”句和受事主語句進行自由的轉換,只能和“把”字句實現自由的轉換。試比較:
(28)a.*他喝胖了牛奶好幾斤。
b.牛奶把他喝胖了好幾斤。
c.*牛奶他喝胖了好幾斤。
(29)a.*她累病了繁忙的工作。
b.繁忙的工作把她累病了。
c.*繁忙的工作她累病了。
三、“被”字句的語義標記度
以往學界試圖用一個句法語義關系來解釋“被”字句,但結果總是不盡人意。我們認為,“被”字句的語義問題也是一個標記度強弱的問題。語言的標記性可以像基因一樣被復制到語言的各個層面,反映了標記所具有的同化特性。標記同化要求有標記的意義或功能由有標記的形式來體現,換言之,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必須要保持一致。“被動關系”是“被”字句最典型的語義表達,是無標記的語義。因為它不僅強調句法形式上的主賓語關系,同時強調主賓語和施受關系的對應。從句式變換的角度來說,表被動關系的“被”字句很容易和“主動賓”句、“把”字句、受事主語句進行轉換。
如果句法上的標記度提高,主語和賓語不再強調施受關系,“被”的功能不再用作被動標記,而是引進發生某個動作或行為事件的“動因”,強調的是“使因—結果”,那么,它則是一種有標記語義。此時的“被”字句所凸顯的是動作行為對其所標記對象的影響。如例(26)、例(27),“牛奶”是“他胖了好幾斤”的使因,而“他胖了好幾斤”是“他喝牛奶”造成的結果;“繁忙的工作”是“她累病”的原因,而“她累病”是“繁忙的工作”造成的。再如:
(30)那人一口氣殺了三條狗,我被這場景嚇了一跳。
(31)他本來想幫你,沒想到你卻被他害了。
(32)他的眼睛被這些小字看花了。
上述例句,如果同樣進行句式變換,A和B是什么樣的語義關系,似乎很難用傳統的施受關系來解釋,而只能從“使因—結果”的關系上得到解釋。和上文中的例子“牛奶”“繁忙的工作”一樣,“這場景”“他”“這些小字”都不是動詞的施事成分,“這場景”無法主動嚇“我”,“他”本無意害“你”,“這些小字”也沒辦法主動地把“他的眼睛看花”。“場景”“他”和“小字”都是語義上的使因成分。“被”字句強調的意義是“使因”和“結果”,而不再是被動關系。這也說明,句法結構的標記度越高,在語義的認知處理上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為“使因—結果”的關系不像被動關系一樣在句式結構中能夠很明顯地體現出來。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用“被動”義來統轄“使因—結果”義,也沒有必要用“使因—結果”義來統轄“被動”義。無論哪種語義功能,都不能涵蓋所有的句子。這是因為“特定的句法形式必然會出現一定的語義內容,相應的語義內容同樣需要借助特定的句法形式來表達”[14]。標記度的引入可以化解以往有關“被”字句句式語義的紛爭,其句式語義隨標記性的強弱而分化:表“被動關系”的“被”字句,在賓語B的強實施性、主語A的強受影響度和VP動作的典型性上,都表現為無標記;而強調“使因—結果”義的“被”字句,從賓語B的低意愿度、主語A的弱受影響度和VP的特征上,都是有標記的。
四、“被”字句的語用語序
典型的、常規的“被”字句屬于致使表達方式的一種類型,其語法意義是“凸顯役事受到致事施加致使性影響的一種結果”[6](P14)。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被”字句中,表“被動關系”和表“使因—結果”的分工是非常明確的。前者是“被”字句的基本意義,只有標記度提高,“被”字句才具備后者的表義功能。“被”字句不同的句法和語義標記度,可以清晰地區分“被”字句的語法意義。在語用層面,也更能體現標記度的解釋力。語用上,標記度的提高會帶來“附加”信息。也就是說,在“被”字句的語用語序中,“被動關系”“使因—結果”都不再凸顯了,得到凸顯的是一種主觀評價、態度或情感。在語法形式上,也表現出很強的標記性。這些特殊的“被”字式往往不要求句法成分的必要性,其賓語的弱施事性說明它本身不是句子的必有論元,因此,賓語可以不出現。下面將要論述的,就是這類高標記性“被”字式的典型代表。
(一)承賜型“被”字句
邢福義指出,現代漢語里承賜型“被”字句的廣泛使用,受到社會發展的語用需要的促動[13]。隨著現代社會評優授獎活動的日益增多,承賜型“被”字句形成了一個具有較強系統性的被動稱心表述網絡。它不僅在內涵上有褒義的規約,在外延上也進行了形式上的圈定:S被(X)授予Y、S被(X)評為Y、S被(X)列入Y,是它的三個代表格式。例如:
(33)他被市長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34)其父也得遂大志,被評為“一級教師”。
(35)劉詩白……被列入美國傳記研究所《國際名人錄》。
邢福義稱這種具有褒義性質的承賜型“被”字句為一個小“獨立王國”,它獨立于一般意義上的、表不幸或者不愉快的“被”字句,這是適應社會社時代發展的需要而出現的新的語用形式。一提到“被授予”“被評為”“被聘為”“被表彰為”“被任命為”等典型的搭配形式,人們便會更自然地聯想到稱心如意的事。在這類“被”字式中,動作涉及到的施事不是交際雙方所關心的,因此,“B”省去之后也并不影響句子的成立,如例(33)省去“被”的賓語“市長”后,就變為“他被授予‘榮譽市民稱號”。相反,人們關注的是評獎評優這件事情本身與受評對象,因此,這兩個成分如果省去不說,句子就無法成立。
(二)“被X”
近年逐漸流行的“被X”現象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這種新興“被”字式和常規“被”字句的不同之處,鮮明地體現出“被”字句的句法、語義和語用的不同功能類型。施春宏指出,“無論是結構形式,還是語法意義,新‘被字式都與常規‘被字句構成了一種背反狀態,因而展現出不同的語用效果。”[6]首先,不同于常規“被”字句VP的述補結構或其他復雜結構,如“被打傷、被摔成碎片”等,新“被”字式出現的謂詞性成分往往為單個動詞或形容詞,如“被自殺、被培訓、被結婚”等,更特殊的是,它還能容納非謂成分,如“被潛規則、被處女”等。其次,常規“被”字句的語法意義是表達“被動關系”或“使因—結果”,而“被X”的語義內容則體現出更為明顯的主觀傾向。
“被”字句語用語序特殊的表意功能,還表現在其意義可以隨語境等的變化而呈現出相當大的波動性。同樣是“被自殺”,在不同語境下,至少可以有三種解釋:其一,A屬于他殺但被人說成是自殺;其二,A被人強迫自殺但被人說成是主動自殺;其三,A并未自殺或他殺但被人誤傳為自殺。這說明,只要構建適當的語境,新興“被”字式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這種多義性的解讀,恰恰反映了人們對新“被”字式理解過程中的不同認知方式。這是常規的“被”字句所無法做到的。
上文提到,隨著“被”字句中各成員的非典型性的增強,“被”字句的標記度也隨之提高,這時,在認知上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像新興“被”字式這類特殊的有標記句式,“被”的施事賓語隱而未現,其認知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語用推理上。典型的表被動關系的“被”字句本身就是一個“完型”,“被自殺”之所以能成立并被理解,在句法上是類推在起作用。所謂“類推”,指的是原有結構沒有發生變化,但因套用某種法則,類推出不同于原來的新結構,新結構的表層不同于舊結構,但兩者的底層意義不變[15]。可以說,“A被B+VP”中B不出現,會大大增加理解的難度,新興“被”字式在語義表達上的不自主性,就需要借助于語用推理。我們認為,新興“被”字式的出現,可以說是常規“被”字句的語法化的結果,實現了句式在共時平面內功能的分工。在類推的作用下,它是由常規“被”字句發展出的一個特殊的表現形式,只是這種形式在整體上不再強調句法成分和語義角色在語序上的對應關系,凸顯的是這個句式的語用含義,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
五、“被”字句的語序、語義和關聯標記模式
從語序的角度講,我們認為,“被”字句可以分為句法語序、語義語序和語用語序三個平面,這三個平面是相互關聯的,體現了標記性的強弱。因此,“被”字句的語法意義也就體現在一個動態的系統之中。我們之所以用標記性的強弱來說明“被”字句的語法意義,就是因為它反映了句法結構和語義特征的對應程度。
從總體上來說,我們認為,“被”字句有兩種最主要的語法意義:表被動關系和強調“使因—結果”。和以往觀點不同的是,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可以分開對待。在句法表現形式上,強調“使因—結果”的“被”字句的標記度要強于表被動關系的“被”字句,甚至可以說,表被動關系的“被”字句在句法和語義上是無標記的,而強調“使因—結果”的“被”字句是有標記的。我們由此可以建立“被”字句的關聯標記模式:
無標記組配 ? ? ? ? ?有標記組配
A被B+VP ? ? ? ? ? ?A被(B)+VP
被動/施受關系 ? ? ?使因—結果 ?情態語用義
句法語序 ? ? ? ? 語義語序 ? ?語用語序
隨著標記度的繼續加強,“被”字句不再體現句法結構和語義結構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承賜型“被”字句或新興“被”字式只能按照語用語序處理,它們是具有特殊語用功能的“被”字句。不過,這種語用意義仍是來源于“被”字句的句法語序和語義語序。
綜上,我們認為,標記是漢語語序選擇的一種調節手段,標記度的強弱和語序的三個平面密切相關,語言的標記性越強,越對應于語用語序,這是因為標記具有語用信息傳遞功能和突出信息中心的功能。“被”字句的標記度和語序的對應關系如圖1所示:
主觀性 ? ? ?弱 ? ? ? ? ? ? ? ? ? ? ? ? ? 強
標記性 ? ? ?無 ? ? ? ? ? ? ? ? ? ? ? ? ? 有
語序 ? ?句法語序 ? ? ? 語義語序 ? ? 語用語序
語義 ?被動/施受關系 ? 使因—結果 ? 情態語用義
圖1 ?“被”字句標記度和語序的對應關系
從圖1可以看出,“被”字句的標記度和其語序可以構成一個連續統,在這個體系中,我們可以動態地、分層地整體看待“被”字句的特點。
本文運用標記理論,從“被”字句的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語序出發,論證了“被”字句句式的標記度和語序的關系。以往有關“被”字句語義的不同解讀,實際指向的是“被”字句不同標記度的句式。研究表明,句式的標記度越高,越傾向于語用語序,對句式語義的理解也越要依賴于主觀性。“被”字句的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實際上體現出一個標記程度的差異:A為典型受事,B為典型施事,VP的動作性越強,則相應的“被”字句越傾向于無標記,語義上表達的是一種被動關系。隨著標記度的提高,句法結構無法再反映被動關系,此時的“被”字句強調的是“使因—結果”,甚至帶上一種主觀傾向,這種主觀性無所謂積極還是消極。
參考文獻:
[1]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2]杉村博文.論現代漢語表“難事實現”的被動句[J].世界漢語教學,1998,(4).
[3]祖人植.“被”字句的表義特性分析[J].漢語學習, 1997,(3).
[4]薛鳳生.“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結構意義——真的表示“處置”和“被動”?[A].戴浩一,薛鳳生主編.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C].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5]邵敬敏,趙春利.“致使把字句”和“省隱被字句”及其語用解釋[J].漢語學習,2005,(4).
[6]施春宏.新興“被”字式的生成機制、語義理解及語用效應[J].當代修辭學,2013,(1).
[7]施春宏.漢語句式的標記度及基本語序問題[J].漢語學習,2004,(2).
[8]張伯江.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對稱與不對稱[J].中國語文,2001,(6).
[9]宋玉柱.處所主語“被”字句[J].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1).
[10]Dowty,D.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J].Language,1991,(3).
[11]陳平.試論漢語中三種句子成分與語義成分的配位原則[J].中國語文,1994,(3).
[12]張伯江.論“把”字句的句式語義[J].語言研究, 2000,(1).
[13]邢福義.承賜型“被”字句[J].語言研究,2004,(1).
[14]張誼生.現代漢語“把+個+NP+VC”句式探微[J].漢語學報,2005,(3).
[15]王寅,嚴辰松.語法化的特征、動因和機制——認知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法化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