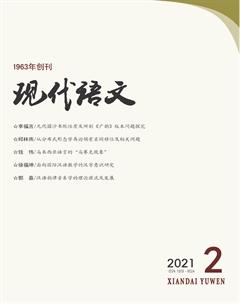面向國際漢語教學的漢字意識研究
徐福坤
摘 ?要:海外漢語教學普遍存在重視拼音而回避漢字難點的教學方式,這種方式并不利于學生的可持續性學習,也不符合漢語和漢字的實際狀況。漢字屬于表意文字,漢字與漢語關系的密切程度,要遠遠大于表音文字與其所依賴語言的關系。從漢字的形體和意義入手,幫助學生形成一定的“漢字意識”、以漢字教學促進詞義和詞法教學,應該成為孔子學院(課堂)的一項重要教學原則。
關鍵詞:漢字意識;海外漢語教學;可持續性學習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漢字教學一直被認為是個難點,漢字難認、難寫和難記成為制約漢語教學的最大瓶頸。因此,有些初級班和短期班便繞開漢字、直接用拼音進行漢語教學。由于教學時間短、學習動機多樣化、學生年齡層次跨度較大等原因,這種現象在孔子學院課堂教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使用拼音進行漢語教學可以回避漢字教學的難點,幫助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引起對漢語學習的興趣。但是,這種做法的弊端也是比較明顯的。以新漢語水平考試(HSK)為例,海外學生的HSK一級和二級通過率普遍較高而三級通過率卻明顯下降[1](P17-21)。這是因為HSK(三級)不僅增加了“書寫”內容,而且“聽力”選項和“閱讀”部分也只有漢字呈現,對于習慣了拼音提示的學生來說,考試的難度陡然增大。作為一項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化考試,新HSK能夠檢驗學生學習的效果,也可以反映國際漢語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可以說,注重拼音而規避漢字難點的教學方式不利于學生的可持續性學習,也不符合漢語和漢字的實際狀況。
其實,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如何處理拼音與漢字的關系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對外漢語教學的前輩和時賢就進行過多種教學模式的試驗,主要有“先語后文”“語文并進”“拼音文字交叉出現”“聽說和讀寫分別設課”等[2](P430-432)。不過,這些試驗主要是立足于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而進行的,對海外漢語教學特別是每周只有一兩次課的孔子學院來說可操作性并不高。
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制定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規定,“教師應具備對自己教學進行反思的意識,具備基本的課堂研究能力,能主動分析、反思自己的教學實踐和教學效果并據此改進教學。”[3](P62)我們認為,海外漢語課堂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激發學生對漢語的興趣,增強他們進一步學習漢語的動機和能力。因此,從漢字的形體和意義入手,幫助學生形成一定的“漢字意識”、以漢字教學促進詞語和詞法教學,應該成為孔子學院課堂教學的重要原則。下面,我們就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一、漢字屬于表意文字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形體構造主要依賴于語言的聲音,而表意文字的形體構造主要依賴于語言的意義。漢字屬于表意文字,漢字與漢語關系的密切程度,要遠遠大于表音文字與其所依賴語言的關系。心理學實驗表明,漢語字詞加工中的語義激活過程不同于拼音文字,它主要是由字形——語義之間的直接激活傳輸(或計算)所決定的,語音信息對語義激活的作用很小[4](P159-184)。具體來說,高頻漢字形音義激活的時間順序是字形——字義——字音[5](P1-6);低頻漢字的字形激活在先,字音和字義的激活同時進行[6](P576-581)。漢字識別中存在著直接的形義通道,以義為本、見字知義是漢字從古至今一直保留的重要特征。
對于習慣了使用表音文字的漢語學習者來說,需要改變傳統的“語音中心論”,正確認識漢字的性質并建立新的認知方式和記憶習慣。基于漢字的表意屬性,漢語教師應指導學習者充分了解漢字“因義構形”的依據和規律。例如,通過字源分析可以了解“日、月、山、水”等字的象形特征;通過部件拆分能夠認識“本、末、太、刃”和“休、從、森、寶”等字的得義緣由;通過歸納總結可以了解形旁對“晴、明、旦、昏”和“江、河、湖、海”等字意義類屬的提示作用,并能夠掌握漢字“按義歸類”和“據形系聯”的文字類聚方法。“六書”是古人對漢字構造類型的總結,其知識的基礎性、實用性,以及教學實踐的歷史傳承性,使得“六書”在今天的語文基礎教育領域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7](P94-105)。根據傳統的“六書”成字規律,找出漢字在構形和表意方面的理據性,這種教學方法不僅可以讓學生深刻感受字形與字義之間的聯系,而且能夠為詞義教學和詞法教學提供有益的幫助。
二、漢字分析是詞義教學的基礎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當學生的詞匯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們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理發”的“發”和“發生”的“發”為什么不同?“發生”的“生”和“學生”的“生”是不是一樣?“關心”和“關懷”的意義和用法是否相同?這些問題反映出學生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語素意識,基于同一語素(漢字形體)構成的詞語集合,開始成為他們學習的重點和難點。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同形語素、同音語素、近義語素的產生過程和形成理據做出詳細的考察,考察的首要環節就是要正確認識語素字的構形理據及其語義衍生過程。
(一)漢字分析與同形語素的識別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8],“理發”的“發”和“發生”的“發”是一組同形語素,兩者讀音不同,意義之間也沒有任何聯系。
從漢字的小篆形體來看,“理發”的“發(髪)”是形聲字,從髟,犮聲,本義為“頭發”。“髟”是會意字,從長,從彡,像頭發下垂的樣子。因此,凡從髟的漢字大都和“頭發”的意義有關,如“髦、髯、髫、鬃”等。“發生”的“發(發)”也是形聲字,從弓,癹聲。甲骨文寫作“”或“”[9](1126),像弓箭發射后弓弦顫動的樣子。在甲骨文向小篆的演變過程中,雖然“發”的形體出現了較大變化(、→),但漢字的構形意圖一直都是“把箭射出去”,即“發射”。“把箭射出去”隱含了一個動態的過程:A.拉弓積蓄力量,B.箭的發射起點,C.箭的運行過程[10](P56-61)。在人們的認知體驗中,觀察一個物體或一個空間場景的時候,必然是從某一視角進行觀察的。就弓箭發射的動態過程來看,如果認知的視角集中在“拉弓積蓄力量”,那么,弓箭的“發射起點”和“運行過程”相對于A階段來說就是“把箭射出去”。如果認知的視角集中在“運行過程”,那么,弓箭相對于原有的空間圖景來說就是新出現的事物。據此,“發射”可轉喻為“發生”和“產生”。例如:
(1)(仲春之月)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禮記·月令》)
(2)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明代王守仁《〈大學〉問》)
例(1)中,“發”用于具體的自然現象“雷”,表示“發生、發出”。例(2)中,“發”用于抽象的思維現象“念”,表示“產生”。“雷”和“念”相對于原有的空間圖景或認知圖式來說突顯度較高,都是新“產生”的事物。
上述分析表明,“理發”的“發”和“發現”的“發”原本在形、音、義三個方面都沒有聯系。只是由于漢字的簡化,二者形成了同形關系。同形語素是外國學生習得漢語的一個難點,同一個漢字形體所表示的不同讀音和義項需要第二語言學習者分別識記。不過,以語素作為中介,將漢字的構形理據與對外漢語詞匯教學結合起來,不僅能夠幫助學習者“知其然”,更能幫助他們“知其所以然”,增強他們進一步學習漢語的動機和能力。
(二)漢字分析與同音語素的判定
“發生”的“生”和“學生”的“生”則屬于另外一種情況。《說文解字·生部》:“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11](P127)甲骨文字形為“”[9](P552),本義指“(草木)生長”。“生長”相對于原有的空間圖景來說,也可以視為草木等植物的“產生”。隨著社會和人類認知的發展,“生”還可以泛指一切新事物的“產生”。可見,“生”在“發生”一詞中體現的意義是從語素字的本義引申而來的。“生”在“學生”一詞中則表示“學習的人”,“學習的人”和“發生”之間看起來沒有任何語義聯系。因此,“生”在《現代漢語詞典》[8](P1166)中被視作同音語素,兩者讀音相同,“意義上需要分別處理”(凡例1.2)。不過,通過考察“生”的語義演變過程,可以發現,“學習的人”也是從語素字的本義引申而來的。
首先,是隱喻映射。人或動物生育同植物生長在性質上具有相似性,因此,“生”可隱喻為“出生、生育”。例如:
(3)莊公寤生,驚姜氏。(《左傳·隱公元年》)
(4)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詩經·大雅·生民》)
例(3)中的“生”可釋為“出生”;例(4)中的“先生”可釋為“第一個出生”。
其次,是轉喻映射。因為第一個出生的孩子在兄弟序列中排行最大,所以“先生”可轉喻為“長兄”;之后,“第一個出生”語義泛化,可表示“出生次序在前的”,“先生”亦可泛化為“父兄”。例如:
(5)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儀禮·有司》)
(6)有酒食,先生饌。(《論語·為政》)
例(5)中的“先生”,鄭玄注:“先生,長兄弟。”可見,這里是指“長兄”。例(6)中的“先生”,何晏集解引馬融:“先生,謂父兄。”可見,這里是指“父兄”。
先秦時期,文化教育主要在家族范圍內進行,施教者通常是父兄、族長等“學士年長者”。據此,“先生”亦可轉喻為“老師”。“先生”的語義繼續泛化,還可指“文人學士的通稱”,即“儒生”。這是因為“老師”是“文人學士”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由“老師”引申為“文人學者”,屬于部分轉喻整體。例如:
(7)(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禮記·玉藻》)
(8)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南朝梁沈約《與陶弘景書》)
例(7)中的“先生”是指“老師”;例(8)中的“先生”是指“文人學者”。
由于語言使用的經濟原則,“先生”在具體的語言使用中可以簡縮為“生”。例如:
(9)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史記·儒林列傳》)
(10)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最后,由于語義的泛化,“儒生”指遵從儒家學說的讀書人,通常是讀書人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群體。由部分轉喻整體,“生”亦可泛指“讀書人”。例如:
(11)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明代宋濂《送東陽馬生序》)
(12)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清代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例(11)中的“馬生”、例(12)中的“廡下一生”,都是指年輕的書生。在現代漢語中,“書生”一般被稱為“學生、學習的人”。可見,“學習的人”和“發生”具有共同的語義來源“(草木)生長”,二者是同一語素、具有語義聯系的不同義項。許多教材和詞典將“發生”的“生”和“學生”的“生”視作同音語素,主要是因為“先生”古義在現代漢語中的消失、“先生”到“生”的簡縮、“生”的語義泛化等因素,造成了“學習的人”與“出生”之間的語義聯系中斷。呂叔湘曾經指出,“辨認語素跟讀沒讀過古書有關系。讀過點古書的人在大小問題上傾向于小,在異同問題上傾向于同”[12](P16)。隨著當代語言生活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生”這類語素性質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一定變化,這種變化有助于第二語言學習者了解漢語詞義的發展演變及其相互關系。
(三)漢字分析與近義語素的辨析
“關心”和“關懷”是一組近義詞。從甲骨文字形來看,心()是象形字[9](P924),本義為“心臟”。古人認為心是思維的器官,因而可以引申為“思想、意念、感情”等。例如:
(13)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周易·系辭上》)
(14)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經·小雅·巧言》)
《說文解字·心部》:“懷,念思也。從心,褱聲。”[11](P218)可見,“懷”是形聲字,本義為“懷念”。懷念是對過往生活的·回憶,表達的是一種心意和情感,因此,“懷”可以引申為“心意、心情、思慮”等。例如:
(15)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漢樂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16)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三國曹操《苦寒行》)
可以說,“關心”和“關懷”都可以分析為“關涉思慮、情感”,表示對人或事物的重視和愛護。不過,二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關心”的賓語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關懷”的賓語一般是人;“關心”的對象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關懷”的對象只能是他人;“關懷”多用于上級對下級或長輩對晚輩,“關心”則沒有此類限制。這是因為,“懷”除了“思慮”之外,還具有“愛護、他人、他物”等語義要素。王力認為,“懷、褱、褢”實為一詞,具體的懷抱為“褱、褢”,抽象的懷念為“懷”[13](P420)。《說文解字·衣部》:“褱,俠也。從衣,眔聲。”[11](P171)段玉裁注:“俠當作夾,轉寫之誤。亦部曰:夾,盜竊褱物也。在衣曰褱,在手曰握。”[14](P686)可見,“褱”的本義為“懷抱、揣著”,用義素分析法可以表示為:[+在衣之中] [+保護] [+他人之物]。同理,“懷念”可以表示為:[+在心之中] [+思慮] [+他人或他日之事]。如果動作主體的身份地位在“他人”之上,“懷念”又可引申為“關懷、安撫”,用義素分析法可以表示為[+思慮] [+愛護] [+他人或他日之事]。當然,在歷史文獻中,“關懷”的對象不止是人,也可以是事。只是由于語境因素的反復作用,“愛護”“他人”等由附帶意義逐步演變為核心意義。
“關心”和“關懷”是一組具有某一相同語素的近義詞,此類近義詞辨析的重點應放在其中的相異語素上。對相異語素字構形理據的分析,有利于學習者更好地掌握近義詞的意義、搭配和用法。
三、漢字分析能夠為詞法教學提供幫助
同印歐語相比,漢語缺少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語言單位之間重意合而沒有明顯的語法標記。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可以通過慣性思維和上下文語境去理解、推測詞與詞、句與句之間的語法關系。但對于第二語言學習者來說,漢語的這種特點可能會給他們造成一定的困惑,同時要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德國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曾經指出,“在一個漢語的句子里,每個詞似乎都要求人們對其斟酌一番,考慮到它可能會有的種種關系,然后才能繼續看下面的詞。由于概念的聯系產生自詞與詞的關系,這一純思維的勞動便把一部分語法加給了句子。”[15](P171)因此,國際漢語教師需要引導學習者認識和理解漢語各級語言單位之間的意合性特點。在這一點上,現代漢語語素的字形分析和語義演變研究能夠為詞法教學提供幫助。
(一)字形分析有助于學習者初步認識漢語的意合性特點
石定果認為,從漢字的內部結構來看,會意字實際上集文字、詞匯、語法為一體,其字形不僅負載了詞匯信息(詞義),也潛在負載了語法信息(復合程序)[16](P274-278)。也就是說,會意字的復合程序和漢語詞、短語和句子的結構原則基本一致。因此,從分析語素字的構形理據入手,把會意字教學與詞法、句法教學結合起來,不僅有助于學生深刻感受漢語各級語言單位從小到大組合生成的規律,而且能夠使整個教學過程變得意趣盎然。比如,《說文解字·香部》:“香,芳也。從黍從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11](P147)會意字內部的復合程序為“黍稷馨香”,體現的是主謂關系。《說文解字·及部》:“及,逮也。從又從人。”[11](P64)其復合程序為“用手抓住前面的人”,體現的是動賓關系。《說文解字·攴部》:“政,正也。從攴從正。”[11](P67)其復合程序為“敲擊使之正”,體現的是補充關系。《說文解字·手部》:“招,手呼也。從手、召。”[11](P253)其復合程序為“用手召喚”,體現的是偏正關系。《說文解字·林部》:“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11](P126)其復合程序為“木與木(在一起)”,體現的是聯合關系。據初步統計,在《漢語國際教育用音節漢字詞匯等級劃分》[17]收錄的3000個常用字和次常用字中,會意字共有617個。雖然數量不多,但在國際漢語教學中卻能發揮較大的作用。
在這一基礎上,字形分析的范圍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沈家煊在論述中西方的不同范疇觀時就曾經提到,“慟”字取“動”之聲加形旁“忄”,跟詞語“心動”的構造法一樣;“遁”字表示逃隱,取“逃”之形旁“辶”加上“盾”之聲及其轉義“隱”,跟詞語“逃隱”的構造法基本相同[18](P131-143)。這均反映出漢字跟西方純粹的表音文字不同,它同時是表音和表意的。中國語言和文字是“包含”關系,語言包含文字,文字也屬于語言,它是衍生的“第二語言”。
(二)語義分析有助于學習者正確認識雙音詞的構詞理據
現代漢語雙音詞大多由上古漢語的短語、句法結構、跨層結構演變而來。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實際上是一種類似于語法化的語言形式的理據性減弱的變化過程[19](P24-36)。語素的某些義項因為不能獨立成詞、自由度不高,在現代漢語雙音詞中的意義比較隱晦,從而造成整個雙音詞的語義透明度較低。對于從小生活在漢語環境中的中國人來說,這些雙音詞一般無需拆解,只要整體理解詞的意義即可。不過,非漢語背景的學習者具有一定的詞匯積累之后,通常會形成某種程度的語素意識。在掌握了該詞的意義和用法的基礎上,有時還希望能了解構詞語素的含義,并對這一語素在其他詞中的不同含義感到疑惑。比如,“除夕”通常是指“農歷一年最后一天的夜晚”,但是“除”的語義是什么呢?它和“排除、清除、刪除”的“除”有沒有關系?分析語素的語義演變能夠幫助學習者正確地理解和猜測這些雙音詞的詞義。
《說文解字·阜部》:“除,殿陛也。”[11](P306)段玉裁注:“殿謂宮殿,殿陛謂之除。因之凡去舊更新皆曰除,取拾級更易之義也。”[14](P1278)據此,“除”的本義為“臺階”。臺階需要一級一級地易階上下,所以由“臺階”可轉喻為“交替、更易”。例如:
(17)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辨證二》)
(18)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尚書·泰誓下》)
“以新易舊”包括“去舊”和“換新”兩個過程,不過,“除”在語義演變中傾向于表示“去舊、去除”。例(18)中的“除”意為“去掉、清除”,由“更替”發展為“去除”,可視為伴隨義的凸顯化或者詞義縮小。
綜上所述,在“除夕”中,“除”表示“更替”,“除夕”一詞的得義理據是“舊歲至此夕而開始更替為新歲”。在“排除、清除、刪除”中,“除”則表示“去除、去掉”。“去除、去掉”由“更替”義發展而來,而“更替”由“除”的本義“臺階”轉喻而來。不過,作為傳承語素,“除”在表示“更替”時,不能獨立成詞,與別的語素組合通常也只能構成“除夕”這一個雙音詞。“更替”義在現代漢語中的出現頻率極低,造成了“除”的引申義列中斷。因此,“除”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視作同形語素[8](P194),“除1”的核心義為“去掉”,“除2”表示“臺階”。
(三)語義分析有助于學習者正確分析雙音詞的語法結構
正確認識漢語的意合性特點,不僅需要了解詞、短語和句子的結構類型和規律,更需要了解各語言單位之間的語義關系。以現代漢語雙音詞為例,“早”和“晚”在現代漢語中是一對反義詞,但是“早點”和“晚點”之間為什么不具有反義關系呢?分析語素字的構形理據,了解“早、晚、點”等重點語素的語義演變過程,能夠幫助第二語言學習者更好地掌握此類結構的意義和用法。
《說文解字·日部》:“早,晨也。從日,在甲上。”[11](P137)段玉裁注:“甲象人頭,在其上則早之意也。”[14](P530)據此,“早”的本義為“早晨”,可用于名詞性成分之前作定語,如“早飯、早市、早點”等。相對于“上午、下午、晚上”,“早晨”指的是“時間在前的”。因此,“早”可轉喻為“比一定的時間靠前”,如“早婚、早熟、離開演還早呢”。《說文解字·日部》:“晚,莫也。從日,免聲。”[11](P138)據此,“晚”的本義為“日暮、傍晚”。相對于“早晨、上午、下午”等,“日暮”指的是“時間靠后的”。因此,“晚”可轉喻為“比規定或合適的時間靠后”,如“來晚了一步、會議晚開了半小時、火車晚點了”等。而“點”為同形語素,既可表示“規定的鐘點”,如“到點了、火車誤點、踩著點來”等;也可表示“點心”,如“茶點、名點、早點”等。“規定的鐘點”和“點心”共用一個漢字形體,但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的語義聯系。上述分析表明,“早點”應釋為“早晨吃的飯”,其內部語義結構為定中關系;“晚點”應釋為“車、船、飛機等開出、運行或到達的時間遲于規定的鐘點”,即“點晚”,其深層語義結構為主謂關系。“早點”和“晚點”語法結構都屬于定中偏正關系,不過,其深層的語義結構并不一致。因此,“早點”和“晚點”之間不具有反義關系。
在現代漢語中,單字與語言單位沒有固定的對應關系,一字多用、多字同用成為漢語用字的普遍現象,這是漢字難學的原因之一,應該成為漢字教學的重點[20](P356-367)。不過,傳統的漢字教學與研究多注重漢字的形體識別與結構理據,對漢字功用的探討不夠。漢字屬于表意文字,漢字與漢語關系的密切程度,要遠遠大于表音文字與其依賴語言的關系。分析語素字的構形理據,有助于認識漢字的本義和引申義,能在詞義理解、詞語辨析、詞法和句法教學方面發揮較大作用。同時,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意義不是漢字的固有要素。以語素分析為中介,將漢字構形理據與國際漢語教學結合起來,有助于探究漢字與漢語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將傳統的“字本位”觀念轉變為“語素本位”。
參考文獻:
[1]羅民,張晉軍,謝歐航,黃賀臣.新漢語水平考試(HSK)海外實施報告[J].中國考試,2011,(4).
[2]趙金銘主編.對外漢語教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3]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國際漢語教師標準[S].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4]周曉林.語義激活中語音的有限作用[A].彭聃齡,舒華,陳恒之主編.漢語認知研究[C].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5]陳寶國,彭聃齡.漢字識別中形音義激活時間進程的研究(Ⅰ)[J].心理學報,2001,(1).
[6]陳寶國,王立新,彭聃齡.漢字識別中形音義激活時間進程的研究(Ⅱ)[J].心理學報,2003,(5).
[7]李運富.“六書”性質及價值的重新認識[J].世界漢語教學,2012,(1).
[8]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Z].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9]李學勤主編.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10]蘭佳睿.“發+X”式心理動詞的認知語義考察[J].語言科學,2007,(5).
[1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12]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
[13]王力.同源字典[Z].北京:中華書局,2014.
[1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5][德]威廉·馮·洪堡特.致阿貝爾·雷慕薩先生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精神的特性[A].威廉·馮·洪堡特.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C].姚小平選編、譯注.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6]石定果.會意漢字內部結構的復合程序[J].世界漢語教學,1993,(4).
[17]國家漢辦,教育部社科司,《漢語國際教育用音節漢字詞匯等級劃分》課題組.漢語國際教育用音節漢字詞匯等級劃分(國家標準·應用解讀本)[S].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
[18]沈家煊.從語言看中西方的范疇觀[J].中國社會科學,2017,(7).
[19]董秀芳.詞匯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20]李運富.漢字的特點與對外漢字教學[J].世界漢語教學,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