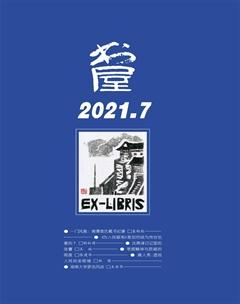一門風雅:湘潭袁氏藏書紀事
袁剛毅
清朝道光、咸豐年間,東南士大夫藏書有名者三人,一朱學勤,一丁日昌,一袁芳瑛。黃濬在《花隨人圣庵摭憶》中說:“(袁芳瑛)其生平有一大事,則為藏書,號為近代第一。”袁芳瑛是湖南湘潭(現屬株洲)人,為曾國藩的親家。曾國藩曾填詞一闋:“無一壓囊錢,童仆饑眠。層層自縛不成蟬。苦買殘書堆破屋,屋小如船。搜索販叢邊,自詫奇緣,摩挲秘本一忻然。默祝年年收異寶,明日新年。”詞后原注:“此首調袁漱六。漱六于歲暮入各書坊收買殘書,窮日不倦,往往自夸得稀世秘本。”原來,早年曾國藩與袁芳瑛為翰林院同事,均有淘書之好,此詞亦見曾對袁相知之深,活脫脫地刻畫出一位藏書家癡迷古籍的真實形象。
藏書聚散臥雪廬
袁芳瑛(1814—1859),號漱六,道光乙巳進士,授編修,由御史出任松江知府。生平唯一大事即為藏書。《中國私家藏書史》贊譽其“為咸豐間崛起之大藏書家,稱雄一時,壓倒群家”。這句評定并非隨意而出,而是其來有自——晚清著名學者李盛鐸稱袁氏藏書之盛為“二百年所未有”。同為清末藏書家的葉昌熾,在其《緣督廬日記》光緒壬辰十一月初四日中寫道:“至木齋寓長談,述袁漱六藏書之富,恬裕、皕宋、海源三家皆不能及。”又在辛卯正月廿一日記載了一次觀書:“木齋招飲,出示宋、元、明本書籍約百余種……泰半皆臥雪廬袁氏藏物,為之心醉。”這些確實是極高的評價。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原恬裕齋)書一千一百九十四種,十萬余卷;歸安陸氏十萬卷樓(皕宋樓)聚書十五萬卷以上;聊城楊氏海源閣蓄書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萬八千三百卷。以這三家對比,借此足見袁芳瑛藏書之富。

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
對藏書一事甚是高自標榜、目無余子的湘潭藏書后輩葉德輝曾慨然自許“一省人物,不及輝之一家”,然其對袁芳瑛卻是高山仰止,佩服有加,評價同治、光緒以前談版本之學者京師只有仁和(今杭州)人邵懿辰、盩厔(今陜西周至)人路慎莊、湘潭人袁芳瑛三位。在其《郋園讀書志》中稱:“湘中精版本之學者,必首推先生,所藏兩宋、元、明舊槧名鈔,皆薈萃南、北藏書家整冊殘篇而自成一派。”在他眼中,袁芳瑛無疑是當時第一藏書家。
袁芳瑛幼而好學,他的舅父石承藻是嘉慶十三年(1808)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袁芳瑛曾遍覽舅父家的藏書。他的夫人楊氏是同知銜楊敦福的女兒,石承藻與楊敦福于袁氏藏書出力頗多,均轉贈了部分藏書給他。前人總結袁氏藏書時說,袁氏“得之蘭陵孫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杭州故家者十之二,得之官編修者十之四五”。袁芳瑛考中進士后,在北京任翰林院編修十余年,讀抄內府藏書,并去廠肆搜求,獲得一批內府散佚出的四庫館底本、稿本和善本。后又宦游蘇滬,皆亦文獻薈萃之所,“大江南北舊家典冊片紙只卷,皆攬有之”,非偏于一隅之藏書家可比,如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孫星衍的藏書,即被他多方購得。尤為可貴的是,袁芳瑛不僅為藏書而藏書,他精于研究比勘版本的異同,是一個學問淵深的版本學家。
袁芳瑛夫人素有內助之賢,對袁芳瑛藏書助力甚巨。太平天國風起之際,袁芳瑛在松江任上病重,楊夫人獨自戎裝從江西輾轉到達松江,使得袁芳瑛支撐了兩年時光。袁芳瑛死后,耗費積蓄收藏的萬卷善本書籍尚在松江官邸。旁人望書興嘆,彼時楊夫人又展現了巾幗氣概——“長舸巨艦載入湘中,寶物因之免劫,其為功德無量”。由此號稱“天下第一”的袁氏臥雪廬藏書,就在省城長沙暫時安了家。楊夫人以保護丈夫藏書為己任,使覬覦臥雪廬藏書者無可奈何,如是又保藏了二十年。
袁芳瑛夫婦父能母賢,然則“其子榆生,不喜故書雅記,堆置五間樓房,積年不問。白蟻累累可見……”袁榆生紈绔無行,打起售賣父親畢生心血收藏的善本書籍的主意。湖南巡撫之子李盛鐸大抵收購臥雪廬藏書的十之一二,僅憑這批書,即一躍而成清末大藏書家。此外郭人漳、曾紀綱、葉德輝、王禮培、繆荃孫、易寅村諸人都曾分得部分。
李盛鐸后人將藏書售賣給北京大學,其中臥雪廬藏書成為北京大學善本書的最精華部分,可謂“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委實相當幸運。向達教授稱“這批書籍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參考價值的專藏之一”,可考的有《漢書》《后漢書》《周禮注疏》《尚書孔傳》等在書史、雕版印刷史上有特殊地位的版本和鈐有翰林院印的名貴書籍(多為四庫底本)二十余種。令人嘆息的是袁芳瑛最珍貴的幾柜書,因屋漏雨蝕,粘不能揭,竟被袁氏后人付之一炬。齊白石曾畫過一套冊頁,在其中一幅《甘吉藏書圖》中題寫道:“親題卷目未模糊,甘吉樓中與蠹居。此日開函揮淚讀,幾人不負父遺書。”另一位工于詩賦駢文的同鄉劉世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偶過袁宅,撫今憶昔,也成詩一首,詩曰:“金榜輝煌沒處尋,行人猶識舊園林。當年太史藏書地,寂寞誰聞弦誦聲。”
袁芳瑛藏書稱雄宇內,然其興也勃,其敗也忽,令人不勝感慨。讓人慶幸的是袁氏藏書之風不泯,書香不絕,未久又橫空出世了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乃是袁芳瑛三叔顯惠的曾孫袁樹勛。顯惠長子世絪,生子瑞澤。袁樹勛(1847—1915)乃瑞澤長子,譜名日盈,字百川,號海觀,晚年自號抑戒老人,歷任天津知府、上海道臺、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兩廣總督。
袁樹勛其人毀譽參半,不過在其主政上海期間,創辦上海第一所也是全國第一所警察學校;建成“貧民習藝所”,招生學習中、英文和職業技能,開設照相、音樂、陶器、泥塑、機器、毛織等課程,成為上海最早的職業學校;1904年,胡元倓在興辦明德學堂之時,時任上海道的袁樹勛捐助明德學堂一萬元,用以為學堂購置了一批理化儀器及博物標本。同年底,黃興因受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牽連與郭人漳等人在上海被捕入獄,袁樹勛斡旋使黃興得以釋放。袁樹勛不遺余力發展教育慈善事業,離任之際,上海士紳民眾還給他立了“袁去思碑”以作紀念,由此可見袁樹勛是一個干吏。袁樹勛在山東巡撫任上,武七行乞辦學,死后,袁樹勛奏準“宣付國史館立傳”,建忠義專祠;還創設山東省圖書館,是為全國建立最早的圖書館之一。袁樹勛“精鑒賞、善書法”,亦喜藏書,收藏書畫極富一時,其子袁思亮、其孫袁榮法又是著名的藏書家,遂使袁氏成為藏書世家,對中國文化傳播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揚州宋版書第一神品的傳奇
宋版書俗稱“一兩黃金一頁書”,歷來是古籍收藏的極品。據悉現在全國所能找到的宋刻本,總量不會超過一千二百部,多數已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其中南宋淮東倉司所刻的《注東坡先生詩》,堪稱現存揚州宋版書的第一神品。這部《注東坡先生詩》全書共四十二卷,是宋人施元之、顧禧注釋的蘇東坡詩集。現存的淮東倉司本《注東坡先生詩》均為殘本,分別藏于北京、臺北和上海的圖書館,以及有“民間收藏第一人”之稱的韋力手中。雖系殘本,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臺北藏本、北京藏本及韋力藏本均與袁思亮有關。
袁思亮(1879—1940),袁樹勛之子,民國詩壇巨擘陳散原弟子。袁思亮為人風雅蘊藉,古文造詣極深。他號“蘉庵”,“蘉”字音“忙”,是用《尚書·洛誥》中“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之典,意為勤勉。用這樣一個十分生僻的字作為號,可見袁思亮性情迥然不群。倒是陳散原先生非常推賞其學問文才,據說一些應酬文字由袁思亮代筆。《散原精舍詩文集》中有多首詩相贈,《陳師曾墓志銘》也是袁思亮所作。袁思亮民國初年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秘書、國務院秘書、印鑄局局長、漢冶萍礦冶股東會董事等職。袁世凱復辟,袁思亮棄官歸,隱居上海終日以著述、購書為事。所藏宋元古籍甚多,喜收詩文集,如有正德木活字本《太平御覽》、原丁日昌所藏的宋本《韓昌黎集》(世稱宋本集部第一)、宋淮東倉司刊本施元之、顧禧注《注東坡先生詩》、姚鼐手稿本《使魯湘日記》、朱錫庚抄校稿本《笥河文集》等十多部精本。袁思亮交游廣泛,時與陳散原七子陳方恪唱和,且有贈梅蘭芳、程硯秋之作。喜作詞,著有《冷蕓詞》,藏書處曰“雪松書屋”“剛伐邑齋”等,藏書印有“剛伐邕齋秘籍”“湘潭袁伯子藏書之印”“壺仌室珍藏印”等。著《蘉庵文集》《蘉庵詞集》《蘉庵詩集》等。
袁思亮藏施、顧《注東坡先生詩》猶值詳述。相較于其他宋刻本,《注東坡先生詩》有三大優點:一是收詩多,書中的卷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追和陶淵明詩》一百零七首及書后附施宿所撰《蘇軾年譜》,為他本所無;二是注文善,書中釋文為吳興施元之與吳郡顧禧所注,其在考證人物、援據時事方面勝于他本;三是版刻精美,善寫歐體字的書法家傅穉手寫上版,字體俊秀,加以紙白墨黝,刊印至精,深為藏書家所喜愛。據傳乾隆時期,大藏家翁方綱得倉司所刻《注東坡先生詩》后甚喜,將書屋改為蘇齋,每年農歷臘月十九蘇東坡生日,即邀請好友共同鑒賞此書,并吟詩題詞留念,“祭書會”因而成為風氣。
這部《注東坡先生詩》到袁思亮手之前,已經過了很多大藏書家的遞藏,比如明代的安國、毛晉,清代的徐乾學、宋犖,之后又到了翁方綱手里。翁得到此書后大為喜愛,為此發明了祭蘇活動。翁方綱之后,又經過吳榮光、葉名澧、潘仕誠、鄧邦述等人之手,清末之后袁思亮以萬金之價購得。不料數年后,袁思亮于北京正陽門外的住所不幸失火,被其視為身家性命的《注東坡先生詩》就在火中,袁思亮萬念俱灰,竟打算以身相殉。家人無奈,冒死從火中將此本救出,被藏書界稱為上蒼護佑的神物。可惜書腦、書口已全部過火,四周都被燒焦,名人題跋和繪畫等損失殆盡,僅剩下燒殘的版心部分,專家將這種善本稱為“焦尾本”。
民國時期,這部劫后余生的國寶由著名收藏家張珩重新裝裱后,贈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館保存。1949年,此書被運至臺灣,現存五冊共十九卷。另有一卷在火災中流散,經修復后歸民國大藏書家陳清華所有。2004年,旅居海外的陳氏后人將《和陶詩》兩冊分別轉讓給國家圖書館和韋力。當今人有幸在展柜中看到這部被火燒殘的國寶,是否仿佛看到了在大火之中顫顫巍巍、痛哭流涕、傷心欲絕的袁思亮先生呢?
2001年,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整理出版了《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收載袁樹勛及其長子思亮兩代所收輯清末民初之名人手書,俱未嘗公之于世,多涉及民國肇始之際之政壇珍聞,參考價值極高。
一生襟抱唯護書
袁榮法(1907—1976),字帥南,袁樹勛二子袁體乾長子,袁思亮從子,王世襄表兄。袁榮法畢業于上海持志學院法律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執律師業于滬上。袁榮法的大舅金北樓為近代京津畫派領袖、中國畫學研究會會長,因家風所及幼好書畫,工古文詩詞,先后加入滬上著名詩詞團體“漚社”及“三八會”等。
袁榮法赴臺后授聘為臺灣東吳大學教授,著有《滄洲詩》《玄冰詞》《宋詞曲宮調經見表》。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時有世交前輩欲鼓動而立之年的袁榮法出任偽職,為其嚴詞斥之,旋取唐韋應物“孤抱瑩玄冰”詩句中“玄冰”名其室,閉門讀書以明其志,亦遣憂時自靖之思。袁思亮畢其一生藏書皆歸從子袁榮法。1948年袁榮法攜其精華赴臺。
袁榮法離滬后,其武康路二百八十弄九號三層洋房一樓經葉景葵介紹,由史學家顧頡剛借住。顧頡剛后來在筆記中記錄了此事:“予于1949年3月1日,自虹口山陰路遷于滬西武康路之袁氏剛伐邑齋,其地鄰近法華鎮。古法華寺者,上海一劇跡,與龍華及靜安寺鼎足而三者也。袁氏多藏書,任予取資。其后,蟄伏家中,整理《浪口村隨筆》。”
1976年,袁榮法去世。1979年袁榮法子嗣尊其遺命,將藏書捐贈給臺北相關圖書館,其中善本以及普通線裝書共三百七十九部,二千一百四十三冊,珍罕并存,極富價值。
袁榮法較之他的先輩,他的名字已不大為人所知。或許從近八十年前他與錢鍾書的酬唱中,可以略窺其世家子弟、才華絕代佳公子的形象。1938年9月,錢鍾書偕妻女從法國返國。在郵輪中遇到剛剛卸任外交官的冒孝魯。二人雖是初識,但論詩談藝甚為投緣,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此后暌違兩地亦時有詩文酬唱。
1941年的暑假,錢鍾書離開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回到上海,詩人間的文酒之會不可或缺。卻說重陽過后,在秋季里的最后一天,冒孝魯又邀錢鍾書、袁榮法去滬上專營花木的黃園賞菊。因冒孝魯系袁思亮弟子,因了袁思亮這層舊誼,錢鍾書與袁榮法遂有相互認識并一同唱酬的機緣。彼時菊花將敗,但三人興致不減,疊韻唱和,鏖詩不休。錢鍾書作《與帥南、孝魯黃園看菊已經雨將盡》:“落英落照并凄寒,濺水沖泥興未闌。來晚不無先發恨,賞殘權當半開看。縱存荒徑家都破,可制頹齡日大難。閑里作癡隨二士,秋容老圃供盤桓。”袁榮法有如下和詩:“野圃幽香帶露聞,荒溪流潦逆斜曛。蒼茫正可容吾輩,搖落猶堪張一軍。莫枉閑情傷老大,尚留佳色與平分。何須送酒酬吟侶,已辦狂書白練裙。”兩詩均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最有影響的小報《社會日報》1941年11月25日刊發。
12月11日《社會日報》還刊有錢鍾書一首《贈帥南》:“風華絕代佳公子,肯向酸寒討活忙。未必文章憎命達,且憑喪亂博詩蒼。不廉能事猶爭席,有余耽佳已擅場。相對頻彈思舊淚,德人泉下夢茫茫。”袁帥南執律師業,故曰“有余”。“德人”指其伯父袁思亮,就是“袁伯夔丈”。和詩見存于《滄洲詩稿》,題曰:“秋盡日同默存、孝魯黃園看菊經雨花離披孝魯有詩屬和兼示默存”“默存亦以詩屬和兼示孝魯”“孝魯疊韻見示因更繼聲卻寄兼柬默存”“次韻答默存見贈之作”“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前一日雪用默存韻”“辛巳歲除和默存”。《玄冰室藏札》存錢先生一詩箋、一翰札,冒孝魯詩四首。其中《次韻答默存見贈之作》正是為《社會日報》所刊《贈帥南》而作,袁詩后半首云:“論交豈為時流重,守道寧辭后世傷。便欲相期老文字,窮通余事任微茫。”于此亦可見二人當日交誼之一斑。惜乎袁榮法大錢鍾書先生三歲,卻早逝二十二年。
藏書志作為一種獨特的目錄體例,上溯可至兩宋,其后數百年名家競立,至清代達至鼎盛。《剛伐邑齋藏書志》可謂私家藏書志后勁,考證詳備,為民國藏書志之大成者。《剛伐邑齋藏書志》的寫作時間正是抗戰艱難之際,袁榮法潔身隱居滬瀆成此巨著。全稿十一冊,共收書四千一百七十余種,近八十萬言,考證詳備,純為行草書就,墨跡粲然,間復注文滿紙。
毫不夸張地說,湘潭石塘山袁氏藏書自清代咸豐、同治間袁芳瑛之臥雪齋,至民國初年袁思亮之剛伐邑齋,再及抗戰時期袁榮法之玄冰室,幾代藏書家雖歷經亂世災年,卻以對中國傳統藏書文化的負責精神相聚相傳,累世負有重名。湘潭石塘山袁氏一門風雅,毫不夸張地說,袁芳瑛、袁思亮、袁榮法是文化創造者、承載者和傳播者,在中國私家藏書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