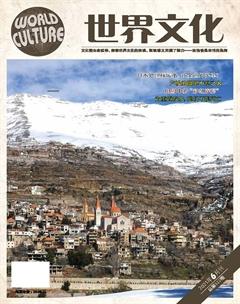盧梭的那把不熄之火
陳洪瀾
在巴黎先賢祠的地宮里有一座墓,墓面上建有兩扇門。門縫微啟,從中伸出一只舉著火把的手。若是在墓園內觀看這個火把,它若明若暗,似乎很弱小。若是你洞悉世界歷史,回望兩百多年來世界各地連綿起伏的政治風潮,便可知道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竟然燒毀了強大的法蘭西封建王朝,然后這把星星之火竟然形成了燎原之勢,一直由歐洲燒到美洲、亞洲,繼而把整個世界都給照亮、熏染了。點燃這把火的人如今就躺在這座墓穴中安眠。可是,他的魂靈仍然在世界各地游逛,人們時常還扯著他的旗子為“自由”和“民主”而吶喊。說到這里,你一定會想起墓中的這個人來—―他就是盧梭。
提起盧梭這個人,雖不能說是婦孺皆知,但他逝世兩百多年來在思想文化界卻仍像個明星似的受人熱捧。人們在他的頭上戴了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等多頂桂冠。當然,也有不少人敵視他,把他當作“瘋子”“野蠻人”“一切革命的始作俑者”和“無政府主義分子”等等,有人甚至還說他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災禍”。那么,盧梭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
在世界思想史上,盧梭是個毀譽參半、爭議極大的人。他在介紹自己時說:“我生來便和我所見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生來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我不比別人好,至少和他們不一樣。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因而他就顯得與眾不同,獨一無二。

1712年6月28日,盧梭出生在瑞士日內瓦風景如畫的萊芒湖畔。他的父親依薩克·盧梭是個鐘表匠,母親蘇薩娜·貝納爾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在盧梭出生的第10天因產褥熱去世。盧梭在姑母的撫育下得以活下來。因此,盧梭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生而不幸的人。
在盧梭列舉的諸多不幸中,首先是他生來喪母,10歲時又失去了父親的庇護——他父親在1722年與議會官員產生糾紛惹上了官司后遠逃他鄉。孤苦無依的盧梭被舅父貝納爾送往包塞,托付在牧師朗拜爾西埃牧師家里學習基本知識。也就是在這里,盧梭初次遭遇了不公正的暴打,起因是牧師的妹妹懷疑他掰斷了她的梳齒但他卻不承認。憤怒的火種從此在他幼小的心靈扎下了根,他說:“即使我活到10萬歲,這些情景也一直歷歷在目。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上……無論不公正行為的受害者是誰,也無論是什么地方發生的,只要我看見或聽到,便立刻怒發沖冠,有如身受。”可見這件事對盧梭的一生影響有多大。他覺得自己歡暢的童年生活到此戛然而止,隨后他便中斷僅有的兩年學習生活去當了學徒。

盧梭早年的許多丑事都是他在自傳中抖露出來的。他在記述學徒生涯時說:
由于師傅的暴虐專橫,終于使我對于本來喜愛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惡習,諸如撒謊、怠惰、偷竊等等。這一時期我身上發生的變化,回憶起來,令我深刻地體會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當奴隸之間的天壤之別。……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候,我肆無忌憚;在朗拜爾西埃先生家里的時候,我無拘無束;在舅父家里,我謹言慎行;到了我師傅那里,我就變得膽小如鼠了。從那以后,我就成為一個墮落的孩子。
他甚至說:“我生來就是為挨揍的。”直到晚年,盧梭對于自己少年時因何撒謊、因何偷東西、因何挨打的經歷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的讀書癖越受到限制,興致也越高”
許多人都說盧梭是一個天才,事實上他是靠勤奮自學成才的,他從來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他說:
我不知道五六歲以前都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樣學會閱讀的,我只記得我最初讀過的書,以及這些書對我的影響:我連續不斷地記錄下對自己的認識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我母親留下了一些小說,吃過晚飯我就和父親讀這些小說。……一本書到手,不一氣讀完是決不罷休的。有時父親聽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難為情地說:“我們去睡吧;我簡直比你還孩子氣呢。”
可知,盧梭的第一任老師是父親,引導著盧梭走進了書中的有趣世界。
盧梭常以自己擁有讀書的嗜好而沾沾自喜。因為讀書上癮,他經常遭到師傅的毒打,租來的書被撕毀或燒掉,可他說:“我的讀書癖越受到限制,興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熱狀態了。”在當學徒的幾年間他把自己的零花錢都送給了租書的老板娘,有時還用自己的衣物作抵押。他這種讀書的嗜好到老都沒有多大改變,無論是勞累饑餓,或是流浪途窮,甚至身染重病之時,他始終把閱讀和求知當作一種解厄除困的靈藥,他甚至說:“死亡的逼近不但沒有削弱我研究學問的興趣,似乎反而更使我興致勃勃地研究起學問來。”
為獲得更多的知識,盧梭博覽群書,從古希臘羅馬的經典著作到當代的啟蒙論著,從文學、歷史到自然科學,無所不讀。他讀書純粹是因為興趣,沒有目標、沒有界限,也沒有人督導勸勉,如同荒原跑馬,經常在文學、哲學、史學、數學、天文、地理和音樂等領域自由馳騁。廣博的學識不僅豐富了盧梭的精神世界,也鑄就了他善于學習、勤于思考、勇于對抗種種壓迫的堅忍品格。
“我這顆興奮起來的心更渴望的是愛情”
盧梭是個浪漫而又多情的才子。愛讀小說使他早早就萌生了朦朧的愛情。據他自白,11歲時就假想自己是個騎士,可以保護女人,并同時愛上了22歲的德·菲爾松小姐和11歲的戈登小姐,初嘗了愛情的滋味。這種孩童們過家家般的戀愛說起來像是笑話,但這種愛的感受卻給盧梭留下了持久而又甜蜜的記憶。
盧梭長著一雙愛美的眼睛,他喜歡長相秀美、膚色柔潤、談吐優雅、舉止大方、穿著飄逸的女子。他曾經模仿小說中的人物,憑著甜美的歌喉到城堡附近或深宅大院的門口去唱歌,幻想能夠邂逅公主或者貴族小姐。他為此曾經唱啞了喉嚨,等到的結果卻是無人理睬。不過,他與華倫夫人的相逢也應是一種奇緣。他認為自己一生中只有和華倫夫人在一起的那段時光才算是幸福,但與華倫夫人的不倫之愛又讓他終生處在既溫暖甜蜜又羞愧悔恨的矛盾中。
那是1728年,16歲的盧梭不堪忍受雕刻匠師父的暴虐性情而出逃,流浪途中他經人介紹去投奔華倫夫人。“本以為她一定是個面目可憎、老態龍鐘的丑老婆子,……然而我現在見到的卻是一個風韻十足的面龐,一雙柔情美麗的大藍眼睛,光彩閃耀的膚色。……我立刻被她俘虜了。”
華倫夫人是個有故事的人。她出身于一個老貴族之家,出嫁后陷在不幸的婚姻煩惱中。當她聽說國王到該地游訪時,竟然冒險越過了安訥西湖匍匐到國王的膝下尋求庇護。這個楚楚動人的小婦人當即就打動了國王的心,被賜予2000法郎年金后皈依了天主教。教會的神父們常常把一些流浪者送到她那兒去救急。
華倫夫人比盧梭大12歲,她稱盧梭為“孩子”,讓生來就失去了母愛的盧梭從此有了華倫夫人這個“媽媽”。最初的幾年里他們形同母子,相互關心,相互照顧。但隨著盧梭年歲的增長,他們之間的情感日益微妙復雜起來。盧梭看待華倫夫人若母、若師、若友、若情人,最終在他20歲時沖破了“母子”關系的束縛,在親愛的“媽媽”懷里吃到了禁果。
盧梭成為著名作家之后,他那秀美柔潤的文字曾博得了不少貴夫人的喜愛,如杜賓夫人、埃皮奈夫人、烏德托夫人和盧森堡夫人等都曾與他有過極為親密的交往,他身邊還有其他各色女子的糾纏,曾留下了一些拈花惹草的風流韻事。但他似乎對這些女人并沒有太多興趣,他說:“我這顆興奮起來的心更渴望的是愛情。凡是可以用金錢得到手的女人,在我的眼里她們所有的動人之處都會蕩然無存。”
盡管盧梭被標榜為浪漫主義文學家,但對于愛情卻有著悲觀主義情緒。他說:“我易于動情,這就注定我在愛情上要栽跟頭。愛情戰勝了我,我會倒霉。我若戰勝了愛情,也許倒霉得更加厲害。”在對待婚姻方面,他也未改變其平民本色,選擇的伴侶是非常務實的。1745年,盧梭在下榻的旅館里遇到了善良而又癡情的洗衣女仆戴萊絲·瓦瑟。此時盧梭33歲,長戴萊絲10歲。他記述了初次見到戴萊絲的情景,被她那雙活潑而溫柔的眼睛吸引了,他們彼此互生好感,成了情侶。戴萊絲雖然沒有文化,卻對盧梭溫柔體貼,不離不棄。直到1768年,年過半百的盧梭在布戈市市長的主持下,才與戴萊絲補辦了婚禮。
不過,平庸的婚姻并沒有化解盧梭心中的浪漫情愫。1761年,他創作了一部情意綿綿的書信體愛情小說《新愛洛伊絲》,借用一對戀人的情書講述了一場在封建社會壓迫下的愛情悲劇。書中的故事如催淚彈似的讓無數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的淚水浸濕了手帕。

“我是為音樂而生的”
盧梭自幼喜愛音樂。他聲稱:“可以肯定,我是為音樂而生的。”雖然在他獲得的諸多桂冠中并沒有音樂家這個美稱,但他卻是一位真正的音樂家,既有終生的音樂實踐,也有豐富的音樂作品和系統的音樂理論體系。
據盧梭自述,他在音樂領域里的成就也完全是自學自練、盲打盲撞得到的。最初的音樂喜好來自幼年時照料他的姑姑,她有一副甜潤的嗓子,經常哼出一些優美的鄉村小調。他常跟著姑姑哼唱,學到了不少小調。從此,音樂就成了盧梭向生活進軍的號角和慰藉。
盧梭能獲得系統的音樂知識受益于華倫夫人的幫助。她發現盧梭的天賦異稟、喜歡音樂且有一副好嗓子,就教他唱歌彈琴,還經常在家里舉辦一些小型音樂會,使他有機會結識一些樂界人士并讀到許多樂理方面的書籍。為了快速記住樂譜,盧梭竟然有了獨到的發現,即用阿拉伯數字識記樂譜,并寫下了論文《新樂譜記譜法》,呈交給巴黎科學院。不料主持評審的三位評委扒出了1665年巴黎方濟會修士蘇埃蒂的論文,認為簡譜的提法早已有之,只是由于當時受到抵制而胎死腹中。倔強的盧梭自然不肯罷了,他繼續補充完善自己的音樂理論,后來將其改寫為《現代音樂論》并公開出版。
為了能在樂界立足,年輕的盧梭加大火力,先后寫下了百余首歌曲,創作了6部歌劇。據說這些作品收益不大,唯有歌劇《鄉村占卜師》最受歡迎,相繼演出400多場。他的音樂才華也受到了百科全書派的賞識而成為《百科全書》音樂部分的撰稿人。他于1768年還出版了一部《音樂辭典》。
此后,盧梭始終沒有放棄音樂這個飯碗。他時常為人抄樂譜,當家庭音樂教師,晚年落難時還以替人抄樂譜為生計。他去世后,有人根據他的賬單做過統計,在最后的7年里,盧梭替人抄寫的樂譜有12000多頁。
“金錢金錢,煩惱根源”
盧梭在金錢面前一直是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對于金錢的極端吝惜與無比鄙視兼而有之”。正是因為這樣的矛盾心理,讓這個滿腹才華的作家一直過著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清貧生活,終生都未能改變其貧窮的命運。
其實,在盧梭的一生里并不是沒有碰到發財的機會,而是他在金錢面前總選擇退縮。比如,盧梭曾受聘到威尼斯法國大使館給蒙太居伯爵當秘書,還在法國財務總管弗蘭格耶處擔任過出納并經管金庫等。這些職位都是肥缺,但他卻煩于周旋、苦于應酬,沒干多久就以自己不能勝任為由辭去職務。
當盧梭的歌劇、論文和小說在巴黎出彩之后,他的聲望日高,報酬也增多,若能努力寫作完全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盧梭卻說:“當一個人只為維持生計而寫作的時候,他的思想就很難高尚。為了能夠大膽地說出偉大的真理,就肯定不能屈服于對成功的追求。我將我寫的書交到公眾面前,相信是為公眾的利益說了話,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惜。”
盧梭出名之后也就有了名家的煩惱。因各種應酬纏身,他覺得自己連享受清貧生活的自由也給剝奪了。“我深刻地體會到希望中的清貧而獨立的生活只是一種奢求。”他拒絕接受權貴們的饋贈,甚至退還人們送給他的禮品。于是人們罵他擺臭架子、傲慢無禮。為了躲避各種煩擾,盧梭離開了熱鬧的巴黎,搬到鄉下居住。可是無論他逃到哪里都難以擺脫金錢的煩惱,比如那些黏著他的“年金”。
第一個要賜予盧梭年金的人是法國國王。1752年,盧梭的歌劇《鄉村占卜師》在巴黎火起來,從巴黎的多家大劇院一直演到了楓丹白露宮。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后看過這個歌劇后都很喜歡,就派使者找到盧梭,說要召見他并賜予一項年金。盧梭猶豫再三,便以健康不佳為由推脫了。盧梭放棄年金的行為遭到了親友們的譴責,朋友還批評他是“愚蠢的驕傲”。
時隔10年,盧梭的名氣更大了,卻因出版 《愛彌兒》遭到了法國當局的通緝。他逃到普魯士境內的莫蒂埃居住,受到了普魯士國王的庇護。1763年,腓特烈國王為了表示自己愛惜人才,不僅饋贈禮品,還決定賜予盧梭年金。他再次謝絕了普魯士國王的饋贈和年金而離開了普魯士。人們紛紛說他是個十足的傻冒兒、偽君子,故作清高、不識抬舉等等。
1766年,他在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的幫助下逃往英國避難。轉年他的朋友幫他向英王喬治三世申請到了每年100英鎊的年金并幫他代取,為此他與朋友鬧翻了。由此可知,在他發出“金錢金錢,煩惱根源”的感嘆背后曾有過怎樣的辛酸經歷。不明就里的人在讀過盧梭《懺悔錄》中的解釋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奧秘:“那筆可以說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丟掉了,但我也就免除了年金會加到身上的枷鎖。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氣也完蛋了。從此以后怎么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我就只得阿諛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我擺脫所有那些誘惑,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心一意過慵懶的生活,讓精神安靜下來——這從來就是我最突出的愛好,最持久的氣質。”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也許是盧梭早年的傷痛太多、疤痕太深的緣故,在他的心靈深處似乎埋藏了一個易燃易爆的火藥罐,讓他的論著處處充滿了火藥味。面對社會的各種不公和壓迫,他那犀利的言辭仿佛連珠炮似的越發越猛。
1749年,盧梭寫了一篇應征論文《論科學與藝術》,在巴黎一炮打響。當時他偶然在《法蘭西信使》雜志上看到了第戎學院的一則征文——“論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否有助敦化風俗”,靈感的火花頓時點燃了他許久以來憤懣的思緒。他顧不得社會大眾對科學與藝術的普遍性贊美,而以慷慨激昂、驚世駭俗的言辭斥責它們都是些虛浮的東西,束縛和掩蓋了自然的美和真,“拋擲花環于人類所戴枷鎖之上,終致人類在日常生活中不堪重負”;認為在文明社會中,由于科學、藝術和文學同財富、奢侈密切聯系在一起,它們不但無助于敦風化俗,反而會傷風敗俗。盧梭的征文以其論點新奇、論證有力、文筆優美而得了頭獎,寂寂無名的他由此一鳴驚人。那一年他38歲,思想體系日趨成熟。
1753年冬,盧梭看到第戎學院又發布了一條“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的征文,這個題目正是經常盤旋在盧梭頭腦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于是,他又寫下了題為《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應征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考察了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過程,從經濟和政治上挖掘出社會不平等的起因。他指出:文明社會的貧困、奴役和全部罪惡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私有制就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唯有用暴力推翻罪惡的封建專制政權,才能建立起平等、合理的社會制度。這篇論文對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來說,無異于一枚重磅炸彈,震動了整個歐洲。結果這篇征文不僅未能獲獎,而且無法在法國面世,幾經努力在荷蘭出版后還導致了敵對階級對他的迫害。

1762年,盧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政治學代表作《社會契約論》,隨之又出版了他的教育哲理小說《愛彌兒》,這兩部著作猶似暴風雨前夜發出的兩顆響雷讓全天下震動。他在《社會契約論》中開篇就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卻比其他一切是奴隸的人更是奴隸。”而這個讓人們失去自由的枷鎖就是國家的強權統治。在這部四卷本著作中,他系統闡述了國家與政府的關系,指出我們應該建立的國家最高權力應屬于人民;人民的主權不可轉讓、不可分割、不可侵犯、不可替代。他還向所有遭受奴役的同胞們吶喊“: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了人性,拋棄了做人的權利和義務。”他在這本書中的吶喊后來被人們評為“人類解放的第一個呼聲,世界大革命的第一個煽動者”。他提出的“主權在民”主張也被看作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僅影響了歐洲的革命以及美國的獨立戰爭,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長篇小說《愛彌兒》原本是討論兒童教育的,他卻指責是罪惡的社會把人給染壞了,認為“自然曾讓人幸福而良善,而社會卻使人墮落而悲慘”。
盧梭的這些激揚文字惹怒了歐洲統治者,于是政府、教會乃至曾以朋友相稱的達官顯貴們都視其為敵,說他膽大妄為、褻瀆宗教、試圖打倒教會和推翻政府。巴黎高等法院向盧梭發出了通緝令;政府查封、焚燒了他的書籍;巴黎大主教畢蒙發布文告把盧梭列為上帝的敵人;沙龍和文化媒介也印發宣傳品、編造謠言,用各種惡毒的語言羞辱、誹謗他……這讓形單影只、孤苦無援的盧梭在余生的歲月里一路逃亡,一路為自己鳴冤叫屈,寫下了一系列浸滿血淚的著作——《懺悔錄》《對話錄》《漫步遐想錄》,它們被稱為盧梭的“自傳三部曲”。
“盧梭將永遠是原來那個盧梭”
1762年,盧梭遭到法國當局的通緝之后,開始走上漫長的逃亡之路:從法國到瑞士,到普魯士,再逃往英國,然后又潛回法國。8年之間輾轉于多個小鎮和荒島,或寄人籬下,或棲息于窩棚、茅舍之中。來自四面八方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敵人紛紛圍剿過來,都要將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最讓他痛心的是朋友的背叛,尤其是自己曾經尊敬的、亦師亦友的學界泰斗伏爾泰,竟然也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猛烈轟擊,說他將自己的五個孩子丟棄給育嬰堂,性生活糜爛導致染上梅毒,還譴責他為人狂妄自大、傲慢無禮等等。隨著這些揭發和宣傳,盧梭被人們看成是瘋子、騙子、野蠻人、人類的敵人……眼見自己被人抹得一團漆黑,逃亡期間的盧梭便開始撰寫《懺悔錄》為自己辯護,他要還原一個真正的清白的盧梭:“休想按照他們的模式塑造一個讓—雅克;盧梭將永遠是原來那個盧梭。”

盧梭的《懺悔錄》在逃難途中斷斷續續寫了4年。在這本書中,他記述了自他出生至1766年被迫離開法國圣皮埃爾島這50多年間的人生經歷,也勾勒出了自己思想形成的心路歷程。他說:“當時我是什么人,我就寫成什么樣的人。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言之切切,擲地有聲。他希望通過《懺悔錄》能為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做些澄清:“我絕不愿有虛假的名聲,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屬于我的美德和惡行歸給我,也絕不愿人家把我描繪得不像我自己。”然而當他完成了這部書稿之后卻無法出版,他曾尋找一些場合去朗讀也被人阻止了。
盧梭逃回法國后到處躲藏,經孔迪親王斡旋,法國當局于1770年默許他回到巴黎卻不能隨意發表言論,盧梭便寄望于通過寫作來消除人們對他的誤解。1775年他完成了《盧梭評判讓—雅克:對話錄》(簡稱《對話錄》),1776年他又開始撰寫《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簡稱《漫步遐想錄》),而當他寫到第10次漫步時,尚未結篇就去世了。
老天不負有心人。盧梭去世僅10年后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歷史的發展變化完全順應了盧梭的愿望。革命者奉盧梭為“法國大革命之父”,并替他昭雪了冤屈。1791年,法國國民公會投票通過決議,給“大革命的象征”盧梭樹立雕像,并以金字題詞:“自由的奠基人”。1794年,革命政府又將埋葬在巴黎北郊埃爾姆農維爾小鎮的盧梭遺骸隆重地遷進巴黎的先賢祠。墓碑上刻的銘文說:“睡在這里的是一個愛自然與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