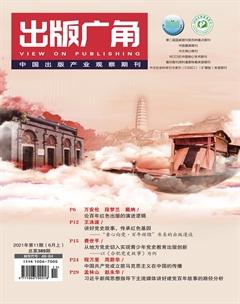兒童繪本對博物館社會教育的影響探析
陳曦?巫驍


【關? 鍵? 詞】繪本;博物館;社會教育
【作者單位】陳曦,南京市博物總館;巫驍,南京市博物總館。
【中圖分類號】G26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1.025
西方博物館學者認為,早期的博物館參觀經驗,尤其是特別正面或者負面的記憶,會持續在記憶中保存、發酵,甚至影響觀眾與博物館的長期關系[1]。因此在“終身教育”理念下,博物館社會教育的目標群體從義務教育階段的青少年擴延到學齡前的幼兒群體。2017年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要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藝術教育、社會實踐各個環節,貫穿于啟蒙教育、基礎教育。”[2]可見,有關博物館主題的繪本是兒童群體了解博物館的窗口之一。
繪本一詞源自日語中圖畫書的叫法,是一種以圖片為主、少量文字輔助“畫出來的書”。繪本自引入中國童書市場后,其多元化培智的教育模式受到多數家長的追捧,成為當下兒童圖書市場的主要出版物之一。博物館主題繪本以館藏文物和陳列展覽為主題內容,旨在科學性、趣味性地展現我國古代歷史文明和優秀傳統文化。
一、蘊含博物館元素的繪本出版現狀
1.歐美博物館主題繪本
歐美地區博物館主題繪本起步時間較早、出版體系成熟。在美國,早在1970年,擁有“博物館群”稱號的古根海姆美術館就出版了兒童繪本I' D LIKE THE GOO-GEN-HEIM,繪本中,男孩安迪被美術館奇特的建筑外形吸引,隨之開啟了美術館建筑藝術的探索之旅;1997年,美國保羅·蓋蒂博物館出版繪本導覽手冊Going to the Getty,以幽默有趣的方式介紹了蓋蒂中心的歷史;1995年,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出版繪本《藝術在哪里》,主人公在尋找朋友“藝術”的過程中,介紹了館藏的64幅藝術作品;1998年,大都會美術館出版經典的無字繪本《你不能帶黃氣球進入大都會博物館》,以小女孩和不能帶進場館的黃氣球為線索,探索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藝術珍品。
與此同時,歐洲的一些博物館開始設立童書出版部門,如英國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簡稱V&A)博物館、泰特美術館等。其中,泰特出版社出品的“遇見藝術家”系列繪本,目前以《世界創意兒童畫美術課堂:遇見藝術家系列》為名引入我國圖書市場,并獲得了較大反響。
除了專門的博物館主題繪本,歐美兒童繪本中也經常涉及關于“參觀博物館”的內容。例如,2—4歲兒童閱讀的數學啟蒙繪本《乘著校車去旅行》,在學習數字4的頁面,校車來到了博物館;英語語言學習RAZ分級繪本,小學一年級別的J級繪本Going to the Art Museum,講述了男孩和姐姐在洛杉磯參觀蓋蒂博物館,鼓勵孩子們走進博物館的故事;家喻戶曉的動畫《小豬佩奇》在《喬治的生日》一集中,全家一起參觀博物館并給喬治慶生。可見,通過繪本,歐美地區博物館有機地融入了兒童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
2.我國博物館主題繪本
我國博物館主題繪本出版方興未艾,在譯制海外博物館主題繪本外,原創博物館主題繪本嶄露頭角。2019年,首都博物館、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社舉辦首屆“博物館主題優選童書”,近200套童書和50多家出版社參與評比,是國內博物館主題繪本出版實力的綜合展示。專業繪本公司對藝術審美的把控,虛構類的故事情節設計使博物館主題原創繪本逐漸擺脫說教式的“水土不服”,《故宮御貓夜游玩記》《你好啊,故宮》《親愛的古代朋友》《哇!歷史原來是這樣》等博物館主題暢銷繪本涌現。
以博物館為代表的文博機構積極參與繪本出版,呈現以國家級博物館出版、省級博物館出版為代表的博物館字體繪本出版中堅力量、市級博物館小試牛刀的情形。例如,國家博物館《兒童歷史百科繪本》,故宮博物院《哇!故宮的二十四節氣》,上海博物館“帶回家的博物館”系列繪本《陶瓷鎮》《青銅國》等均為博物館主題繪本的經典著作。綜合實力較強的大型博物館,如上海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繼續深化博物館主題繪本的品類和內容創作,近兩年推出作品《探秘古畫國》《你好呀!故宮》,并以“互聯網+”的模式鏈接音頻閱讀,豐富了小讀者與繪本間的互動。中國港口博物館出版的《我從遠古來》,杭州博物館出版的《尋找回家的路》,杭州工藝美術館、中國刀剪博物館以及中國扇博物館出版的《我的木偶師朋友》,南京市博物總館出版的《城回江水流——秦淮姐姐話南京》均在傳播地域文明、構建“無邊界博物館”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兒童是民族的未來,開發本土題材原創博物館題材繪本,有益于構造中國兒童的精神家園,把民族的故事用孩子們喜歡的形式出版,可以使孩子看見中國的文化之根[3]。
二、繪本元素融入博物館社教活動的方式
繪本是兒童與博物館教育之間的橋梁,融合繪本元素與博物館社教活動是博物館延伸社教活動廣度和深度的有益參考。繪本評論家賴嘉綾認為,博物館主題繪本的分類可以參考圖畫書的基本分類,即虛構類、非虛構類和活動手冊。虛構類繪本由一個故事串聯起博物館的參觀經歷,讀者代入書中的角色,和主人公一起參觀博物館的建筑空間和展品展示;非虛構類繪本以展示館藏藝術品為主,偏向于藝術啟蒙;博物館活動手冊類似于導覽手冊,多以問答形式激發兒童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1.構建兒童講解詞
講解詞是講解員向觀眾解說博物館陳列展覽的書面語言,是博物館開展公共教育的語言信息。優質的講解詞能使觀眾產生共情,提升參觀游覽體驗,是博物館社會教育的核心。我國博物館的講解詞通常是一套標準,以成人認知范疇去介紹文物的歷史、出處、材質、工藝、紋飾和有關人物及歷史事件等。這些非虛構類語言風格的講解詞雖然專業性和知識性強,但對于兒童來說枯燥、晦澀、不容易理解,難以使其在博物館參觀中找到共鳴。
基于兒童認知模式的繪本語言能給博物館撰寫兒童講解詞提供有益示范。博物館主題繪本語言突出描述文物的旨趣轉達,兼顧具體性和生動性。例如,靈活運用兒歌和童謠描述歷史片段和歷史場景,在講解詞《青銅國》中:“一個人在煮粥、兩個人在蒸飯、三個人在燉肉,四個人都嘴饞,五個人正在調味”[4],通過兒歌把35件青銅器的功能介紹得面面俱到,兒童即可對青銅器面貌和用途了然于心。同時,講故事的方式,生動親切、朗朗上口的語言也能夠激發兒童在發展中的口語表達能力。
2.虛構類繪本主角引導
兒童處在“自我為中心”和“萬物有靈”的思維模式下,虛構類的博物館主題繪本及文物故事敘述能力強,卡通角色形象生動,易于將兒童帶入歷史場景中。虛構類博物館主題繪本的主角有第三人稱視角《故宮御貓夜游玩記》的“御貓”、《你好呀!故宮》的“龍爺爺和小松鼠涂涂”、《你好啊,故宮》的“神獸”導游;還有第一視角《我從遠古來》的河姆渡少年“吉澤”、《我的木偶師朋友》的南宋木工學徒“安安”、《尋找回家的路》的建德男孩“杭小建”等,擬人化的動漫形象拉近了兒童與厚重歷史的距離感。
館藏文物擬人化,是用兒童的姿態與之對話,是博物館文化傳播的天然媒體人。陜西歷史博物館在宣傳平臺中大量使用卡通人物“唐妞”,制作與該形象相關的文創產品和IP授權,使“唐妞”收獲了極大知名度[5]。此外,在博物館展廳重點展品處放置虛構類卡通主角,能為兒童提供有效的參觀路徑。而博物館社教人員通過“文物吉祥物”,以兒童認知視角講解文物,也有助于提高兒童參觀博物館的興趣和學習內驅力。
3.問答形式的參觀手冊
在博物館主題繪本中,主人公多以問答式形式展開對文物的介紹,這是一種啟發式的教育方式,不僅可以培養兒童的語言學習能力,還可以培養兒童欣賞文物的專注力。如比利時的一些博物館就制作有卡片、小冊子形式的兒童導圖冊,導圖冊中多以問答方式引導兒童游覽參觀,附帶的卡通貼紙能夠輔助兒童完成博物館打卡任務。2019年,杭州工藝美術館針對低年齡層的兒童觀眾制作了兒童導覽圖,這是一份“知識可視化”的思維導圖,使用具有兒童思維的語言文字,繪制具有場館特征的童趣彩圖,內容涵蓋館區分布、互動體驗、精品課堂等,豐富了兒童與博物館的交互式體驗。
4.“第二課堂”的教材
利用好博物館這個“活教材”是促進課程觀、教育觀轉變的重要方式,是推動學校、家庭、社會共同構建教育循環圈的一個選擇[6]。針對兒童開展博物館課程或者相關社教活動時,繪本可以充當“博物館教材”,供兒童在參觀博物館之前學習。繪本鏈接博物館與兒童的知識儲備,使兒童的博物館參觀過程不止于“逛”,而是給予兒童充分的時間去思考、去探索。
三、繪本提升博物館公眾影響力
公眾影響力是博物館實現社會價值的衡量標準之一,表現為博物館的存在、傳播文化、實施教育及其他社會活動對公眾在觀念或行為改變方面的作用[7]。繪本通過傳播博物館文化,豐富了博物館教育形式,提升了博物館的公眾影響力。
1.加強博物館公信力
博物館是收藏、保護、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機構屬性決定了其公信力的根源。博物館藏品物化見證一段歷史或一個事實,是博物館存在的根基,是觀眾參觀博物館的主要吸引力。博物館主題繪本的創作基于向兒童觀眾展示博物館藏品的實物性特征,故事內容趣味性的前提是專業性和科學性。博物館參與繪本創作,可增強圖書內容來源的權威性,達到向觀眾還原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的目的。
2.提升博物館文化力
博物館匯集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生產、生活、文化及自然環境相關的物證,是人類文化與自然知識的殿堂,蘊藏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博物館主題繪本通過精美的彩圖和兒童思維邏輯架構主題故事,讓深藏閨中的博物館文化信息活了起來。博物館主題繪本是對專業類文博書籍品類的補充,是公共科學解讀文物歷史的有效憑證。此外,博物館主題繪本的閱讀群體不僅限于國內兒童,海外兒童同樣也是受眾讀者,因此繪本在創新與傳承中國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增加博物館親和力
博物館主題繪本塑造的卡通化、擬人化的文物角色,“文物開口說話”的語言童真意趣,使博物館的形像更為親和。博物館主題繪本通過思維引導的方式,潛移默化地促進了 “終身教育”理念下兒童的社會發展。同時,繪本中大量的游戲互動、有聲閱讀指導也提高了博物館的交互式功能,縮短了博物館與公眾間的距離。
繪本作為博物館出版物的衍生品,對博物館傳播文化的作用重要。繪本中益智有趣的教育價值,對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博物館社會教育有所啟發。將繪本元素融合博物館社教場館活動,有益于深化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內涵,提升博物館在公眾中的影響力,對博物館社教功能多元化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Recall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EB\OL]. (2015-11-02)[2021-04-18]. https://www. tandfonline. com/doi/abs/10. 1080/10598650. 1995. 11510292.
[2]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 [EB\OL]. (2017-01-25)[2021-04-18]. http://www. gov. 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 htm.
[3]趙菁. 博物館元素融入兒童繪本創作方法研究[J]. 中國博物館,2019(4):92-97.
[4]肖凱倫,馮鳴陽. 上海博物館兒童教育系列文創繪本研究. [J]. 創意設計源,2020(3):62-65.
[5]李博雅. “活化”語境下唐妞的誕生、成長與未來[J]. 中國博物館,2019(4):85-91.
[6]馮偉群,徐慧. 多元教研助成長,多方支持促探究——以“博物館項目主題活動”教研為例[J]. 早期教育(教師版),2017(9):32-34.
[7]劉迪. 博物館公眾影響力研究[J]. 東南文化,2013 (3):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