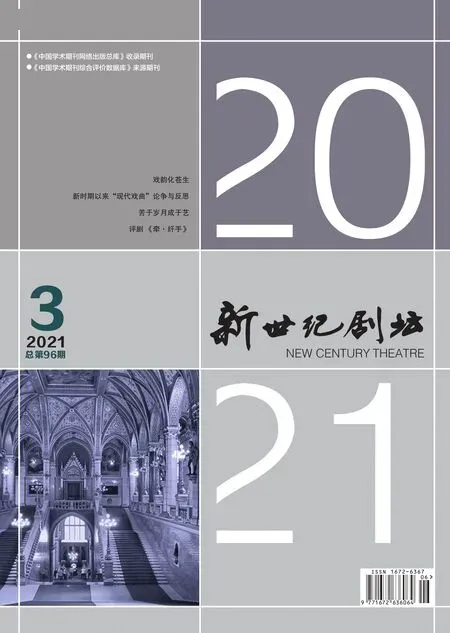新時期以來“現代戲曲”論爭與反思
文/康建兵

川劇《巴山秀才》劇照
“現代戲曲”作為一個詞匯、術語被使用,往上可追溯到20世紀早期,宋春舫在1925年使用過“現代戲曲”一詞。[1]往下可延續到當前,比如最近陸續刊發的圍繞2019年“張曼君與中國現代戲曲學術研討會”的多篇文章。如果把“現代戲曲”視為一種新的戲劇形態或文體形式,尤其是作為對新時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戲曲新現象的理論表述,主要始于孟繁樹教授的倡導和研究。孟繁樹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現代戲曲”一詞,用來描述當時的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的創作情況。進入21世紀以后,呂效平教授在對戲曲本質的研究中同樣提出“現代戲曲”,并系統論證了現代戲曲的內涵外延、文體特征和藝術精神等,為現代戲曲注入全新的理論話語,被認為是“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戲劇理論研究課題”[2],對我國戲劇理論具有建構意義。由此,從現代戲曲引申出的戲曲現代化、戲曲現代性、現代戲曲的情節整一性等話題,引起大家的爭論。梳理和探討有關新時期的現代戲曲理論研究及其爭論,無疑有助于深化對戲曲現代化、現代戲、戲曲性等問題的理解,這些問題依然是當前和今后戲曲發展與研究的重點。
一、“現代戲曲”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戲劇的發展步入新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階段,一大批杰出的戲劇家連同他們的戲曲新作脫穎而出,震動劇壇。如魏明倫的《易膽大》(1980)、《巴山秀才》(1983)和《潘金蓮》(1985),鄭懷興的《新亭淚》(1981),周長斌的《秋風辭》(1985),郭啟宏的《南唐遺事》(1986),王仁杰的《節婦吟》(1987),徐棻的《紅樓驚夢》(1987)和《田姐與莊周》(1988),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1988),盛和煜的《山鬼》(1987)等。
隨著這些戲曲新作和舞臺演劇的涌現,以宏觀視野和理性思維對這個階段的戲曲進行梳理和提煉,不僅成為劇作家們的自覺,也是理論界的重要課題。比如,郭啟宏把《南唐遺事》《秋風辭》《新亭淚》《晉宮寒月》等體現了劇作家的主體意識和現代意識的新史劇稱之為“傳神史劇”,并對“傳神史劇”作了理論分析。徐棻把《泥馬淚》《邯鄲夢》《山鬼》《還魂記》以及川劇《潘金蓮》《四川好人》《紅樓驚夢》《田姐與莊周》等稱之為“探索性戲曲”,并指出這是一個暫時的、相對的概念。她認為理論家要“提出新的理論以引導實踐。從而幫助‘探索性戲曲’健康發展,促進‘探索性戲曲’取得成功”。[3]
面對新時期戲曲創作和舞臺演劇的新現象及其理論訴求,理論界起而應之。率先對其進行整體研究的是孟繁樹,他提出“現代戲曲”的概念。誠如孟繁樹所說,“現代戲曲”是他提出的嶄新的理論命題,他圍繞這一命題發表了一批學術文章,闡述“現代戲曲”的形態特征、思想內涵和美學結構,“從而證明這是一種由現代人創作、供現代人欣賞、體現現代審美精神和規律的新型戲劇藝術。”[4]孟繁樹在1988年發表的《現代戲曲的崛起》一文中,從表現內容、表現形式和審美特征三個方面,對新時期涌現出的一批優秀的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進行了全面論述,認為它們在三個方面發生的深刻變化,“改變了戲曲藝術的性質,使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以現代戲曲的嶄新面貌出現。傳統戲曲屬于古代藝術范疇,以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為標志的現代戲曲,則屬于現代藝術范疇。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戲曲。”[5]孟繁樹圍繞“現代戲曲”主題相繼發表了《關于“現代戲曲”的思考》(1987)、《戲曲文學的新時代》(1987)、《論新時期的現代戲》(1988)、《造劇思潮不可阻擋》(1988)、《論現代戲曲系統》(1990)、《現代戲曲文學主體性的復歸》(1990)、《現代戲曲文學的視角與形式特征》(1990)等文章。他認為“現代戲曲”是一個新概念,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是“現代戲曲”的兩種演劇形態,但不是“現代戲曲”的成熟形態,只是“現代戲曲”的雛形或過渡;只有通過“現代戲曲”的創造,才能使戲曲從根本上擺脫危機;戲曲文學作為戲曲表演的從屬品的時代已經結束,現代戲曲文學主體性的復歸成為“現代戲曲”的重要標志;“現代戲曲”的興起開辟了戲曲藝術的一個新時代,即“現代戲曲”的時代。孟繁樹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戲曲新創作、新現象進行及時的把握和理論研究,并開創性地提出“現代戲曲”的概念,又予以詳細的理論建構,開“現代戲曲”研究先河。或許因為當時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還處在發展中,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尚未拉開宏觀審視這一歷史階段的足夠距離,對“戲曲現代化”的新界定還需時日檢驗。因此,孟繁樹的“現代戲曲”概念及其研究,在當時的影響并未達到應有的熱烈程度,但他的破題必然為后來的研究提供諸多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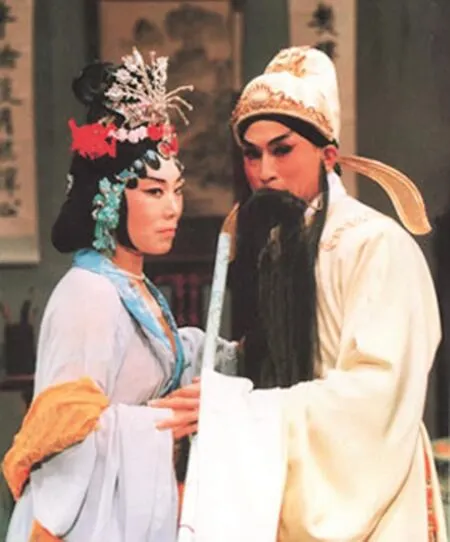
昆劇《南唐遺事》劇照
此后,對“現代戲曲”的討論斷斷續續,有的倡導建立“現代戲曲”學,有的討論“現代戲曲”的二度創造美學。但這些大都屬于零散化研究,對“現代戲曲”的討論并未形成自足完備的理論體系,直到呂效平的“現代戲曲”研究。呂效平對新時期戲曲的研究較早見于《試論當地戲曲的文學化》(1998)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并未使用“現代戲曲”一詞,而是用的“當代戲曲”。此后,他在2002年發表的《戲曲特征再認識——質疑〈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概論〈中國戲曲〉》中,認為戲曲的現代化過程就是戲曲文學本質的回歸,提出要充分認識20世紀80年代以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魏明倫的《潘金蓮》、郭啟宏的《南唐遺事》等為代表的現代戲曲作品的共同文學本質,“把它們看作戲曲發展的第四階段,即‘現代戲曲’階段”。[6]呂效平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戲曲本質論》中,集中探討了“現代戲曲”的來龍去脈、內涵外延、文體特征和藝術精神。此后又發表了《論“現代戲曲”》(2004)、《再論“現代戲曲”》(2005)、《論現代戲曲的戲曲性》(2008)、《現代戲曲:中國戲曲的當代文體》(2012)等文章,加上他與一些學者的往來商榷,十分清晰地呈現出他對于中國戲曲第四個發展階段即“現代戲曲”的許多極具開創性的思考和理論創新。
呂效平的“現代戲曲”研究,并非單純地對20世紀80年代的戲曲創作中出現的新作品、新現象進行理論歸納。他在對中國古典戲曲800多年浮沉的歷史勾勒中,提出并討論元雜劇的抒情詩本質,明清傳奇的抒情詩與史詩并立的特征,古典地方戲使用非文學語言的特點等重要問題,對這類戲曲本質問題的討論,最終歸于對“現代戲曲”的確認和彰顯。而對“綜合性”、“虛擬性”、“程式性”等原本已是約定俗成或似是而非的問題的追問和反思,則對以往的一些傳統觀點和理論都構成了不小的挑戰和沖擊。加之他的“現代戲曲”研究,“借用了歐洲傳統戲劇以及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戲劇理論作為參照系”,[7]往往又不免招致“以西釋中”或是“以西套中”等的猜疑。因此,當前有關“現代戲曲”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呂效平的“現代戲曲”理論而展開的。
二、“現代戲曲”的界定
依照呂效平對“現代戲曲”的外延界定,“現代戲曲”指的是新時期以來以魏明倫、郭啟宏、陳亞先、鄭懷興、周長斌等劇作家的創作為代表的戲曲作品。這一界定在兩方面對于何謂“現代戲曲”作了規約:一是在時間上是指新時期以來的戲曲;二是對象上是指以魏明倫等的創作為代表的戲曲。但“現代戲曲”并不是新時期以后才出現的新術語,這個詞在20世紀50年代圍繞現代戲等的研究中就被廣泛使用。何況用“現代戲曲”界定新時期戲曲是否妥帖,以及即便認可用“現代戲曲”命名新時期戲曲的可行性,那么起止時間依然有爭議。具體地講,討論的方面包括有無必要以“現代戲曲”來為新時期戲曲命名,應該怎樣界定這個概念等。
龔和德教授認為:“現代戲曲這個概念在運用中有時間、題材、性質三種不同的規定。時間概念用以區別古代戲曲、近代戲曲;題材概念用以專指表現廣義的現代生活;性質或品格概念是指追求現代文化精神和現代敘述方式中為大家比較公認的優秀作品。”[8]在這其中,首先要界定時間概念,“研究現代戲曲的構建,首先要確定現代戲曲開始的時間”。[9]有研究者否認“現代戲曲”一說,認為“中國戲曲,不論發展到什么年代,不管發展到什么模式,始終還是中國的傳統戲曲,不應該有中國‘現代戲曲’之說。”[10]1983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按古代戲曲、近代戲曲、現代戲曲三個歷史階段進行戲曲目錄編排。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論》(2010)在討論中國戲曲的人民性時,對中國戲曲的歷史階段區分僅作“古代戲曲”和“當代戲曲”之分,認為當代戲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戲曲,即社會主義階段的戲曲。朱恒夫教授認為:“現代戲曲是和古代戲曲對應的,它僅是戲曲發展史上的一個時間上的概念,即為今日之戲曲。”[11]但朱恒夫新近發表的《振衰起敝、艱難前行——新時期戲曲概論》(2018)中,又以“新時期戲曲”來指“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40多年的戲曲。羅懷臻則認為:“我們現在沒有現代戲曲,只有現代題材的傳統戲。”[12]他認為現代戲曲應該是現代題材和新的戲曲創作方法、表現手法的結合,實現戲曲的現代表達。
即便贊同“現代戲曲”這一專有名詞,但對“現代戲曲”所屬的時間階段仍存在不同的觀點。學者孫紅俠認為:“將‘戲曲現代化’之后的形態命名為‘現代戲曲’,當然是寶貴的學術推進,但一個新的概念還需要我們不斷推敲。因為‘現代’雖然比其表面上代表的時間概念要更有內涵得多,但究其產生卻無法完全去除其時間屬性和指向。”[13]金登才教授則認為現代戲曲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并以1928年田漢倡導“新國劇運動”為現代戲曲的時間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呂效平的“現代戲曲”,陸煒教授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第四種戲曲美”。陸煒雖然贊同從1956年的《十五貫》《團圓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的《曹操與楊修》和魏明倫劇作,一種新的戲曲文體已經形成,但認為“現代戲曲”的概念意圖雖好,很鮮明,卻不甚合適,原因是“現代戲曲”一詞可以理解為現代社會的戲曲或是具有現代性的戲曲,不便作為某種特定戲曲美的專有名詞。認為它可以做專有名詞,實際上是認為戲曲現代化只能產生一種戲曲美,而且這種美已經定型,再也不會變化了,這種想法是不合理的。“把欲確認的戲曲新形態叫做‘第四種戲曲美’,則能夠充分達到與古典戲曲區分的目的而沒有上述弊病。”[14]陸煒歸納了“第四種戲曲美”的八個特征。但他在繼提出“第四種戲曲美”的三年后,在新發表的文章《“現代戲曲”的三種美學趨向》(2009)中,卻不再使用“第四種戲曲美”,轉而沿用“現代戲曲”的表述。
李偉教授在《“現代戲曲”辯正》(2018)一文中,對當前“現代戲曲”的三種用法作了詳細區分,認為從時間上看指現代時期的戲曲;從題材上看指表現現代生活的戲曲;作為一個文體概念和文化概念,指具有現代戲品格的戲曲。關于“現代戲曲”的時間界定,他認為若以表達“現代性”思想的標準來考察,那么現代戲曲的誕生應該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那時起所有表現民族解放、個性解放,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的戲曲,包含所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因應變革的戲曲,“不管它的文體是雜劇、傳奇,不管它的音樂是曲牌體還是板腔體,不管它的題材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是‘現代戲曲’。”[15]總體上,李偉分析了對“現代戲曲”的各種用法的特點,并提出自己的新見解。他更看重“現代戲曲”的精神內涵,即現代性品格,這種現代性品格不會因戲曲的題材、文體或技術之別而受限。“現代戲曲”是現代人改編和創作的具有現代精神、表現現代觀念的戲曲。這個界定不拘戲曲文體原則和舞臺技術手段的限制,體現出很強的容納性、靈活性和適用性,也更符合當下及今后戲曲發展的實際和多元形態。

呂效平教授著《戲曲本質論》
以上學者對“現代戲曲”的各種界定和解讀,無論在時間層面、創作主體或題材等方面,大家既有交集也有分歧。要抓住“現代戲曲”的本質特征,還需要進入文體層面,需要從戲劇性、現代性等維度加以詮釋。由此,圍繞“現代戲曲”的內在本質問題,自然引申出對“情節整一性”、“戲曲現代性”等的討論。
三、“情節整一性”問題
“情節整一性”是“現代戲曲”研究的重要問題,引起的爭論較多。關于地點、時間和動作(情節)的三種整一性(“三一律”),從亞里士多德起,西方理論家爭論不休。黑格爾認為,在三種整一性中,真正不可違反的規則是動作的整一性,“而真正的動作整一性只能以完整的運動過程為基礎”。[16]
呂效平的“現代戲曲”研究借用歐洲傳統戲劇以及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戲劇理論,認為“現代戲曲”是文學的戲劇,文學家成為創作的主體,文學的藝術成為戲劇作為“綜合藝術”中主動執行綜合功能的施動者,戲劇首先被文學的原則規范,而不是首先被表演的原則規范。他通過對《巴山秀才》《曹操與楊修》《新亭淚》《駱駝祥子》等戲曲作品的分析,認為這些戲曲無一不體現了表演的聲腔與身段之美,遵從并服務于情節的整一性,“這種以情節整一性原則顛覆表演至上原則的結果就是一種戲曲新文體的誕生”;“情節的整一性原則是這個戲曲新文體最基本的文體原則”;認為獲得戲劇性的“情節整一性”是“現代戲曲”文體的基本要求,這一要求在元雜劇、明清傳奇和古典地方戲文體中都沒有出現過。總之,“現代戲曲,就其文體形式而言,是中國戲曲與歐洲傳統戲劇情節樣式的結合”。[17]呂效平之所以概括出“現代戲曲”的“情節整一性”特征,是基于《曹操與楊修》《巴山秀才》等戲曲在客觀上存在對情節性的明顯追求。正如他所說:“我的這個結論并不依賴思辨的支持,它可以獲得統計數據上的支持: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戲曲新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全都奉行了這一條原則。我所做的,只是描述當代戲曲劇場的‘情節整一性’與明清傳奇作為案頭作品的‘情節整一性’之間的差別,至于它與元雜劇的抒情詩歌藝術整一性和古典地方戲折子戲的舞臺藝術整一性之間的差別,則是一目了然的。”[18]
呂效平對“現代戲曲”的情節整一性的概括,是對新時期能夠被納入其理論考量范疇的典型戲曲作品的歸納,但并非要窮盡每一部現代戲曲。這是從個別到一般、從局部到整體的理論格局和視野。但這些個別、局部是很能代表新時期戲曲創作成就的。正如“三一律”是對歐洲古典戲劇(尤其是17世紀法國古典悲劇)的情節藝術的概括,但并非適用于每一部古典戲劇作品。呂效平提出“現代戲曲”,又希望形成一個能“指稱全部當代戲曲作品的專有名詞”,“把當代戲曲作品統稱為‘現代戲曲’”。[19]他用“指稱全部當代戲曲作品”“把當代戲曲作品統稱為”等表述,一方面意在將“現代戲曲”提升到能與“元雜劇”、“明清傳奇”、“地方戲”相提并論的對等高度,另一方面又想將“現代戲曲”與前面三種戲曲所屬的古典戲曲的歷史階段作區別,因為“現代戲曲”是現代戲曲。在此前提下,盡管呂效平特別強調“現代戲曲”的“情節整一性”是指“劇場的情節整一性”,指的是戲曲對情節整一性的追求,應能體現于劇場,呈現于表演,是案頭與舞臺的相得益彰,合二為一。但他所說的“現代戲曲,就其文體形式而言,是中國戲曲與歐洲傳統戲劇情節樣式的結合”等表述,容易引起爭議。
龔和德指出:“如果現代戲曲只有“情節整一性”,沒有動作的感性形式的多劇種的豐富多彩,觀眾何必來看戲曲?現代戲曲當然要追求情節整一性,但又必須安排好動作歌舞化的技巧整一性,實現情節線與技巧線的有機結合。否則,不可能成為優秀的受觀眾歡迎的現代戲曲。”[20]管爾東教授認為“故事不是戲曲的必須,文學也不是戲曲的本質,只有表演才是聯系編、演、觀的核心要素,戲曲的表演這一形式本就應該大于劇情內容。”[21]“戲曲歸根結底是一種博大精深的舞臺藝術,獨樹一幟的表演才是維系其生命的源泉。而且無論在表演還是文學上,戲曲都與西方戲劇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能要求戲曲和話劇一樣走‘舶來’的道路,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戲劇情節、代言等要求來改造戲曲。”[22]
李偉認為“情節整一性”的文體原則與“現代戲曲”沒有必然聯系,若將其視為對20世紀現代戲曲的典型樣式和成熟形態的概括,大體不錯。若是對全部“現代戲曲”的描述及對未來“現代戲曲”發展的要求,則不全面。“‘情節整一性’對于‘現代戲曲’而言,只能是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現代戲曲’的文體選擇應該像‘現代性’一樣,可以是開放的和自由的。”[23]
如果將表演和文學視為戲劇的兩極,某種程度上,關于“情節整一性”的討論,焦點是戲曲的本質屬性究竟是文學還是表演的問題。單看各家觀點,均言之有理。但如果呂效平的觀點是限定在對“現代戲曲”的討論,那么有關“情節整一性”的爭論,應該有的放矢,否則有的商榷就容易出現失焦,成為泛泛而談。筆者認為,新時期的戲曲作品的確普遍呈現出文學性追求的特點,并且在戲劇文學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文學成就在先支撐舞臺呈現,即魏明倫說的編劇主將制。但用“情節整一性”這個源自西方的概念歸納中國戲曲,容易引起質疑。
新時期的一部分戲曲作品,在故事編排和情節結構等方面與西方的情節整一性理論不謀而合,究其原因,既有呂效平所說的,新時期戲曲之所以產生對于歐洲傳統戲劇情節樣式的追求,源于當代戲曲作者受到發端于五四的新文化的教育,及其在此教育影響下形成的知識結構與戲劇觀念,更由于源自西方現代劇場演出方式和同樣受到新文化教育的現代觀眾提出的要求。此外也有另外的因素,如部分戲劇家的自覺追求,符合戲劇創作的一般規律。特別是當編劇擔當創作主將時,對劇本的文學要求必然高于以往時期。其實,情節整一性的背后還有其他緣由,如20世紀80年代文化反思熱的影響,提升了對戲劇文學性的追求。
四、戲曲現代化與現代性
現代性的話題比較復雜,是百余年來中國戲劇研究的焦點和難點。“20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是最值得關注的研究對象,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現代性因素的介入,促使甚至直接導致中國戲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24]特別是當把對戲曲的現代性討論與戲曲現代化等問題結合起來,情況更復雜。比如,戲曲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關系?戲曲要不要現代性?如何理解戲曲的現代性?什么是現代戲曲的現代性?總之,由“現代戲曲”引出,這些問題同樣引發大家熱議。
呂效平之所以把新時期的部分重要戲曲概括為“現代戲曲”,就“現代”二字而言,原因主要在于兩方面,一是這些戲曲展現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情節特征,即具有情節整一性的共同點;二是比情節整一性更重要的現代性問題,這是對現代戲曲的“質”的規定。“比情節整一性的文體形式更為要緊的,是‘人’的發現與解放,是創作的精神自由的狀態。這是‘現代戲曲’的精神本質”;[25]“根據它的‘現代性’特征,我建議就用‘現代戲曲’作它的名稱”。[26]現代戲曲的這一現代性特質,源于戲劇家的現代性的精神狀態,同時又能完美地融于劇作,呈現為劇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即“‘現代戲曲’的精神本質源自劇作家獨立、自由的精神狀態,但是它之得以實現,不是依賴劇作家的宣言,歸根到底,是要在作品中‘人’的描寫上體現出來。”[27]對于這些看法,大部分研究者都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比如,龔和德認為,“現代戲曲的質的規定性有不同的表述,需要梳理和深入探討。我的粗淺想法,就是要有人性描寫的深度并有益于當代人的心靈建設”。[28]張曼君也認為:“落實戲曲的現代性特質,最重要的是落實于對人學的觀照”,“戲曲現代性的命題中,人學是首要的價值核心。”[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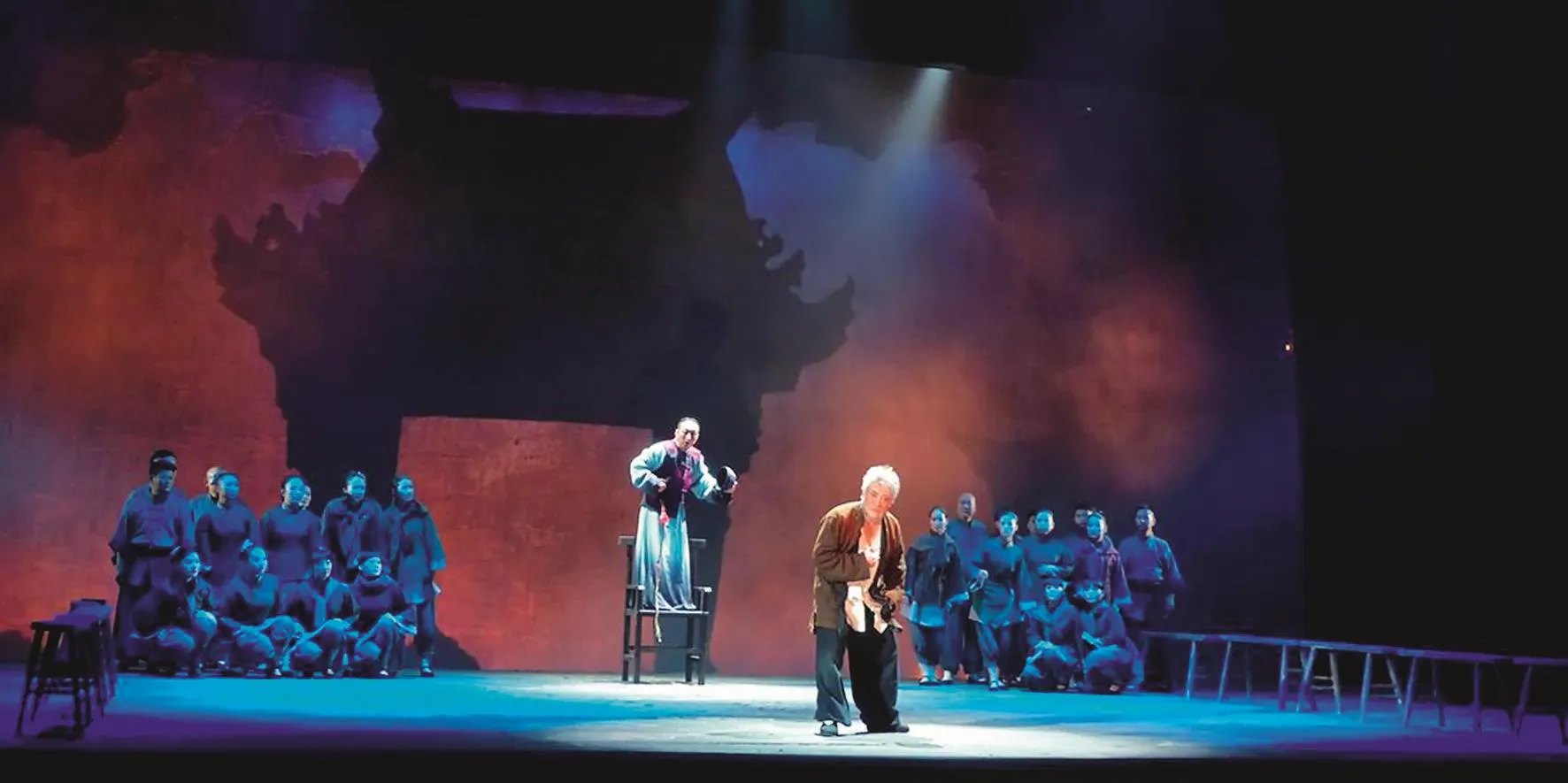
秦腔《狗兒爺涅槃》劇照
李偉指出:“‘現代戲曲’的現代性就在于用反思與批判等現代精神,平等、獨立、自由、人權等現代價值理念去觀照并表現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爭取自由與解放的心路歷程。這是‘現代戲曲’的一般形態。”同時他也認同呂效平的概括與論述,即“‘現代戲曲’超越倫理,從精神的高度審視人性,塑造矛盾的、發展的、辯證的性格是它的美學理想”[30],并認為這是“現代戲曲”的高級形態。
對于戲曲現代化、戲曲現代性的時間屬性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戲曲現代化具有時間屬性,其起始時間有的認為應從梁啟超號召“小說界革命”、陳獨秀提倡改良戲曲算起;有的認為應從五四啟蒙運動“戲劇改良”的討論算起。胡星亮教授認為:“中國戲曲現代化的起始在五四時期”。[31]戲曲現代性不具備時間屬性。戲曲現代化不一定有現代性,戲曲現代戲與題材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羅懷臻認為:“現代性是一種價值取向,而不是一種時間概念。不要把現代性理解為時間意義上的現代。現代題材不代表具有現代性、現代意識,相反,我們的一些古代神話、歷史題材往往卻會充滿了現代意識或現代感。”[32]張曼君也指出:“戲曲現代性不等同于現代題材的表現,現代戲與現代性之間也沒有天生的必然聯系。”[33]
存在爭議的地方主要是對現代性的質的規定性的理解。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現代性是內容規范還是形式界定,或者兩者兼備?呂效平的現代戲曲理論中對現代性的認識主要從思想內涵、精神本質進行界定,注重戲曲作品表現的內容。陸煒的“第四種戲曲美”也認為這一戲曲新形態的第一條特征是思想內容具有現代性。李偉認為“戲劇的現代化應該是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從物質外殼到精神內涵的全面的現代化。相應的,作為現代化的結果的現代性也應該是全面的。”[34]傅謹教授表示“文學藝術的現代性訴求應該從更廣泛的角度理解,尤其是應該從藝術本身的形態與變化去理解”,他認同啟蒙思潮是20世紀中國戲劇呈現現代性轉型的重要契機,但啟蒙對戲劇的影響不僅僅在于作品表現的內容層面,而且更進一步要在表現手法和舞臺樣式方面進行深刻變革,“才可以說中國戲劇獲得了它的現代性”。[35]傅謹對于戲曲現代性、現代性等問題的思考,集中體現在《20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追求》(1998)、《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與本土化》(2003)、《三十年戲曲創作的現代性追求及得失》(2009)等文章中。李偉在《“現代戲曲”辯正》(2018)一文中對其做了系統深入的探討,本文不再贅述。在傅謹新近發表的《20世紀戲曲現代化的迷思與抵抗》(2019)一文中,再次明確了戲曲現代化包括戲劇內涵、戲劇形態和戲劇體制三大方面,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戲曲現代化思潮以及孟繁樹的現代戲曲研究作了深入的評析,也為我們重新認識何謂戲曲的現代性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啟發。
對于戲曲現代性的不同看法,折射出如何認識20世紀中國戲劇變革的主潮、何謂戲曲本體,以及對戲劇與啟蒙、戲曲文學的現代性與戲曲多元生態的現代性、“演什么”與“怎么演”等關系的不同理解。多年來對戲曲現代化、戲曲現代性討論的深入,尤其是21世紀的現代戲曲創作的歷史性突破,相信對于戲曲現代性的認識也將形成更多共鳴。正如有學者指出:“在討論現代化的文獻中,長期以來,一個占主流地位的觀點是:不論現代化的起點有何不同,所有現代化的社會,在最終出現的現代格局或‘現代性’上,都將是近似的,甚至是同一的。”[36]
對“現代戲曲”的討論,當然并不止以上幾個方面,諸如現代戲曲的戲曲性、戲曲性與現代性、“樂本位”、“詩本位”、程式化等戲曲美學問題的討論,都是復雜而極富有意義的話題。在過去一段時間里,隨著作為對新時期這一特定階段描述的“現代戲曲”的創作走向式微,有關“現代戲曲”的理論探討一度漸入平靜。最近,孟繁樹的《我與“現代戲曲”》(2020)、傅謹的《“現代戲曲”與戲曲的現代演變》(2021)、孫紅俠的《現代戲曲:“文體”再辯——兼評呂效平“現代戲曲”研究》(2021)等佳作的問世,一方面對歷史語境中的“現代戲曲”作了勾連和當下闡釋,另一方面在再思考和再辨析中仍見新思想的碰撞和新觀點的涌現,這也折射出“現代戲曲”作為重要命題的理論空間和生命力。呂效平當年指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現代戲曲并沒有持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艱難面對三方面的挑戰,他所說的第二、三方面的挑戰,即繼承古典戲曲傳統和戲曲發展空間的問題,在當下已呈現出新面貌。對于第一方面挑戰即“現代性”的精神品格等方面,恐怕仍舊是一個未竟問題,依然存在反思的必要。
注釋:
[1]宋春舫在1925年發表的《法國現代戲曲的派別》(《猛進》1925年第14期)一文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戲曲”一詞,但正文中未提及。
[2]陸煒:《關于建構中國的戲劇理論的思考提綱》,《戲劇文學》,2009年第7期,第4-9頁。
[3]徐棻:《關于“探索性戲曲”的獨白》,《文藝報》,1988年3月4日。
[4]孟繁樹:《現代戲曲藝術論》“自序”,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版,第1-2頁。
[5]孟繁樹:《現代戲曲的崛起》,《戲劇藝術》,1988年第1期,第49-57頁。
[6]呂效平:《戲曲特征再認識——質疑〈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概論〈中國戲曲〉》,《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第85-93頁。
[7]呂效平:《戲曲本質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8][20][28]龔和德:《陽春白雪,返本開新——王仁杰劇作的古典化追求及其意義》,《藝術評論》,2012年第7期,第33-44頁。
[9]金登才:《現代戲曲形態的構建》,《戲劇藝術》,2008年第4期,第71-79頁。
[10]曾倫:《傳統戲曲與“現代戲曲”之我見》,《南國紅豆》,2003年第5期,第20頁。
[11]朱恒夫:《論提升戲曲現代戲表演藝術水平的方法》,《中國文藝評論》,2017年第5期,第58-66頁。
[12]羅懷臻:《中國戲劇:因時維新70年》,《中國戲劇》,2019年第5期,第10-12頁。
[13]孫紅俠:《“現代”與立場:傳統戲曲的轉化與建構》,《民族藝術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43頁。
[14]陸煒:《論第四種戲曲美》,《戲劇藝術》,2006年第1期,第65-74頁。
[15][23][30][34]李偉:《“現代戲曲”辯正》,《文藝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第140-147頁。
[16]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51-265頁。
[17]呂效平:《論“現代戲曲”》,《戲劇藝術》,2004年第1期,第38-48頁。
[18][26]呂效平:《論現代戲曲的戲曲性》,《戲劇藝術》,2018年第1期,第13-24頁。
[19][25][27]呂效平:《再論“現代戲曲”》,《戲劇藝術》,2005年第1期,第4-16頁。
[21]管爾東:《戲曲的兩種“形式大于內容”》,《戲曲藝術》,2014年第1期,第79-87頁。
[22]管爾東:《中國戲曲的本質屬性:文學還是表演》,《求索》,2009年第10期,第173-175頁。
[24][35]傅謹:《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與本土化》,《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第155-165頁。
[29][33]張曼君:《我的現代戲曲觀》,《中國文化報》,2019年2月21日。
[31]胡星亮:《論二十世紀中國戲曲的現代化探索》,《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第48-63頁。
[32]羅懷臻:《中國戲曲的“地域性”與“現代性”》,《當代戲劇》,2016年第4期,第4-7頁。
[36]金耀基:《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第20-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