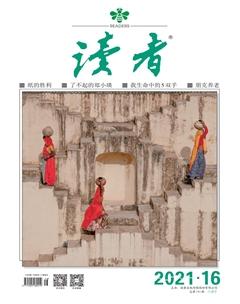“自私”可能推動了經濟發展

在經濟學家眼里,“自私”未必是一個十分令人討厭的詞語。
“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寫道:“我們能夠喝到牛奶,吃到豬肉,并非因為奶農和屠夫的饋贈,而是因為他們在追逐利益。”他要表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并非來自同情心或利他主義,而是來自利己之心,來自每一個人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欲望。
所以亞當·斯密接著說,人們從事勞動,未必抱有增進社會利益的動機,但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人們會受到一只“看不見的手”的牽引,而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們本意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即請給我我所需之物,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求的東西。
由于人與人之間天賦與才干有所不同,為了更有效率地賺錢,每個人都會依據自己的專長,選取自己能以較低成本從事生產的工作,然后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進行交換,以獲取自己所需。這樣一來,社會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專業化分工,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隨之提高。
在《國富論》出版近100年后,達爾文又從生物學家的視角,佐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
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的核心思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其實就是在說,所有生物的繁榮和自然選擇,都是生物體從自身欲望和動機出發所產生的結果。
又過了100年,1976年,英國演化生物學家、新達爾文主義的忠實擁躉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出,人的自私并不是后天養成的,不僅僅是適者生存的結果,而是源自基因。也就是說,自私不是一個假設,而是源自基因的本能。
舉個例子,雌鳥在感知到危險時,可能會假裝一瘸一拐地行走,從而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雌鳥為了保護雛鳥而甘愿承擔被獵食者獵殺的風險,大概會讓你想到“奉獻”一類的詞語。但理查德·道金斯近乎冷血地發問:雌鳥的行為會不會正是由自私的基因驅動的呢?雌鳥的自我犧牲純粹是因為基因在雛鳥身上能夠獲得更長久的傳承。
經濟學家與生物學家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向了一個共識,即人的自私或者利己行為,能在無意之中創造出公共福祉。
現在,你對“自私”大概有了新的理解。
一個極度自私的人,是沒有真朋友的,注定是孤獨的,無法成就任何事業,但自私本身并不可恥,可恥的是兩種極端的狀況:第一是拒絕對等付出的極端自私,第二是打著大公無私的旗號來攫取個人利益。
當我們能夠以更理性的態度面對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我們就會對自己和這個社會有更清醒的認識。
(楊子江摘自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辛 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