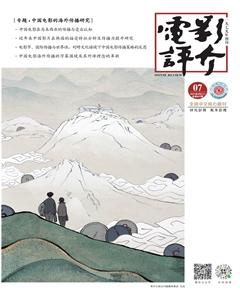論國產動畫電影受眾的界定、細分與增值
林一楠 邵楊
作為中國電影藝術大家庭中一個別具特色的重要成員,動畫電影近年來進入黃金發展期,成為電影產業體系里最具有上揚前景的版塊之一。然而表面的繁榮并不能讓人無視基礎的薄弱、創意的貧瘠、市場運作的欠缺規范。未來何去何從,依然需要學術界與理論界用求真務實的嚴謹態度,對其各個產業環節進行不斷的理性分析和深入探索。
其中,作為傳播對象和消費主體的受眾資源,是整個動畫電影產業體系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一切動畫電影作品實現其藝術價值、社會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基本前提,也是動畫電影營銷行為的對象、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如能正確分析中國動畫電影受眾的群體構成、習慣好惡、心理質素、審美需求,探討受眾、作者、作品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找準受眾的合理位置與角色,及其可能發揮的效能作用,必將對中國動畫電影培育出真正嶄新而健康的產業生態,產生決定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一、受眾角色的界定:傳受關系的倒置與“協商立場”的價值
哈貝馬斯的所謂“交往理性”認為,所有參與傳播的人,都能有相同的機會自主選擇及使用言辭行動,相互質疑言辭內容的真實性或合理性。[1]在當下高度復雜的動態傳播系統中,很難絕對地分辨出“來源處”和“接受物”的差別,主客體關系隨時都在重置,受眾已經具有了主體或“類主體”的性質。具體到電影產業當中,對于電影受眾消費態度與審美態度的正確判斷,對難以捉摸的大眾心理的主動識別乃至迎合,是整個產業體系與時俱進和推陳出新的催化劑。
可是,中國動畫電影依舊保持著一種逆反的、較為原始的傳受關系。“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大前提和基本職能定位,將中國動畫電影從一個經濟或藝術命題,上升到文化安全、意識形態、社會風氣的宏大敘事當中。這種“育人”與“立人”的優越感,使得回蕩在受眾周圍的總是年齡小、知識少、涉世未深的結構性偏見,那么一應從營銷現實出發所理應掌握到的受眾需求,就長期被賦予“天真、幼稚、不切實際”的誤讀。
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傳播鏈條體現為:傳播者向受眾提供傳播產品從而滿足“受眾的需要”。那么當下中國動畫的情形則是:傳播者用傳播品去建構受眾將之塑造定型成符合他們概念的“需要的受眾”。這種打著“受者本位”幌子的“傳者本位”,足以解釋中國動畫電影在說教傾向和慢節奏的道德倫理鋪陳中,與一切夸張的情節或幽默的人物無緣,也足以解釋那種“受眾缺乏自主判斷能力”的主觀臆斷,是如何設下了愛情、動作、驚悚等一系列題材禁區,以及感傷、頹廢、江湖義氣、為所欲為等一系列情緒和性格禁區,無情地剔除了一切商業化和娛樂化的必要元素。我們依然在嚴重地低估我們的受眾,拒絕與受眾進行平等的對話。
當然,在動畫電影這個比較特殊的領域內,相應地側重一些對社會效益與教育價值的講求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寓教于樂”這個詞本身就含有復雜的層次,將根本著眼點放在“教”還是“樂”上,“寓”的效果將大相徑庭。如果不能恰當掌握“寓”的平衡與巧妙,讓“教”的過度擴張,傷害了作為基礎而存在的“樂”,那么模式化與板滯化的教條主義誤區必將隨之跟進。很顯然,傳播者本位的態度與角度、一廂情愿的傳播內容與傳播觀念、不得當的傳播方式,都可能導致“過度傳播”對于受眾思考空間的擠壓侵占,進而誘發出受眾逆反心理的形成。
斯圖亞特·霍爾為大眾傳播的意義輸送過程提出過三種解碼方式:其一是“主導霸權立場”,即受眾始終服從傳遞者與預想性意義的支配;其二是“協商立場”,即一方面承認支配意識形態的權威,另一方面也強調自身的特定情況,受眾與支配意識形態始終處于一種矛盾的商議過程;其三是“對抗立場”,即受眾和支配意識形態徹底決裂,以一種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碼信息。[2]中國動畫電影當下所采用的單線性操控的“主導霸權立場”需要否定,直接采用“對抗立場”又潛藏著徹底失控、代溝無限制擴大的危險。于是結論明顯,“協商立場”,是最適宜中國動畫電影去采用的受眾培養策略與受眾和解態度,是打造良好的營銷大環境所必須做好的鋪墊。
動畫電影的本質屬性是一門視覺藝術,“再強大的意識形態預設,也必須運用恰當的造型手段與審美符號來進行受眾審美需求上的匹配。”[3]受眾的觀念變化是與其審美心理的變化同步發生的,是在欣賞著驚心動魄的故事、賞心悅目的風景、漂亮帥氣的明星的同時,不知不覺地接收那些環繞在它們周圍的隱含觀念的。只有良好的電影觀賞效果,才能促成良好的教育宣傳效果。
正如查·阿爾特曼在《電影史論辯》中指出的那樣,作為當下最普遍和完善的電影娛樂形式,類型電影(無論是真人還是動畫)恰恰應當同步具有文化和反文化、主流和反主流的意識形態。“把被禁止和被許可的雙重體驗結合起來,竟能使前者顯得合理、后者得到豐富。”[4]《獅子王》(羅杰·艾勒斯、羅伯·明可夫,1994)講述男人的責任,《飛屋環游記》(彼特·道格特,2009)講述愛和承諾,《玩具總動員》(皮克斯,1995)講述珍惜童年和善待身邊的每一樣事物,這些都是最主流的價值觀念,只不過在實現希望的時候掌握了靈活性與討巧的策略,所以獅子辛巴可以去經歷富于浪漫色彩的流浪(《獅子王》),熊貓阿寶可以從一開始就呆板蠢笨、愚頑憨直(《功夫熊貓》約翰·斯蒂文森和馬克·奧斯本,2008)。即使那只插科打諢的木須龍對理解木蘭的孝心與勇氣并無實質性的幫助(《花木蘭》托尼·班克羅夫特、巴里·庫克,1998),即使那只健忘癥的多莉并未強化“用愛戰勝內心恐懼”的主題(《海底總動員》安德魯·斯坦頓,2003),但它們攜帶的趣味性暗含了一種對于受眾喜好的尊重與認可——哪怕他們是一群未成年人。
如果能夠向受眾適度開放一部分被忽視甚至禁止的情感、價值、觀念、欲望,求得更大的心理認同和情感注入,往往能讓主流的宣傳更加順暢和具有力度。這就是“協商立場”下,傳播主體與受眾在相互理解、相互承認、相互溝通、相互妥協中完成意義的分享與延伸。
二、受眾細分:打破籠統命名
美國學者溫德爾·史密斯在廣告學研究中率先提出:必須改變傳統觀念里“市場是同質體”的認識,力圖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差別,有針對性地提供不同產品。[5]電影的受眾是由大量分布廣泛的個體構成的,受眾“因為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經濟收入、職業和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決定了受眾“會選擇不同類型的電影”。[6]那么,一個成熟的電影大國,勢必需要根據這些選擇上的差異性,進行受眾群體的進一步歸類與分割,在制片、發行、放映特別是營銷的目的性上,從模糊的“面向大眾”,轉入針對具有特定需求的“分眾市場”,這也是電影產業保證經濟效益的最佳選擇。
當前的中國動畫電影產業建立起一個屬于自己的成熟“分眾市場”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沿用以往習慣,將“少年兒童”指認作動畫電影的核心受眾。這個模糊而籠統的命名里,也至少包含了幼兒(學齡前)、兒童(小學生)、少年(初中)以至青春期以上年齡(高中甚至大學),這四個群體涵蓋了將近十五年的跨度,彼此間因成長階段的不同,認知深度、觀賞水平、美學與情感需求、思維能力與方法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當其被視作一個形而上的靜態整體加以評估,必將因對象層次的模糊,導致營銷策略的顧此失彼,與回報率上的大幅縮水。
首先,它導致了內容的失措,因兼顧不同年齡層次需求而呈現出的大雜燴面貌,和往往最終出現的“幾頭不落好”的慘淡。以2020國慶檔影響力頗大、備受期待的《姜子牙》為例,盡管預告片里有那句“建議八歲以上兒童觀看”,盡管它所表現的洪荒世代、封神宇宙、光怪陸離的原始想象和萬物有靈的生命哲學體系,都足以使其主動扛起“動畫走向全齡主流藝術”的旗幟,但是顯然,主創還是時時刻刻想把這部成人化、中年人向的作品,往更符合大眾理解上的“動畫片”拉一點回來:從坐騎變成了寵物的四不相,被塑造成鐵憨憨還得舍身取義負責催化淚點的真愛申公豹……也就是說,在倡導與標榜更加成熟、也更加反低齡化的觀看素養同時,《姜子牙》還在受制于某些根深蒂固的東西、擔心“觀眾會認為我太不符合他們對動畫片的觀看預期”,結果,也只能在這種風格上的搖擺不定。
其次,它導致了傳播效果的模糊。兒童、少年、青年人在思想成熟度上有著根本差異,在無法對傳播物可能構成的正負面影響做出準確預期的情況下,只能本著傾向最弱者的原則,將標準設定在最低年齡的階段,就仿佛規定一歲、五歲、十歲、十五歲的四個孩子吃同樣的食品,鑒于一歲的消化不了任何谷類與肉類,所以十五歲的也不能完成正常的食物攝入。這直接導致了上面講過的中國動畫電影“保護欲過剩”現象,以及創作者在道德自律和創新創意上的兩難。
最后,它同樣會影響到產業鏈的其他環節,考慮到衍生產品的開發肯定將成為中國電影拓展生存空間、尋求贏利手段多樣化的主要措施,那么各年齡段兒童在消費目標和能力上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動畫主題對圖書、玩具、文具、服裝、主題游樂設施的注入理應有所側重。
總之,受眾細分是一種復雜而動態的實踐過程,它需要我們在未來的繁榮中時刻保持敏銳的嗅覺與市場洞察力,也需要將這種嗅覺和洞察力轉化為成果文本的創作能力。
三、受眾增值:爭取延伸群體的三大步驟
丹尼斯·麥奎爾曾對受眾進行過這樣的表述:“受眾既是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導致相同的文化興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產物,也是特定媒介供應模式的產物。”[7]可見受眾并非一個先在的概念,他可以受到媒介的后天建構。一種電影作品的“核心觀眾群體是相對固定的”,而延伸觀眾群“會隨著外界的各種影響而變化”[8],這個群體在接收傳播信息的過程中隨機性與彈性更大,有時甚至因為一個營銷細節上的調整就能被吸引過來。
當“少年兒童”被定義成核心受眾的時候,他們身邊那些具有最密切關系、最容易受到其觀看行為影響的人——家長,就自然地成為這個以年齡為標準的封閉結構向外擴展時,最直接的觸點,成為營銷空間拓展和營銷效果增值時一個新的可能性。
作為電影的動畫,播出媒介、傳輸渠道、接收環境均有別于電視動畫片。中國家庭寵愛孩子,很可能讓孩子在家中掌握電視頻道選擇權,但電影領域的消費行為并不發生電視機前,要通過購票進入電影院的直接支付行為來實現。沒有經濟收入的兒童,只能依賴于家長“帶他去電影院”來滿足審美需求。因此在動畫電影這個特殊傳播物里,延伸受眾同時具有“付費受眾”的性質,手中直接掌握著核心受眾的消費行為能否成功。
家長對于動畫電影的潛在消費欲望,起碼包括了陪伴、把關、自身娛樂等多個層次。只不過因為年齡與社會角色上的限制與慣性,暫時沒有完成向動畫電影的無保留投放。所以,動畫電影在營銷過程中有待完成的受眾擴容,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充分激活上述潛在的需求,將潛力轉化為實際消費。
以大獲成功、老少咸宜、日益成為每年春節檔動畫第一IP的“熊出沒”系列為中心樣本加以檢視,爭取延伸觀眾可分三個步驟:
第一,看見。引發延伸受眾群的注意,取決于一系列傳播策略的成功疊加:立體化規模的宣傳推介,由電視、廣播、平面媒體、新媒體不同媒體層次,以及車身、路牌、燈箱、大屏幕、公交和樓宇移動電視、影院LED等全方位廣告手段,跳出對“少年兒童”的糾結,直指全部成年人活動空間,用調動一切資源、橫跨多個渠道的集束轟炸法,將之上升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文化熱點與時尚話題;上線時期的恰當選擇,針對“家庭共享型”定位,選擇春節期間——成年人最渴望團聚、最愿意花時間陪伴兒女的時段;安全的故事構成,去除暴力粗口不良觀念,反派人物也非大奸大惡,斗爭停留在機智幽默的游戲層面,其間又蘊藏進團結互助、不怕困難、樂觀向上等“教育意義”,迅速通過了家長驗收。
第二,習慣。避免在新鮮感逐漸告一段落時注意力的重新外移,需要建立起一種固定欣賞習慣。“熊出沒”系列采用的方式,恰恰來自于在題材選擇上對媒介互滲的利用,對電視這個家庭內媒介所建立的親和感與牽連感的借力:選擇在電視媒介上已經充分形成受眾基礎的作品加以提煉和濃縮、實現劇場版和影院化,有效地降低風險。換句話說,不去電影院的家長們也不會拒絕每天給孩子一段動畫片時間,當熊大熊二光頭強占據這個時間日復一日地出現在生活中時,終于逐漸成為他們陪著孩子有意無意地建立了熟悉和好感的故事。
第三,迷戀。這是將延伸觀眾群提升成核心觀眾群的決定性步驟:陪伴孩子的被動性被自我內心的滿足所代替。事實上,一部優秀的動畫電影必然進行過“雙重編碼策略”,在照顧未成年人心理的同時,也從不曾放棄與成年人心理上的互通,在兒童化與成年化的并行中尋找一個“契合點”,成為流動性的多層次文本,在內部實現兩種文化行為的轉換。熊出沒系列確實牢牢吸住了兒童的心,而對于家長們來說,亦存在各取所需的可能。風趣幽默的惡搞滿足了他們緩解壓力、保持童心的希冀;符號化的人物設置和其樂融融的整體氛圍對應著他們對家庭生活的期許;對熱點話題的收攬與對網絡經典語言的采用,與父母們關心社會時政的習慣并行不悖。
綜上所述,中國動漫電影的發展,需要從受眾本位出發進行換位思考,以“協商立場”重建良性的傳受關系;需要從多個指標出發進行動態的受眾細分,營造更加健康的分眾市場;需要調整營銷細節,分三個步驟完成對延伸受眾群體的爭取。這是本文所提出的分析與建議,也是中國動畫電影在未來的路途中,應當采取的較為理想的受眾策略。
參考文獻:
[1]單波.評西方受眾理論[ J ].國外社會科學,2002(1):1.
[2][英]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M]//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王廣州,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345-358.
[3]羅湘來.受眾心理與中國原創動漫的發展對策[ J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3):61.
[4][美]查·阿爾特曼.類型片芻議[ J ].宮竺峰,譯.世界電影,1985(6):74-86.
[5]邵培仁,陳兵.媒介戰略管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106.
[6][8]金冠軍,鐘謹.電影創意產業[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92,95.
[7][英]丹尼斯·麥奎爾.受眾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