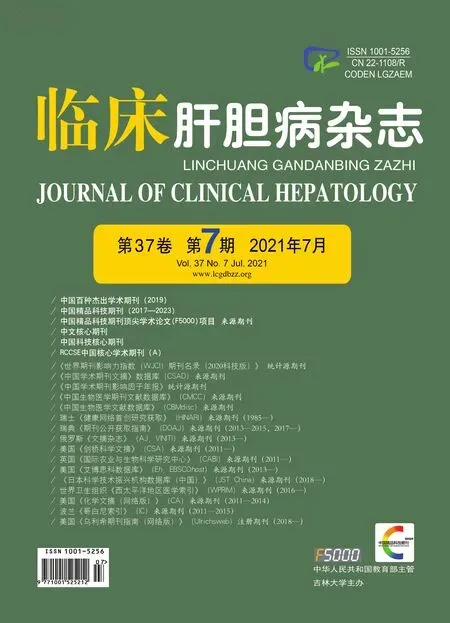以黃疸為表現并發自發性脾破裂的原發性脾淋巴瘤1例報告
姚秋艷,吳澤生,施榮杰,楊理偉
大理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云南 大理 671000
自發性脾破裂是臨床罕見的非創傷性急癥,常發生于病理性脾臟,主要因血液系統、炎癥性、腫瘤性疾病導致,亦有相當一部分患者發生于無潛在疾病的脾臟[1-2]。原發性脾淋巴瘤(primary lymphoma of spleen,PLS)并發自發性脾破裂既往僅有零星病例報道,現就1例以黃疸、自發性脾破裂就診,行脾切除術后診斷為PLS的病例報告如下。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71歲,因“腹脹、尿黃、眼黃1周”于2020年7月31日于本院就診。患者就診1周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腹脹、尿黃、眼黃,伴納差、體質量減輕2 kg,無腹痛、發熱、畏寒、寒戰,無惡心、嘔吐、嘔血,無陶土樣大便、皮膚瘙癢、雙下肢浮腫等不適。既往否認慢性病、傳染病、藥物濫用史。門診血常規檢查:WBC 5.22×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52.3%,淋巴細胞百分比33.7%,RBC 4.59 ×1012/L,Hb 128 g/L,紅細胞比容 38.4%,PLT 92 ×109/L。血生化:TBil 125.9 μmol/L,DBil 108.6 μmol/L,IBil 17.3 μmol/L,ALT 157 U/L,ALP 337 U/L,AST 150 U/L,TP 53.9 g/L,Alb 30.5 g/L,GGT 240 U/L,TBA 216.8 μmol/L,血淀粉酶、乙型肝炎六項、丙型肝炎抗體、HIV回示未見異常。腹部彩超示:肝脾大,肝內、外膽管無擴張,腹腔大量積液(下腹部探及厚約8.0 cm液性暗區)。遂以“黃疸、腹腔積液查因”收入院。入院后查體:體溫36.5 ℃,脈搏95次/min,呼吸20次/min,血壓97/63 mm Hg。一般情況稍差,神清,全身皮膚黏膜黃染,全身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心肺查體未見異常,腹平坦,全腹軟,全腹輕壓痛,無反跳痛,肝脾觸診不滿意,移動性濁音陽性。入院后急診查腦鈉肽正常,凝血全套:PT 14.1 s,凝血酶原時間比值1.23,PT對照 11.5 s,PT-INR 1.23,D-二聚體 2.02 μg/ml,纖維蛋白降解產物 5.91 μg/ml;腫瘤標志物:CA-125 40.08 U/ml,其余項未見異常。患者黃疸、腹腔積液、肝脾大,原因不詳,行腹腔穿刺術,抽出鮮紅色血性腹水,考慮患者腹腔出血可能,予急診行腹部增強CT示:(1)脾臟不規整無強化區,脾梗塞待排;(2)腹盆腔積液;(3)肝內、外膽管無擴張(圖1)。遂轉普外科行腹腔鏡探查。術中見:腹腔、盆腔內中等量血液,約600 ml,脾腫大,約22 cm×13 cm×6 cm,脾中極見一長約1 cm裂口,不時有血液滲出。術中診斷:脾臟自發性出血。中轉開腹行脾切除術(因急診手術,術中見腹腔積血多,故未行肝活組織檢查及膽道探查)。術后標本示:脾臟體積為17 cm×10 cm×3.5 cm,重300 g,被膜完整,表面光滑,表面見直徑2~4 cm的破口,切面暗紅實性質軟,未見明顯包塊。病理學檢查:脾臟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非生發中心型,侵襲性,并脾破裂。腫瘤呈彌漫浸潤性生長,紅白髓結構不清,瘤細胞異型明顯,中等偏大,易見核分裂象。免疫組化染色示:CD20(+),CD79a(+),Ki-67(+80%),MUM1(+),PAX5(+),Bcl-2(+),Bcl-6(部分+),CD10(-),CD15(-),CD3(-),CD30(-),CD34(-),CD5(-),CK-P(-),C-Myc(-),Vimentin(-),CD21(-),CD35(-),CD43(-),CD45RO(-)(圖2)。術后查全身淺表淋巴結彩超未見腫大淋巴結。骨髓涂片示:目前骨髓巨核系、粒系增生,紅系稍低。骨髓活組織檢查示:骨髓增生活躍,造血組織容積約占40%,三系可見。粒紅系比例大致正常,各階段細胞可見;巨核細胞小簇狀聚集,形態無明顯異常。未見確切淋巴瘤累及骨髓。術后10 d復查血常規:WBC 11.33×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 64.1%,單核細胞百分比 15.3%,RBC 3.57×1012/L,Hb 105 g/L,紅細胞比容 31.7%,PLT 569×109/L,降鈣素原 0.59%。復查肝功能:TBil 79.5 μmol/L,DBil 63.9 μmol/L,IBil 15.6 μmol/L,ALT 64 U/L,ALP 244 U/L,AST 60 U/L,GGT 233 U/L。脾切除術后,未行化療前患者肝功能較入院時明顯好轉。予R-COP方案化療,具體為:利妥昔單抗針0.5 g d0、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10 mg d1~5、環磷酰胺針1 g d1、長春地辛凍干粉針4 mg d1。化療1次后(術后20 d)復查血常規:WBC 6.12×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 42.4%,單核細胞百分比 10.3%,RBC 3.98×1012/L,Hb 119 g/L,紅細胞比容 36.8%,PLT 417×109/L,降鈣素原 0.43%,網織紅細胞百分比 2.03%。復查肝功能:TBil 38.2 μmol/L,DBil 34.3 μmol/L,IBil 3.9 μmol/L,ALT 19 U/L,ALP 179 U/L,AST 23 U/L,GGT 97 U/L。現隨訪患者已完成化療3次,無特殊不適,復查指標提示完全緩解。

注:a,肝脾大,肝內膽管無擴張;b~d,肝外膽管無擴張,脾臟內多發片狀低密度影,邊界尚清,增強后未見明顯強化,未見淋巴結腫大。圖1 腹部增強CT檢查結果

注:a,CD20陽性(免疫組化染色,×200);b,瘤細胞異型明顯(HE染色,×200)。圖2 病理學檢查結果
2 討論
約40%的淋巴瘤患者脾臟受累,在尸檢患者中該比例約為70%,然而,PLS發病率低,僅為惡性淋巴瘤的1%[3]。其定義尚無統一標準,主要有如下3種:Dasgupta等[4]嚴格定義PSL為只涉及脾臟和脾門淋巴結,沒有肝臟或其他部位受累,如出現其他部位受累,須間隔PLS 6個月以上。Skarin等[5]建議任何累積脾臟、脾腫大的淋巴瘤均可診斷為PSL。Kraemer等[6]進一步定義PSL為淋巴瘤,表現為脾腫大,無外周淋巴結腫大。Ahmann等[7]依據PLS進展程度將其臨床分為3期:Ⅰ期淋巴瘤完全局限于脾內;Ⅱ期病變累及脾門淋巴結;Ⅲ期有肝內、腹腔淋巴結浸潤。PLS病理類型以彌漫性大B細胞性淋巴瘤最為常見,為22%~33%,其次為脾邊緣區淋巴瘤,約為8%[8]。PLS臨床癥狀缺乏特異性,主要為腹痛、腹脹、乏力、發熱、體質量減輕等,早期可能無任何明顯癥狀,也因此其診斷困難。影像學檢查可能為診斷提供有用的信息。CT增強掃描可以判別脾腫瘤的性質,同時可以顯示腹腔其他臟器如肝臟、胃腸道、胰腺等有無侵犯,可為疾病分期提供依據,脾腫瘤的CT診斷符合率高達90%以上[9]。PET-CT檢查并不作為常規檢查,但對于普通CT診斷困難者,可考慮使用,有研究[10]顯示,18F-FDG-PET-CT對PLS的敏感度為90.9%,特異度為91.4%,并可用于準確分期。然而,最終確診仍需依據病理學檢查。研究[11-12]報道了脾臟細針穿刺、脾穿刺活組織檢查對PLS有較好的診斷準確率,但由于其獲取標本不充分,且有16%的患者可能出現如出血、脾破裂等風險,也使其運用于臨床備受爭議。鑒于此,脾切除術后病理學檢查應作為診斷金標準,也是一種治療的選擇。Morel等[13]認為早期脾切除術可以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因脾切除術后患者血細胞數可得到改善,使患者能夠耐受輔助化療。Xiros等[14]提出診斷性脾切除術輔以化療,術后的中位生存時間約為24個月。化療方案主要為R-CHOP(利妥昔單抗、環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堿及強的松)。但本例患者因年齡大,未使用多柔比星。文獻報道的患者部分獲得了完全緩解,本例患者亦是如此,但仍有小部分患者因并發癥死亡。
PLS既往文獻多以病例報告為主。本例PLS患者以黃疸、腹脹入院,門診彩超提示肝脾腫大,腹腔積液,原因不詳。臨床上表現黃疸、肝脾大、腹腔積液的疾病主要以肝臟疾患、膽道梗阻、心力衰竭、血液系統疾患為常見,但患者腹部彩超、CT均未顯示膽管擴張,無心力衰竭其余表現,外周血象亦無明顯異常,故行腹腔穿刺術明確腹腔積液性質,抽出鮮紅色血液后考慮腹腔出血,行剖腹探查見脾臟滲血,遂行脾切除術,術后病檢提示脾淋巴瘤,術后完善淺表淋巴結彩超及骨髓穿刺檢查排外其他部位浸潤,至此PLS診斷明確,符合上述的3種診斷標準。查閱既往文獻,劉松濤等[15]報告了9 例以肝功能異常起病的惡性淋巴瘤患者,張婷婷等[16]報告了2例以肝內膽汁淤積癥為首發表現的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施亞軍等[17]報道了1例以發熱、黃疸就診的PLS。此外有2篇國外文獻[18-19]報道了以肝浸潤、腹水為首發表現就診的脾淋巴瘤。結合既往文獻,目前認為PLS引起黃疸、肝功能異常的原因主要為:(1)腫瘤細胞直接浸潤肝組織,壓迫肝內小膽管,導致膽汁的合成、分泌、排泄等障礙;(2)有研究[20-22]發現,HCV、HIV、HBV與PLS的發病相關,上述3種病毒亦可侵犯肝臟引起黃疸及肝損傷;(3)腫瘤細胞誘發機體免疫應激反應,激活一系列細胞因子如IL-6、IL-10、TNFα等,這些細胞因子可導致全身炎癥反應而造成肝損傷,這與炎癥及免疫調控有關[23]。遺憾的是,本例患者因年齡大,家屬拒絕行肝穿刺,未能清楚患者黃疸、肝損傷的確切原因,但患者肝炎病毒學、HIV均陰性,腹部CT未提示肝臟有明顯的腫瘤浸潤病灶,且脾切除術后、未行化療前患者肝功能已明顯好轉,黃疸消退,考慮其黃疸、肝損傷的原因為PLS誘發機體的炎癥、免疫反應,產生細胞因子導致肝損傷,暫不考慮PLS惡性腫瘤細胞的浸潤。
自發性脾破裂在臨床上較為罕見,其發病率僅為 0.1%~0.5%。自發性脾破裂多發生于病理性脾臟,根據文獻回顧,目前已報告約200例血液系統疾患導致的自發性脾破裂,其中慢性髓系白血病(15.8%)和霍奇金淋巴瘤(36.2%)是主要病因之一[24]。然而,PLS并發自發性脾破裂報道不足20例,其機制考慮為:(1)惡性細胞直接浸潤脾臟,超過了相對不膨脹的脾包膜的能力,導致脾包膜破裂、脾出血;(2)PLS可能導致血小板減少及凝血功能障礙,亦可引起脾出血;(3)腫瘤細胞壓迫脾血管,導致脾梗塞,繼而導致出血,這3種機制可能在脾破裂中發揮協同作用。本例患者起病隱匿,無突發劇烈腹痛,除血壓偏低外無心率快、Hb下降等失血性休克的臨床表現,導致診斷困難,直至行腹腔穿刺術抽出血性腹腔積液后方能診斷,提示自發性脾破裂患者可無明顯臨床表現。脾破裂需急診處理,亦有報道[25]保守治療有效,但對于原因不詳的患者,脾切除術無論對于治療還是診斷都是必要的。
除本例患者,目前國內外文獻暫無同時發生黃疸和自發性脾破裂的PLS的文獻報道。因此,以黃疸、腹水就診的患者除外膽道梗阻、肝臟、心臟疾患等常規病因后,也需考慮到PLS合并自發性脾破裂的可能,診斷需結合影像學檢查和細胞學分析,最終以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診,治療方法以脾切除聯合術后化療為主,部分患者可獲得完全緩解。
利益貢獻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姚秋艷負責課題設計,資料收集、分析,撰寫論文;楊理偉、施榮杰負責收集數據,修改論文;吳澤生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