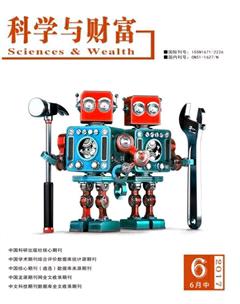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
吳曉君
(云南省普洱市鎮(zhèn)沅縣按板鎮(zhèn)中心衛(wèi)生院)
摘 要:由于綠色會計作為當前社會發(fā)展新興的一門會計學科。對于會計核算工作來說,可以在多元化的因素及其有關(guān)因素等方面做出準確的判斷,并且和以往會計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基于此,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進行分析,筆者依據(jù)自身積累的經(jīng)驗,提出相關(guān)建議,旨在進一步提高醫(yī)院的管理質(zhì)量,促使醫(yī)院能夠在未來的發(fā)展中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目的,為我國的經(jīng)濟建設做出重要的參考。提供給相關(guān)人員,供以借鑒。
關(guān)鍵詞:醫(yī)院;綠色會計;必要性;可行性
所謂綠色會計,也可以稱之為環(huán)境會計,屬于會計學科中新誕生的一門學科。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對企業(yè)多元成本所產(chǎn)生的價值做出真實的反映,從而進一步促使企業(yè)獲得最大號的經(jīng)濟效益。從醫(yī)院當前的發(fā)展形勢來看,隨著綠色會計落實到實際工作中,除了可以符合當前醫(yī)院發(fā)展的要求,同時也是促進全球一體化的必然趨勢,在社會發(fā)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醫(yī)院有效落實綠色會計以來,就慢慢具備了實施的可能性。對此,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筆者依據(jù)自身多年經(jīng)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提供給相關(guān)人士,旨在推動我國醫(yī)療行業(yè)的不斷進步,從而為我國的經(jīng)濟建設做出重要的貢獻。
1 綠色會計的產(chǎn)生及其理論基礎
綠色會計核算的目標及范圍大于傳統(tǒng)的財務會計,其成本范圍和效益范圍也遠遠大于傳統(tǒng)財務會計。綠色會計理論認為,空氣、水、土地以及臭氧層等,都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以及他們子孫后代所共有的“特定財產(chǎn)”。并且這些資源總是稀缺的,理應賦予一定價值并得到補償。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會計所提供的信息既有經(jīng)濟性信息又有社會性信息,不僅能為企業(yè)自身服務,而且能為社會大眾服務,符合市場經(jīng)濟的要求,并有助于會計理論的發(fā)展。這些環(huán)境問題的研究,相對于會計學來講屬于一個新鮮的、邊緣性的科學,是站在會計的角度來看待環(huán)境問題,是用會計的思想體系和方法體系對環(huán)境問題加以分析和考慮,以解決發(fā)展經(jīng)濟與維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矛盾。
2 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的必要性
2.1 實施綠色會計,滿足我國環(huán)境現(xiàn)狀的要求
從宏觀的角度出發(fā),對于醫(yī)院以往的會計模式來講,還沒有把環(huán)境資源融入到核算工作中,這種現(xiàn)象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對醫(yī)院的發(fā)展帶來一定的影響。從醫(yī)院自身發(fā)展來看,倘若沒有長遠的目光考慮自身的發(fā)展前景,那么就會對醫(yī)院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帶來嚴重的影響,經(jīng)濟效益的提升也依然不能彌補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隨著綠色會計落實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社會經(jīng)濟活動來保護生態(tài)平衡,從而促使國民經(jīng)濟可以達到穩(wěn)定增長的效果。所以,在醫(yī)院的不斷發(fā)展下,及時將環(huán)境資源的核算工作滲透到經(jīng)濟核算系統(tǒng)中,進而為綠色會計的有效實施帶來益處。
2.2 綠色會計是醫(yī)院自身發(fā)展以及責任擴展的必然結(jié)果
立足于醫(yī)院發(fā)展的基礎上,來對醫(yī)院長遠利益進行總體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只有增大環(huán)境保護的投入力度,促進綠色會計的順利實施,才能夠促進醫(yī)院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尤其是現(xiàn)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科技的進步,對醫(yī)院的運行模式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在此種情況下,企業(yè)應當積極轉(zhuǎn)變以往單純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的理念,積極過度到追求經(jīng)濟、社會、自然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模式,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對醫(yī)院環(huán)境成本以及環(huán)境效益進行準確可靠的計算和記錄,從而更好的履行醫(yī)院自身的社會責任。因此,綠色會計的實施,是醫(yī)院自身發(fā)展以及責任擴展的必然結(jié)果。
2.3 實施綠色會計是衡量國民經(jīng)濟以及醫(yī)院業(yè)績的重要方式
就綠色會計的實施情況來看,其能夠?qū)︶t(yī)院的社會資源成本進行科學化的核算,并將國民經(jīng)濟水平以及醫(yī)院生產(chǎn)成本進行準確的反映,從而促進醫(yī)院內(nèi)部資源的合理化應用,為社會創(chuàng)建一個優(yōu)良的社會資源環(huán)境。在對醫(yī)院經(jīng)營成果進行計算的過程中,其結(jié)果的合理性和準確性與醫(yī)院對環(huán)境影響的耗費之間的聯(lián)系比較密切,并且醫(yī)院資產(chǎn)負債率的真實性與環(huán)保負債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對多元化因素進行精準計算和分析的基礎上,方能夠明確醫(yī)院運行過程中的財務風險。綠色會計能夠有效的反映出醫(yī)院所履行社會責任的相關(guān)信息,立足于社會的層面來對醫(yī)院經(jīng)營管理的業(yè)績進行考核,進而對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情況進行有效的把握,因此,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具有明顯的必要性。
3 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的可行性
3.1 會計及相關(guān)法律制度的完善,為綠色會計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綠色會計在醫(yī)院有效落實以后,會計以及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機制日益成熟,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為綠色會計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不僅僅如此,社會群體逐漸對環(huán)保意識引起了高度重視,能夠為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提供了可能性。在我國相關(guān)部門、管理及其不斷推動下,為綠色會可以得到有效了落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隨著當前醫(yī)院所具備的環(huán)境有著較高的責任性,當醫(yī)院在不斷發(fā)展的時候,需要站在社會效益的立場出發(fā),從多個角度進行準確的判斷,從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及其管理模式,加大自然環(huán)境核算的力度,最大程度促使醫(yī)院獲得最大化的經(jīng)濟效益,為綠色會計的有效落實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3.2 醫(yī)院內(nèi)外部環(huán)境為綠色會計的實施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從當前醫(yī)院在社會發(fā)展的形勢來看,醫(yī)院的發(fā)展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為綠色會計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并且隨著醫(yī)院在尋找發(fā)展的時候,應當大量借鑒外來資源,并在激烈的市場中站位腳步。目前,國家社會已經(jīng)將目光投入到會計行業(yè)中,在這種形勢下,能夠為我國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帶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從而推動理論的不斷優(yōu)化,由此可見醫(yī)院內(nèi)部環(huán)境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為綠色會計的有效落實帶來益處。
結(jié)束語
通過以上內(nèi)容的論述,可以得知:隨著我國經(jīng)濟水平的日益發(fā)展下,我國各行各業(yè)都得到了蓬勃的發(fā)展。從當前醫(yī)院有效落實綠色會計以來,由于綠色會計在實際實施的時候會具有一定的繁瑣性,它是環(huán)境問題及其相關(guān)的社會問題的融合,屬于一種系統(tǒng)化的工程,這樣就有涵蓋較多的內(nèi)容,并且內(nèi)容具有一定的繁瑣性,不管是對社會來說,還是對醫(yī)院而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顯而易見的是,在醫(yī)院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要進一步加大綠色會計落實的力度,并促使醫(yī)院可以朝著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方向前進,從而為我國的經(jīng)濟建設做出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孫松陽.試析醫(yī)院實施綠色會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中國經(jīng)貿(mào),2016(9):230-230.
[2]馬伊琳.我國推行綠色會計存在問題及策略研究[J].大眾投資指南,2017(01).
[3]崔君平,盧爽,劉旭.試論綠色會計在遼寧的發(fā)展[J].科技經(jīng)濟導刊,2016(32).
[4]劉志剛.實施綠色會計的必要性與對策研究[J].現(xiàn)代營銷(下旬刊),2016(10).
[5]王晨.綠色會計在我國能源行業(yè)的應用研究[J].全國商情(經(jīng)濟理論研究),2016(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