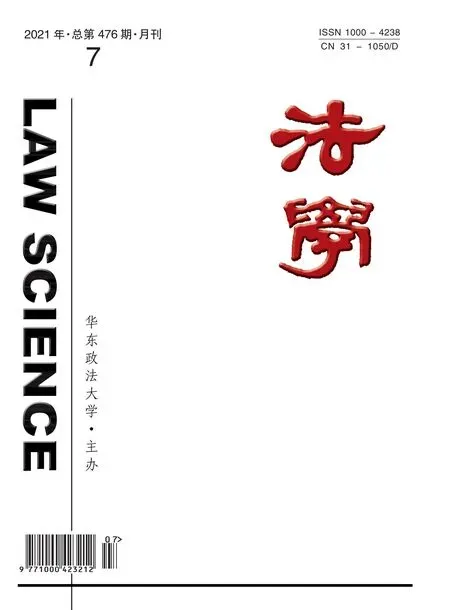緊急狀態下公民權利克減的邏輯證成
●劉小冰
鑒于大多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未知特征和事先缺乏充分的防備,各國在疫情大流行開始時將整個社區、城市乃至國家置于封鎖、隔離之下可能是合理的。〔1〕See Sanja Jovi?i?, COVID-19 Restrictions on Human Rights in the Light of the Case-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RA Forum (2021) 21:545–560,Published Online: 6 October 2020.從法律上說,此類措施實際上就是緊急狀態制度中的公民權利克減(以下簡稱“權利克減”)。“克減”(Derogation)原意為“消減”“減少”,將Derogation 譯成中文“克減”確實“造成了許多模糊的認識”,但“緊急狀態下,克減權利不僅是內國法最經常援引的一項緊急措施,而且也得到了公約的支持和許可” 。〔2〕李衛海:《緊急狀態下的人權克減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年版,第45 頁。因此,制定《緊急狀態法》以落實緊急狀態的《憲法》規定并建立權利克減制度,業已成為我國社會的高度共識。但是,由于現行立法并沒有引入權利克減概念,因而我國建立權利克減制度的首要問題是回答權利克減各內在要素之間的必然性聯系,以確立其理論邏輯。其次,需要明確闡述權利克減在客觀關系系統和制度關系系統中的基本作用,以確立其實踐邏輯。最后,需要全面論述權利克減的基本原則,以便為緊急狀態的立法與權利克減制度的建立提供規范向度,并實現其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高度統一。
一、權利克減:緊急狀態下的特別法律限制
1966 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ICCPR)最早使用了“克減”概念。其后,《歐洲人權公約》第15 條、《美洲人權公約》第27 條沿用了該概念。上述公約將克減規定為締約國的一項權力,即“締約國得采取措施克減其在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從法理上說,國家義務的減少,同時意味著公民權利的減少和公民義務的增加,轉換成另外一種理論范式就是公民權利克減。〔3〕國際公約和區域公約通常表述為“人權克減”(Derogation of Human Rights)。See Abdulla Azizi, Derog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in RNM during the State of Emergency Caused By COVID-19, SEEU Review Volume 15 Issue 1: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of COVID-19, DOI: 10.2478/seeur-2020-0002, p. 24;孫萌:《緊急狀態下人權克減與保障的歐洲標準和實踐》,載《東岳論叢》2010 年第12 期,第173 頁。據此,權利克減是指,在緊急狀態下,當一般法律限制不能實現預定目的時,國家依法臨時對除不得克減權利以外的其他公民權利適用的特別法律限制。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一)權利克減是實施緊急狀態的邏輯結果
這一表述可作如下理解:(1)緊急狀態下的緊急權力來源于權利克減。根據人民主權這一現代法治的基石理論,無論是正常權力還是應急權力,都來源于人民的讓渡和授予。在法理上,這就是公民權利的減損。在正常狀態下,權力和權利的內容及其數量從理論上說是相對恒定的,國家只能在其法定權限范圍內依法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公民可以行使除憲法和法律限制之外的一切權利。但在緊急狀態下,這種先定的運作模式被打亂,權利克減成為緊急權力擴張的主要方式。〔4〕參見劉小冰:《國家緊急權力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 頁。(2)沒有緊急狀態就沒有權利克減。在權利克減的歷史發展中,最為危險的就是不存在突發事件而濫用權利克減,這也是ICCPR 等將宣布緊急狀態作為權利克減的首要條件的主要原因。(3)緊急狀態的結束意味著權利克減的結束。緊急狀態的結束方式,大致有規定期限屆滿、目的已經達到、緊急狀態被撤銷等,無論以何種方式結束,權利克減也必須隨之終止。因此,在國家管理的整個過程中,權利克減最終都只能是臨時性、階段性的。
既然權利克減是進入緊急狀態的邏輯結果,因而什么是緊急狀態即成為關鍵問題。在我國,這一概念“很容易和戒嚴、戰爭狀態、突發事件等相近概念混淆”。〔5〕陳聰:《“緊急狀態”的事實判定與法律規定》,載《理論探索》2015 年第1 期,第109 頁。理論界對此主要有兩種觀點:廣義說認為,緊急狀態包含了戰爭、戒嚴、動員、軍事管制等,因而“應當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與建構緊急狀態制度”;〔6〕郭春明:《緊急狀態法律制度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年版,第21 頁。類似觀點,參見于安:《國家應急制度的現代化:緊急狀態立法的背景》,載《法學》2004 年第8 期,第3-5 頁;徐高、莫紀宏:《外國緊急狀態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5 頁。狹義說認為,緊急狀態制度是與戰爭、戒嚴等相并列的一種法律制度,因為“過于寬泛的緊急狀態概念可能會使緊急狀態法制成為一種亞法制甚至偽法制”,這“構成對緊急狀態法制精神的反動”。〔7〕肖金明、張宇飛:《另一類法制:緊急狀態法制》,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3 期,第136 頁。
上述理論分歧源于我國應急立法的“碎片化”現象,〔8〕我國現行《憲法》以地域范圍為原則規定了緊急狀態制度,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國務院“依照法律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范圍內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2004 年修改后的《憲法》以緊急狀態取代了戒嚴,但因并沒有據此制定“緊急狀態法”,而已經缺失憲法依據的《戒嚴法》仍然有效。同時,在“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中,使用了“緊急狀態”概念的現行有效立法共68 部。除《憲法》外,僅12 部中央立法,以及《廣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規定》所使用的“緊急狀態”概念符合《憲法》的規范要求,其他54 部地方立法所使用的皆非憲法意義上的“緊急狀態”概念,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緊急狀態概念的混亂,以及立法的“碎片化”現象。各有其合理性和不足之處。筆者認為,應對上述廣義說和狹義說進行修正,“以緊急狀態法為重心整體重構我國的應急法制體系”,以明確界定“緊急狀態”的法律概念與制度邊界。〔9〕參見劉小冰:《以“緊急狀態法”為重心的中國應急法制體系的整體重構》,載《行政法學研究》2021 年第2期,第34-35 頁。我國憲法和法律將“緊急狀態”“戰爭”“動員”等規定為相互獨立的法律制度,因而狹義說更能得到實定法的支持;而廣義說則有效解釋了緊急狀態、戒嚴、突發事件應對這三者之間在現實、理論和制度上的相通性,即三者都只是國家緊急權力的不同表現形式。因此,“緊急狀態”不應包含“戰爭”“動員”,但應包含“突發事件應對”“戒嚴”的制度內容。這一修正既能避免廣義說與現行法律規定的形式沖突,又能避免狹義說無法將除戰爭、動員以外的所有重大突發事件納入《緊急狀態法》調整范圍的困境,從而保證“緊急狀態”概念符合現行《憲法》的規定、滿足現實需要。從學術角度看,這是一種可取的折中說。
(二)權利克減是緊急狀態下增加適用的特別法律限制
在正常狀態下,國家依法適用一般法律限制即能維持社會秩序。在我國,相關《憲法》表述是第51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有學者認為,這一規定“能被作為權利限制制度依據的間接規定”,〔10〕方樂坤:《論精神安寧權的克減——兼及警察權的行使限度》,載《西部法學評論》2017 年第3 期,第60 頁。國家可據此“克減自身對公民基本權利進行保障的義務”。〔11〕劉長秋、趙之奕:《論緊急狀態下公民健康權的克減及其限度》,載《法律適用》2020 年第9 期,第33 頁。其實,該憲法規范是對公民權利概括性的一般法律限制,如將其解讀為權利克減條款,則其限制范圍將包括不得克減權利在內的所有權利,這一結論“既不符合我國憲法保護人權的精神,也與克減條款的宗旨相違背”。〔12〕王禎軍:《克減條款與我國緊急狀態法制之完善》,載《當代法學》2011 年第1 期,第129 頁。為恢復正常秩序,緊急狀態必須適用權利克減這一特別法律限制。那么,一般法律限制和權利克減具有什么樣的法律關系呢?
1.只有一般法律限制失靈導致社會嚴重失序進而進入緊急狀態,才能適用權利克減。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關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各項限制條款和可克減條款的錫拉庫薩原則”(以下簡稱“錫拉庫薩原則”)明確指出:“如果根據公約特定限制條款采取普通措施便足以應付對國家生命的威脅,則不應采取緊急情況所嚴格需要的措施。”〔13〕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of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nex, UN Doc E/CN.4/1984/4 (1984).也就是說,在應對突發事件中,根本不存在以一般法律限制維護社會秩序的可能性,才能適用權利克減。反之,適用權利克減這一特別法律限制,則表明國家已經進入緊急狀態。
2.可根據不同的調整對象同時適用。無論在正常時期還是在非常時期,一般法律限制都可永久適用。進入緊急狀態后,國家必須實行權利克減,以確保實施機關擁有足夠的權力以應對突發事件。但在緊急狀態下,并非只有權利克減才能發揮作用,權利克減與一般法律限制實際上分別作用于不同的場域。權利克減作用于影響緊急狀態措施的特別事項,其目的在于恢復社會秩序;一般法律限制則作用于沒有涉及緊急狀態措施的一般事項,其目的在于維持社會秩序。權利克減勢必波及一般法律限制,如2021 年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增加規定了“行政機關對違反突發事件應對措施的行為,依法快速、從重處罰”,這實際上是權利克減的配合措施,而非權利克減措施。整體而言,權利克減是“增加”適用的法律工具,并與一般法律限制共同形成應對突發事件的合力。
3.作用的程度有所不同。特別法律限制之所以“特別”,主要表現在權利克減將影響權力與權利、權利與權利、權力與權力之間的比例關系。(1)權利克減需要實現緊急權力效益在法律范圍內的最大化,并為其行使提供正當性和合法性證明,國家將形成秩序與自由在主從意義上的二元結構。(2)權利克減將導致權利與權利之間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既定邏輯關系被改變,國家將重新排定權利的序列和位階。〔14〕緊急狀態下的權利與權力、權力與權力之間法律關系的變化獲得較多學術關注。其實,緊急狀態之下的權利相互之間的法律關系也會發生變化。據統計,國外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私權利主體對權利的侵犯大幅增加,家庭暴力增加約30%,這在私人建筑的禁閉環境中尤為明顯。(See Audrey Lebret, COVID-19 Pandemic and Derogation to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1–15 ,doi:10.1093/jlb/lsaa015, Advance Access Publication 4 May 2020.)現在,我國學界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對權利克減的研究正逐漸向健康權、監護權等私權領域擴展。(參見張夢蝶:《論緊急狀態下的國家監護制度》,載《行政法學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164 頁。)(3)權利克減將導致行政權急劇擴張,被授權的行政機關有權進行緊急立法,對違反緊急立法的行為設定行政拘留、行政處罰等法律措施;執法機關的執法程序和行政機關制定緊急立法的程序相應簡化;在緊急狀態期間,行政機關可在強力部門配合下依法采取隔離、宵禁等措施。同時,立法權的克制與司法權的謙抑共同構成對行政緊急權力的兩大支持系統,特殊情況下將導致軍事力量介入民事生活。
4.在規制對象和手段出現競合時,因《緊急狀態法》的優先適用而帶來權利克減的優先適用。例如,《防洪法》等法律的具體規范包含了導致緊急狀態的基本要素,因洪水引起的社會安全事件同時是《防洪法》和《緊急狀態法》的規制對象。再如,因洪水引起社會安全事件而進入緊急狀態,在對違法行為實施行政處罰時,會出現《緊急狀態法》與《行政處罰法》在規制手段上的競合。這時,需要遵循“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后法優于前法”的法律沖突規則確認《緊急狀態法》的優先適用,由此也帶來權利克減的優先適用。只有當《緊急狀態法》沒有規定或其后制定的其他應急立法有特別規定時,才能導致《防洪法》《行政處罰法》等普通法律及其一般法律限制的適用。〔15〕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即新的一般法與舊的特別法發生沖突,如《突發事件應對法》和《傳染病防治法》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的規定上存在矛盾。此時,各國解決的辦法主要有“新的一般法優于舊的特別法”“新的一般法不變更舊的特別法”、立法裁決等。有學者指出,依據《立法法》,我國的解決辦法為立法裁決,為此我國“急需出臺立法裁決的程序性規定”。(參見王鍇、司楠楠:《新的一般法與舊的特別法的沖突及其解決——以〈突發事件應對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為例》,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第10 頁。)筆者認為,在缺失立法裁決的程序性規定且有權機關放棄立法裁決的情況下,執法和司法中可適用“新的一般法優于舊的特別法”的法律適用規則。
二、權利克減的正當化:回應對緊急權力的意義期待
緊急狀態的本質就是增加政府緊急權力、依法克減公民權利。因此,權利克減乃是緊急狀態的制度核心,其基本作用在于回應對緊急權力的意義期待。
(一)滿足規制型社會對法律發展的基本要求
我國正處于“速度型發展模式向規制型發展模式”〔16〕薛瀾、陳玲:《制度慣性與政策扭曲——實踐科學發展觀面臨的制度轉軌挑戰》,載《中國行政管理》2010 年第8 期,第7 頁。的轉型中,而規制型發展模式乃是因為存在著具有內生性、泛在性、系統性等特征的風險、危險所致。按照我國學者張寶的分析,風險和危險僅具有相對的界限,隨著科技發展,某些風險造成損害的蓋然性逐漸顯著,從而使得風險往往轉化為具體明確的危險。突發事件往往是“復合危機”,〔17〕祝哲、彭宗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挑戰和對策》,載《東南學術》2020 年第2 期,第12 頁。因而其應對也必然是“復合應對”。從這一角度看,現實中還存在已經發生或必然發生的,對公民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或者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的“嚴重危險”。因此,如將損害發生的蓋然性程度視為一個漸變頻譜,由淺到深分別代表著損害發生的可能性高低。法律在進行綜合應對時,必須在代表損害發生的蓋然性較高的深色頻譜一端劃出一道風險與危險、危險與嚴重危險的分界線,在另一端劃出一道風險與剩余風險的分界線。行政管理適用于“剩余風險”,現行《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的應急狀態適用于“風險”,緊急狀態適用于“危險”,而戰爭狀態則適用于“嚴重危險”,而這些應對措施都必須建立在應急法治的基礎之上(見圖1)。〔18〕參見張寶:《從危害防止到風險預防:環境治理的風險轉身與制度調適》,載《法學論壇》2020 年第1 期,第25 頁。圖1 乃是筆者在其研究基礎上的改造,特此致謝。

圖1 剩余風險、風險、危險、嚴重危險的界分與法律應對
我國憲法對上述風險的應對作了原則性規定,并為此制定了《突發事件應對法》《國防動員法》等管理型立法,為應對“剩余風險”“風險”和“嚴重危險”提供了形式法律依據。但在應對“危險”時,憲法所確立的緊急狀態制度并沒有具體立法,導致緊急狀態的憲法制度落空,也導致權利克減缺失法律依據。而緊急狀態下任何一項緊急權力的產生都是以克減公民權利為前提的,因而在立法上確認權利克減制度是滿足規制型社會對法律發展的現實需要,其在客觀關系系統中具有正當性。
(二)依法防范化解權利克減的法律風險
由于權利克減在防范自由所遭遇的個別危險的過程中“也在整體上削弱了社會秩序的自由品質”,〔19〕[德]迪特兒·格林:《憲法視野下的預防問題》,載劉剛編譯:《風險規制:德國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4 頁。因而實為一種具有高度法律風險的國家行為,這就需要通過“憲法—法律—法規—規章”的制度關系系統加以防范。自“緊急狀態”載入我國憲法以來,雖然我國沒有制定《緊急狀態法》,沒有正式啟動過緊急狀態,沒有引入“權利克減”概念,但相關應急立法及其實踐規定了類似于權利克減的措施(或稱“類權利克減”),這為研究緊急狀態下的權利克減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我國,使用了符合憲法規范意義上的“緊急狀態”概念的13 部現行立法中,“類權利克減”主要有三種模式:(1)概括限制模式,即對權利限制不作規定或僅作原則規定。例如,《戒嚴法》第4 條規定,國家可以“在戒嚴地區內,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作出特別規定”。雖然該法第13 條對戒嚴實施機關采取的措施作了禁止或者限制集會、游行、示威等列舉式規定,但“禁止任何反對戒嚴的活動”這一兜底規定賦予戒嚴實施機關過于龐大的自由裁量權。(2)概括限制加比例模式。如《國家安全法》第65 條規定,國家決定進入緊急狀態后,“有權采取限制公民和組織權利、增加公民和組織義務的特別措施”。這一規定與《戒嚴法》基本一致,體現了對概括限制模式的偏愛。但該法第83 條的規定體現了比例原則的部分要求,即“在國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特別措施時,應當依法進行,并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為限度”。在概括限制模式中加入了適度的比例原則,這是一種立法進步。(3)個別限制模式,即明確規定具體限制的權利內容。如《行政訴訟法》第13 條規定,法院不受理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提起的訴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2 條則規定,所謂“國家行為”包括“經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宣布緊急狀態等行為”。這實際上是對緊急狀態下行政訴訟權利的一種明文限制,從而排除了對緊急狀態的行政訴訟監督。同時,在應對突發事件的實踐中,我國的許多緊急措施已經構成事實上的權利克減。〔20〕同前注〔2〕,李衛海書,第65 頁。由于我國沒有確認權利克減概念,因此,我們雖然能夠理解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政府所采取的許多緊急措施的正當性,但正當性并不必然帶來合法性,因而通過所謂的“小區立法”〔21〕“小區立法”乃是對各物業公司或村民小組等類組織針對出入其小區或自然村所作的缺乏法律依據、有悖法治精神的各種限制性或禁止性規定的形象說法。等形式推行的剛性管制等“類權利克減”“可能會導致在實踐中公權力過大,對公民權利造成威脅”。〔22〕陳聰、周運祥:《緊急狀態下人權克減的價值取向研究》,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 年第6 期,第8 頁。就其理性要求而言,由于缺乏不得克減權利這一底線要求,且相稱性原則的規定不全面,上述“特別規定”“特別措施”等“類權利克減”,以及“事實上的權利克減”無法應對因社會結構性緊張而產生的大量社會矛盾和風險,也容易導致權利克減缺乏必要的法治限度,這些都足以證明實現權利克減法治化以防止其嚴重脫序的重要性。
各國實施緊急狀態的實踐為分析權利克減的法律風險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實證樣本。這些法律風險主要表現在:(1)“秩序優先”常態化的法律風險。權利克減表明,法律將秩序優先作為價值取向,這有其必要性。但從緊急狀態的歷史發展來看,欠缺相稱性原則的強制約束也會導致權力主體特別喜歡將其作為常態化的國家治理工具。(2)缺乏底線原則的法律風險。緊急狀態下,權利保障的關鍵判斷標準在于不得克減權利能否得到切實保障,〔23〕參見張志銘:《如何保障權利:操作層面上的一般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54 頁。這是概括限制模式最大的風險,也是構建權利克減制度的核心要素。(3)缺乏法律依據的法律風險。權利克減乃是對權利施加的特別法律限制,但在事實上,權利克減或“事實上的權利克減”缺乏法律依據或法律依據不足,所依據的法律相互沖突的情況等多有發生。(4)自由裁量權失去控制的法律風險。為應對突發事件,既需要在立法上給予執行機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又需要對其進行適度的控制,否則,再良善的緊急狀態立法也無法達致良善的治理效果。從各國緊急狀態的實踐來看,自由裁量權失去控制的法律風險,始終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三、權利如何克減:確立權利克減的基本原則
“緊急狀態法律制度是一個相對現代的發展,起源于法國大革命,到20 世紀中葉在大多數國家法律制度中都占有一席之地。”〔24〕Sheeran, Scott P., Reconceptualizing States of Emergency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ory, Legal Doctrine, and Politics, 34, 3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p. 496.各國以及國際公約的緊急狀態及其權利克減的制度形態并非完全相同,因此,為防范、化解權利克減的法律風險,我國需要借鑒域外相關經驗,結合具體國情,在《緊急狀態法》中明確規定權利克減的基本原則。
(一)相稱性原則
相稱性原則是權利克減的基礎原則,包含適當性、必需性和最小限制性等構成要素,其核心內容是行為的性質、強度或手段的選擇問題。〔25〕參見溫樹英:《歐共體法中的相稱性原則》,載《政法論壇》2004 年第3 期,第178 頁。相稱性原則在權利克減中的具體要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只要存在突發事件,就必須依法進入緊急狀態并進行權利克減。此類突發事件主要包括政治安全事件、社會安全事件、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生態環境事件、事故災難等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事件及由此引發的嚴重次生事件和衍生事件。判斷是否存在導致緊急狀態的突發事件,及如何實施權利克減,原本全部屬于國家主權行為,但現已發生了某些變化,如ICCPR 規定締約國負有通知義務,“錫拉庫薩原則”則直接要求“確定克減措施是否為緊急情況所嚴格需要時,不應將國家當局的判斷視為決定性判斷而予以接受”。歐洲人權委員會還確立了評估是否存在導致緊急狀態的公共緊急情況的原則:應是現實的或迫在眉睫的;整個國家深受其影響;社會有組織生活的延續受到威脅;危機或危險應該是“例外的”,即維護公共安全、健康和秩序的正常措施或限制明顯不足以應對危機或危險。〔26〕同前注〔1〕,Sanja Jovi?i? 文,第545–560 頁。這表明,判斷是否存在突發事件,及如何實施權利克減已經由主權國家的單一行為進入國際社會可以對其進行適度介入的新階段。
2.只有那些與實施緊急狀態具有強烈對抗性的權利才能被克減。在緊急狀態下,既需要防止干預不足,更需要防止干預過度,必須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27〕David B. Resnik, Proportionality in Public Health Regulation: The Case of Dietary Supplement[J]. Food Ethics, 2018, 2(1):1–16.因此,被克減的權利必須是非歧視性的。權利克減“牽涉到一系列基本的倫理價值判斷”,〔28〕張新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相稱性原則”探討》,載《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1 期,第2 頁。因而不應基于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語言、國籍或者社會地位的不同進行克減,否則,就會違反國際法上的“非歧視”要求。同時,被克減的權利并非僅僅是“基本權利”或“法定權利”。有學者指出:“克減權是一項能夠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造成直接影響的緊急權。”〔29〕同前注〔12〕,王禎軍文,第126 頁。這一觀點整體上是正確的,但不能將“基本權利”理解為我國《憲法》第2 章所規定的“基本權利”,因為權利克減既針對“基本權利”和“法定權利”,也針對“非基本權利”和“非法定權利”。為了追求法律與秩序,法律必定克減與這一目標相反的權利。例如,《戒嚴法》規定,可在戒嚴地區“禁止罷工、罷市、罷課”。此類在我國現行法律上的“非基本權利”和“非法定權利”之所以被“禁止”或克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與緊急狀態的實施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否則,權利克減既無必要,也不正當。
3.權利克減程度必須與緊急情況嚴格相稱。在緊急狀態下,權利克減應當與突發事件造成的社會危害的性質、程度、范圍和階段相適應;有多種應對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對當事人權益損害最小的應對措施;對公民權利與自由的限制,不得超出控制和消除突發事件造成的危害所必需的限度。
(二)不得克減原則
有權利克減,就會有權利的不得克減。權利克減是對權利的特別限制,不得克減則是對權利克減的反限制,是權利克減的底線原則,其基本特性主要有:(1)從范圍上說是最低程度的權利保障,這些權利是其他權利的前提和基礎,是為最低限度地維護自然生命所必需的權利(如生命權),為最低限度地維護法律生命所必需的權利(如平等權);(2)從影響上說是影響最小的權利,因此,如姓名權等對緊急狀態措施基本沒有實質性影響的權利同樣是不得克減的權利;(3)從本質上說是最后的權利,按照“錫拉庫薩原則”的要求,這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即使聲稱維護國家的生命之目的也不得克減”;(4)從依據上說須得到法律的事先規定,這是相關國際公約的普遍要求。
當然,要在法律上明確列出一張不得克減的權利清單非常困難。首先,權利本身的性質非常復雜。權利的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長期處于糾結之中,〔30〕See Douglas Lee Donoho, Relativism Versus Universalism in Human Rights: The Search for Meaningful Standards,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7, 1991), p. 388-389.其內容本身也糾纏在一起。幾乎所有的法定權利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復合權利,“既是一種防御他人不法侵害的消極權利,也是一種請求國家提供幫助的積極權利”。〔31〕陳云良:《健康權的規范構造》,載《中國法學》2019 年第5 期,第69 頁。例如,克減人身自由也往往意味著同時克減教育權,這使權利克減和不得克減的權利清單都難以擁有公認的法理基礎。其次,權利公約的表現形式、實施主體非常復雜。在表現形式上,既有ICCPR 等國際公約的規定,又有《歐洲人權公約》等區域性公約的規定;既有國際法協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規定,又有各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實施主體上,國際公約關于國家義務的實施機制偏向于主權國家,僅要求各國采取必要措施以實現公約的預期結果,導致難以確定衡量權利遵守情況的統一標準。再次,權利,尤其是不得克減權利的內容不統一,甚至相互沖突。例如,ICCPR 規定,不得克減的權利主要有生命權等7 項;《歐洲人權公約》僅承認生命權,免受酷刑或殘忍的、不人道的待遇的權利,免受奴役的自由,以及不受有追溯力法律約束的權利是不得克減的權利;《美洲人權公約》和國際法協會通過的《緊急狀態中人權規范巴黎最低原則》各有12 項和16 項之多。各國雖大多遵循了國際公約關于不得克減的權利的規定,但規定和保留的內容各不相同。最后,因文化、歷史、制度和觀念的差異,社會各界對權利及其克減的理解各不相同,這使權利克減難以擁有共同的法律標準。
但上述情況不應成為拒絕在理論上提出一張我國應堅持的、在緊急狀態下不得克減的權利清單的理由。如上所述,各國法律,以及國際公約的權利規定不統一,甚至相互沖突,權利克減的國際監督與國家主權之間也一直存在緊張關系。對此,國際社會解決的方法主要有三種:(1)依靠本國憲法或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由各國賦予具體的權利內容;(2)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的判斷和經驗,確定絕對的最低限度權利;(3)繼續推進聯合國制定關于酷刑、種族滅絕、兒童和難民等“單一問題”公約的進程,以集中精力制定那些受文化和政治變化影響最不嚴重的最低權利要求。〔32〕同前注〔30〕,Douglas Lee Donoho 文,第388-389 頁。因此,一方面,我國應負責任地積極參與制定國際和區域人權公約,以在一般和靈活的抽象基礎之上達成對權利克減的國際共識;另一方面,我國《緊急狀態法》應明確將生命權、平等權、人格尊嚴權、公正審判權、不受虐待或酷刑的權利、不受奴役或者苦役的自由等規定為不得克減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人類社會所公認的資格性權利,〔33〕參見李步云主編:《憲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479 頁。其重要性具有“不證自明”的公理性質,且符合國際公約和區域公約的共同約定;同時,這些權利也特別容易受到緊急狀態措施的侵犯,需要法律的特別保護。在此基礎上,應在《緊急狀態法》上設立兜底條款,明確規定與緊急狀態實施不具有強烈對抗性,或法律未予承認,或僅在較小范圍內予以承認的其他權利并非必然屬于克減的權利。
需要注意的是,國際公約和各國法律對上述權利的概念表述并非是一致的。例如,大多數國家憲法表述為“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個別國家則表述為“生存權”(Survival Rights)。實際上,這是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權利。考慮到“生命權”已經開始成為我國的法定人權,〔34〕《民法典》第1002 條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權。”雖然這一規范從表述形式到內容更應該歸屬于憲法調整的范圍,但既有規定至少表明我國已經開始了生命權作為法定人權的進程。因而我國《緊急狀態法》將“生命權”規定為不得克減的權利時應該更為準確和規范。同時,上述權利也并非是絕對的。例如,在緊急狀態下,生命權雖然屬于不得克減的權利,但“死刑和合法戰爭導致的死亡除外”,這符合ICCPR 等國際公約的明文規定。
(三)合法性原則
權利克減是對部分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暫停適用,是一般法律限制的例外。但任何例外都面臨兩難局面:憲法的最高性不容侵犯,而緊急狀態下憲法和法律的部分規定也必須被克減。〔35〕See Beaud O., Anything Goes: How Does French Law Deal with the State of Emergency, Edited by Auriel P., Beaud O.,Wellman C., The Rule of Crisis: Terrorism, Emergency Legi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Springer, 2018, pp. 229-240.正是因為這種“內在矛盾的悖論組合”,〔36〕孟濤:《緊急權力法及其理論的演變》,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1 期,第108 頁。緊急狀態的合憲性問題才一直存在爭論。國外學術界對緊急狀態素有保守主義(合憲性)和自由主義(超憲性)之爭,〔37〕See Sotirios Barber, On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9.我國法學界對此也有不同看法。超憲性觀點認為,“憲法的最高性并不是絕對的”,“當嚴峻的社會現實需要采取超越憲法的措施時,憲法必須讓步”。〔38〕郭春明:《論緊急狀態下的憲法效力》,載《法學》2003 年第8 期,第39 頁。合憲性觀點則主張,當國家處于緊急狀態時可以對憲法權利進行限制,但“任何形式的限制都應在合理的限度內進行, 在客觀上保持個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平衡”。〔39〕韓大元:《論緊急狀態下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與保障》,載《學習與探索》2005 年第4 期,第80 頁。因此,用成文憲法規范緊急權力“已經成為看似矛盾但又必須實現的‘合法性’問題”。〔40〕方旭:《緊急狀態與社會治理——緊急權力理論基礎述評》,載《北京社會科學》2015 年第3 期,第122 頁。其實,政府權力受憲法和法律支配的假設,與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事件需要廣泛運用自由裁量權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系,〔41〕參見楊海坤:《非典,讓我們正視行政緊急權力》,載《法制日報》2003 年5 月8 日,第6 版。但這種緊張關系并非是不可調和的。只要憲法和法律在授權與監督之間能為緊急狀態提供合理的制度張力,那就能夠實現緊急狀態與法治之間的統一性或者達成統一的可能性。因此,我國既需要廢除《戒嚴法》,將其相關內容納入《緊急狀態法》,以建立統一的緊急狀態制度,也需要通過《緊急狀態法》建立統一的權利克減制度,以實現一般法律限制與權利克減的銜接。
同時,權利克減也不得與我國根據國際法所承擔的法定義務相抵觸,這是ICCPR 對各締約國的明確要求。由于我國僅僅簽署而沒有批準ICCPR,因而現在需要明確回答下列問題:(1)我國在現階段是否應遵守ICCPR?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于已簽署但尚未批準條約的國家,“有義務不做將破壞該條約目的和宗旨的行為”。因此,我國整體上應遵守ICCPR 關于權利克減的規定。(2)批準ICCPR 時,我國是否對相關條款予以保留?有學者認為,權利克減條款與我國現行的人權保護制度不存在價值沖突,“在未來批準《公約》時,我國政府不需要對緊急狀態條款做出保留”。〔42〕王禎軍:《論緊急狀態法制中的不可克減原則》,載《河北法學》2012 年第9 期,第40 頁。筆者對其結論不敢茍同。我國之所以至今沒有批準ICCPR,就是因為與其在權利表述及內涵、實施程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前者如生命權、思想和良心自由等,我國憲法皆沒有規定或表述不同,且死刑的法律規定短時間內難以達到公約的要求;后者如ICCPR 要求宣布緊急狀態“應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得立法機構的確認”,就我國《憲法》目前的規定而言,國務院宣布的“緊急狀態”并無須得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確認”。〔43〕《戒嚴法》第3 條規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與《憲法》的明文規定不同,《戒嚴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戒嚴決定增加規定了“由國務院提請”的程序限制。因此,我國未來批準該公約時應在盡可能遵守公約規定的前提下對其個別內容,如生命權等予以保留。〔44〕美國對生命權等也作出了保留:“按照現行的美國法律,有權對任何人判處死刑。”(3)ICCPR 規定的“其他義務”是什么?一般來說,這是指《聯合國憲章》《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公約》《反酷刑公約》等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法中規定的“不得從事戰爭”等的國家義務。
(四)裁量性原則
無論何種法律體系,其權利克減的法律規定大多呈現為三元結構:立法為緊急狀態及其權利克減提供較為寬泛的“工具框”;權利克減的相稱性原則、不得克減原則、合法性原則可以被視為在已制定的法律規則基礎上的授權選擇,〔45〕See Evan J. Criddle,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during Emergencies: Delegation, Derogation, and Deference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45, DOI 10.1007/978-94-6265-060-2_8, p. 203.其所提供的實為權利克減的“工具箱”;而裁量性原則下的權利克減則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工具箱中的工具”。
裁量性原則是《歐洲人權公約》通過司法實踐確立起來的一種具體司法工具,并非為ICCPR 所明確承認。《歐洲人權公約》賦予各國減損某些公約義務的權力,并為處理危機的國家提供了一定靈活性的選擇。通過“Lawless 訴愛爾蘭案”(1961 年)等,歐洲人權法院發展出了一種被稱為“裁量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46〕滕宏慶:《論人權克減及其監督機制》,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8 年第2 期,第22 頁。或“克減原則的彈性”(the Resilience of Derogation Standards)〔47〕同前注〔45〕,Evan J. Criddle 文,第203 頁。的解釋技術,其要義是締約國無須等待災難發生后再采取措施處理,而是在各國就某些事務尚未達成共同原則,又有一定共識前,容許各國保留某些程度的自由裁量余地;〔48〕同前注〔30〕,Douglas Lee Donoho 文,第388-389 頁。其考量因素主要有:所爭議人權內容在成員國之間的法律或實務是否存在共識;所保護的人權性質及其輕重;人權公約條文的具體規定。〔49〕關于裁量性標準的概念、發展、擴充適用及其司法過程,參見王玉葉:《歐洲人權法院審理原則——國家裁量余地原則》,載《歐美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485-511 頁。
與歐洲“司法自我克制”〔50〕Dominic Mcgoldric, A Defence of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and An Argument for Its Application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CLQ vol 65, January 2016, pp. 21–60, doi:10.1017/S0020589315000457.的裁量性原則不同,我國權利克減中的裁量性原則應該是一種“行政自我克制”。一方面,雖然各公約都非常重視緊急狀態下的司法保障權利,認為不管是明示還是暗示剝奪這些權利“都是與國家所承擔的公約義務不相符的”,〔51〕Habeas Corpus in Emergency Situations(Arts. 27(2), 25(1)and 7(6),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8/87 of January 30, 1987, Series A, No. 8, p. 36.但由于體制差異,也由于《行政訴訟法》第13 條的明文規定,我國司法權尚無法發揮“裁決緊急狀態的有效性”〔52〕同前注〔36〕,孟濤文,第118 頁。等權力監督和權利救濟的作用,且難以介入單一制體制下的相關緊急權力糾紛之中。另一方面,作為主要的執行機關,我國行政機關應對突發事件中的緊急權力必須得到保障和制約。因此,我國裁量性原則的目的主要是為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幅度內提供實體和程序相統一的更為方便和具體的解釋和操作規程。
例如,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國大多采取權利克減或限制人身自由和教育權等措施,但在實際操作中,克減人身自由可供選擇的裁量工具有:限制公共集會、公共活動、會議,關閉博物館、劇院和電影院,取消演出和會議,暫停國際客運航班,聚餐限制,建立對進入國境者實行隔離檢疫的特別規則,對公民的流動采取禁止和特別管理措施,對居民區實行隔離、宵禁等。克減教育權可供選擇的裁量工具有:暫停各級各類教育的正常教學程序,在家遠程學習,封閉校園,延期開學,進校隔離或檢測等。由此可見,在具體的克減項下,其更為具體的裁量性措施是多元的、可供選擇的。
因此,緊急狀態既需要確立相稱性原則、不得克減原則、合法性原則以劃定權利克減的制度范圍,也需要確立裁量性原則以提供具體的權利克減工具。當然,對裁量性原則的確切幅度很難提前確定,〔53〕See Ronald St. John McDonald,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of Its Codific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Ago 187, 207 (A. Giuffré ed. 1987).但可以確定的是: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延長緊急狀態期限的決定,以及緊急狀態的執行決定皆可根據突發事件的具體原因及程度,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自由裁量具體克減的權利;實施機關不是非得全程使用全部的權利克減工具,而應根據相應的時間、地點、對象等進行理性的務實判斷和動態的行為選擇,并不斷評估權利克減的嚴格必要性,根據局勢的逐步改善或惡化而減少或加大侵入性措施;應特別注意運用權利克減工具,以控制突發事件并避免可能誘發的次生或衍生事件;裁量性原則不得侵犯不得克減的權利并須符合比例原則。〔54〕韋偉強認為,需要用比例原則來規制緊急行政權。梅揚則認為比例原則更適用于常態意義下的行政權力行使,在緊急狀態中的適用應當受到一定限制。(參見韋偉強:《比例原則——政府應急管理特權的規制》,載《社會科學家》2006 年第6 期,第52 頁;梅揚:《比例原則的適用范圍與限度》,載《法學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57 頁。)筆者認為,后者的觀點難以成立,恰恰相反,比例原則在緊急狀態中的規定和適用更能體現對緊急權力的授權和監督。同時,為了“使模糊的立法原則明確化,使寬泛的裁量權范圍具體化”,〔55〕周佑勇:《行政裁量基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 頁。“裁量基準即使應該公布,但此一公布并不構成行政規則之成立或生效要件。”(周佑勇、周樂軍:《論裁量基準效力的相對性及其選擇適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9頁。)裁量基準對外實質性影響了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因而上述觀點既與法治原理的核心要求相悖,也已被我國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第34 條關于“行政處罰裁量基準應當向社會公布”的規定所否定。可在《緊急狀態法》中引入裁量基準,明確規定“實施機關可以依法制定緊急狀態措施裁量基準,并向社會公布”。
四、結語:我國的權利克減最終是個憲法和立法問題
緊急狀態下,國家面臨的主要社會、政治和法律挑戰乃是國家是否擁有有效應對 “剩余風險”“風險”“危險”“嚴重風險”的能力,同時應保證所采取的措施不會違反民主、法治和人權的價值觀。〔56〕同前注〔3〕,Abdulla Azizi 文,第30 頁。從這一角度看,權利克減制度應歸屬于憲法范疇,因為只有憲法才能實現這三者的高度統一,并保證權利克減和不得克減規定的最高性。由于我國實行憲法間接保障主義,因而需要依據《憲法》制定《緊急狀態法》。當然,更為理想的立法模式是實現緊急狀態立法“從法律化到法典化”的跨越,即將《緊急狀態法》的制定視為一個“法典化”過程,將《突發事件應對法》《戒嚴法》,以及其他應急立法中含有緊急狀態要素的立法規定納入其結構體系化和功能體系化之中予以綜合考量。〔57〕李曉安則主張以“專門法”形式構建“國家緊急權力”的規約體系以滿足法治的邏輯需求。(參見李曉安:《“國家緊急權力”規范約束的法治邏輯》,載《法學》2020 年第9 期,第64 頁。)這一觀點富有想象力,但筆者認為,通過“緊急狀態法的法典化”以重構我國的應急法制體系更具有現實可能性。但無論何種立法模式,我國皆須引入權利克減的概念,并構建起以相稱性原則為基礎、以不得克減原則為底線、以合法性原則為范圍、以裁量性原則為操作規程的綜合模式,為權利克減提供明確而有效的法律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