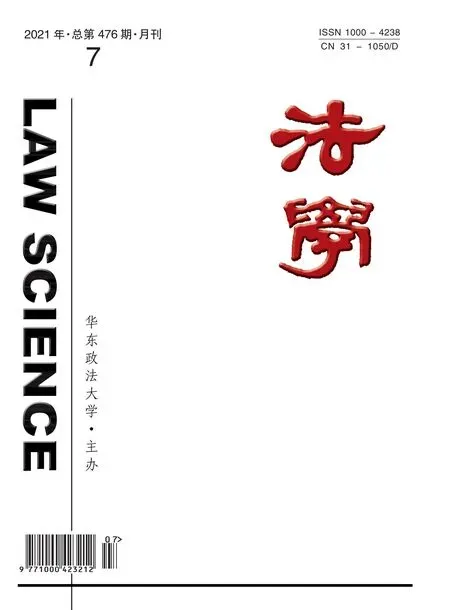過失領域被害人風險同意的刑法意義
●王煥婷
引言
2006 年我國學者將德國“在不法理論中重新發現被害人”發展出的,一定的被害人行為能夠阻卻行為不法之依據的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引入我國。〔1〕參見馮軍:《刑法中的自我答責》,載《中外法學》2006 年第3 期,第93-103 頁。該原則所應對的事實包括未曾引起我國學界關注的,行為人參與(“教唆”“幫助”)下被害人明知風險仍自己實施風險行為,如受行為人唆使,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撈錢(“跳水撈錢案”),或者同意、要求行為人實施,如明知行為人醉酒后無駕駛能力而仍乘坐其車輛(“乘坐醉酒駕駛車輛案”)、與行為人共同實施風險行為,如行為人多次告知被害人自己有艾滋病,被害人仍與行為人在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下實施性交行為(“艾滋病案”),因而導致行為人并不期待的法益損害結果發生的過失犯類型。此類情形下,雖然被害人亦不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卻在明知有風險時而主動選擇陷于風險,學理上將其稱為被害人風險同意。〔2〕我國學者對此情形的稱謂不盡相同,如張明楷教授將其稱之為危險接受,車浩教授等將其稱之為被害人自陷風險,筆者在博士論文中也使用了此一概念。但實際上被害人自陷風險涉及的事實情形過于豐富而不僅包括正文所列舉的情形,為實現對精準化事實類型規范問題的研究,筆者認為采取與故意領域的被害人同意相關聯的被害人風險同意概念較為妥當。受此影響,我國學者相繼開展對域外相關理論的學習,對被害人風險同意應否、能否,以及如何影響過失行為不法進行了研究,不過因理論主張的差異性而產生了諸多爭議。
這主要表現在:1.從事實層面看,將被害人風險同意類型化為自我危害的參與(前述“或者”之前的情形)和合意的他者危害(“或者”之后)必要性和可行性;2.從價值層面看,統一適用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排除被害人風險同意中行為人行為的不法性成為新見解;適用故意領域中的共犯理論解決過失犯歸責的主張是“優勢”理論;鑒于被害人風險同意與故意領域中的同意均是被害人自主決定權的行使方式,將同意理論延伸至過失領域的風險同意上,是第三種理論見解;〔3〕參見黎宏:《過失犯若干問題探討》,載《法學論壇》2010 年第3 期,第5-14 頁。堅守同意須涉及結果對象的論者〔4〕參見車浩:《過失犯中的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風險》,載《政治與法律》2014 年第5 期,第27-36 頁。則否認該理論的延伸適用;3.從規范層面看,出現死亡結果的被害人風險同意尤其是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亦無行為不法,亦為個別論者所主張。與此相反,我國實務未形成在過失領域中考量被害人風險同意刑法意義的意識,而均從行為人刑法立場以“行為人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過于自信地認為能避免危險的發生”為由認定被害人風險同意下行為人的可罰性。這從實務對“鐘平過失致人死亡案”〔5〕行為人和被害人為能近距離觀賞野鴨,在考察冰面厚度認為可以駕車行駛于冰面上后遂開車載被害人前往對岸,途中因冰面破裂致使車輛沉沒水中,被害人溺水身亡。《鐘平過失致人死亡案》,載北大法寶,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204880.html?match=Exact,2016 年4 月21 日訪問。“逃避結扎跳窗死亡案”〔6〕2005 年6 月,被告人田玉富與其妻康騰青因違法生育而被要求實施結扎手術。為逃避結扎,被告人對工作人員謊稱其妻要到住院部三樓廁所洗澡。隨后其先用手掰開木窗戶,然后用事先準備好的尼龍繩系在其妻胸前,企圖將其妻從廁所窗戶吊下去逃逸,但由于繩子在中途斷裂,致使康騰青從三樓摔下后當場死亡。《田玉富過失致人死亡案》,載北大法寶,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147845.html?match=Exact,2016 年4 月21 日訪問。“周某過失致人死亡案”〔7〕2002 年2 月作為旅店負責人的被告人應被害人的要求,將有火炕的餐廳儲藏室出租給他以便住宿,次日被害人因室內滯留大量一氧化碳而中毒身亡。《周某過失致人死亡案》,載北大法寶,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215877.html?match=Exact,2016 年4 月21 日訪問。及“跳下水撈錢案”的處理可看出。
短短15 年內,我國學界對此命題的探討似已窮盡,應有解決方案亦已基本全面呈現。但既有研究并非盡善盡美,從宏觀層面看,存在的首要問題是相關主張未能得到詳細的闡釋和論證,導致理論的說服力不足,這也為對觀點的評析與采納帶來了挑戰。其次,就微觀問題的討論而言,有關類型區分并未形成真正的學術之爭,區分與否的原因力、標準為何并非不言自明;作為解決被害人風險同意問題的“優勢”理論——共犯,卻成為域外多數學者摒棄的學說,究竟何者為勝?何以被害人踐行自主決定權的不同情形,要以或者不以其對法益損害結果的期待與否決定行為不法?這樣的主張與被害人自我負責又有著何種差異與關聯?緣何封鎖受囑托殺人同意效力的做法能適用于“不意誤犯”之過失情形?這些都是我國理論并未深入甚至鮮未論及但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受限于目前對此命題的研究現狀,深化研究需要借助比較法。其可行性緣于被害人風險同意的刑法意義命題超脫了實體法規定,對其的法理分析能夠跨越國別差異而具有普適性。加之我國既有主張多受域外尤其是德國影響,為能全面呈現相關理論之譜系,追根溯源亦屬必要。因而,為能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尋找足以支撐處理被害人風險同意問題的法理方案,并正確指引實務對相關案件做出公正的裁判,論者嘗試結合對此命題予以全面和詳細論證已達半世紀之久〔8〕從1973 年Roxin 發表《過失犯之規范保護目的》一文,開始探討該主題,至2018 年發文《合意的他者危害——一個沒有終結的討論?》再次聲明其主張,德國理論界及實務界展開了一場未有定論的持久論戰。的德國理論和實務主張,展開敘述。
一、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的區分與融合
(一)普遍的二分法及標準
在被害人風險同意類型的區分上,我國部分學者主張將其分為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中危險接受的法理》,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5 期,第112-131 頁;車浩:《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載《中國法學》2012 年第1 期,第89-105 頁。至于為何區分則鮮少被提及。個別論者亦提出不區分的反對見解。〔10〕參見江溯:《過失犯中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體系性位置——以德國刑法判例為線索的考察》,載《北大法律評論》2013 年第14 卷,第115-142 頁。德國多數論者采納二分法且為此找到了可參照的實體法依據。根據該國《刑法》第216 條規定,受囑托殺人是犯罪;依總論第26 條、第27 條的規定,結合共犯從屬性原理,可認定教唆、幫助自殺不是犯罪。由于立法區別對待兩種情形,學理一向將受囑托的“他殺”視為同意(合意的他者損害),參與他人“自殺”是自我損害的參與。〔11〕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3. Aufl., 2013, Rn. 190.基于在客觀行為結構上的相似性:教唆、幫助之自我損害與自我危害,是被害人自己實施損害/風險行為,同意與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由行為人實施損害/風險行為,將被害人風險同意進一步類型化亦有其必要性。在使區分具可行性面向,我國論者采納了與正犯論相關聯的行為支配概念,這同樣為部分德國論者認可。不過此一主張也受到批判,新的區分標準由此產生。
1.行為/風險支配標準
在區分故意領域中自我損害的參與和同意的準則選取上,德國多適用劃分正犯與共犯的行為支配概念。在風險同意類型的區分上,司法部門沿用了此標準。聯邦最高法院(以下簡稱“BGH”)在“加速試驗案”〔12〕B、H 作為駕駛人,O、S 作為乘車人進行汽車加速試驗,由O 和S 記錄競賽過程。開始前B、H 均將車速降至80km/h,在O 發出信號后,兩車開始競駛。當時速達120km/h 后,競賽仍在進行,當其嘗試以240km/h 的速度超過位于其旁邊的未參與競賽的G的車輛時,由于道路狹窄難以操控車輛,其中一輛車拋錨并翻車,乘車人O 在此事故中不幸身亡,B 身受重傷。BGHSt53, 55ff.判決中明確指出:過失犯情形,自我危害與他者危害的區分取決于對事件流程的支配。其可根據判斷故意犯中的行為支配所適用的客觀標準確定。此即BGH在處理“吉澤拉相約自殺案”〔13〕16 歲的被害人Gisela 與被告相愛,但遭到父母的反對,根據Gisela 的提議,雙方決定一起殉情。在被告人建議并經被害人同意情形下,被告將一根軟管連接在排氣管上,并從汽車的左側窗戶處插進車內,其從外面堵住了左側車門,從右側車門進入車內,坐在了駕駛座上。其又盡可能地關上左側的窗戶。被害人坐在挨著被告的右邊的副駕駛座上,并關上了右側車門,被告啟動了發動機、踩著油門,直至灌入的一氧化碳使其失去意識。二人于次日早晨被發現,但僅被告被救活。BGHSt19,135(139).時提出的,“誰在事實上支配著導致死亡的事件,個案中取決于被害人掌控其命運的方式和方法。當被害人將其托付給行為人,意欲容忍死亡結果時,行為人即有行為支配。相反,盡管有行為人的幫助(實施了殺人之正犯行為),但被害人直至最后仍能支配其命運,亦應認定為自殺。”〔14〕BGHSt19,135(140).不過由于行為支配原本具有的“對實現構成要件行為的故意支配”〔15〕Claus Roxin,Die Streit um die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GA2012,S.659.的內涵難以體現在過失情形,BGH 使用風險支配概念加以替代,并指出:在判定誰擁有風險支配時,直接導致結果出現的風險事件是重要指標。〔16〕BGHSt53, 61.即當行為人直接支配該風險事件時,是合意的他者危害,反之是自我危害。針對以上案件,判決認為由于對事件的支配從超速過程的開始就直接存在于駕駛人處,……其獨自決定汽車速度并掌握方向盤。乘車人不具有親手回避該風險的可能性,而只能忍受被告人B 和H 的駕駛行為后果……〔17〕BGHSt53, 61.風險支配歸于駕駛人。據此,“乘坐醉酒駕駛車輛案”應歸屬于他者危害,“跳水撈錢案”屬自我危害。
亦有論者認為,以上標準很多時候能夠將兩者予以區分,但針對那種從外觀上看由參與者分工協作,共同實施達致目的的風險行為情形,區分就顯得有些困難且產生更多分歧。如對“艾滋病案”的區分,G?ttigen 認為該案中受支配的事件并非性交行為而是由被告所攜帶的HIV 的傳染,這是他者危害。〔18〕G?ttigen, Strafrechtliche Aspekte der Aids-übertragung, GA1989, S. 219.J?ger 卻主張,被告無法控制HIV 的傳染,非他者危害。〔19〕J?ger, Die Lehre von der einverst?ndlichen Fremdgef?hrdung als Grenzproblem zwischen T?ter und Opferverantwortung,Festschrift Schünemann, 2014, S. 423.Grünewald 則認為應以行為人在直接的風險流程中,是否具有事實及規范意義上的優勢地位為準。該案中,由于各方均有參與或徹底終止性交的支配可能性,應將此視為“準共同正犯”〔20〕Grünewald, Selbstgef?hrdung und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GA2012, S. 371.類型的自我危害,張明楷教授亦持相同觀點。而從其對其他類型案件的分類主張來看,由雙方共同實施風險行為情形,均應歸屬于自我危害。
2.對行為/風險支配的否定及標準重塑
除在過失領域適用行為/風險支配難以實現對由行為人和被害人共同支配之情形進行類型的區分說明,因而受到批判外,該標準更是基于以下理由被否定:將與正犯和共犯相捆綁的行為支配運用于過失領域,是在過失犯中區分共犯與正犯,這與作為過失犯基礎的單一正犯體系相矛盾;且過失犯中結果的出現違背所有參與者的意愿,并無參與者對所實現的犯罪構成有支配;〔21〕Claus Roxin, Die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eine Diskussion ohne Ende?GA2018, S. 659.而將直接引發結果的風險與支配理論相結合,更是不妥當的做法。基于此,Roxin 提出新的區分標準——誰創設了直接流出結果的風險。當風險由被害人創設時,如被害人自己注射了致命的海洛因,屬自我危害類型;風險由行為人創設,被害人認知風險而仍予以容忍,如“艾滋病案”,則是合意的他者危害。〔22〕Roxin(Fn. 15), S. 660.
以上標準的共同之處是單純對客觀外在事件進行區分,本身并不包含價值、規范意義上的歸責要素,這樣的主張因此受到批判。針對“艾滋病案”,Murmann 指出,為何能夠將行為人也具有同等支配力的情形,傾向性地認定為自我危害并要其自我負責,該規范結論并不能夠從行為支配標準中推導出來。〔23〕Murmann,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Opfers im Strafrecht, 2005, S. 410.在其看來,事實類型的區分標準也應部分承擔著解決歸責的任務,否則區分毫無意義。基于此,含有“規范性基點”的區分標準被提出。
規范性標準最初由Zaczyk 提出,他將被害人能否基于法律的規定而“信賴”他人經由義務的遵守,以控制損害結果的發生,作為區分的準則。論者認為,若被害人不能信賴,是自我危害,而能否不歸責于行為人,應看其對被害人是否有保護義務。針對“艾滋病案”,教授認為被害人并沒有要行為人遵守義務的信賴存在,且他作為理智的成年人,行為人對于他的這種自我危害也無保護義務。相反,在“乘坐醉酒駕駛車輛案”中,由于被害人可以信賴行為人要么調整駕駛方式要么完全停止駕駛,此時存在一個過失的他者危害。〔24〕Zaczyk, Strafrechtliches Unrecht und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Verletzten,1993, S. 56ff.Zaczyk 的這種基于規范的信賴為標準的主張,因其“倒果為因”而欠缺說服力,也鮮少得到學界認可。畢竟信賴與否,取決于行為人有無回避結果的義務,其不僅不能成為解決行為人有無不法的理由,也無法作為類型區分的標準。
Murmann 提出了規范性分類主張:若沒有被害人的同意,行為人的行為是否仍為刑法所禁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是自我危害,反之則是他者危害。論者據此將“艾滋病案”視為合意的他者危害。從生命和身體完整性法益視角看,患有HIV 的被告與被害人實施性行為,確實違反了注意義務。〔25〕Murmann, Zur Einwilligungsl?sung bei der Einverst?ndlichen Fremdgef?hrdung, Festschrift Puppe, 2011, S. 774f.
(二)不予區分的一元論
域內外部分論者主張區分不可行且無必要的理由首先在于行為支配標準的不妥當性:一是,基于法益受損者的特殊地位,即介入風險之人本身就是法益受到損害的主體。對于一個在其自由領域行事之人和參與者關系的處理,不能遵循對第三人實施共同犯罪的正犯和共犯予以責任分配的規則。〔26〕Manuel Cancio Melliá, Victim Behavior and Offender Liability:A European Perspective,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7,p.526(2004).二者即是前文已提及的,其在過失領域的適用造成與單一正犯的沖突。且從行為人角度看,在風險現實化前,最后的行為并不具有對被害人相關法益的處分性質,這導致對事實的區分成為純粹的偶然事件。〔27〕Otto,Eigenverantwortliche Selbstsch?digung und-gef?hrdung sowie einverst?ndliche Fremdsch?digung und-gef?hrdung,Festschrift Tr?ndle, 1989, S. 170.其次,在故意領域尚不能被一以貫之的行為支配標準,在過失領域的適用,使得直接導致法益侵害的最后行為的支配者成為正犯。對于過失的前行為者,只能將其視為不可罰的過失幫助者,而僅有后行為人受到歸責。該結論〔28〕Puppe, Mitverantwortung des Fahrl?ssigkeitst?ters bei Selbstgef?hrdung des Verletzten, GA2009, S. 492f. Puppe舉出的例子是,根據主管要求打開開關的工人,實施該行為會導致未經處理的廢水流入河中,但這并非是德國《刑法》第324 條所規定的污染環境罪之正犯而僅是幫助犯。并不恰當,畢竟后行為人并不總是正犯。
行為支配標準的被否定及替代性標準的缺失導致區分喪失可行性,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概念因此消弭于論者筆端,取而代之的是“被害人自我危害”〔29〕Puppe, Die Selbstgef?hrdung des Verletzten beim Fahrl?ssigkeitsdelikt, ZIS 2007, S. 247.概念。
二、區分論視角下的歸責路徑及依據
相比于區分與否問題,適用何種標準如何解決被害人風險同意情形中的歸責問題,則更為復雜也最為重要。在此,域內外論者提供了多元、豐富的歸責路徑。
(一)自我危害的參與之歸責依據
對于自我損害的參與不可罰的論證,不管是我國學者還是德國理論和實務的普遍做法是類推適用共犯規定:依據行為支配標準,實施自我損害的被害人具有“正犯”資格,參與者相當于教唆犯或幫助犯。由于被害人行為并不該當犯罪構成,欠缺可罰的主行為,依據共犯從屬性原理,參與者的行為也不具可罰性。在“繩圈案”〔30〕被告人和被害人W 相約自殺,根據約定,雙方挨著柵欄坐下,被告人在他的麻繩的兩端打了兩個繩圈,并將麻繩繞兩圈系在柵欄的橫木上,隨后兩人將繩圈套在各自的脖子上,W 說她數到三時,各自向右拉。當被告感覺脖子被緊緊卡住時,突然產生恐懼隨后用刀將繩圈剪斷并且試圖用手松開卡住W 的繩圈,但并沒有成功,W 死亡。RGSt70, 113.中,判決即據此認為相約自殺的被告人提供繩索、打繩圈,以及將麻繩系在柵欄橫木上的行為,是“幫助”自殺行為因而不具可罰性。
在對自我危害的參與之歸責的說明上,張明楷教授打破故意與過失犯罪的體系壁壘,沿用自我損害的參與的以上歸責路徑而直接認定自我危害的參與者是不可罰的“共犯”。根據論者主張,在“跳水撈錢案”中,由于導致損害結果出現的行為出自被害人本人,該“正犯”行為并未該當構成要件,行為人作為被害人實施自我危害的教唆者,并不具有可罰性。由于論者將“艾滋病案”視為自我危害的參與,該案亦可做無罪處理。
與前述論證模式明顯不同,德國主流理論和實務在過失領域中一貫奉行單一正犯體系,無法將參與者視為共犯。不過在經由和自我損害的參與的對比中,其采取了較為曲折的路線完成對參與者不可罰的論證。此即“共犯論證+‘舉重明輕’”的“當然推論”模式:性質較重的故意自我損害不是犯罪,性質較輕的過失自我危害也不是犯罪;故意的參與自我損害不是犯罪,過失的參與自我危害因此也不是犯罪。〔31〕Claus Roxin/Greco, Strafrecht Allgeneiner Teil, Band I, 5. Aufl., 2020,§11Rn. 107.在“警察手槍案”〔32〕行為人是一名警察,與一位同其關系密切的女性一起驅車旅行。他將上膛的槍放在汽車的儀表板上。該女士在停車時趁其不注意拿起槍并朝自己開槍。實際上,他知道此女士經常(特別是在飲酒之后)突然變得抑郁和憂傷,卻仍把手槍放在儀表板上而不將子彈取出。BGHSt24, 342ff.中,判決即適用這種論證模式排除過失引起他人故意自我損害(自殺)情形中行為人對該結果的負責性。在“海洛因注射器案”〔33〕BGHSt32, 262ff.中,盡管BGH 首次使用了被害人自我負責這樣的概念,但嚴格來說,其得出提供注射器的行為人無罪的結論依舊出自“當然推論模式”,被害人自我負責因而是行為人無不法的結論而非依據。
(二)合意的他者危害之歸責分析
在合意的他者危害歸責問題的說明上,張教授繼續適用共犯理論,將支配了導致法益受損的行為人視為可罰的正犯。實際上,這樣的歸責路徑在德國僅為個別論者所承認。〔34〕Walther, Eigenverantwortlichkeit und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1991, S. 144.該國實務明確將其置于違法性階層的被害人同意體系之下探討,部分學者亦將同意理論運用于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張明楷、車浩、Roxin 對此予以明確反對。后者在否定共犯理論解決方案的同時又提出新見解。
1.同意理論解決合意的他者危害問題
從既有主張來看,對以下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能否將合意的他者危害視為同意來解決。其一是,同意的對象是否僅限于行為;二是,出現重傷、死亡結果之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同意是否有效。
(1)同意之結果對象的非必要性
否定論者認為該當構成要件的不法是由行為與結果共同組成的,因而作為阻卻整體不法的同意,其對象必須包括行為和結果。理由主要在于從“有同意無侵害”所表達的阻卻不法的意義來看,同意本身就有放棄法益保護的特征。且同意作為意志的表達方式,具有“支配性”特征,法秩序允許法益主體以同意的方式處分客體,若同意僅涉及一定的風險情狀,則無此特征呈現,因而并非是法益的放棄。〔35〕Duttge, Erfolgszurechnung und Opferverhaltan, Festschrift Harro Otto, 2007, S. 232.甚有論者主張僅有對行為人創設的風險行為的同意,或許能排除違反義務之行為不法,但不能否定結果不法。〔36〕Hellmann,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und objektive Zurechung, Festschrift Roxin, 2001, S. 277.更為極端的觀點認為,同意的內容僅涉及法益客體之損害,并不包括行為。〔37〕Weigend, über die Begründung der Straflosigkeit bei Einwilligung des Betroffenen, ZStW1986, S. 70.
以上主張在反對論者看來是過度“忠實”但“偏離”了刑法作為法益保護法的理念。將同意“劃地為牢”式地理解為主體有意的放棄法益,其對象要“兼具認識與意志的雙重要素”〔38〕同前注〔4〕,車浩文。,此時同意對于過失領域中獨有的合意的他者危害的價值和意義,自始就被“剝奪”了。而“切割”被害人意志與結果之間的關聯,僅將行為視為同意客體的主張成為同意在過失領域得以發揮的重要理論基礎。〔39〕[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年版,第710 頁。
(2)合意的他者危害下有限封鎖同意的效力
在法無明文規定情形下,我國論者一向主張對重傷、死亡的同意無效,不能據此阻卻行為不法。黎宏教授雖主張可以適用同意理論否定行為人對重傷結果的負責性,但在出現死亡結果情形,亦排除了同意的適用。〔40〕同前注〔3〕,黎宏文。支撐此觀點的主要理由在于刑法的家父主義立場。〔41〕同前注〔9〕,車浩文。為保障公民自身福祉,個人自主決定權并沒有得到立法者的完全肯認而被限制,限制的方式是對第三人參與并實現他人的自我損害身體和生命行為的禁止。在將合意的他者危害亦視為被害人自主決定權之實踐形式前提下,被害人自主決定陷于由行為人支配的風險情境,并因此重傷、死亡的,同樣可依此立場認定自主決定權行使的無效性。既有立場看似合理但仍受到質疑,在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下,重傷、死亡結果的出現具有偶然性,該主張使得規范的適用喪失確定性。于法理層面,是否有可能打破這樣的理念束縛從而使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之行為仍能出罪,我國論者卻不曾提及。相反,德國學者幾十年來,依托該國既有實體法的規定卻為此做出了各種嘗試。雖與我國立法不同,德國刑法規定了同意他人侵害自身法益的正當化效力受第216 條受囑托殺人及第228 條善良風俗(針對故意的身體傷害)條款的限制。但由于既有規定通常亦被視為刑法家父主義的具體體現(所謂善良風俗與家父主義的適用效果并無二致〔42〕Puppe(Fn. 28), S. 494.)。因而該國論者圍繞針對故意領域中同意效力的封鎖條款能否延伸適用于出現重傷尤其是死亡的合意的他者危害而做出的多元闡釋,或許能為我國對此問題的處理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案。
德國論者多認為逾越第216 條、第228 條規范的字面含義而擴張其適用范圍,違反禁止類推原則。〔43〕Martin, Die Einverst?ndliche, beidseitig bewusst fahrl?ssige Fremdsch?digung, 2016, S. 199.而主張同意理論延伸適用的論者,則肯定了封鎖規定的延伸適用性。不過論者卻又從不同路徑、依據不同準則限制其在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中的適用,并形成以下兩種模式三種觀點。
第一種模式是以規制故意犯罪的第228 條之善良風俗條款來約束規制過失犯罪的第222 條(過失致死罪)。這首先為司法判決所適用,在“加速試驗案”中,BGH 指出:對危險駕駛行為的同意,其正當化效力通常僅能用來排除一般的保護道路交通安全的構成要件。在僅保護個人法益的規范(如第222 條)下,不考慮現實的法益損害結果,以客觀立場從事前角度看,行為逾越善良風俗——引發了“具體的死亡危險”,同意無效。〔44〕BGHSt53, 55(63).J?ger 亦認為,當他人實施的風險行為,從事前角度看僅會導致輕微的身體傷害或者存在明顯的客觀依據,如行為人對風險具有專業性的支配抑或該風險僅對生命造成“抽象的危險”時,可適用同意排除合意的他者危害之行為不法。〔45〕J?ger(Fn. 19), S. 432f.如明顯完全醉酒的A,應C 要求載其回家,最終導致交通事故,C死亡。對此,論者亦主張C對A的醉駕行為的同意并未違背善良風俗。因為從事前看,A 之行為對B 之生命僅有抽象的危險;不過針對“梅梅爾河案”〔46〕在一個暴風雨的天氣,兩名乘客到渡口要求船夫將他們送到河對岸,盡管他們知道在那樣的天氣渡河有生命危險。起初船夫以渡船危險為由加以拒絕,但還是拗不過這兩名乘客而同意開船。結果船行至河中央被浪卷翻,兩名乘客被淹死。RGSt57,172.,他卻認為行為人駕船渡河的行為產生了“具體的死亡危險”,同意因而無效。
依善良風俗條款否定對“具體的死亡危險”的同意效力做法,受到了批判。因為不管從文義還是體系角度看,規制“故意”侵害“身體”犯罪行為的規定,并不能當然地約束規制“過失”“致死”的條款。〔47〕Puppe, Nomos Kommentar, 4. Aufl., 2010, Vor § 13ff. Rn. 194.有論者更是指出,即使不考慮主觀罪過和結果樣態的差異,行為本身違背善良風俗并不能單獨決定其違法性。〔48〕Frisch, Zum Unrecht der sittenwidrigen K?rperverletzung,Festschrift Hans Joachim Hirsch, 1999, S. 506.事實上,即使是主張延伸適用者,大多也不贊成此種模式。相反,對于出現死亡結果的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多數論者是在與第222 條具有相同(死亡)結果樣態的第216 條之受囑托殺人罪的立法思想下展開的,此即第二種模式。
現代國家理念之下,在對受囑托殺人仍是犯罪的價值和目的解讀上,不管是Stratenwerth 將個體生命視為個人存續和發展的長期利益,還是Engisch〔49〕Engisch, Die Strafwürdigkeit der Unfruchtbarmachung mit Einwilligung, Festschrift H. Mayer, 1966, S. 412f.和Hirsch〔50〕Hirsch, Einwilligung und Selbstbestimmung, Festschrift Wezel, 1974, S. 775.認為的該條創設了抑制殺害他人的反對動機,不同主張的核心主旨均是——他人生命不可侵犯的基本價值,不因同意而被動搖。若將這種對生命的絕對保護原則一以貫之,那么侵害生命的行為方式及程度如何就在所不問。亦即禁止故意殺人和禁止過失致死的基本立場并無二致。這樣的立場實際亦為車教授所主張,其基本是要求同意的效力取決于個案中現實的法益損害結果樣態是否是死亡。如此,就不需對合意的他者危害行為本身,再做是否違背善良風俗的倫理性/家父主義立場的評價,以事前角度分析行為本身的危險性大小。
不過,D?lling 則嘗試對這種“硬性”的主張進行“軟化”式修正。其將出現死亡結果的合意的他者危害區分為具有正當化和不具有正當化效力的同意兩種情形,標準是將行為所實現的目的價值和同意所實現的被害人自主決定價值與過失致死的不法程度做對比。若前者優于后者,同意有效;相反,若日常生活中較小利益的實現不足以抵消行為不法,〔51〕D?lling, Fahrl?ssige T?tung bei Selbstgef?hrdung des Opfers, GA1984, S. 91.行為人即要為過失致死負責。
理論上的第三種主張是對第一種模式的修正。Murman 認為將違背善良風俗規定延伸適用于過失致死情形,是一種當然推論。不過,論者并不認可BGH 所主張的以“具體的死亡風險”作為善良風俗的具體化準則。其所關心的更為實質的問題是,額外增加對身體損害以及過失致死情形中的同意效力的限制,是否具有正當性。論者指出善良風俗作為限制同意效力的標準,具備合法性的依據只能在于保障被害人決定之自由。具體情形下,可將有瑕疵的同意,即從法益主體自身角度看,同意決定并非是“理性”地作出,作為具體標準。〔52〕Murmann(Fn. 25), S. 787.對于“加速試驗案”,論者認為被害人當時并非是瞬間作出參賽決定,他是經過長期訓練,不僅知曉風險也必定接受了自己作出的決定,同意應被視為有效。
受制于立法對故意領域中侵害生命和違背善良風俗的重傷同意效力的限制,BGH 和Murmann較為巧妙地將屬于行為而非結果特征的善良風俗條款,經由不同渠道和過失致死罪相關聯,開啟從行為不法的大小或有無角度來檢驗同意效力的模式。該模式與僅將行為作為同意的客體的基本前提更為契合,畢竟既然結果并非同意的必要對象,就不應是判斷同意效力必須要考慮的要素。而第二種模式,雖有行為同意之名,卻仍將結果不法作為同意效力的決定性標準,因而有違結果同意之實。
2.有條件同等對待理論
在合意的他者危害歸責的解決上,Roxin 提出有條件同等對待理論:當被害人認知風險、對風險行為有同意、對共同行為負擔如同行為人一樣甚至更大的責任時,合意的他者危害可與自我危害的參與應被同等看待,行為人行為不可罰;如果行為人負擔較大的責任,則應對其行為予以客觀歸責。〔53〕Roxin(Fn. 15), S. 662.
在最新文獻中,他又將該主張具體化為以下兩個條件:一是,風險情狀由消除行為人疑慮的被害人主動提議而產生。如在“艾滋病案”中,被害婦女受感染,其不采取安全措施性交的要求起主導作用,該情形在規范意義上等同于自我危害。二是,風險情狀由所有參與者同時共同創設,即行為人和被害人共同策劃且實現某一風險事件。針對“汽車漂移案”〔54〕一群年輕人閑暇時玩汽車漂移活動,他們每個人在車頂上,通過開著的車窗抓住汽車門把,A 以80km/h 的速度繞過一個彎時,由于巨大的離心力的影響,V 從車上被拋出去并受傷嚴重。Vgl. OLG Düsseldorf , NStZ-RR1997, S. 325.,論者認為被害人V 也共同參與創設了風險事件,與被告人A 對事件具有同等責任,損害結果不歸責于A。〔55〕Roxin(Fn. 21), S. 256.
三、一元論下的同等對待理論
在區分不具可行性或區分僅是一種教義學上的方法而不具有規范意義的論者看來,不管是自我危害的參與,還是合意的他者危害,被害人自主決定同意陷于風險時,其均要對法益損失的結果自我負責,此即同等對待理論。其主要涉及為馮教授所認可的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及被害人教義學理論。
(一)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
被害人自主決定,因而要自我負責,成為為我國諸多學者解決相應歸責問題的基本前提,也漸而成為法學人士的“口頭禪”。只是被害人自我負責何以能夠與自主決定建構起關聯,并因此使法退卻對他人行為不法的評價,亦非不言自明而需學者為此尋找充足的法理依據。對此,馮軍教授和馬衛軍博士秉持了主體自主決定,因而承擔自我保護義務的基本立場。〔56〕同前注〔1〕,馮軍文;馬衛軍:《被害人自我答責的理論根基探析》,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3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84 頁。Jakobs 亦從社會哲學視角觀察,借用針對不作為而創設的“組織管轄”標準,指出被害人要對其自愿陷于風險并因此造成的損害自我負責的理據在于被害人和行為人的角色分配,被害人管理著這一侵害。〔57〕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lf., 1991, § 21Rn. 78.針對“艾滋病案”,他認為被害人的損害并不能歸于不幸,而要歸因于其對“自我保護義務”的違背。〔58〕同上注,邊頁78a.這種以賦予自主決定主體以“自我保護義務”,并據此否定行為人注意義務違反性的思考方式,是在私人主體間分配法益保護義務,如此則法益主體的自主決定亦被賦予了“義務”屬性。
與“自我保護義務”的立場相反,賦予自主決定以“權利/自由”屬性,并從此立場證成自我負責的觀點,不僅有深厚的法哲學依據,在德國更有著作為基本法的憲法規范的支撐。前者如Zaczyk 從康德法哲學意義上的人之自由角度,導出被害人的自我負責性并將其與行為人不法相關聯。得出被害人自我危害是其自由的實現方式,此時行為人并未侵害其自由,因而無不法的結論。〔59〕Zaczyk(Fn. 24), S. 18ff.后者如作為康德法哲學思想的結晶,為憲法所保障的人性尊嚴(Art.1 ABs.1GG)〔60〕1949 年《德國基本法》第1 條第1 項開宗明義規定,“人性尊嚴不容侵犯。尊重并保護人性尊嚴,是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或該項及第2 條第1 項規定的前半句——一般行動自由條款。論者據此確立了以被害人“自主決定權”排除風險同意下行為人不法的準則。這主要緣于人性尊嚴通常被理解為“人”認識自我、決定自我、形塑自我的“自主決定自由”〔61〕BVerfGE 65, 1(42).,且其被視為人之固有價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1978 年在“變性案”中則更為明確地將其理解為個人可依“自我負責”的方式自愿且自由地處分自己事務,以此締造自己未來的命運。〔62〕BverfGE 49, 286(298).在此理念下,被害人同意陷于風險時,法益損害作為行使自主決定權之后果,由其自我負責被視為是當然的結論。
(二)被害人教義學理論
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之外,深刻貫徹被害預防刑事政策思想和刑法最后手段原則的被害人教義學,其核心主旨是公民具有優先于國家的,對自身法益的自我保護義務。該理論主張在規范評價上應以被害人的應保護性和需保護性決定行為人的應罰性和需罰性。這具體表現為當被害人“可能且可被期待”實施自我保護以防止自身法益受損而怠于行為時,刑法不需對其予以保護,行為人也喪失了需罰性。〔63〕Schünema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GA1987, S. 11.因而,被害人明知風險時,其理性的自我保護是最好的預防法益受侵害的手段,當他并未實施該自保行為而陷于風險,即喪失了需保護性,〔64〕Fiedler, Zur Strafbarkeit der einverst?ndlichen Fremdgef?hrd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viktimologischen Prinzip, 1990, S. 119.法益損害結果就不能不歸責于行為人。
對被害人風險同意的事實、價值與規范命題,域內外的主張及由此得出的結論,究竟何者具備自洽的邏輯、充足的說理、實質的根據,具有處理過失領域被害人風險同意的資格,值得進一步思考。
四、必要的二分法:規范評價之于事實的尊重
(一)區分超脫于實體法的規定
德國《刑法》第216 條的規定表明要將受囑托殺人和參與自殺區分開來,后者并不受該條款的規制,而立法為何如此規定,需要被說明,其本身并非是區分兩者的原因。既有將該條所體現的立法思想和規范目的作為區分原因力的主張,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區分的基本前提——事實結構的差異,卻常常被忽略。如果幫助、教唆自殺和受囑托殺人的事實結構完全沒有差別,區分不僅客觀上不可能,更無規范意義上的必要性。兩者之間的關系體現為:事實結構的差異是規范意義上區別對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亦即規范意義上的區別對待以存在事實結構的差異為前提,但不區別對待也不意味著事實結構無差別。就此而言,區分兩者與否,與實體法規范并無關聯,其更多的是出于對事實的基本尊重。而尊重事實,當然很重要!
同樣,被害人風險同意類型下,實施風險行為的主體及被害人對于風險的控制性程度并不相同,被害人對自己實施行為所帶來的風險意欲容忍至何種程度,自始均由他本人控制支配。而當其要容忍他人創設的風險時,其便難以介入從而控制或中斷該風險。相反,只有行為人本人能夠如此為之,〔65〕Claus Roxin, Zum Schutzzweck der Norm bei fahrl?ssigen Delikten, Festschrift Gallas, 1973, S. 243.而不管是一般的行為/風險支配還是風險創設標準,其首要目的就在于將那種事實結構有別的被害人風險同意的不同情形區分并呈現出來,其并不依賴于實體法的規定。這,就如同依照顏色的不同將玫瑰分為白玫瑰、紅玫瑰、藍玫瑰,依照植物莖的形態不同而將其分為喬木、灌木、亞灌木……
由是,德國《刑法》第216 條的規定及立法思想,并不能夠當然說明過失領域被害人風險同意區分的必要性。而能否適用它說明在規范意義上可否將其區分并區別對待,是涉及價值評價的規范性問題,這和基于事實結構差異而做出的區分,并不是相同層面的問題。我國刑法盡管沒有如同德國刑法般的規定,從事實角度觀之,學理上仍可將兩者予以區分。
(二)規范意義上區分與否的形式與實質差異
我國論者關于被害人風險同意類型的區分并未形成真正的學術之爭,因而區分與否在規范意義上的差異究竟為何,在學理上就未被呈現出來。德國論者對此的闡釋和論證則相當詳細和完善。從既有主張來看,Roxin 依照風險創設標準區分兩者,在規范評價上卻主張,當被害人對風險事件負擔如同行為人一樣甚至更大的責任時,合意的他者危害可被視為自我危害的參與。其屬于客觀構成要件層面問題,應在構成要件效力范圍內加以解決,此時行為人行為同樣沒有該當構成要件。從目的理性犯罪論體系看,在此層面驗證過失行為人是否對結果負責,表明行為人行為已被認定創設且實現了不被容許的風險。而同等對待理論之下,針對“被害人自我危害”情形,Puppe 經由被害人自由的自主決定歸責原則的運用,雖然亦于構成要件階層,得出行為人對法益損害結果并不負責的結論,但是不歸責的理由卻和Roxin 的主張有別。在此情形下,論者認為行為人自始沒有創設法不容許的風險或無注意義務之違反。但不管如何,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的結構性差異在論者的主張之下,均被忽視或否定了,其在法律上的基本意義也因此被簡化。而為Roxin 所極力反對的,在違法性階層適用同意理論解決合意的他者危害的主張,卻受到諸多論者的追捧。從此來看,區分與否的形式差異即在于——合意的他者危害是歸屬于構成要件還是違法性階層。
區分與否更為實質的問題是,對注意義務違反的判斷,是否要考慮被害人的意志?Geppert 認為當被害人明知風險仍同意行為人之行為,行為人對被害人即無保護義務。〔66〕Geppert, Rechtfertigende Einwilligung des verletzten Mitfahrers bei Fahrl?ssigkeitsstrafrechtaten im Stra?enverkehr? ZStW1971,S. 993.此即被害人意志決定行為人義務違反與否的“注意義務相對化”理論。反對論者認為,構成要件的任務顯現的是一個通常被禁止的行為,規制該行為的規范效力并不受個體意志的左右,注意義務違反的判斷也不取決于被害人的意志。因而對他人風險行為的同意首先應在違法性階層,作為違法阻卻事由來加以考慮。〔67〕Grünewald(Fn. 20), S. 367.這是與法益主體同意行為人對法益客體的侵害,行為人仍該當構成要件的傳統的教義學立場相一致的觀點。
在對合意的他者危害做不同規范評價的主張下,區分的規范意義也呈現出來——自我危害的參與下,行為人“無”注意義務違反;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有”注意義務違反。雖然按照相關主張,后者最終可依被害人的同意而否定其違法性,但這和自我危害的參與下自始無義務違反畢竟有別。而刑法教義學應將兩者予以區分。至于如何能得出該評價結論,則需在價值和規范層面深入分析。
(三)可能的區分標準
既有區分標準中,作為事實標準的行為/風險支配,因未能與規范性歸責相關聯而被Murmann批判。與純粹在事實層面區分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相比,論者所構建的規范性標準,被認為不僅可以避免事實區分標準在行為人和被害人共同支配實施風險行為歸屬于何者而生的分歧,在區分自我危害和他者危害的同時也能說明自我危害的參與下,行為人為何不需對被害人自我危害的后果負責。而對此歸責問題的解決,起決定作用的也并非是被害人的行為支配而是其“自主決定權”。畢竟一般而言,行為支配與規范性歸責之間,不具有必然關聯性。即使是實際支配結果發生的人,也并不必然對事件負責;而欠缺行為支配者,若其認識或應當認識被害人并無自我負責的能力卻仍加以利用的,仍可能對此結果負責,關鍵是看個體對法律關系的實現負擔了何種義務。〔68〕Murmann(Fn. 23), S. 354.但即便如此,從Murmann 的相關主張來看,他實際上并沒有完全放棄支配思想,而是認為這對法不容許的風險行為的確定,具有相對有限的作用。就此來看,論者的規范性標準實際上比行為/風險支配標準多往前走了一步。但問題是,即使是依行為支配標準區分的多數論者,大多也沒有據此直接認為行為人作為正犯時(合意的他者危害)要歸責而作為共犯時(自我危害的參與)不予歸責。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檢驗規范性歸責問題并提出具體依據。就此來看,對于事實類型的區分,不與規范性歸責相關聯,也并沒有什么不妥。而將兩者予以分離,首先借用一定的標準將被害人風險同意的事實區分為不同類型,進而予以價值評價,這樣的邏輯進路似乎也更為清晰明確。
在區分標準的選取上,行為支配之所以備受批判,緣于其和共犯理論的捆綁,否認適用共犯理論解決故意的自我損害的參與及過失的自我危害的參與、合意的他者危害的論者,也總是會對與共犯相關的、作為區分標準的行為支配主張予以批判。事實上,誠如Martin 所言,行為支配概念完全可以脫離共犯理論,其并非僅是指具有區分正犯、共犯意義的、對犯罪構成實現的支配。而可在一般意義上將其理解為對事件的支配,即是指控制著對法益造成侵害的最后行為。如此,自我危害/他者危害類型的區分便與共犯理論無直接關聯性。〔69〕Martin(Fn. 43), S. 199.德國司法并未使用正犯與共犯概念,而是采納了同意理論解決合意的他者危害,但在區分標準上仍采納了行為支配/風險支配標準,這表明采納該區分標準完全具有可行性。并且此一意義上的行為支配概念和Roxin 的風險創設標準就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因為所謂風險創設的實質內涵也是對導出法益損害結果的行為的控制、支配力。
對被害人和行為人共同支配實施風險行為之事件,行為支配標準下,更應將其視為合意的他者危害,畢竟行為人完全親自或參與實施了一定的風險行為,法益損害結果是否要歸責于他,應經由更為嚴格的程序和條件來驗證。張明楷教授以被害人具有完全的支配力為由而將“艾滋病案”視為自我危害的參與類型,〔70〕同前注〔9〕,張明楷文。并不妥當,畢竟此時行為人也有行為支配,應將其視為合意的他者危害類型。
五、歸責依據評析與立場重塑
直至今日,圍繞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的歸責依據的論戰依舊沒有停止,在學術成果上產生了多元的歸責主張。而不同的見解之間是真正決然有別還是時有融合,在對歸責的說明上,是完全立場錯誤還是實質依據不足,是尚待完善還是臻于完美,則是需要論證的另一主題。
(一)實質依據不足的共犯論證
既有歸責依據中,適用共犯論證自我危害/損害的參與不可罰,雖為域內外部分論者和實務所堅守,但亦遭致了反對:一方面,借助與共犯關聯的行為支配來區分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又將其用來說明前者不具可罰性,這種“一體兩用”的做法并不妥當。Neumann 較早就反對“共犯論證”模式,因為就規范評價而言,成立共犯的前提是被教唆者或被幫助者的行為已被類型化為構成要件行為。但自我損害/危害的被害人行為顯然并未被如此對待。〔71〕Walther(Fn. 34), S. 60.另一方面,“舉重明輕”的論證方法也受到批判:在幫助自我損害情形下,法益主體有意愿犧牲法益客體……而在幫助自我危害情形下,主體只預想到行為僅對其法益構成威脅而非損害。相比前者,后者行為性質并非輕而是重了,參與自我損害之行為的正當性與自我危害的參與行為的正當性相比是輕而非重了。〔72〕Puppe(Fn. 28), S. 489.實際上,深入分析會發現,真正有問題的并非是德國理論模式中的“當然推論”,而是為何能夠以被害人是“準正犯”為前提,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依此排除歸責。這是作為當然推論前提的共犯論證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正是其根本缺陷之所在。這種企圖以純粹的事實支配來決定規范性歸責的主張,并不具有對行為人欠缺不法而無刑罰可罰性的實質依據。在涉及被害人參與的歸責理論中,理應受到批判。
盡管Roxin 嘗試為此形式性的論證尋找“實質”的支撐依據——注意規范保護目的,即禁止侵害規范并不包含自我危害,因而由此而生的法益損害結果并不在刑法構成要件效力范圍內。〔73〕Roxin(Fn. 65), S. 246.但是這樣的論證看起來更多的是在為自我危害的參與進行的體系性定位而并未涉及實質內容之依據。而當保護目的思想直接由共犯論證所推導出的結果(自我危害下,行為人對法益損害結果并無支配)來呈現時,這樣的形式與“實質”說明,只不過是在循環論證。并且,同樣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體系定位(客觀歸責第三階層——構成要件效力范圍),表明Roxin 也認為自我危害的參與下,行為人已經創設且實現了不被容許的風險。但并不清楚的是,諸如為被害人自己注射海洛因提供注射器的行為人,究竟為何就被認定為已經創設且實現了“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不被容許的風險。
由于自我危害的參與不可罰的實質依據不足,Roxin 主張的特定條件下合意的他者危害等同于自我危害,因而排除行為人的負責性的主張,也欠缺正當性。這從Roxin 為合意的他者危害與自我危害的參與同等對待所設定的標準即可看出,首先,被害人對行為人創設風險之行為的同意,只是說明合意的他者危害的客觀事實情狀。其次,所謂被害人和行為人對風險事件負擔同等責任的主要判斷標準實際是雙方對風險持有同等認知,即行為人無優勢認知。但問題是,行為人對風險存有優勢認知,即使在自我危害的參與情形下,其同樣可能要對法益損害結果負責。因而這種基于事實性標準區分兩者進而以此為條件實現合意的他者危害和自我危害的參與的同等對待理論,內容過于簡單也沒有真正闡釋出排除合意的他者危害的歸責依據。
張明楷教授一以貫之地適用行為支配理論,其直接將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下的行為人視為“正犯”要為該結果負責的主張,實際是將行為支配與規范性歸責相等同。至于該情形下,被害人對風險的明知、對行為人風險行為的同意的基本事實的規范性意義,在將被害人同意理解為故意放棄法益而非使其陷于風險、作為阻卻違法實質根據的自主決定權之行使必須涉及犧牲或徹底放棄法益客體的基本前提下,就被徹底否定了。但為何刑法意義上的同意只能作此理解,論者顯然沒有展開進一步論述,其據此得出的結論,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德國刑法規定受囑托殺人是犯罪,而幫助、教唆自殺非犯罪,其實質的法理根據并不能由正犯與共犯理論來充當。因而形式性地類比故意犯中的此類規定來處理過失領域被害人風險同意的歸責問題,并非妥當。且由于我國并無諸如德國刑法的這般規定,這樣的類推模式也很難移植至我國。超脫實體法規定而從實質法理根據來闡述此類歸責問題的自我負責原則和被害人同意理論,更值得關注。
(二)自我保護無力取代刑罰功能
與同意的實質依據是自主決定權的主張不同,被害人教義學論者提出法益主體承擔著自我保護的義務之主張,旨在國家和公民個人之間分配法益保護義務。這樣的立場同樣為部分自我負責原則論者所認可。雖然既有主張以平等主體之間的義務分配為訖點,并借由人之自主決定劃分各自的負責范圍,主體對其負責范圍內事項負擔義務,其中包括自我保護義務。但這兩種不同的主張,在歸責結論和實質依據上實際并沒有差異性。此種意義上的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在Schünemann 看來,是被害人教義學的“變體”。只是不管有無區分,以自我保護替代刑罰功能的做法均難以被接受。
自我保護義務或思想不僅作為一種哲學主張出現在康德著作之中,〔74〕在康德哲學理論中,對于生命與身體完整權的保全義務,遂構成了個人行使自由權的內在限制的主張,建構出具有德性的對己義務。也更多反映在私法規范〔75〕《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 條規定:“機動車行駛時,駕駛人、乘坐人員應當按規定使用安全帶,摩托車駕駛人及乘坐人員應當按規定戴安全頭盔。”中。但這并不能夠成為在刑法規范層面亦貫徹被害人自我保護義務理念,從而據此排除刑法對于法益的保護之依據。因為即使是康德也僅將其視為一種道德性義務而非法定義務,而私法上關于受害人要防止損害發生的要求,也并非是“對己義務”的體現。此類規定體現的更為實質的理念應是,要求受損者在能夠避免或減少損失時采取一定措施,是平等主體之間在人際交往中為減少交易成本,所達成的共識。這看似是賦予了受損者一種“對己義務”,但實質上仍是受損者針對交易相對方應承擔的,減少對方損失,因而仍具有“利他性”的“對他義務”,此一共識經由法的確認而具有強制力。而規制犯罪與刑罰的刑法,顯然欠缺如同私法般的要求被害人在面對行為人的不法侵害時,要自保從而使行為人獲得刑罰的寬宥之機能。
為此,Schüneman 將社會契約思想作為自我保護義務的實質根據,〔76〕Schüneman, Das System des strafrechtlichen Unrechts: Rechtsgutsbegriff und Viktimodogmatik als Brücke zwischen dem System des Allgemeinen Teils und dem Besonderen Teil, in: Schüneman(Hrsg.), Strafrechtssystem und Betrug, 2002, S. 65.但這樣的理解是對該理論的誤讀。社會契約思想更應能說明為了更好地發展、形塑自我,公民在人際交往中時刻謹慎提防他人的不法攻擊的負擔被解除。〔77〕Roxin(Fn. 31), Rn. 20.而公民的自我保護立場,建構出的卻是因個體難以相互信賴,為了純粹的自我保全而限縮自身行為空間的社會。從此導出自我保護,并非不可但顯不妥當。
該主張同樣沒有刑法規范的支撐。從刑法規定的正當防衛制度的成立要件來看,在面對他人的不法攻擊時,公民僅能在欠缺及時有效的國家救濟情形下,針對不法侵害人實施攻擊。這足以說明個體的自我保護相對于國家的保護,僅有輔助性而非優先性。并且在正當防衛制度中,自我保護作為人之本能,是為國家認可的一種私人的自我“救濟權”,且其要克制行使該權利而不能過度對不法侵害人造成不應有的侵害。關于自我保護義務的主張與公民防衛權的法規范相矛盾。
(三)實質不法立場下自主決定權證立行為無不法
在對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理論的闡釋上,多數論者從多重視角以被害人自由而非自我保護義務為實質內容,賦予其影響行為不法之功能。未使用被害人自我負責術語而主張適用同意理論解決合意的他者危害的觀點,實際亦是將被害人自主決定權/自由作為排除行為不法的法理依據。秉持此一立場的論者,在對自我危害的參與不可罰的論證上,亦摒棄了形式的共犯論證模式,并同樣依據被害人自主決定權證立該情形下,行為人并無創設法不容許的風險因而無不法。〔78〕Murmann(Fn. 25), S. 775.就此而言,這些論者亦是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的倡導者。因為同意的法理規則即是被害人對法益損害結果負責,行為人無不法。兩種立場之間的差異僅在于是否區分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以及兩者在犯罪論體系中的歸屬問題。暫且撇開此一問題,就被害人風險同意下,依自主決定權否定行為不法的成立主張,首先受到的質疑是,自我損害的參與和同意(他者損害)情形下被害人認可法益損害結果,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下,被害人并不期待法益損害結果。因而何以被害人對于法益損害結果的不期待甚至否定這樣的心理事實,在規范評價上成為對不法有無之認定并無影響的要素。
我國既有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對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的建構主要立基于法益主體的“自我保護義務”,其和以“自主決定權”為根基建構的同意理論,因自主決定的屬性差異,而并未被加以關聯審視,兩者所各自主要應對的事實類型之間的差異,緣何并不影響規范性結論即行為無不法的同一性,亦未受到重視。另一方面,主張過失領域中的被害人風險同意和故意領域的同意具有相同法理依據的論者,因堅守同意結構的固有立場,否定了風險同意的下位類型——合意的他者危害,可依據同意理論排除行為不法。該觀點實際是對以上被質疑問題的否定回答,即在論者看來,法益主體不期待損害結果發生的心理事實,因使自主決定權產生重大瑕疵而影響了對不法的阻卻。〔79〕同前注〔4〕,車浩文。再者,盡管黎宏教授認可同意理論對合意的他者危害歸責問題的解決,但通篇來看,其并未真正對前述問題給予充足的且有說服力的論證。不僅如此,從德國憲法導出自主決定、自我負責的德國論者,實際上對此也并未清晰地予以說明。前述可依同意理論解決合意的他者危害的既有理論介紹,如緣何在此情形,對風險行為的同意即已充足,僅是結論性觀點之呈現,其中欠缺的關鍵一環,即被害人此種自主決定權之行使與行為人行為無不法的關聯,究竟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尚未被充足論證,這恰恰是關于被害人風險同意的刑法意義研究中,不得不面對的法理難題。如無法證成,則關于該主題的學理研究,就不能更進一步而只能停留在能夠阻卻不法的同意必須包含有主體對法益損害結果的期待要素之階段。
論者認為,從體系性視角實現對以上問題的解決,Zaczyk 的以下法哲學觀點首先應被接受和肯定。即法是人際沖突調整規則,其要求在人際交往中,作為“自我目的”的個體,為實現自由而行為時,以對他人自由的尊重和承認為限,其表現為人際相互承認此一實質的法律關系。而不法即是對人際相互關系中,平等主體自由的否認。〔80〕Zaczyk(Fn. 24), S. 165.人際相互承認關系原則,準確闡釋了法/不法的實質內涵。不過顯而易見,此一抽象性原則并非是具體的行為指引,需于實定法如刑法上實現對其的具體化。由于如何行為才是對該原則的踐行,取決于一定的具體條件,在此之下,個體作為平等、自由的主體能夠被聯結起來。〔81〕Murmann(Fn. 25), S. 370.在此理解之下,刑法所保護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就不僅是指歸屬于一方主體的,對其自由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的客觀存在,即法益不僅是自由的存在要素,〔82〕同上注。在法的概念之下,其也是使人際相互承認關系得以被建構的條件。亦即,一方面,對于法益,不能單向地從人際關系的一方主體面向理解,法益主體處分客體的自由的邊界——不侵害他人的自由,也應內涵在法益的概念之中,畢竟自由實現于一定的人際關系之中,不侵害他人的自由即是對人際關系另一方主體的尊重。另一方面,法益主體自主決定處分客體從而實現何種行為自由的事項,也應受到他者的承認和尊重,刑法中的行為規范,即是從他者面向一般性地禁止不當干預法益主體處分法益客體的事項。
一方面,個人法益作為主體自我完善的條件,旨在服務于主體。這具體表現為,其不僅能夠自主決定放棄法益客體,更是可以將其置于風險情境中,以獲取新的利益或者使自己擺脫不利的困境。事實上,后者才是主體利用法益客體的常態化情形,如將自有現金投入有風險性的股市中企圖賺取更多的錢;為了變得更美而甘愿冒險接受整形手術;為恢復身體健康而自愿服用尚未被實驗的藥物……可以說,不管主體是否期待法益客體遭受損害結果的出現,作為主體自我實現的不同方式,兩者均是在踐行對法益的自主支配權。另一方面,實質不法觀下,對于自我危害的參與和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下行為人不法的認定,應做以下處理。
自我危害的參與情形下,被害人明知風險而仍自己實施風險行為,在具備完全責任能力且決定并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瑕疵時,完全是親手、獨立行使自主決定權之情形,此時并無刑法意義上的歸責問題產生。因為作為自我實現風險的參與人的“教唆”和幫助行為,根本未觸及主體對客體的自由支配,不具有創設法不容許的風險資格,即行為人行為自始欠缺不法性。據此,我國實務對“跳水撈錢案”處理結論,有失公正。此一情形下,合理的規范評價結論應是唆使被害人下水撈錢的行為,因被害人明知河水冰冷,下水有溺亡風險而仍自主地做出撈錢決定,而不能被視為創設了不被容許的風險。
對于合意的他者危害歸責的處理,首先仍應堅持禁止性行為規范的效力原則上不受被害人意志的影響,即行為人注意義務違反的判斷不考慮被害人意志的主流見解,而認定行為人行為在一般意義上創設了法不容許的風險,該當了構成要件。進而在違法階層例外地考慮被害人風險同意能否阻卻不法的問題。由于被害人自愿接受了這樣的風險情狀,因而不管是行為人與被害人共同支配實施風險行為還是由行為人獨自實施風險行為,被害人均是在利用行為人行為來實現自己的意志,此時行為人的行為應被視為被害人自己的行為,是對被害人意志自由的尊重,因而不再被評價為破壞、干擾了被害人對其法益客體的自主支配關系的違法行為。也即法益主體的自主決定,使為法所禁止的行為轉化為了合法行為。法益主體是否期待客體遭受損害,對于不法的認定,實際并不具有意義。在事實結構上存在差異的合意的他者危害與同意,亦獲得了相同的規范評價。
這樣的立場,不僅于司法層面能較好地處理被害人風險同意案件,其還能于立法層面說明緣何一定情形下的合意的他者危害行為并未為法所禁止。在競技運動領域,因在競技過程中由合意的一方對另一方造成的傷亡結果之情形,如上官鵬飛被拳擊致死事件,〔83〕2011 年在中國武術散打功夫爭霸賽的一場80 公斤半決賽中,武警隊選手崔飛在比賽進行到第二回合時用擺拳KO 了河南名將上官鵬飛,其隨即失去知覺昏倒在地,隨后因頭部受到重擊受傷嚴重而在一個月后不治身亡。參見慈鑫:《官方今日就上官鵬飛事件表態》,載《中國青年報》2011 年4 月14 日,第4 版。理論和實務并未將其視為侵害他人法益的犯罪事項。既有主張將社會相當性理論作為該類行為具有法容許性的依據,但所謂相當性的內核只不過是“模糊的社會道德觀念和法感情”〔84〕陳璇:《社會相當性理論的源流、概念和基礎》,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頁。,以此決定類型行為的法律性質,并不合適。應當認為,個體明知參與競技運動往往伴隨傷亡風險,但為尋求刺激、實現通過比賽獲得豐厚的獎金等目的,而仍決定參與其中,便接受了來自對方對其可能造成身體損傷力量的施加,而相互“攻擊”行為恰恰是一方對另一方參與競技運動決定的尊重,該情形自始就表現為一種相互承認關系,法將各自“傷害”對方的行為設定為禁止性行為,是限制雙方自由的不妥當做法。
(四)自主決定的瑕疵性封鎖同意效力
合意的他者危害的結果樣態常常是死亡,域內外實務和多數論者基于家父主義立場或善良風俗規定主張行為人需對此結果負責。部分論者并不想將身體、生命的絕對不可侵犯思想貫徹于合意的他者危害情形中,并為適用同意排除過失致死歸責擴張空間。但不管是抽象的死亡風險標準還是行為追求之目的價值和被實現的自主決定價值之和大于死亡風險的程度主張,并無多大的說服力。因為不管是事前還是事后的風險大小之考量并在此前提下的行為選擇,只是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立場。這樣的上帝視角撇開擁有自主決定能力。在具體情形下,知曉風險及可能的死亡后果而仍選擇陷于風險的個體,并對涉及行為人和被害人的雙方關系予以審視。但問題是,被害人才是具體事件中的當事人,其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的選擇才是其作為個體而為的真實決定。第三人顯不能夠越俎代庖,以己立場切換設身其中的被害人決定。否則即是對他作為自主決定個體的不尊重。因而論者從過失行為不法為限縮出現死亡結果的合意的他者危害的可罰性嘗試,對我國理論和實務并不具有借鑒性。
以上限縮過失致死可罰性做法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基于家父主義立場的可罰性觀點的妥當性。一方面,讓同意的效力由是否出現屬于偶然事件的死亡結果決定,是對純粹結果不法的偏重而忽視了行為不法。雖然這能全面周全的保護被害人,但對應其同意而實施風險行為的行為人,過于嚴苛。另一方面,適用刑法予以事前預防和事后懲治,不僅法治成本極大、功效甚微且更多地壓縮了法益主體的自由。這樣的立場不僅不符合社會主體的多元價值訴求精神,也違背了刑法之基本原則——損害原則,即“只有在為了保護他人免受傷害時,才能違背社會成員的意志限制其行為自由。相反,自身的福祉則不能構成限制其自由的理由,個人不能被強制去實施或者放棄特定的行為以使其更加幸福。因為在只涉及其自身的身體與意志時,個人才是最高統治者。”〔85〕[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1 卷),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32 頁。因而將法益主體自主決定權與法益剝離,忽視主體的自主決定權,而單純地對法益客體予以保護的“例外”做法,并無有力的理論支撐。而若一貫地從實質不法觀點出發,則被害人同意行為人實施侵害法益或使法益陷于風險的行為,可被評價為并未創設不被容許的風險因而無行為不法,即使出現死亡結果,由于欠缺行為不法,該結果亦無不法性。被害人應承擔基于其自主決定而致的死亡風險,是合乎法理邏輯的結論。我國實務中的“練膽溺亡案”〔86〕被害人為戰勝恐懼,聽從教練建議主動嘗試在水中閉氣訓練,并由其他學員將其多次按入水里、拉出水面,后因溺水窒息而亡。《廣州一老板為練膽溺亡 涉案導師學員雙雙獲刑》,載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10-26/5427961.shtml,2016 年4 月21 日訪問。及諸如行為人受被害人請求在實施性行為時,和被害人一起用手指掐其脖頸,并致其窒息而亡案件,〔87〕《河間民警“掐死”歌廳女案一審宣判》,載百度貼吧,https://tieba.baidu.com/p/265266039?red_tag=1096747115,2021 年3月20 日訪問。依照本文主張,得出的結論均應是被害人對于潛在死亡風險的明知、自主決定地接受行為人施加的風險行為,以此實現自我目的,此時行為人對被害人自主決定權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并未破壞相互承認的法律關系,因而行為無不法。死亡是歸屬于自主決定一方的不幸事件。
自主決定權作為排除行為不法的依據,其適用理應滿足一定的條件,如被害人有完全責任能力、對處分法益或使法益陷于風險有明確認知且該認知并不比行為人對相關情狀的認知少、自愿而不能基于欺瞞或脅迫陷于風險等。〔88〕王煥婷:《被害人自陷風險中的刑法歸責研究》,華東政法大學2017 年博士學位論文。這些條件旨在防范被害人在行使自主決定權上可能存有的瑕疵,導致相互承認的法律關系為行為人所破壞。在相應條件欠缺時,刑法即發動對被害人的保護而限制行為人的行為自由,此即刑法的“軟父權主義”立場,〔89〕同前注〔85〕,喬爾·范伯格書。也是刑法干預公民自主決定權行使的唯一根據。
據此,在“逃避結扎跳窗死亡案”中,如果在行為的當時,丈夫發現所使用的繩子中間有幾捆已經斷裂,如果繼續用此捆綁妻子,將她從樓上吊至樓下,極有可能發生繩子全部斷裂,其妻墜落而亡的事故,但由于情狀緊急,在未如實告知妻子情形下,繼續實施原計劃,結果其妻墜亡。此時由于丈夫對風險情狀的認知優于其妻,他未告知真實情狀便剝奪了妻子基于繩子有斷裂危險時,是否仍會選擇跳窗的自主決定自由,丈夫行為的不法性不能被消解,丈夫要對妻子的死亡結果承擔責任。在“周某過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害人作為旅客對于帶有火坑的儲藏室的可居住性情況的認知自然較少,旅店老板則更應清楚地知曉儲藏室通風狀況、經年累月中室內殘留的一氧化碳量。其作為負責人并未積極向旅客詳細告知風險事項,致使旅客在認知欠缺情況下選擇居住于儲藏室,此時難以認定該決定完全出自自主性,旅店老板未給其提供有安全保障的客房行為之不法,不能因此被排除。
在自主決定瑕疵性的認定上,多數論者選擇了決定不具有“理性”——從客觀或主觀角度看,陷于風險是魯莽、未經深思熟慮的思考之結果這樣的標準。根據見解,則不管是“乘坐醉酒駕駛車輛案”“艾滋病案”還是前述在性交過程中要行為人掐住脖頸而窒息死亡情形,由于被害人明知醉酒之人的駕駛能力降低或者喪失而仍乘坐其車輛、明知行為人患有艾滋病卻在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形下而與之性交、明知掐自己的脖頸有窒息死亡的風險僅為尋求刺激而要行為人為之,其行為決定均不具有理性,行為人仍要對死亡結果負責。這樣的觀點在筆者看來并不成立:限定標準本身具有模糊性因而并不能夠提供一個清楚的邊界確定何時是理性的何時又是非理性的,以致理性與否最后只能由是否出現了死亡結果情狀認定。但此一不利后果的出現與否,在行為當時,被害人對此并不能夠清楚知曉。應當認為,行為當時,被害人對認知有風險,仍自主地做出了行為選擇,就是一種理性的決定,將自主決定切割為理性與非理性,是沒有任何法理根據的任意性操作。
六、結語
以上是對過失領域被害人風險同意的刑法意義展開的討論。從實質不法立場理解被害人自主決定權何以成為排除行為不法之依據,并據此證立被害人對法益損害結果的期待與否的心理事實不會影響行為不法的認定。研究不僅為故意犯罪領域的自我損害的參與、同意和過失犯領域中的自我危害的參與、合意的他者危害,建構了同一法理根據,且在適用效果上也使其獲得相同的評價。該觀點或許過于“超前”、甚或有點“離經叛道”,但卻是出自法的本質理解下的應有結論。且從其他地區或國家對被害人風險同意案件的處理看,已有判決承認該情形下,被害人對法益損害結果的負責性而據此排除行為人不法。如對“游玩溺水死亡案”〔90〕被告人和被害人大量飲酒而精神狀況不佳后同至深水魚池內游玩。二人跳上竹筏,在往對岸折返時,因重心不穩,均不慎跌入魚池內。旋即二人再度爬上竹筏,將至岸邊時,被害人突然自行跳下竹筏躍入魚池內游泳,結果溺斃而死。,我國臺灣地區桃園地方法院87 年易字第3523 號刑事判決即指出:“在損害的發生結果是因被害人自己有意識投身進入的風險所實現……根據自我負責原則,其結果原則上應由被害人自我負責,對第三人而言則此結果欠缺可罰性……。”〔91〕http://fyjud.lawbank.com.tw/list2.asp,2016 年4 月23 日訪問。西班牙最高法院在對“Bridge Case”〔92〕被告人在毗鄰一條河的海濱長廊上舉辦音樂會,在這條河上有一座用繩索和木頭自制的小橋,在舉辦音樂會之前其已經向當局申請并獲得許可,也有警察負責安保,節目順利結束后的晚上,四十位醉酒之人又在該橋上激情地跳起舞來,結果橋不負重負而斷裂,致使2 人死亡,38 人受傷。See Manuel Cancio Melliá, Victims and Self-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Vol. 28, p. 745(2008).案的處理上,亦以被害人自主選擇在橋上跳舞,自陷于風險即應接受其行為之后果為由認定被告人無罪。遺憾的是,我國大陸地區實務至今不曾考量被害人風險同意對行為不法影響的意義。論者以較大篇幅對以上論題展開論證,不僅是想在理論上為對被害人風險同意的處理提供合乎法理邏輯和價值的方案,亦欲期待實務能據此對該類案件做出公正裁判。